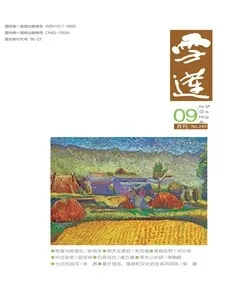森森碉楼
【作者简介】刘群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天涯》《安徽文学》《散文百家》《湖南文学》《山东文学》《延河》《草原》《鸭绿江》《滇池》等刊,多次被《散文》海外版和《散文选刊》转载,并作为高考模拟题。
雪山的风,调头而下,让岷江尤其荒凉、惨白。矗立的碉楼,像青苔里龇牙的巉岩,清亮、狰狞。
在羌寨,碉楼如擎天之柱,狠狠地捅向湛蓝的天穹。它的锋利,如经年不化的坚冰,盘桓了几袅洁白的剑风。我像一只雪山来的苍鹰,盘旋于碉楼之上,似是寂寞,似是闲散。如果没有羌人来关注,我则收了翅膀,蹲在碉楼,像一块墨黑凝重的石头。
其实,我在羌人的视阈中,斑斓的羽毛,流畅的身段,仅仅是碉楼暂时附着的一部分。一旦被阳光径直照耀,灰暗的身体发出箭镞一样蓝色的光芒,我就飞走了。
我爱这些碉楼,我之所以流连,是因为尘埃里涌出的温暖,让我阴暗的心不再迷茫。
微风拂动我光滑的羽毛,呈现出雪山亘古不变的苍凉与遒劲。绿草在碉楼之下疯狂地生长,花也在疯狂地绽放。在五月,雪山也在疯狂地长大,似乎还增高了,被厚厚的青翠覆盖。
一些草和我一样徒增好奇之心,偷偷地仰望碉楼,在我们晶莹剔透的目光中,碉楼过得无声无息,又平静坦荡。
我就这么恍惚,但很快明白,我不是鹰,在阳光里,那些飞翔的鹰和风,以及碉楼,这三者都是雪山的。我可以感受到,它们都是和大地统一的,并和谐地生存。这好比一条翻腾的岷江,途中遇到一个旖旎的海子,浪花就莫名幽蓝了,仿佛生长了一面片绿油油的青稞。
一袅阳光倏地追了过来,只见远处的一座雪山,像一头牦牛在奔跑,接着,被涌出的一层厚雾所笼罩,雪山不见了。雪山在雾里喘息、挣扎,影子若隐若现。戴在头上的一顶白色的狗皮帽子,竟也藏匿了,还是那么娇小。当再次出现时,它高兴的样子像一只松鼠一样可爱、聪慧,或如一只臭鼬一样灵活,散发出浓郁的香气。
我知道,此时的雪山,除了迷朦、飘逸、神秘,还有圣洁。碉楼仿佛更有力量擎举了,把胸脯挺得高高的,立在羌寨里,像羌人举着的一个火把,像一朵格桑花,更像一只白狐在雾里蹀躞迈步,试图将雪山神一样的高耸,一次次地比矮下去,让人景仰。
羌寨环绕着碉楼,碉楼依山而立。石板屋里的羊群,时而沉默如金,时而暴躁如雷。只要有羌Ub/mwY4PAv6LJNNaUjMosSOe3PWftpGkvm+D8fC9uoQ=人从兽圈门外经过,羊听到熟悉的脚步,就哼出一阵阵呼叫,想获取食物和自由。由石块堆砌而成的碉楼,早听到这些羊的声音。它的高度决定了它的敏锐,感觉整个羌寨都是羊的世界。或许,在雪山,除了羊,就是嵯峨的石头,没有其他什么了。
不!这是不对的。还有玉米、青稞、土豆、枫树、松树、雪莲、冬虫夏草、牦牛……
一线山泉从我对面的雪山上如一只白狸一跃而下,清澈的水面泛起一点点波澜,像一双眼睛,偷偷瞄向碉楼,似乎它不认识碉楼,也没有见过。而淙淙的泉水见多了羊,学着一群羊的声音,不屈地漫漶,曲折回旋。
羊叫的再凶,也不会让羌人放下手里忙的活计,去欣然放它们上山。但依附于雪山生长的花木开了花,风雪决定它们的荣枯,会及时赶来,悄悄地妥善解决它们的宿命。
这一天的清晨,一个羌人骑上了一匹快马,出了羌寨,路上的露水和格桑花打湿了风一样的马蹄。马蹄上沾满了湿漉漉的花瓣,呈彩霞一样绽放、粉红。在薄雾中摇曳的草叶,看羌人走得很急,纷纷探出头来,草叶的一只只眼睛睁得像蓝色的星星,溢出了孤独与凄清。
羌人常在雪山上跑马,放牧了不少的牦牛。一群牦牛在雪山的草地上,悠闲地啃食,皮毛黑褐如漆,低拙的个子,矫健的四肢,让羌人很欣慰,很满足。牦牛不时用头颅拼命抵撞嶙峋的崖脚,轰隆隆,轰隆隆,骤然而来的巨响,震碎了飘过的白云,及草地上繁盛的格桑花和无数不知名的花草。
远处低矮的羌寨,突出了的碉楼,像一座小小的雪山,鹤立鸡群。它比真正的雪山,少了嶙峋的气质和伟岸的精神。阳光之中,碉楼长了长长的鬃毛,仿佛一匹骏马,也来到了草地,更像一朵散淡的雪莲花,迎风而立。我抬起头来,一只山雀窜出碉楼的一个瞭望口,似乎在前方发现了什么情况,叽叽喳喳地向羌人汇报去了。然后,它边飞边尖叫,如一弯吹响的号角,惊醒了我和全寨的羌人。
我想,土匪又来打劫羌寨了?
没人回答我。
我认真一想,这是一只山雀的恶作剧,真是一只幽默的山雀。
时光像飘落的几片羽毛。在碉楼,我看到了一卷破烂的纸张,是一卷古卷,古卷上残留的文字如雨一样打湿了我的眼睛。我觉得,看到这些古卷,就会看到很多的古羌人从旧黄色的史籍中走出来。他们手提刀戈,骑上快马,驰骋疆场,至今没有真正回来过。而冥冥之中,我觉得这只山雀抖动的翅膀,正是古羌人的灵魂,缓缓地升腾于碉楼之上、雪山之上,穿越了羌人的前世今生。
阳光猛地停了,天地暗了下来。再经风一刮,雪又涌来了。
在阿坝这个地方,出晴天或下雪,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雪落在碉楼之中,碉楼也落在了雪之中,像一根光洁的温度计,触及到了大地的寒冷。在我之前,雪还没下这么大过,这会儿,雪像漫漫的时光,已经洁白地覆盖了碉楼。
哦,这些雪像碉楼穿上的素洁的白衣,正祭奠古羌人在各个时期的枭雄和战将,或者是几许行走的商旅和僧众,抑或是三五个吟哦期间的诗客骚人、七八个达官贵胄。这会儿,他们都来了,就算这场雪也不可覆盖他们的足履。
至于藏在青石之中的骨骸,我就不说了。说那些碑石吧,这飘扬的雪,像石匠铭刻石碑时溅落的碎石,落在土地上砸出了一个个坑,砸得深刻。在千百年以来的劲风里,石碑上的字,一直没有羌人试图磨没和消弥过。
我听到雪飘散出细细的羌语,羌语洁白无瑕,羌人敦纯如雪,空渺地融入了草木的苍翠和峰峦的逶迤。
当阳光再一次出来,雪像蜗牛一样把蜷缩的触角伸了出来。羌寨生出的烟火把暮色点燃了。一轮月光流泻下来,好似寨子里的羊奶倾倒了一地。
是谁的小孩这么不小心?我说。
不是谁,就是你。夜色中的碉楼,对我说。
为什么是我踢倒了羊奶?
因为你是客人。碉楼说。
是客人就应该踢倒羊奶吗?
是的,在羌寨,凡来的客人,都要吃上羊奶。
哦,我恍然大悟。这是羌人的待客之道,也是雪山的待客之道。
月光在羌寨潺潺流动,如一些花瓣在风里飘移。而弥漫的香气,则在雪山上氤氲、波动。
我从月光散发出的一种复古苍老的气息中,发现碉楼上石头的纹理里,也嵌入了曾经的来客踢倒的羊奶。这些羊奶已陈黄,陷落在石头深处,与石头交错、纠缠,或真实,或渺幻,或影影绰绰,或飘曳无定。这些羊奶嵌入碉楼迟滞而沉重的影子里,很深沉。
我伸出手去抠,羊奶与石头不可分离了。和那些石头外的月光一样,抠了一层,还有一层,它们已经看尽这沧桑的土地和河流,并且融化其中了。如果月光凭空来一些意念,认为它就是羊奶,我也同意。可能,比羊奶更浓烈。
是的,是更浓烈的。在月光中,是羌人与客人对酌的一杯青稞酒,是草地与牦牛的相依,是我与一团篝火的亲近。这些,比羊奶更浓烈,我可以欢愉地接受,并想在碉楼里写出月色中的古老和情愫。
在夜里爬上碉楼,我比白天多了一些感受。原因是白天的碉楼太尖锐,让我有了挎刀摸剑的侠客般的豪放情怀。夜里,是朦朦胧胧的世界,让朦朦胧胧的神秘感慢慢围拢我。
我行走在曲折的楼梯上,如一只青虫走在一节节生长的青稞上。当来到一处瞭望口,这瞭望口像一株青稞的花蕊,我感觉到它正张着口,吐纳着天地间的灵气。再走几步,便来到了楼顶,依然会感觉到是一束橙黄的青稞,花已落,结上了沉甸甸的青稞子,散发出带刺的光芒。
我站在碉楼上,可以清晰地听到羌寨里发出的一切声音,哪怕谁在梦里说了一句悄悄话。有一个羌人在月光中,坐在低矮的石板屋里吹响了一支羌笛。羌笛修长,声音清亮,像一朵黄花将碉楼揽在WcukAa1vIHfWdqLeMUcN09qSTs6WQ96Zgi3DHs034RQ=怀里,平平仄仄,高高低低,曲曲折折。而曲子如一群牦牛奔腾于草地和雪山,十分厚重动听,如同身临风雪之中,产生无数的幻觉和思想。
我放慢了步履,特别地小心、谨慎,生怕一个脚步重了,发出了一声响,便打断了一支羌笛的倾诉。我在悠长的羌笛里,似乎更深入了,可听到暌隔千年的凄美长歌。滚滚的历史啊,在这个宁静的夜晚,泛起了连绵不绝的波澜。
可是,当一片云遮住了月光,瞬间又把我浮动的心绪掩埋了。我抬起头来,雪山与我近在咫尺,尖峰上的雪,已然让我迷离恍惚,好像我走到了尖峰,让牦牛的鬃毛,随风飞扬,抖落了紧粘的尘埃。
古羌人对羌笛是那么的热爱,可以说,一曲羌笛可见铁骨铮铮,也可见诗书儒雅。我仿佛看到曲子上,有古羌人的灵魂,被年轻的羌人吹响。羌曲发着幽光,跟苍穹上的星星一样照耀了古拙的碉楼。
羌寨的碉楼散布于雪山的沟壑,有青铜般的质地,有沉稳的面容,有厚重的目光,有磅礴的身影,这些,都凝聚了羌人的精神和情怀。在这个如水的夜晚,我如一个晚归的羌人,骑着一匹马进了寨。我的前头,是一群牦牛,从远远的四姑娘山上下来。牦牛群昂首挺身,四蹄矫健,好像要借着这浩荡的月光,绝尘而去。
不!绝尘而来。
我踏过岷江上进寨的绳桥,晃晃悠悠地,穿过了一片庄稼地,才跳下了马。前面是我的石板屋,心爱的女子已经倚门而立,羞涩地搓着手,等待着我。而庄稼地里的土豆花,在月光下开放,发着淡蓝色的光,笼罩了云一样的柔美与朦胧。
我还是清醒吧,我怎么配得上做一个纯真的羌人!
风窸窸窣窣地响,月光跳出了云儿。我下了碉楼,痴痴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蓦然发现碉楼像羌寨一名普通的羌人,手提镀满月光的锄头,挑着晶莹澄澈的犁铧,站在我的面前。夜晚的羌寨,波诡云谲,在时间里变幻,在空间里生长。安静与恬淡的碉楼,像旷古的风,步子迈得很轻很小,却无意踩痛了流泻的月光。
我愿在碉楼,踩住随风来的、丝丝缕缕的破旧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