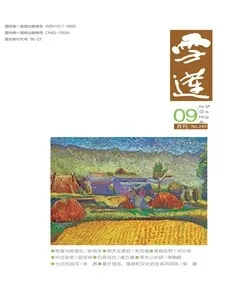村庄秘密
【作者简介】胡宝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冰心散文奖、全国孙犁散文奖、第二届丝绸之路青年散文大赛银奖、全国报纸副刊年度佳作奖、第六届秦岭文学奖等奖项。出版散文集《时光简:二十四节气里的寻常生活》《此生此地》。作品刊发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延河》《时代报告》《散文百家》《海燕》《胶东文学》《小品文选刊》等报刊。
早 晨
早晨,三姑站在家门口。牛圈里空荡荡的,对面树上一只蜘蛛跳来跳去结网,三姑眯着眼睛看。
四岁的妞妞走过来,两个竖着的髻髻,一晃一晃,发梢弯下来,跳来荡去。
蜘蛛勾一条线,线断了,蜘蛛又勾。
妞妞走过去几步了,又折回来,扭头对三姑郑重地说:
“哎,我给你说,你家的牛瞅我哩。你要把它管嘎。”
妞妞一双大大的圆眼睛,像一双黑宝石,一片纯净。
那天,妞妞手中拿着馍馍,边揪边走过来。牛斜过身子,堵在路上,眼睛鼓鼓地、直直地看着她,眼仁像豆腐一样白。
妞妞的小脑瓜接收到了不友好的信号,有些生气:这村里,每一棵草、每一株花、每一条狗、每一个人都和和气气的,还没这样待我的呢。
妞妞深深地瞪了牛一眼,牛长长地瞅了妞妞一眼。妞妞有些委屈,绕过牛后,就把这事儿记心上了。
三姑愣了一下,这是这个碎娃第一次跟自己拉话。
“对。没骂你吧?”三姑从皱纹中挤出了一丝笑容。
“你问问牛。”妞妞说,“我又没惹它,它为啥瞅我。”
说完,就又往前走了,她还有正事,要跟小丫头洋洋跳方去。
妞妞的步子很轻,很快,就像跳跃一样。
旁边的洋槐树叶,被风吹得哗哗响,对她哈哈说笑。
河里的水潺潺而过,还是那么温柔,她站在桥上,水像镜子一样照着她的影子,她扮了个鬼脸。
桥上的白栏杆还在那里,上面留着妞妞画的两个道道,摸上去,凉凉的。
向南望去,河边,几棵杨树下,东东家的羊还在吃草。羊抬起头,咩咩叫了两声,妞妞知道它在跟自己搭话,妞妞朝它咩咩了两声,吐了吐舌头。
桥根竹子丛里,一棵竹笋又长高了一小拇指头高。这是妞妞最先发现的秘密,她捡了片玉米叶子把嫩笋苫住了,谁都没发现。现在,玉米叶子被顶起来了。
“小笋笋,你乖乖儿长吧!”妞妞悄悄对它说。
河东面那一排房子还在,跟自己昨晚睡觉以前看到的一样,没有像梦中那样,飞了。
路上又多了两个坑坑,一个像栗子,一个像梨,不知道是昨晚谁磕出来的,只有妞妞的眼睛能发现,只有她的小脚丫才能试出来。
路边放的一截子桐木,侧面竟然探出了两片嫩嫩的绿叶叶!妞妞趴过去一看,呀,有四五个枝呢,全在背人处偷偷长呢,藏得真好!谁说树躺下了,就不能长了?老桐树睡睡觉,更精神,不是还在长吗?
一疙瘩蚂蚁在渠边忙碌,走近一瞅,是在一个梨核上爬上爬下。谁心急火燎地,把这梨咬了几口就扔了,是谁呢?
妞妞咽了一口唾沫,看看发黄的梨核,想一脚踢到路边去,又怕伤了蚂蚁,又把脚收了回来。
到了艳儿家的硬柴堆跟前,看看四下没人,她朝柴堆里面瞅,好,自己的棍棍还在。那是和洋洋她们玩耍,扮老师,自己给自己找的一根洋槐教棍呢,幸亏没被艳儿外婆当柴烧了。
妞妞,有点想念艳儿。艳儿爸爸妈妈到很远的城市打工,把艳儿在这里只放了半年就又接走了。玩熟了的伙伴就像鸽子一样飞远了,妞妞看着东面山梁上歪歪扭扭的山路,艳儿就是从这里走了的!
太阳慢慢爬上了山梁,照亮的先是河西面,现在才到河东面。妞妞觉得,是自己的小脚丫踢着太阳走过来的。快走到洋洋家时,自己的前脚就踏在暗处,她的脸却迎上阳光了,她闭上眼睛,让爷爷婆将她好好暖了一暖,眼窝里有鸡蛋黄在晃。
旁边门前,两绺白菜地,边用枣子罩着。小白菜,伸展开叶手,露珠儿在上面滚来滚去,亮晶晶的。一绺地的绿叶上有好多麻点点,那是虫子吃过的,这虫子嘴真馋。妞妞想去给这家人说说,但那门上挂着锁。每一回经过,都看见这家门上挂着锁,没人了吗?
到了洋洋家,推开虚掩的门,院里静悄悄的。进到里屋,没见洋洋,洋洋奶奶说,“妞妞,洋洋去她姨家了,你后儿来。”
妞妞出来,心里有些湿漉漉,有好多话儿在心里蹦来蹦去,一颗一颗都像金子一样闪光,本来要给洋洋说哩。想了一晚上哩,一早上就赶紧过来给洋洋说来,还怕这些话儿跑了呢。
风吹过来,凉丝丝的,阳光在菜叶上闪光,一行鸟儿在头顶飞过。
桐树上停着的两只长尾巴雀儿,一只“嘎”了一声,头一拧,飞走了。另一只赶紧振翅追了上去,翅膀上掉下一支长长的花羽毛,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往下落,妞妞接住了。
妞妞的心又暖和起来,心里的话儿也叫风吹光了,想别的了。
“妞妞——”河对面传来呼喊的声音,是奶奶,叫她吃饭。
爸爸妈妈在城里打工,好长时间才回来一次,奶奶经管她。
“哎——”妞妞应了一声。往回走,随脚踢起一颗小石子,小石子骨碌骨碌,踢一脚滚几步,踢一脚滚几步,像陀螺,妞妞看着,就像自己的影子。
菜地、蚂蚁、桐叶、小河、影子、羊……一样一样又从妞妞的眼角过去。妞妞又睁大眼睛,就像她头一次来到这里,就像她头一次睁开双眼看到早晨,从桥东往桥西,那是全新的一条路。
在妞妞的眼里,啥都像第一次见到。
过了桥,远远看见,牛已经拴在了木桩上。瞟见了牛,妞妞决定,不理它!妞妞生它的气了,妞妞吊着脸,连牛看都不看,往前走。
织了半面的蜘蛛网斜挂在那里,沾着露水。
北边过来几个人,三姑夫的手里拿着一截牛缰绳,是那头牛的。妞妞转头一瞧,圈里拴着的不是大牛,却是一头黄牛犊。黄牛犊忧郁地望着她,眼珠里一圈一圈蓝莹莹的,最深处也站着个小女孩。妞妞对它和气地点了一下头,眼珠里也点了一下头。
牛贩子将一沓钱给三姑夫,三姑夫将钱递给了三姑。三姑的眼窝里有泪。
两边的洋槐树,往后退去,妞妞的脚步越来越快。妞妞在心里将那头大牛原谅了,将小牛当朋友记在了心里。
快到家门口了,小狗花花摇着尾巴迎了上来。
“大牛妈妈走了,小牛会不会哭?”
将一碗玉米糁子放在门前的大石头上,剜了一筷子,递进口里的时候,妞妞这样想。
风吹过,树梢的叶子哗……哗……
风一吹,从雀儿身上掉下的那支羽毛孤单地飞了起来,牵走了妞妞的目光,妞妞的心也起起落落……
忽然,脚心一阵痒痒,小花狗在逗她,花花最懂她了。这痒痒真痒啊,比挠胳肢窝还痒呢,她又咯咯咯笑起来,短暂的不快又烟消云散了。一件一件开心的事儿又在心里争着挤着闹,她心里乐乐的,大口大口吃起饭来。
在这个平凡的早晨,早起的小女孩妞妞发现了这个村庄许多新鲜的变化和秘密。这些秘密带着露珠儿,那些散布在远方城市角落里打工的这个村庄的男人、女人们,留在这个村庄经管娃的老汉、老婆们都没有发现。
妞妞的心里充盈着发现的喜悦。
晌 午
晌午,全村人都到过事的张家吃饭,喝醉了。家里无人,门上着锁。
大红公鸡跳上了院墙,气宇轩昂地踱了一圈步。突然,看到墙根立着一根甘蔗粗的木桩。那是修厨房时,山墙根搭毕架遗留的一根。红公鸡,瞅着四下无人,心血来潮,竟然振翅一跃,双脚抱住木桩,一溜烟退到了地面,然后扯开左膀子,蹬了蹬左脚,弹了两下,就飞快地撵花母鸡去了。
这一幕,被藏在崖头栎树冠中的妞妞悄悄看在眼里。红公鸡竟然有这种绝技,还一直大隐于圈。这么重大的事,妞妞竟然不知道。父亲扎那么高的墙,它们想出就出想进就进,在妞妞们面前,竟然装得都是飞不过去的样子。
鸡们给妞妞留足了面子。妞妞要重新认识家里养的这些鸡。
和食的细竹竿倒了,倒在圈中躺着的一截老桐木和脸盆之间横着。鸡娃跳上竹竿小小心心晃晃荡荡从大头走到小头,又得意地从小头往大头走,不慎打了个趔趄,翻了下来,掉在小水潭里,滚了个蛋儿,又站起来,一身花。
鹅从猪圈中跳上圈门,扑地,落下来。然后,一步一摇,走到院门下。门槛没有安,鹅就从门下钻出去了。母鸡带着七八只鸡娃,追随着鹅,也出去了。公鸡则在院子里溜达了一圈,飞上猪圈的豁口,再飞上崖下的二台。院子里顿时变得空空荡荡而且安静下来。
妞妞打了个盹。梦影中,有个熟悉的身形在眼角晃动。是一只小鸡娃,刚从家里溜出去的,已经爬到崖上,没到栎树跟前来,却顺着小路拐到北面一排人家崖背上的树林子里去了。
它们干啥去了?妞妞从栎树上跳下来,悄悄绕到树林上面的那片地里,再慢慢爬到塄坎边。这片树林,有柿树、柏树、枣树、洋槐、竹子、杨树、土槐、椿树,长得茂盛,将这里围得密密匝匝。中间有一道空地,长着些狗尾巴草、蒿草、莎草。两棵柏树中间是一从茂密的竹子,妞妞潜伏到了竹子丛中,往下瞅,哇,来了这么多!
一根倒伏的洋槐树,搭在塄坎上,拱成了一座高高的桥。桥顶端的树枝上挂着一个大竹圈圈,悬在空中两米高处。五米开外,严家的黑狼狗、何家的灰哈巴狗、陈家的白板凳狗、吴家的花狗等挤在一块。花狗,没有谦让,直奔过来,在跳跃的一刹那,尾巴磕在了竹圈上,竹圈圈晃了几晃。白板凳狗,也跟着跑,到跟前,却刹住步,犹豫了,返回去了。这时,黑狼狗低沉地叫了一声,几只狗马上给它闪开。它挖脱就跑,到竹圈圈前,一跃而起,从竹圈圈中穿过,像黑色的闪电。动物们都惊喜起来,将爪子和翅膀在树上拍得哗哗响。
两只翘着大尾巴的松鼠,尾巴上拴着一根红头绳,跳到两个大土疙瘩上蹦紧了。一群鸡、鸭、鹅你挤妞妞,妞妞搡你,跃跃欲试。妞妞一看,各家各户都有代表哩。站在洋槐树上的大红公鸡,“喔——”地叫了一声,这群鸡鸭鹅争先恐后向前跑去。站在前排的英子家的瘦母鸡非常灵敏,就在大红公鸡发令前的一瞬,它已嗖地冲了出去。这只母鸡,下蛋不行,鹐仗勇猛,常把隔壁邻家的公鸡鹐得毛发飞扬,是骂街无人敢惹的角色。村里几个主妇给英子妈建议:把这不生蛋不罩窝的货不卖了去留下做啥呀。英子妈说,等下长肥些划着卖了一卖。这鸡善于保养身材,老不见肥。看着这只鸡跑出去,其余的,都往前撵,钩钩绊绊。妞妞家的那只鹅,也矫健地往前跑,妞妞从来没见这家伙这么快当过。在家里,它总是个慢性子。跑了十几米,红线在望,瘦母鸡埋头冲刺,艾子家的鸭子和几只鸡紧随其后,到了红线跟前,它们一头从红线底下钻过去了,红线太高它们够不着。这时,鹅跑了过来,头仰得高高的,胸脯将线带走了。两只松鼠跳到了鹅的背上,鹅赢了!树林里又一阵噪闹庆贺。瘦母鸡和几只鸡鸭不服气,撵着松鼠鹐,松鼠哪有那么好捻弄的,嗖地蹿到树上去了。瘦母鸡领着鸡鸭围着树骂。
小牛犊和山羊抵仗。小牛犊是严家的,山羊是陈家的。牛犊猛冲上去,山羊左面一躲,扑空了。牛犊有些恼怒,掉过头,又冲过来,山羊往右边一闪,牛犊又扑空了。它愈发焦躁,匆匆转身,气咻咻地一下又一下攻击。山羊还是不急不躁随着它的节奏闪避。旁边的动物们看得紧紧张张,叫好的叫好,拍掌的拍掌。牛犊的眼愈发的红,它一头拥到山羊的脖子底下,将羊往崖边掀,大公鸡赶紧打鸣,做裁判的骡驹将两个居中分开。骡驹刚回身,牛犊又向山羊冲,山羊发怒了,一头顶在了牛脖子上,牛犊收不住脚步,直冲过去,绊倒在崖根。骡驹顶着个花环过来,两只松鼠姗姗过来,将花环从骡驹头上卸下,套在了山羊角上,山羊赢了。
接下来,猫和兔子比上树,松鼠和老鼠比打洞,蚂蚁走正步,斑鸠和麻雀跳了舞,青蛙和鸡娃比叫鸣……最后,这些动物,能飞的站在树上,能跑的站在地上,会打洞的站在洞口,全部肃立。大红公鸡飞到柿子树伸向空白场地的那根枝上,扯开嗓子开始训话。公鸡的叫鸣,妞妞听了好多年,略能揣摩来一点意思。它说:
“世道变了。这个山沟沟已经不是以前的模样。但是,不管世道怎么变,咱们都要寻自己的活路。要向祖先学习,长翅膀的要把翅膀练硬,能飞得又高又远;长腿的要把腿练得又强又壮,能跑得又远又快;会打洞的要把爪子磨得又锐又利,能把洞打得深深的。鸟要活出鸟样,畜要活出畜样,虫要活出虫样,总之,要有个样子!万不敢学村里那种懒倯人,游手好闲。但是,还要保持低调,你知道,世界上最爱害红眼病的不是我们鸡,而是人。”
远处传来了喧哗声,吃酒席的人们,正往家里赶。
“散了吧!”
一声之后,天上的飞,地上的走,洞边的散。一会儿,树林里变得空空荡荡,安安静静。妞妞沿着小路回家,人们歪歪斜斜相互搀扶着寻找家门。进了屋,鸡在圈里,鹅在圈里,斑鸠在树上,一切照旧,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半 夜
妞妞在高粱地打了个盹,睁开眼。
天空倒垂下一股炊烟,一只猴子自山顶一跃而起,揪住了烟头,蜷身翻卷而上,炊烟“簌簌簌”缩短、膨胀,最后团成了个球,直上天空而去。
妞妞站起身来,伸出了手臂,是想抓住,还是想招手?
恍惚间,天空一片碧蓝,只剩下一片棉花丝似的白云,月亮高悬于山梁之上,硕大无比。
高粱,带着自己的影子,密密匝匝站在地里,还有妞妞。
这是这个村子几十年发生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一只猴子拽着炊烟飘到天上去了!妞妞激动地想在山坡上大喊,把全村人叫起来。
回到庵子,妞妞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妞妞跑到村里,敲开一家一家的门,说:“猴子,一只猴子拽着炊烟飘到天上去了,你看到了么?”
披着衣服的男人、女人,全是神秘地一笑,不言语。
一扇扇的门关上了,妞妞又回到了野地。
月亮的大脸盘子,落在山梁粗犷的线条上,月亮肯定是看见了。
“月亮,你看见了么?”妞妞大喊。
月亮,黄着脸,神秘地微笑,不言传。
月亮,你也不肯做证么?妞妞躲到庵子里,透过麦草的缝隙,偷偷看月亮。一丝儿云,慢慢游过去,又荡回来。月亮仍然装样子。
妞妞溜下庵子,隐到高粱地里,像一棵高粱一样站着。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脸像一面鼓。妞妞终于忍不住了,妞妞从地里捡起一块像骨头一样的石头,像射箭的人一样,拉开倒弓步,身子后仰,然后使出浑身的力气,将石子扔出。石子飞了起来,像一枚利箭向月亮疾驰而去,在碧蓝的天宇飞、飞、飞,最后直接扎入了月亮当中,不见了踪影。
没有声音。没有涟漪。
月亮是一面破鼓,不响。月亮是个虚空,月亮的背面还是虚空。
妞妞俯下头,让妞妞拉长的眼神重新弹回。
眼前的一根高粱,强大的龙须根从地面腾跃而起,收束到主干。一行蚂蚁,顺着最粗的须根列队前进,爬过须根拱桥一般的顶,然后集中到秆根。它们散开队形,将主干围了一圈,然后像比赛一样向上爬去,像给高粱秆套了一个黑色的环。
蚂蚁,你今晚上也不睡觉了么?
环慢慢向上升去,眼看就升到高粱头了。这株高粱慢慢也长起来,伸出了高粱地的海平面,像一只鹤立在鸡群里,接着像一竿饱满的竹子一样,向空中长、长,越长越高,拉远了妞妞的目光。寂静的山谷就起了一根竹竿一样的高粱,一丈、两丈、三丈……黑色的环儿旋转着向上疾追而去……
所有的高粱都仰着头看,惊呆了。
这时,就在这时,架着月亮的山梁上,从月亮的阴影里,突然发出蓝色的声响。一个小黑点,跳跃而出,画出了一道悠扬的弧线。黑点像滴在宣纸上的立体墨点,濡染成一溜飞转的小黑团,黑团越来越大,待到半空中,黑影变亮,方显现出一只兔子的形状。兔子,像绵羊一样大,通体像圆润的玉瓷,耳朵长竖像两只长长的翅膀,眼睛像红色的湖泊飞旋着光芒,向下扑来……
所有的高粱和妞妞都倒吸一口凉气,心紧紧收缩在一起。
这时,那秆高粱急速迎上去,在高高的离月亮不远的空中,蚂蚁环滑出粱头,像黑玉镯在高粱顶旋转,越旋越大,像一个巨大的铁环。
玉兔,长开耳翅,伸开四脚,滑行而下,正好从黑玉镯中穿越而过,似流星一般飞向远方。
黑玉镯,倏地从高粱顶滚下,高粱急速地缩短,蚂蚁环急促地抢着下旋,生怕被遗留在空中。
一阵风过,高粱地重又恢复了安谧。月亮,在身外的山梁之上只剩下了半边脸。
妞妞对着高粱地也神秘地一笑,没有言语。
在这个山村的那过去的成百上千个夜晚,不知秘密地发生多少神奇的事情呢。
后 夜
后夜,妞妞走上崖头。白雾当中,围绕一方麦田的小径勾勒出三十年前的老村庄的轮廓。爸爷后院的椿树们像在地下潜伏一样,唰唰长出来,长成三十年前的模样,妞妞都以为那根都掏尽了呢。一个院落就站在妞妞的面前,妞妞站在三十年前的时光里。妞妞的左胳膊开始疼痛,那就是在后面的路上摔的。
一围土墙,朝东的是大门,闭着。朝西的,往椿树林开的,是后门,关着。爸爷就在这院子住着。他是妞妞爷爷的叔叔,是妞妞听说过的胡家最老的老人,是妞妞们所知道的胡家最老的祖先。他活到八十多岁,无儿无女无伴,一个人居住在这院屋子里。
妞妞再趴在门上,透过门缝往院子里看。院子里,依然杂七杂八堆着羊吃过的洋槐树梢子,一摞一摞的。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脚步踏出小路,绕着摞子。羊在一个堆子后面,露出头,拽着一根树梢子,啃上面的绿芽芽,铁链子一动一响。院子里的两间老土屋,应该是厨房和卧室连着,朝南的门开了半扇子,里面黑乎乎的。妞妞细看,看出是个案板,稀稀拉拉放着几个碗碟。案板旁边是灶火。灶火那边应该是炕了,妞妞看不见。
雾,化成一丝一丝的,聚成一股,在树林子,在院子里,绕来绕去。浓的,在月光下,泛着白光。恬淡的,犹犹豫豫,似乎要不见了。月亮悄悄露出脸,慢慢长大,白晃晃的,走到了晚上的晌午时分。
屋子里有了响动,妞妞闪到院墙的侧面。一阵,爸爷扛一个锄头,牵着那只羊,出来,轻轻地把门阖上,将门钥吊搭在门环上,然后朝南走去。他从不锁门。爸爷披着棉袄,妞妞只看见他高大而又瘦削的背影,这影子弯折,像一把弓箭。妞妞没有看清他的面容,或许是妞妞忘记了。忘记了一个人的面容,即就是再见也看不清他。
爸爷朝南走了一段路,顺着崖上刻出的窄窄的小路,往沟里走。羊,跟着他,小心翼翼,身子贴着崖壁,怕掉下去。妞妞在后面远远跟着。爸爷和羊,从小路下去,走上围堰。沟里,空空荡荡,和往常一样寂静。爸爷扛着锄头,牵着白羊,往前缓缓移动。围堰侧面,一个人影,扛着一个头的影子,带着一个四只蹄子的影子,也在走。有时平坦,有时弯曲。走到东面梁根,羊一步跃过小河,顺着坡上的小路飞奔而去。爸爷不紧不慢,上了小路到一片地里,这片地是他的地。一年四季,只要日头出来,他就要到这地里来挖。地南北吊,中间塄坎根有两个土堆,土堆上长着两棵核桃树。地边的塄坎上随意地长着些小洋槐、酸枣树、杂草。地南头,挨着一片树林,大树已经伐了,剩下一窝一窝的次生矮个子树枝。
爸爷一锄头一锄头挖着。那么多年,人们远远地看见他,一个黑影子,在这片地里挖、挖、挖,一年四季挖,长年累月挖,仿佛地里有黄金、有宝似的,好像他有使不完的劲。
这天夜里,爸爷仍然在挖。他把锄头抡得高高的,在月光下一闪,挖向地里,无声无息。羊儿在地头的树林里埋头吃草,嘴不停地动,没有声音。妞妞远远地看见,地里新挖的土疙瘩,印着尺子般的头印,像一个个长长的印章,亮晃晃地摆在地里。新土与旧土,就这样分别出来。爸爷挖谁的地呢?现在,这块地分给文家人种了。妞妞去过一回,发现,地是平出来的梯田,土壤单薄,料礓石特别多。这薄薄的地,这料礓石,他像挖宝一样,挖了一年又一年。爸爷一年一年,将料礓石挖出来,堆在了地头。地和树林之间,原先是一片荒草坡,爸爷将荒草挖了,他一年一年耕种,将生土种成了熟地,这地就长了许多。为什么把这样的地分给爸爷,妞妞不知道。今夜,爸爷像往常一样,将力气从身体里使唤出来,将锄刃挖进土和料礓石里,将汗水洒在土里。他挖着三十年前的地,将汗水像往常一样流下,滴落在地里,无声无息。这土地,是他的地,又不是他的地。他劳作在三十年前,又不在三十年前。今夜,是他在劳动,又不是他在劳动。看到他的是妞妞,又不是妞妞。
几个时辰过去,月亮向西。肚子圆圆的羊出现在地头小路,爸爷头上挑着一捆洋槐树梢子,跟在后面。下了地,跨过河,走过围堰,攀上崖来。他们走了一路,影子也走了一路。爸爷轻轻地将门钥吊取下,推开门,羊儿敏捷地一跳,进去了。爸爷将洋槐梢子一扔,悄悄将门关上了。
妞妞有一种欲望,想呐喊,喉咙又喊不出。这夜晚,没有声音。爸爷劳动,没有声音,羊吃草没有声音,妞妞走路没有声音。这是没有声音的世界。爸爷对妞妞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说过话,这村庄就没有话。只有说过的话,三十年后,才能被听见。或许是妞妞太小,爸爷跟妞妞没有啥话说。他跟妞妞隔着100多年的岁月,他觉得说的话,妞妞听不懂。他没有给妞妞这个小不点的晚辈留一句话,捎给长大的能懂的那个妞妞,让妞妞听懂记住。他没有。还有那只羊,在妞妞眼里,它只吃草,没有朝妞妞叫过一声。今夜,所有看过的,都能再现,所有听过的,也能再听,但是没有声音,悄无声息。
妞妞想问问爸爷,他父母的事情,他自己的事情,他兄弟姐妹的事情,妞妞们的祖先的事情。这些,妞妞都想知道,但不得而知。妞妞只能问到他,他是妞妞见过的最长的长辈。但妞妞的声音传不过去,他的门闭着,他听不见妞妞的话。
雾越来越淡,几乎不见。椿树们像融化的冰棍,慢慢变矮,最后长回了地里。这一院屋子,也越来越淡,越来越像个影子,最后飘散,成为一片麦田。
妞妞是个爱做梦的女孩,午睡做梦,夜眠做梦,玩累了打个盹就能做个梦,一个梦接一个梦。她梦见晌午,梦见动物们的运动会。她梦见高梁地,梦见猴子拽着月亮上了天。她在梦里追寻老去的人,寻找自己这个小娃娃的祖先。梦在她心里全是真的,就像她走过村庄留下的一个个小脚印,别人看不见,她却看得清清楚楚,因为那一个个小脚印,都在发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