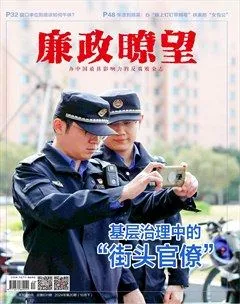古代官僚体系中的微末小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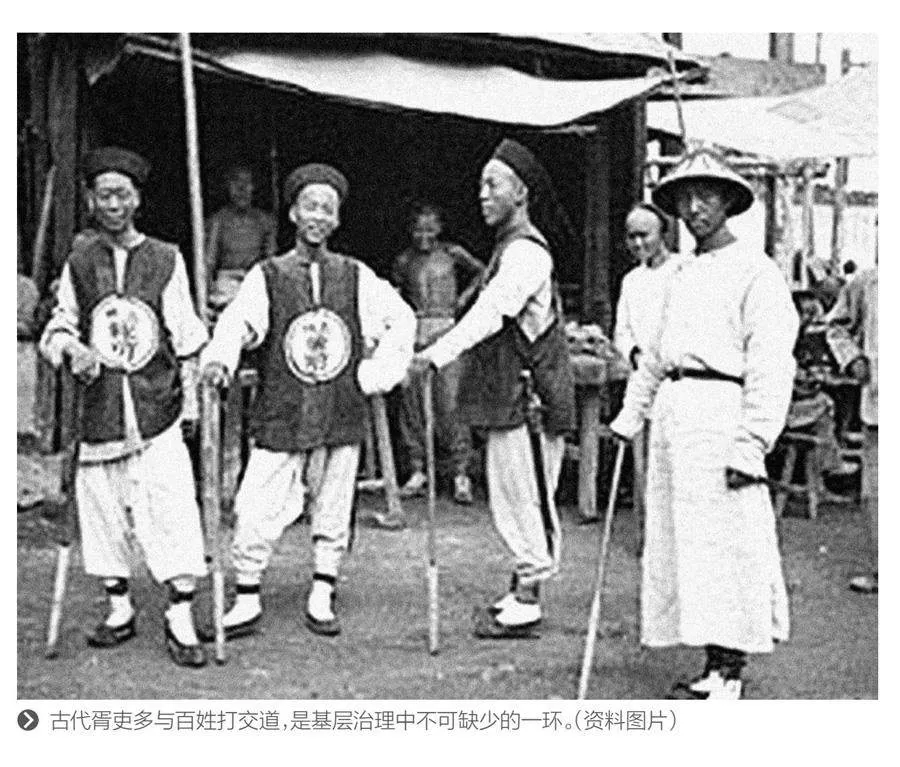


秦朝末年群雄并起,魏国名士张耳、陈馀二人也位列其中。二人原是刎颈之交,在秦灭魏后,为躲避秦国追捕,他们更名改姓逃到陈县(今河南淮阳),以里监门一职谋生,负责看守里门,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
张陈二人的故事中,最令人唏嘘的大概是这对挚友最终在楚汉之争中,走上了各为其主、你死我活的道路。不过,细读史料,张耳、陈馀在隐姓埋名期间有一段经历也颇有意思,为后世一窥古代早期“街头官僚”的形象留下线索。
支撑国家政权的基层力量
《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记载,“里吏尝有过笞陈馀,陈馀欲起,张耳蹑之,使受笞”。这句话讲的是陈馀在当里监门时被里吏找麻烦,陈馀本想反抗,却被张耳悄悄阻止,老老实实承受了里吏的笞打。
秦汉时期,“里”是县乡以下的行政层级,可以说是最基层的组织。而所谓“里吏”,就是“里”中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拥有一定执法权的人员。不过严格来说,里吏并没有“编制”,也不享有正式官吏应有的升迁途径,他们似官又非官。在张耳、陈馀的故事中,陈馀被里吏寻到了过错,于是里吏有权惩罚他。但张耳似乎不太看得起里吏,他劝陈馀忍耐时说:“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意思是如今才遭受小小的屈辱,就要死在里吏这里,不觉得不值吗?
实际上,张耳、陈馀担任的里监门一职也是里吏的一种。先秦、秦汉时期,里门是用来严格管理百姓进出的。里监门的职责就是按时开关里门,并监督进出者,如果有异常情况须及时上报给一里之长——里正或里典。颜师古在注《汉书·张耳陈馀传》时写道:“监门,卒之贱者,故为卑职以自隐”,至少在先秦、秦汉时期,里监门、里吏这样的职务是被人看不起的,正适合隐姓埋名。像刘邦的谋臣郦食其那样,担任里监门时“贤豪不敢役”,只是特例而已,因此他也被称作“狂生”。
费孝通曾提出“双轨政治”说,他认为在中国古代,自上而下的皇权有所不及,“到县衙门就停了,并不到每家人家大门前或大门之内的”,还有一轨是自下而上的绅权。但实际上,里吏这样类似“街头官僚”的角色就是“皇权下县”的触手。里吏被称作“吏”,说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官府的“代言人”,既是官府政令的传达者,也是具体的办事人,是庞大官僚系统中的神经末梢。他们深入触及每家每户,与一般百姓密切接触,配合更高层级的官员对百姓进行管理,具体负责户籍管理、催征赋役、维持社会秩序、组织社会生产等工作。
里吏虽是“位卑人轻”,却在秦汉时期的政治兴亡轮转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有学者认为,“秦代的速亡,里吏是催化剂”。像张耳、陈馀、郦食其这样的人物,都曾是里吏。就连建立西汉的刘邦,也是出身亭长这种基层职务,拥有击鼓召集里吏、维护地方治安的权力。这些与地方父老频繁打交道的“街头官僚”,在基层有广泛的影响力。
就治理智慧而言,类似里吏这样的“街头官僚”设置的初衷是支撑国家政权。他们虽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官员,但确实由国家正式任命、由国家发放微薄报酬、由国家严格管理约束,以保证他们忠实地执行国家政策。然而,在社会力量此消彼长的变化中,基层小吏很难不受到地方势力的影响,他们具体的行政行为直面两股压力——上层官僚与地方豪强势力,某些情况下甚至不得不在两者中做出取舍。《汉书·酷吏传》中就记载了一些小吏对一些豪强大姓避之如虎,“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两千石,无负豪大家。’”意思是宁可得罪食禄二千石的太守,也不要得罪地方豪绅。显然,作为“街头官僚”,这些小吏在权衡利弊时,更倾向选择向自己接触更多、对自己影响更大更直接的地方豪强靠拢。
当然,即便没有地方势力的影响,小吏也会出于一些自身的考量,与国家利益背道而驰,如东汉官员左雄指出的,“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小吏事务繁杂、俸禄微薄,统治阶级也看在眼里,西汉时,汉宣帝曾特意颁诏,认为“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对此,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简单的加俸。此举效果明显,“汉世良吏,于是为盛”,但显然只是一时的,不足以从制度层面防范小吏鱼肉百姓。到了封建社会后期,所谓“小吏”的胡作非为就变本加厉了。
备受诟病的明清胥吏
“街头官僚”一词是西方概念,当人们将其放入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态中,试图寻找适配角色时,很容易联想到明清时期的胥吏。相比于早期的小吏,封建社会晚期的胥吏的形象更为明晰,并且大多数是负面的。他们政治地位低下,大部分属于“贱民”,子孙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但可以借公务之便对一般百姓磋磨拿捏,从中渔利。
要用胥吏来适配“街头官僚”的概念,就不得不厘清“官”与“吏”。一般认为,官吏分途的现象起源于魏晋南北朝,并且在隋唐之际成型、持续到清朝灭亡。官吏分途后,在具体的衙门中,官员主要负责领导和决策,胥吏则是执行具体公务的行政辅助人员。其中胥与吏也有所区别了,前者与基层百姓接触更多,主要是执行一些体力任务的人员,如衙役、捕快都属于胥;后者工作更类似文员,如书吏、师爷等,他们辅助官员的文书工作,提供参谋等。由此看来,官吏分途后的胥,更贴合街头官僚的含义,只是在古代政治语境中,胥与吏往往合在一起,难以剥离而分论。
明清时期的胥吏往往为人诟病,在史料和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描述与刻画。对于他们来说,与百姓的接触正是捞好处的珍贵机会,甚至一些衙役会从书吏手中购买“差票”,获得这样的机会。古代衙门在办理案件时,承办的房科书吏有权染指派差公务的佥点程序,并暗中操作,衙役便花钱争取出公差的机会,下乡传拘犯人或证人。当然,前提是他们了解到这趟差能从“民间加倍取偿”,才舍得花这笔钱。清朝雍正年间的名臣田文镜说这些人,“一到被告之家,即索取酒饭差钱”,“有钱者人犯不必见官,即便销案;无钱者故意延挨,多般吓诈,必遂其欲而后止”。
除了案件涉及的人外,一些无辜百姓也可能会受到牵连,遭受差役滋扰。清朝嘉庆末年就出现了所谓“贼开花”“洗贼名”等现象。所谓“贼开花”,指的是盗案发生后,差役将事主邻近一连串的“殷实而无顶戴者”诬陷为窝户,将他们拘押起来勒索钱财;“洗贼名”则是指被诬陷的百姓出钱、差役分肥后,百姓被释放,身上的污名被“洗”去。
古代胥吏在执行公务中欺压百姓是普遍现象,拿捏衙门官员也是屡见不鲜。清代学者、官员刘衡在《州县须知》中记载了他所听闻的一起差役与门丁合谋挟制县令的事件,告诫地方官员慎重选用差役、门丁。说是某县让某差役限期捉拿一名要犯,并给出了一千圆的悬赏。差役按期完成了任务,押送犯人到县衙时,负责看门的门丁李某却拦下了,让差役先把犯人藏起来,并向县令禀告称犯人已经逃远,“增三千圆则可”。县令不情不愿地加钱到两千圆,门丁和差役仍觉不够。县令转向找差役的麻烦,不料差役早就被门丁藏起来了。最终,县令只好支付了三千圆,门丁与差役“始将所获之犯交出”。
有学者认为,尽管胥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低下,但很多人却对这一职务趋之若鹜,“甚至服务期满后,以更换姓名方式继续留任。这其中除了在承办公务中可以捞取实惠外,日常出入公门,在衙门中办事可以作为一种‘护身符’,防止受到他人的欺压”。
胥吏的蜕变
客观来说,胥吏这样的“街头官僚”在古代是皇权与基层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他们在与基层交往过程中,如果能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将是基层治理中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不乏一些正面的胥吏形象,折射出这个群体中的闪耀部分。
元杂剧《玎玎珰珰盆儿鬼》讲述了小商人杨国用出外经商,回家途中寄宿在瓦窑村的“盆罐赵”家里,却被赵家夫妻二人谋财害命的故事。赵家夫妻将杨国用的骨灰捏成了一个瓦盆,送给退休衙役张撇古(一作张别古)。杨国用的鬼魂向张撇古陈诉了自己的冤情,张撇古决定挺身而出替杨国用伸冤,多次遭遇挫折也没有放弃,最终真相大白,赵家夫妻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张撇古有一段独白,大概表达了一些坚守良知和正义的胥吏的心声:“俺为甚的无柴少米不纳民间价,为甚的穿衙入府不受官司骂。也则为公心皮道从没分毫诈,也不是强唇劣嘴要做乡村霸。”他们在基层治理中实际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但得不到应有的权利和待遇,甚至被看轻、歧视。在古代的局限性下,他们要么因办事不力被官府责罚,要么忠实于官府被百姓视作走狗鹰犬,很难找到微妙的平衡点。长期心理失衡与挫败之下,能始终保持良善本性、为百姓奔走的值得钦佩,而选择剑走偏锋,非法获得一些利益补偿的行为,也不难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胥吏的形象多以负面为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掌握了话语权和叙事权的是官员。在官员的视角中,胥吏不仅害民,还病官,类似“州县之吏病民而止尔,司道之吏能病官,督抚之吏病大吏”这样的话语,几乎将吏治的问题一股脑推到胥吏身上。可更普遍的情况是官员、胥吏合作分肥,胥吏是官员贪赃枉法的趁手工具。
清朝有官员就认识到,胥吏是否能在与基层打交道中欺压百姓、捞取油水,在某些情况下取决于本衙门官员的态度、性情和能力。田文镜在《钦颁州县事宜》中写道:“官有胥吏……其中虽不乏勤慎之人,然衙门气习,营私舞弊者多。苟本官严于稽查,善于驾驭,则奸猾固皆畏法而敛迹,否则纵恣无忌,虽勤慎者亦且相率而效尤。”这段话可谓一针见血指出了部分胥吏在乌烟瘴气的官场中,因“畏法之心不胜其嗜利之心”,从而“奉公之事皆化为害人之事”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