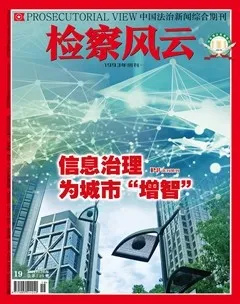“职业骗薪”案的治罪与治理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是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检察机关积极发挥法治服务保障作用,聚焦企业发展过程中多发性、类型化、普遍性的法律问题,通过公正司法引导公平竞争、定分止争,切实保障企业健康发展,促进改善民生就业,这是以检察工作融入经济发展大局的体现。对于“职业骗薪”案件,检察机关不仅要在刑事层面予以打击,确保准确适用法律、依法取证,还要关注其背后的犯罪治理问题。
刑民法律适用
陈苹:在“职业骗薪”案件中,犯罪分子通常会伪造简历材料和夸大工作能力;而在企业招聘过程中,应聘人员为取得入职机会也会有编造简历和夸大能力等欺诈行为。两者之间存在哪些差异?司法机关应当如何精准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进而对“职业骗薪”行为进行定性?
石玮:我认为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具体到行为性质的认定,应当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违法性。行为人以非法占有目的,骗取入职机会、虚构劳动事实,最终骗取被害企业发放薪酬,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具备违法性,就应当认定为刑事诈骗。二是社会危害性。需要结合被害企业所处行业、所造成损害及对市场公平就业的挤占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不能“一刀切”。三是刑事惩罚必要性。“职业骗薪”通常由团伙实施,成员“化整为零”同时入职大量企业,在骗取巨额薪酬的同时,又具有较大隐蔽性,被害企业往往难以发现,也难以通过民事途径获取救济,故有必要以刑事手段介入予以打击。
郭勇辉:我稍微有一些不同看法,刑事诈骗和民事欺诈间还是存在明显区别的。从事实基础上看,刑事诈骗是虚构事实,没有基础事实和履行可能性,而民事欺诈则是夸大事实或者虚构部分事实,一般有基础事实和履行可能XcI5i8MPFrE+Ned28lkbIg==性;从履行态度上看,因为履行劳动合同的基础不存在,刑事诈骗行为人没有履行的积极性,而民事欺诈行为人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履行瑕疵,但还是有积极履行合同的行动。当然,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最重要的区别是侵犯对象的不同,民事欺诈侵犯的是民事主体的权利,刑事诈骗侵犯的则是社会秩序,即国家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民事主体有序行使权利的状态。当侵害行为发生时,民事主体如能够进行自救,侵害行为不足以影响社会秩序的,那么侵害就属于民事欺诈。当民事主体受到侵害而不足以自救,需要公力救济时,此时侵害就属于刑事诈骗。
何银松:我认为需要综合考虑三个方面要素对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进行区别:一是主体要求。行为人不具备职位要求的资格、能力等要求,却通过伪造应聘材料骗取工作机会,其初步符合刑事诈骗的主体要求。二是主观故意。刑事诈骗的故意是直接故意。以房产销售宣讲会为例,如行为人招募大量群演组织宣讲会,其主观目的仅是为骗取薪酬向公司维持积极工作的假象,则其行为构成刑事诈骗;如果目的是销售房产,仅招募部分群演活跃气氛,对其行为应在民事层面的评价;整体上看,对欺骗行为的性质应放在整体行为中分析具体的作用,再进行主观故意的分析。三是危害后果。刑事诈骗相较于民事欺诈对社会秩序的危害显然更大,“职业骗薪”案打乱了市场要素的正常配置,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产生了持久的危害。结合刑法相关罪名的追诉标准,构成刑事犯罪的,应当依法予以打击。


李振林:我认为确证关键在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标准因诈骗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常见的诈骗类型主要有交易型诈骗、资格型诈骗、使用型诈骗等。“职业骗薪”案件属于交易型诈骗,形式上表现为行为人付出劳动,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交易行为。交易型诈骗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要重点关注有无交易的基础事实,以及是否提供了交易对价。“职业骗薪人”获取工作机会的学历、工作经历、其他符合职位要求的证明材料系伪造,是属于没有交易的基础事实;通过伪造工作日志、招募“群众演员”伪造工作业绩等方式骗取企业薪水,是属于没有提供交易对价。既没有交易的基础事实,也没有提供交易对价的,可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能将“磨洋工”“摸鱼”等职场消极怠工行为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为员工获取工作的基础事实是存在的,只是没提供交易对价。也不能将不具有交易基础事实但提供了交易对价的行为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伪造应聘材料获取工作机会,但入职后胜任工作的情况,行为人虽然不具有交易的基础事实,但提供了交易对价,因此这不能被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证据固定认定
陈苹:“职业骗薪”案通常涉案人员众多,团伙作案与个人作案相交杂,有着大量的被害企业和庞杂的涉案金额,这一方面反映了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性,另一方面也造成司法实务打击其犯罪行为在取证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对此有哪些应对策略?
何银松:从侦查机关角度看,“职业骗薪”案需要搜集的证据范围很广,包括:行为人的身份、工龄、学历、简历、资格证书等与履行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信息;上家单位的离职证明、联系方式;社保记录、薪资流水,以此了解行为人的工作经历与时长;是否存在竞业限制义务或商业利益冲突的情况;是否涉诉或存在司法负面征信信息;证人证言,被害企业负责人、关系人的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聊天记录、视频信息等与团伙犯罪相关的证据;鉴定意见和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等。
围绕前述证据,侦查机关要有针对性地运用取证手段和技巧。首先,可以采用信息化手段。需要对犯罪嫌疑人留下数据信息进行分析。调取视频监控以核实关联证据,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常见关系人进行分析,发掘是否存在犯罪团伙及全部涉案人员。关联犯罪嫌疑人的通信信息、出行信息、上下班信息及暂住地信息,以掌握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活动轨迹及生活习性。其次,适时并案侦查固定证据。“职业骗薪”系有预谋犯罪且通常是团伙作案,需要侦查机关拉大时空跨度,在充分收集个案证据材料的基础上,严密审查判断是否并案处理。最后,加强对讯问笔录的分析。“职业骗薪”犯罪内部的组织性使得犯罪分子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需要重视对讯问笔录的关联分析,结合同案嫌疑人供述,充分调查犯罪嫌疑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
石玮:在侦查机关取证的基础上,检察环节需要围绕“职业骗薪”案犯罪的组织性和套路性来查明基本事实。一方面查证“职业骗薪”犯罪的组织性,另一方面查证“职业骗薪”犯罪的套路性,进一步聚焦证明“非法占有目的”来构建证据体系,证明是否“没有能力做”“没打算做”“没有做”。
李振林:证明“非法占有目的”是取证的重点,需要从“无交易的基础事实”和“无交易对价”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展开。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因为只要行为人有作假或欺诈行为,就一律以诈骗罪认定。
涉仲裁程序治理
陈苹:为增加骗薪成功率,“职业骗薪”案中的行为人往往通过劳动仲裁、申请法院执行等程序和手段,达到非法获取被害企业财产的目的。对于这种隐藏于劳动仲裁、申请法院执行中的“恶意”,要如何防nGS1FJao3x4TBJsWjoA8EfeO8bEyvzD7bMIS9/Vlrl8=止此类案件的再发?检察机关有哪些依法履职的路径?
郭勇辉:劳动仲裁属于劳动纠纷诉讼的前置程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活动,检察机关对劳动仲裁直接进行监督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这不代表检察机关无计可施。检察机关在职责范围内有两种履职路径:一是对劳动仲裁的间接监督。对于进入民事诉讼活动的劳动仲裁案件,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再审检察建议等方式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进而实现对劳动仲裁的间接监督;仲裁裁决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检察建议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从而实现对劳动仲裁的间接监督。二是向企业制发检察建议。对“职业骗薪”案反映出的被害企业制度管理上的疏漏,以及虚假劳动仲裁频发等问题,可通过依法制发检察建议,帮助有关单位堵漏建制,以防止案件的再次发生。
李振林:仲裁裁决的效力源自法律的授权及国家司法权力的分割,实质上是准司法活动,对仲裁活动进行监督与对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具有相似性。我国《刑法》第399条规定了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第399条之一规定了枉法仲裁罪,两罪在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相似,所以就枉法仲裁罪,涉仲裁的犯罪活动也应当在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内。若着眼于“职业骗薪”案的预防,检察机关也可以有针对地推动同仲裁机构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一方面建立仲裁裁决书和调解书共享机制,检察机关通过大数据模型分析的方式获取虚假仲裁案件线索;另一方面建立取证协助机制,明确检察机关在调查虚假仲裁案件过程中行使调查核实权,查询、复制仲裁机构案卷材料等,仲裁机构予以协助。
何银松:对于虚假劳动仲裁案件,检察机关要有所作为。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五起依法惩治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典型刑事案例中的“周某云虚假诉讼案”,检察机关便是以制发检察建议的方式开展工作。推进“职业骗薪”案的综合治理,要重视职能部门间的协作,检察机关可以结合典型案件,推动与公安机关合作,对中小企业加强防范宣传。同时,加强与劳动监察部门合作,将案件中的行业共性问题移送相关部门,以便开展劳动监察,对招聘存在违法违规情况,要求企业整改,以防范风险。
(声明:本内容仅代表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投稿邮箱:zhanghongyuch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