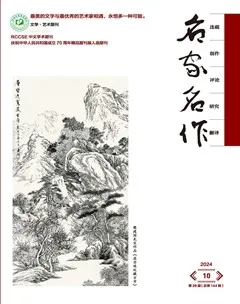论《驶下摩根山》中女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建构
[摘 要] 阿瑟·米勒是美国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评论界对其作品的研究成果繁华壮观,其中对于人物形象的研究多集中于男性角色,女性角色的研究资料相对鲜少。虽然米勒大部分作品都以男性作为主角,但他同样赋予笔下的女性角色同命运抗争的生命力。在延续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伊里加蕾的差异论女性主义理论,分析《驶下摩根山》中的女性从丧失主体性到重建主体性、从接纳自我到守望相助,并最终实现女性主体间性的建构过程。
[关 键 词] 阿瑟·米勒;女性主体性;主体间性;伊里加蕾
米勒在大部分剧作中都将男性作为主角,这导致评论界对米勒笔下的女性角色有了不谋而合的评论。这些评论可大致分为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这些女性角色相对于男性角色显得过于平淡和扁平,通常由圣母/妓女相对出现;二是认为米勒作为男性作家,带着男性凝视的视角,将女性角色边缘化为被看的他者。而米勒并不这样认为,他提到笔下的女性角色时这样说道:“评论家把我的女性角色看得比她们本身要更被动些,事实上她们并非如此。”[1]如同《驶下摩根山》中被重婚行为伤害的女性,她们并未一直沉溺在痛苦中,反而借此直视自身的人性虚弱之处,并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意义。总体来说,米勒剧作中的女性角色,并没有得到评论界与读者足够的重视。本文在研读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伊里加蕾的女性主义理论,通过分析《驶下摩根山》中女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建构过程,形成对米勒笔下女性角色新的思考与总结。
一、女性主体性的丧失
西方文明总体上是父权制的,这种概念外化于社会结构以及所有文化领域的组织构成,内化为权威的父权意识形态,即女性从属于男性。在传统的父权意识形态下,女性成为相对于男性的第二性,成为男性的客体,从而丧失了主体性。伊里加蕾将女性主体性丧失的根源归结为两点:一是“父权文化的创建使母亲于创世纪初和远古时代就已消失”[2];二是由于女性根据父权文化界定自己,因此相对于男性被定义为匮乏,从而导致女性由极具创造力的主体,变为父权秩序的维护者。父权文化切断了女性谱系,排除了女性之间的社会性。这样的父权意识还渗透在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这样的文学作品往往以男性主人公为中心,主要以男性的行为特征和情感方式来体现,同时将女性设置为边缘或从属角色,是男性事业或欲望的服从与补充。女性读者往往需要站在男性角度,从男性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甚至从这些角度来反对自己的女性经验。而米勒恰恰相反,他切实地描述美国社会中普通女性的生活,赋予笔下的女性角色充分的人性,并对这个时代中削弱女性的自主性且“将她们贬低为简单商品”[3]的方式进行批判。
米勒始终关注时代问题,《驶下摩根山》的时代背景正对应里根时代。在里根时代,对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信仰再次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膨胀为无边无际的梦想。在这个梦里,个人的繁荣、自负的妄想和过度的乐观主义模糊了人们对现实的认知。从各种意义上讲,该剧不仅是对里根时期政治文化的诊断和预言,更是对这种文化日后发展的诊断和预言。莱曼是里根时代的获利者,他既沉浸在里根时代的欲望中,又被其裹挟。于是因为莱曼的欲壑难填,作为莱曼客体的两位妻子成为牺牲品,成为莱曼游离在规则之外的注脚。
两位妻子在一开始皆丧失主体性。希奥是莱曼的原配妻子,她是牧师的女儿,她维护且遵守社会规则,兢兢业业地做一名好妻子、好母亲。然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希奥无法赢得一席之地,她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莱曼,从而不自主地沦落为客体,成为丈夫的附属。利娅是莱曼的重婚妻子,她与希奥完全相反,她青春且不遵守规则,她与莱曼一样是保险从业者,并且在社会丛林中战胜许多男性获得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从经济独立的角度来看,利娅非常有主体性;但从心理机制上来看,利娅无法把握自己的主体性。她与莱曼的结合,源于她的孤独,于是她下意识地放弃追究莱曼是否真的离婚。在堕胎事件上,利娅陷入了莱曼为她编织的美梦,放弃了堕胎,放弃了对自己身体和人生的掌控权,也失去了自己的主体地位。米勒将莱曼描绘成一位对婚姻制度漫不经心的旁观者,而希奥与利娅因经济与心理的主体性丧失,导致两人没有得到作为主体应有的尊重,反而被客体化为满足莱曼需求与野心的组成部分,最终成为重婚事件的受害者。
二、自我身份的认同
伊里加蕾认为,女性要获取主体性,首先应该回到女性与女性的关系中。在这段关系中互相沟通,重获女性自己的语言,因为“侵害她与自己以及其他女性的关系,就是重述男性的再现体系”[4]。而女性获取主体性的第一步,始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女性的状态永远是被动的、沉默的。男性不需要女性的回答,女性被潜移默化地固定到听从的位置。女性被“被排除在象征秩序之外,就是排除在语言之外,排除在律法之外,排除在同文化和文化秩序之间任何可能的关系之外”[5]。女性的身份随着成为男性的客体而模糊了。米勒剧作中的女性,都不同程度地通过自我认同来追求自我的主体性,《驶下摩根山》中的女性尤为如此。
希奥一出场被莱曼称赞为“圣女”,她穿着合脚的鞋子,镇定地安抚女儿,沉稳地守候在莱曼的病房外,甚至还有余力给予陌生女人(利娅)积极的情绪传递。第一幕第一场戏中的希奥被塑造成完美女性的形象,而重婚这个事件将希奥完美的女性形象冲击得满是裂纹,真实的希奥随着她痛苦地剥开表象展现出来。希奥认同自我身份的方式有两种:否认与回归。巴塞尔·范德考克(Bessel van der Kolk)认为当人受到精神创伤时,大脑会趋利避害地进行遗忘,“遗忘的一种方式就是否认当时发生的伤害”[6]。希奥的那段航海旅行的记忆曾十分美好,她一直记得,面对鲨鱼的威胁,莱曼拯救了自己。但这段记忆恰恰就是希奥回避的精神创伤,当希奥直面重婚事件的冲击时,她想起了当初真实的场景:莱曼并没有努力警示她,莱曼曾经想过杀死她。随着这个真实回忆的痛苦再现,日常生活中那些被希奥否定的瞬间霎时浮出水面,比如莱曼嫌她无趣,比如两人早已无话可说。此时希奥对婚姻的失望与对莱曼的愤怒到达顶点,她无意识地采取了“回归”这种防御机制。巴塞尔认为当人感到不知所措时,人会回到一种不成熟的应对形式。希奥面对来自莱曼的伤害,她脱下裙子露出大腿,推翻自己的坚守和信仰,彻底撕破完美女人的外衣,表现出跟一开场完全对立的样子。在当下的羞辱与痛苦的往事回忆的相互交叠下,希奥正视了自己。在这段婚姻中她与莱曼一样煎熬,她看不上莱曼的粗鄙下流,真正让她无法离开的不是情感本身,而是莱曼给予的优渥生活。当认清事实后,希奥打破“金枷锁”,主动离开了莱曼,以优雅的姿态重获自己的主体性。
利娅一上场穿着浣熊皮大衣和高跟鞋,与囿于家庭的希奥形成鲜明对比。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认为:“衣服是身体的身体,从它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性格。”[7]在利娅的人物塑造上,衣服 “揭示了人的内在和外在的和谐”[7],向读者展示出一位在物质上可以实现自己主体性的女性。利娅比莱曼小24岁,她事业有成、老于世故,在与莱曼的这段关系中,她更有可能成为掌权者。然而讽刺的是,在这段关系中她一步步地迷失了自己。她先是没有堕胎生下儿子,又因孤独而故意忽略莱曼可能没有离婚的事实,她将自己从前的工作能力用在了接受谎言、处理谎言上。在直面重婚问题之前,利娅已然失去自我,变成莱曼的客体。与希奥不同,面对重婚的冲击,利娅没有晕倒,她迅速起诉,让莱曼签署财产与儿子的归属文件,游刃有余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找回自我。利娅通过自己职业能力的展示,以及对自己有能力过上美好生活的信心,将她积极的生命状态和强烈的自尊心淋漓展现,至此她重新掌握自己的主体性。
三、女性话语体系的建立
传统的父权社会排除女性之间的社会性,女性之间无法进行真正的沟通,这导致女性之间的关系呈现瘫痪状态。所以为了“女性之间进行亲密无间的对话,彼此有爱”[8],势必要建立女性话语体系。女性的主体性也是通过她们的话语构成,所以要让建构独立的女性身份与话语体系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支撑女性掌握真正的自我,在社会中由他者变成主体,作为主体与另一个女性主体沟通,结成互助的纽带关系。特里·欧登认为米勒“有能力创造坚强的女性人物”[9],在《驶下摩根山》中,米勒通过四位女性人物展示了女性之间的互助关系,以及女性作为独立个体在社会中所呈现的力量。
首先是希奥与利娅。这本是一对互相竞争的“妻子”关系,最后峰回路转成为一对互相鼓励的女性关系。在这对关系中,希奥首先伸出援手,一开场在等待病房消息时,她安抚了焦躁的利娅。紧接着重婚事件暴露,希奥晕倒,利娅又急切地救助希奥。尽管两位女性实际上是竞争对手,但她们谈话中多次出现“我们”,这个词表明了她们之间因被伤害带来的联系。当她们彼此冷静后,意识到自己都是重婚的受害者,不应该为莱曼的错误买单时,她们继而彼此鼓励。关于如何安慰孩子的共同话题,迅速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她们开始认同对方,并为对方所受到的伤害而愤怒,利娅认为莱曼配不上希奥,甚至为希奥的离开提供帮助,两人从最初的竞争对手变成了最后的同盟。利娅与希奥之间有了社会性的联结,自此两位“妻子”结成了互惠的主体间性女性关系。
希奥与贝茜这对母女更是如此。希奥在一开场理智地安慰女儿,带领贝茜用积极的态度面对困难,为贝茜提供了一个正面的女性角色模型,贝茜被成功安抚,凸显了母女间密切且互惠的联结。面对被伤害的母亲,贝茜也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在整部剧中,贝茜都坚定不移地鼓励、支持、维护希奥。从童年的非洲旅行开始,面对莱曼对希奥的恶意调侃,贝茜坚决地让莱曼道歉;到当下重婚事件暴露,希奥情绪崩溃,贝茜严厉指责莱曼;再到剧终,对于莱曼的挽留,贝茜果断且强硬地劝希奥离开,无不展示了母女间流动的爱。伊里加蕾在《你、我、我们》一书中曾提到,女儿应该帮助母亲,让母亲重获主体,她认为“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母亲,也可以相互教育”[10]。在重婚事件暴露后,贝茜表现出比希奥更强烈的愤怒,这种愤怒既是维护母亲,也是为自己发声。贝茜意识到了父亲作为男性与她们作为女性之间的不同,女性的作用是“为社会秩序和欲望秩序奠定基础”[8],父亲无视的道德规则与社会契约,却是以母亲为代表的女性的行为规范准则。这个认知让她前所未有地意识到女性联结的重要性,也夯实了母女二人最终离开莱曼的决定,自此主体间性母女关系确立。
《驶下摩根山》的舞台场景设置为医院,医院环境与米勒惯用的家庭环境相对,医院作为公共环境排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让读者以更客观的视角看待人物。同时,医院环境也带来一丝治愈里根时代社会问题的希望。女护士洛根在剧中戏份不多,但她与周围人物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洛根用她的宽容与爱将剧中所有人紧密联结在一起。洛根的家庭虽不富裕,但家庭氛围和谐美好,且对生活的要求低于欲望,与里根时代的氛围格格不入。她善于倾听,且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时刻给予别人帮助。洛根第一次出现,是在照顾莱曼;并在剧终所有人都离开莱曼时,还陪着莱曼,并给了莱曼一个安慰的吻。莱曼有过名望、金钱、爱情等一切美好的战利品,但在最后,莱曼失去了这一切,而洛根的吻,给了绝望的莱曼活下去的力量。洛根对莱曼富有同情心的回应,给了莱曼重回正途的指引;她心无旁骛且乐于平淡的生活态度,成为里根时代社会问题的解药。而洛根的独立与仁爱,正是米勒对女性主体性以及女性与他人的主体间性关系的肯定。
四、结束语
米勒笔下的女性角色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都没放弃过对主体性的追寻与建构,他的作品超越了时代对性别认知的局限性。尤其是《驶下摩根山》,两位丧失主体性的女性,通过对男性话语的反思与痛苦的自我审视,从而实现自我认同,最后建立起互助的女性主体间性关系,尤其是良好的主体间性母女关系。女性应该置身于女性话语体系之中,保留自己的身份,书写自己的历史,这样就能“虽然相隔甚远却可以彼此拥抱”[11]。女性主体性与女性之间的主体间性的实现,也是促进性别和谐共生,实现多元文化发展的推力。
参考文献:
[1]罗丹,马修C.与阿瑟·米勒的对话[M]. 杰克逊: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87:370.
[2]邱小轻.主体间性与母女关系的社会伦理建构[J].求索,2010(8):116-118.
[3]阿妮塔·萨克塞纳. 性别动力与社会压力:探索阿瑟·米勒的《骑马下摩根山》中的女性形象[J].综合研究,2024(5):12.
[4]露丝·伊里加蕾. 性别差异的伦理学[M]. 卡罗琳·伯克,吉莉安 · C.吉尔,译.伦敦: 阿斯隆出版社,1993:85.
[5]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M].刘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
[6]巴塞尔·范德考克.不可避免的休克,神经递质,和创伤成瘾: 走向创伤后应激心理学[ J ].生物精神病学,1985:314-315.
[7]丹尼尔·罗什. 服饰的文化: 古代政体中的服饰与时尚[M]. 让·比雷尔,译.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6,7.
[8]露丝·伊里加蕾.与母亲的身体接触[M]//大卫·梅西,译.伊里加蕾读本.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1:44,35.
[9]奥顿,特里. 阿瑟·米勒戏剧中的纯真诱惑[M]. 哥伦比亚: 密苏里大学出版社,2002:16.
[10]露丝·伊里加蕾.你、我、我们:走向差异文化[M]. 艾莉森·马丁,译.纽约: 劳特利奇出版社,1993:50.
[11]露丝·伊里加蕾.这不是一个性别[M]. 凯瑟琳·波特 ,卡罗琳·伯克伊萨卡,译. 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5:215.
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
作者简介:王思雅(1992—),女,汉族,黑龙江抚远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戏剧影视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