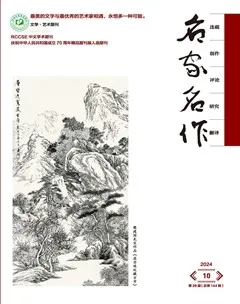当欧醉翁遇上范覆霜
[摘 要] 范仲淹和欧阳修均是北宋的大文豪,分别以《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流传于世,二者的作品虽均为借景抒情性散文,但在诸多方面却不尽相同。采用对比分析法,剖析作品在呈现方式上的对立统一,并在此基础上把握作者的共同价值追求。
[关 键 词] 抒情性散文;对立统一;共同追求
欧阳修喜爱喝酒,自号“醉翁”;范仲淹善抚琴,时称“覆霜”,二人均为北宋时期的大文豪。尽管政治仕途失意,但在文学上都颇有造诣。范仲淹曾受滕子京之托,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岳阳楼记》。历代文人读之有悟,也受之鼓舞。时隔一年,在滁州的琅琊山,自称“醉翁”的欧阳修也写下世代称赞的《醉翁亭记》。同为力主变法的主心骨,同是胸怀志向、心系苍生却又仕途坎坷的文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特质,也有着个人独特的魅力。基于二者的代表作,探求作品的不同艺术呈现方式,把握他们在价值上的共同追求。
一、表现手法上的“虚”与“实”
据史料记载,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只是受友人之托,凭一幅《洞庭晚秋图》和一些资料写下千古流传的《岳阳楼记》。欧阳修则不同,他到过琅琊山,在那边与友人喝过酒、赏过景,并亲手种下一棵梅树,是在赏景宴乐时写下了《醉翁亭记》。因此,就景色描写而言前者属于想象,后者属于纪实。
尽管范仲淹没有去过岳阳楼,那里的景色对他来说仅是通过图画和文字想象出来的“虚景”,但从他笔尖流露出来的情感却让读者感到情真意切。撰写该文时,范仲淹正处庆历新政失败、仕途不顺、身体抱恙的境遇下,然而他不抱怨、不消沉,反而发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感慨。可见,仕途不是他最关心的,得失也不是他最在乎的,唯有百姓才是他最牵挂的。再者,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不到两年就“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取得一番丰功伟绩。作为好友,他深知滕子京好大喜功,担心好友惹祸上身,于是他借机委婉规劝好友要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怀,才能经得起世间沉浮,因此他对友人的关心是推心置腹的。文末,他借“古仁人”表达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让读者由衷地感受到他不追求功名利禄、淡泊明志的人生志向也是真心实意的。
欧阳修与范仲淹的经历颇为相似,《醉翁亭记》也是他被贬时所著。但和范仲淹追求“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不同,欧阳修在生活上主张“及时行乐”。他不仅将这种人生理念付诸实践,也在文中大方地将其表现出来。阅读他的《醉翁亭记》,其一是景真“美”:沿途“林壑尤美”“水声潺潺”,山上“天高云淡”“野花幽香”“佳木繁阴”,这样的山水美景令人陶醉,也令人向往;其二是人真“乐”:这种乐是游山玩水的怡然自得,是众人相聚的宴酣之乐,更是百姓安居乐业的与民同乐。《醉翁亭记》中的景色美丽、众人皆乐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欧阳修对景色的描绘及流露的情感只停留在眼前的一切。仔细品读,会发现这种真景真境中也蕴藏着作者的想象与展望。虽然欧阳修来此游玩只是“暂时”的,所见景色也只在一个时间段,但他却写道:“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可见,在欣赏眼前美景时,他联想到四季的美景,又由眼前的游玩之乐进一步畅想不同时间段游玩有不一样的快乐,因而感叹道:“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接着后一小节,由眼前的0bRLpOGvfk7L+GZbTfqnY8Bf9KplOPbFjCIn8CkPheE=滁人出游之乐、众人宴酣之乐,发出了“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的感慨,这里的感慨是对眼前热闹祥和景象的欣喜,更包含了对未来的美好愿望,他希望滁州的百姓能安居乐业,一直拥有如同今日一样的快乐。
总之,同是被贬时写下的抒情性散文,范仲淹在“虚”景中表达了真情,而欧阳修则在“真”游中展开了想象,表达了对未来的期许与展望。
二、创作风格上的“狂”与“雅”
据史料记载,范仲淹文武双全,能写诗弹琴,也能带兵打仗,不仅是个政治家、文学家,更是一个军事家。他性格豪放,所著作品也大多属于豪放派。《岳阳楼记》便是他气势恢宏的代表作之一。该文章用词大气磅礴。在开头写洞庭湖全景时,他这样写道: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
这里的“衔”和“吞”二字将静止的洞庭湖人格化,“衔”字在空间上写出了山在湖中的浩大气象,“吞”字则写出了湖蓄江水的壮观景象。精确的动词运用展现了洞庭湖的宏伟气势。文章描写雨中洞庭湖和晴天的景色时笔法凝练大气。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两种景色的描写都采用骈文的句式,运用宏观大视角,短短的数十字中包含了众多景物,每个景物点到即止,却又特色凸出,组合起来气势雄浑,震撼人心。
欧阳修文章的风格偏于清新雅致。在《醉翁亭记》里用词与写作视角的选择与《岳阳楼记》大有不同,如在写泉水时,欧阳修这样写道:
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
欧阳修用动词“泻”展现了泉水涓涓细流、轻巧缓慢的状态,与前文的“潺潺”相呼应,让人仿佛能听到泉水动听的声音,品味到泉水的甘甜。全文描写大多采用微观视角,无论是景物的形态,还是游人的动作,抑或是宴会时的场景,欧阳修都精于细节描写。如在写滁人出游的场面时他落笔于细微处,用“歌”字写出了游人出游时快乐的心情,用“呼”和“应”描绘了游玩时欢快热闹的场面。
总之,从行文风格来看,《岳阳楼记》给人大气磅礴之感,《醉翁亭记》让人感到细腻雅致,不同的创作风格也是二者不同性格的体现。然“狂”与“雅”在两者身上并不是绝对的标签,豪放不羁的范仲淹也曾写过清新婉约的作品,如世代流传的《苏幕遮》,而清新婉约的欧阳修也曾写过荡气回旋的《浪淘沙·把酒祝东风》。这与诗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境遇有很大的关系。
三、思想观念上的“忧”与“乐”
两篇文章都涉及“忧”与“乐”的议题,只是在表现这两种思想时,二者采用了不同的形式。
欧阳修“乐”得耳目昭彰,“忧”得委婉含蓄。欧阳修的“乐”是所见景色皆如画的欢乐。尽管被贬,但丝毫不影响他用发现美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事物。
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
一幅清新脱俗的山水画展现在读者的脑海里,山水亭台、花草树木在欧阳修的笔下一应俱全,在用词上更是不惜运用“尤”“美”“佳”这样直接表示赞美的字眼,可见美景让欧阳修心生喜悦,所以他才会用尽丽句清词,把这如诗一般的意境描绘在文字里。
欧阳修的“乐”还是宴酣之时的尽兴。
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他从宴席丰盛、野趣十足;众宾欢聚、觥筹交错;太守颓然、醉坐其间三方面展现了一幅热闹的宴饮图,相聚的快乐跃然纸上。
这种“乐”也能看到百姓“安居乐业”的欣喜。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
作者运用“歌”“休”“呼”“应”这几个动词写了出游时快乐热闹的心情,又用“佝偻提携”“往来不绝”告诉读者出游的人不仅多,而且连老人、小孩也在出游的行列,足以表明滁人生活美满、祥和安定,俨然一幅和谐快乐的游乐图。
赏景之喜、宴饮之欢、祥和之美,这种层层递进的快乐,让欧阳修不仅把它们描绘成三幅美丽的画卷,更是用“乐”字来直抒胸臆。短短402字的文章中共用了10个“乐”字,可见当时的他喜不自胜。
仕途失意的他难道心中没有一丝忧愁吗?不,他有。只不过这里并不是以“乐”景衬他的“忧”情,他的“乐”是真真切切的,但“忧”也是由心而生的。文中作者说:“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欧阳修写这篇文章时仅39岁,按理来说,这个年纪正当壮年,怎会苍颜白发?究其原因,为“太守醉也”。酒使人生愁,也易使人生幻。因此,酒兴正起时,太守难免想起自己被贬至此的经历,瞬间产生“苍颜华发”之感。但这种忧愁又是短暂的,很快又被当下的快乐吹散了。欧阳修的与民同乐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为民而忧之情。在滁州就任时他还写过另一篇较出名的《乐丰亭记》,文中他批判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痛苦,歌颂了太平盛世让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因此,欧阳修并不是无忧,只是这种“忧”以隐秘的方式藏在了他的“乐”之下。
反观《岳阳楼记》会让读者感到显而易见的“忧”。了解其历史背景,可知范仲淹在写这篇文章时在为朋友滕子京担忧。在“记”中他又为君王担忧,为百姓担忧。多忧多虑的范仲淹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其实他也是有快乐的。只是他将这种快乐表现得比较含蓄。首先《岳阳楼记》的第一自然段中,作者用“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来叙述滕子京取得的成就。“越”字表现了时间之短,反衬滕子京办事效率高。“通”“和”则道出了友人的治理有方。“百”和“具”更是写出了友人的功绩卓著。从选词和用句上不难看出,作者其实也在为他取得的成就而高兴。最后,文末作者也为自己何时而乐做出了回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原来作者是把百姓的喜忧放在自己的喜忧之上。因此,范仲淹为人民而“忧”,也因人民而“乐”。只是他“忧”得显而易见,“乐”得不动声色。
二者在文章中都涉及了“忧”与“乐”的议题,但其表现形式却有所不同,这与他们的生活背景有关:欧阳修的父亲早先也是当官的,尽管他的父亲早逝,但是他聪慧过人,他的叔叔非常看好他,因此他基本上没有吃过什么苦。这就养成了他看待事物比较积极乐观的性格。他更是遇到了一个非常体恤他的上司,非常支持他游山玩水,这也对他后来即使被贬也依旧乐衷于游山玩水有很大关系。可见欧阳修并不是在被贬后才有这等爱好。但是范仲淹相对没有那么幸运,同样自幼丧父,却吃了较多的苦,经过十年寒窗苦读才有了一番作为,因此他特别体恤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辛,无论在文章上或者行动上更加着眼于百姓的困苦,他曾建立老人会所来赡养老人。如果说范仲淹会为贫民建疗养所,欧阳修则更倾向于为百姓构建娱乐城。但是《岳阳楼记》里提倡的“先忧后乐”与《醉翁亭记》里的“与民同乐”,都是心系百姓的体现。对于百姓来说,物质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快乐都是同等重要的。
由此可知,两位作者都有“忧”和“乐”,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百姓。百姓的“忧”和“乐”牵动着他们个人的“喜怒哀乐”。
四、人生态度上的“醉”与“醒”
两篇作品皆出现了“酒”这个意象,但却有不同。一方面,饮酒的对象不同。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描绘的是迁客骚人登楼,“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的状态;而《醉翁亭记》写的是欧阳修“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的情形。另一方面,写酒的目的不同。《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写“酒”主要是想通过“迁客骚人”在欣赏洞庭湖美景时,受美景所感染而表现出“喜洋洋”的状态,反衬出自己“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然,文中范仲淹的状态是清醒的,他清醒地探求“古仁人”的思想,清醒地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而欧阳修在文中呈现的主要是“醉”态,这里的“醉”是欣赏美景而“陶醉”、欢聚饮酒而“酣醉”、与民同乐而“沉醉”。
尽管在写“酒”时,两位作者呈现出“一醉一醒”的不同状态,但他们所表达的人生态度却是一致的。面对美景众人皆醉时,范仲淹仍清醒地追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欧阳修尽管把酒言欢,沉醉在美景美食、游山玩水中,但这并不是他被贬后意志消沉、借酒消愁的表现,而是醉时与民同乐、醒时亦能为民解忧的情怀。因此,无论是“醒”或“醉”,他们都指向了“一心为民”的人生追求。
尽管《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在呈现方式上看似存在许多对立面,但其实在价值追求上是不谋而合的,作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为百姓谋福祉。
参考文献:
[1]苏许旭,齐雪艳. 从《醉翁亭记》窥看欧阳修的人生困境与破局之路[J]. 名作欣赏, 2024 (17): 84-86.
[2]曲倩玉. “以物观我,以景观人”:《岳阳楼记》之景物隐喻[J]. 今古文创,2024(30):26-29.
[3]王子玥. 传统经典之美中的“言象意”:《岳阳楼记》小议[J]. 中国故事, 2024 (5): 37-38.
作者单位: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紫帽中心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