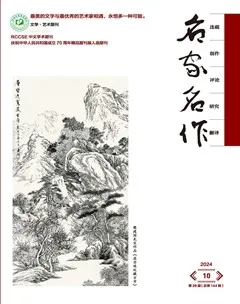从实践的角度看待自然美
[摘 要] 在当代美学架构中,自然美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回溯至德国古典美学领域,康德与黑格尔等巨匠虽将自然视为非直接“审美典范”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其后现代环境美学思潮的兴起。以卡尔松为领军人物,现代环境美学界广泛接纳了“自然全面蕴含美感”的普遍观念。美学演进的历程中,众多美学大家围绕自然美的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不仅丰富了美学的理论宝库,也促进了人们对自然审美价值的重新认识与评估。然而,鉴于自然美所展现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目前尚未达成一个普遍认可且逻辑严谨的统一阐释。这一现状自然而然地促使自然美成为美学探索的关键领域之一,特别是在其基础上围绕生命本质及其表现的美学理论得到了显著的深化与拓展,进而孕育出一种根植于自然美的实践美学体系,该体系强调将自然之美融入美学实践中。
[关 键 词] 美学;自然美 ;实践美学
在我们的自然审美感知历程中,自然之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它深刻融入并丰富了我们的审美体验。这种体验不仅凸显了自然美的独特魅力,也进一步印证了其在美学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如果我们用哲学的方法去思考,那么我们就必须先了解自然美,然后再用经验来理解它。然而,我们不能就此止步,必须以“先知”与“自然美”的体验为基础,在理论上给“自然美”下一个严谨的定义。虽然自然美在美学界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学术界对自然美的讨论却从未停止过,并涌现出许多有关自然美的理论与著作。在审视国内外学术界的视角时,关于自然美的探讨可归纳出以下若干主流观点与见解。
第一种是主观主义者。从主观角度来看,自然美体现在人的内心,也就是人的主观心态。其中,朱光潜和高尔泰等是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朱光潜认为自然美就是人类的一种理念或一种态度。他以为,大自然本身就存在着美,如果没有人来欣赏,美仍在那儿。大自然本来是没有美的,但是当我们内心把它看作美的时候,它就成了一种形象、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粗犷的自然。古语云:“各花入各眼。”此言恰为前述之精妙注解。高尔泰等学者虽对朱光潜的某些观点持有批评立场,但在自然美的认知上,他们却与朱光潜不谋而合,共同否认了自然美在客观世界中的缺席,仅将其视为一种观念上的构建。此外,在西方美学界亦盛行着一种以主观情感体验为核心的自然美理论,即“移情论”,它强调个体情感向自然对象的投射与融合。
第二种是客观主义者。其核心观点聚焦于自然美的本质,认为其根植于自然对象的客观特质中,诸如色彩的搭配、光线的运用、比例与对称等物理特性的和谐统一,而非源自观者的主观感受或情感投射。在中国,蔡仪先生作为该理论的杰出代表,坚持认为自然之美根植于自然实体的本质中,这一美的概念及其内涵超越了人类主观意识的范畴,是自然界万物所固有的、客观存在的属性,而非人类意识所赋予或构建。蔡仪进一步阐释,自然美体现为个别自然事物鲜明地彰显出其所属类别的一般特征,如某棵树以其独特形态展现树木种类的共性;某座山峰则以其独特风貌体现山峰类别的普遍性,这些个别实例被视作自然之美的典范。客观主义在自然美研究领域所做出的贡献是显著且值得肯定的,它着重指出自然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独立性,即自然美并非依赖于人类主观意识而产生,而是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一种美学特质。然而,该观点在过分强调自然美的先验性与独立性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类主体在审美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这无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三种是主客观和谐共生的体现。此观点深刻指出探讨自然美必须融合天地、物我以及客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当我们感知某一自然物之美时,实则是其客观特质与我们的主观感受相契合的结果。换言之,自然美的诞生,其基础在于自然物本身的外在特性,而这些特性需与我们的主观审美意识相融合,形成主客观间的和谐统一,方显其美。尽管此派别强调自然美既依托于自然实体,又需人的感知介入,但总体上更侧重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自然本身并不自带美感,而是经由人的主观意识赋予其美的属性。
第四种是社会实践的体现。该理论植根于马克思的唯物实践观,将自然美视为“自然人化”过程的产物。它认为,在人类文明曙光初现之前,自然并无美丑之分,自然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从对立、陌生的状态转变为与人类生活紧密相连、有益的存在,使之成为展现人类本质力量的舞台。然而,当实践美学试图解析未经人类雕琢的自然之美时,其理论架构在某些方面显得较为机械与拘谨。李泽厚先生巧妙地将“自然的人化”这一概念细化为狭义与广义两个维度进行剖析,狭义指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而广义则涵盖了社会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性变革。他进一步阐述道,那些未经人类直接干预与改造而展现出的自然之美,实则更多的是广义层面上“自然与人和谐共生”这一进程的必然产物,即通过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与发展,自然被赋予社会意义和价值,从而使其美不再局限于物理属性或个体主观意识,而是深深扎根于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实践探索与活动历程中,其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息息相关。
上述各类理论均蕴含其独特的合理内核与局限性。相较之下,实践美学中的“自然人化”理念展现了更广阔的阐释维度与潜在的发展前景,它在国内自然美学领域的历史进程中,曾占据最显著的地位。从远古时期岩壁上的原始岩画起,经由人类对工具美学价值的探索,直至日常生活中工艺美学表达的兴起,这一系列文化演进的脉络始终紧密缠绕于自然之网中。当书法与绘画跃升为主导的艺术表现形式时,人们对美的深切追求愈发倾向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框架内寻觅灵感与答案。
一、自然美是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下,自然美的探讨被深刻地嵌入人类实践活动这一宏大叙事中,被视为此类活动的直接产物与显著表征,其根源深深扎根于人类改造并赋予其意义的自然——即人化自然的肥沃土壤里。这一视角不仅拓宽了自然美研究的边界,还强调了其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动态生成性,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实践关系。这一视角为自然美的起源与本质提供了科学合理的阐释。因此,我们有必要且必须立足于人类实践活动的透镜,以人与自然的相互关联为基石,深入剖析自然美的真谛。
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详尽剖析了“自然的人化”理念,明确指出:人类作为实在且具体的存在立足于坚实的大地之上,并汲取自然界的能量,通过一种外化机制,将自身固有的现实性与对象性本质潜能映射至外在对象时,此过程远非单纯的主观行动所能概括,而是深刻体现了对象性本质潜能的主体性释放。这一释放过程本质上要求这些潜能的活动须具备明确的对象性指向,从而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构建出独特的实践关系。马克思强调,在自然人化的进程中,人作为主体,是感性的物质存在,其对象化活动则是感性物质活动的客观社会性体现。“自然的人化”即是将人类自觉、有意识的创造力能动地“物化”“现实化”于客观世界,这一进程促使自然界以感性化的形态,烙印下人类本质力量的痕迹,进而转化成一个映射人类本真的对象性世界,作为人类自我反思与认知的镜像存在。
“人的本质对象化”或“自然的人化”其本质在于深刻融合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等多个维度的和谐统一。然而,这种统一的基础何在?美的根源又在何处?答案指向了人类的社会实践,它是自然美产生的根源,也是解开自然美本质之谜的关键。实践活动作为基石,构筑了人与现实环境、主体与客体之间既复杂又充满辩证意味的对象性关联。
二、实践在自然美领域中的作用功不可没
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持续拓展与深化,自然物逐渐融入人类文明的轨迹,实现了从自在之物向人化自然的转变,这一过程催生了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美现象,使得在自然领域进行精神层面的审美活动成为可能。从理论层面剖析,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成正比,进而促进了自然人化程度的加深,自然美的疆域也随之拓展。
一方面是那些经过人类改造而焕发新貌的自然现象之美。此类自然物无论其本质还是外在形态,均已超越了原始的自然状态,成为人类创造力与智慧的结晶。它们直接映射出人类的创造潜能,让人在审视中得以自我观照,其美学价值不言而喻。正如歌德所言:“自然塑造人类,而人类则重塑自然,从浩瀚宇宙中圈定一隅,使之成为自身意志与形象的展现。”这些自然物作为人类征服自然、彰显本质力量的印记,散发着独特的美学魅力,使人在直观体验中收获审美的愉悦。
另一方面则是那些虽保持原貌但已被人类认知的自然现象之美。此类自然物外观依旧,但其社会内涵则需通过更间接、隐晦的方式去领悟。在自然美的广阔天地中,这类美以多样化的形式占据重要地位,它们主要通过自身独特的自然形态吸引人心,仿佛其美仅蕴含于物质构成、性能特性、自然规律及形态之中,与人无涉。然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与社会的演进,某些自然物逐渐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自然属性与人的关联日益紧密。此外,人类实践的深化促进了认知能力的提升与视野的拓宽,进而增强了人的本质力量,使得众多未经人工雕琢的自然事物得以融入人类生活圈,成为亲切宜人的生活环境。这些自然物因被赋予人化的意义,从而获得了审美上的价值。
三、从实践角度出发解释自然美的缺陷
“自然的人化”这一概念在解释纯粹自然美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李泽厚对此有独到见解。他将“自然的人化”概念视为一项具体而物质化的实践活动,核心聚焦于劳动生产领域,而非仅仅局限于意识、精神或艺术的抽象层面。在深入剖析纯粹自然美的本质时,李泽厚巧妙地将“自然的人化”概念细化为狭义与广义两个维度。在他看来,狭义上的“自然的人化”,即人类通过劳动技术手段对自然界进行的改造,构成了广义范畴内“自然的人化”的坚实基础,同时也是推动人与自然关系深刻变革的根本动力源泉。然而,广义的“自然的人化”并非直接源自狭义层面,而是在其基础上于特定历史阶段逐渐显现。李泽厚将纯粹自然美的根源归结于广义“自然的人化”过程之产物。然而,此概念的具体含义仍显含混不明。细察李泽厚的论述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其理论在狭义与广义“自然的人化”间构建了一种逻辑自洽的关系框架,但广义范畴的精确界定却引发了学界的诸多疑问:它是否仅仅指代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界所施加的广泛且浅表的影响,致使自然物表面留下人类活动的痕迹?对此,李泽厚坚决否定了这种表面化的解读,他着重指出,“自然的人化”概念实则触及了人类实践活动与自然历史进程之间那些更深刻且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在未受改造的自然中或许难以察觉。
据此而言,李泽厚先生提出的“自然的人化”理论,诚然触及了自然美感生成的根本动因,但若将此理论过度泛化,视其为自然美之普遍本质,则恐显其涵盖面过广,难以精准而全面地阐释自然界中纷繁多样的美学现象。在《美学四讲》的语境下,广义“自然的人化”概念未能获得详尽且明确的界定,它更多是作为李泽厚为阐述未经雕琢之自然美所构想的一个框架而出现。尽管此构想表面构筑得颇为周全,却有可能在不经意间模糊了自然美本质的鲜明界限,进而潜在地扭曲了关于自然美的真正源头及其固有属性的认知。诚然,人类的审美探索,尤其是对自然美的向往,深深植根于实践活动之中,然而,将劳动直接等同于自然美或美的根本属性,则显得过于简化且偏离了问题的核心,未能全面把握美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因此,实践美学若要深入探究自然美问题,必须不断完善自身理论框架,兼收并蓄,以更全面地揭示自然美的本质。具体而言,应进一步细化“自然的人化”过程,区分不同历史阶段、文化背景下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美的不同塑造方式及其结果,从而揭示出自然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具体性与文化多样性。同时,还需引入生态学视角,考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如何影响自然美的感知与评价,这不仅能够丰富自然美理论的内涵,也能促进人类更加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亦不可或缺,如结合环境美学、生态哲学等理论,从多维度探讨自然美的本质与特征,以期构建一个既深刻又全面的自然美理论体系。总之,实践美学在探讨自然美时,需保持开放与审慎的态度,不断反思与修正,以期更加精准地把握自然美的真谛。
四、结束语
实践美学自然美论的局限非致命缺陷,但作为一门学科,需保持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不断吸纳新内容以弥补不足。相关人员应以开放、包容及契合自身特性为原则,积极汲取他派自然美论的合理成分,突破局限,方能使实践美学更科学,实现长远发展。然而,自然美这一难题非单篇论文所能解,需持续努力探索,在既有理论基础上丰富发展,以真正推动美学进步。
参考文献:
[1]耿婷婷. 美育视角下初中生物自然美元素的挖掘及教学实践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2022.
[2]蔡一娉.在劳动实践中感受与表现自然美[J].福建教育,2021(38):16-18.
[3]胡友峰.自然美理论重建的三条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1(6):140-149,178.
[4]尤西林.生命美学与自然美: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深度关系[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3(6):65-66,60,124.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简介:张雨蝶(2000—),女,汉族,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