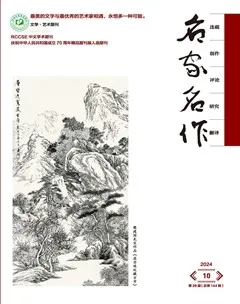德国汉学期刊对余华的译介与阐释
[摘 要] 德国汉学期刊既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亦是将中国文学及文化传播到西方的主要阵地。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重要代表人物余华在德国汉学期刊中的译介情况。德国汉学期刊对余华的译介起步较早、周期较短、视角多样,且持续至今。余华受到了德国汉学家的广泛喜爱,不同学者的文评呈现出观点多元、审美异趣的特点。
[关 键 词] 德国汉学期刊;余华;译介
余华是中国在海外最具声名的当代作家之一,其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及《第七天》的德译本分别于1998年、2000年、2009年、2012年及2017年由Klett-Cotta 、S. Fischer等德国著名出版社首次出版发行,译者皆为德国翻译家、汉学家高立希(Ulrich Kautz),其中部分为再版作品,例如《兄弟》德文版销量达几万册,再版四次,一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德语图书市场上能引起这样的反响是较为鲜见的。《法兰克福汇报》《德国世界报》《德国时代周报》《焦点周刊》《南德意志报》《新苏黎世报》等德语主流报刊多次刊登由作家、记者等撰写的对余华著作的推介、文评。《袖珍汉学》(minima sinica)、《取向》(Orientierungen: Zeitschrift zur Kultur Asiens)、《东亚文学杂志》(Hefte für ostasiatische Literatur)等德国权威汉学期刊亦常登载对余华作品的翻译与批评。
余华在德语区的译介载体按照面向的读者群体可大致划分为两类:一是面向普通读者的作品单行本及主流报刊媒体的文艺副刊;二是面向专业读者的汉学期刊。前者的译介影响因素颇为复杂,与市场关系较为紧密,作品的声名(作者、奖项、影视化等)、诗学观、赞助人等均可成为操控因素;后者的译介则由专业学者的审美趣味主导。从长期影响来看,专业学者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引领作用不容忽视。德国汉学期刊是观察德国汉学发展的重要窗口,本文研究其对余华的译介,即是考察当代德国汉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重要作家的认识和诠释,对预测未来中国文学在德语区的译介趋势有一定助益,或可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策略支持。
一、及时而持续的译介
德国学者注意到余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故将其引入德语文化圈,试图对本土文化形成“异”的刺激。
德国汉学期刊较早地开启了对余华的译介与研究。早在1989年,汉学杂志《袖珍汉学》刊出了由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顾彬(Wolfgang Kubin)及其夫人张穗子合作缩译的余华中篇小说《河边的错误》。该篇译文集中呈现了主角的解谜过程,而对话和心理描写则被大幅削减,这应是余华作品首次进入德语世界。杂志创刊伊始,立即将青眼投向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坛涌现出的一批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青年作家群体。除余华外,同期还推介了残雪、洪峰、莫言等中国先锋派作家的作品,体现了德国汉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85新潮”“向内转”的热切关注。
德国汉学期刊对余华的译介及时而迅速,《河边的错误》首次发表于1988年,第二年就传入德国,可以看出德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坛的关注,且对其变化非常敏锐。相较而言,德国图书市场的反应相对滞后。余华小说《活着》首次发表于1992年,而其德文版于1998年出版,晚了整整6年,其间发生了许多提升作品国际声誉的事件,对出版商的出版意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艺谋将该小说改编为同名电影并于1994年在戛纳电影节首映。该作品赢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Premio Grinzane Cavour)等多项国际性文学奖项,其法语、荷兰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等译本均已发行。即便如此,译者高立希作为余华走向德语世界的重要推动者,仍需为促成此事四处奔走,努力说服出版机构。
此外,德国汉学期刊对余华的译介还体现出稳定性、持续性的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一旦余华有重要作品发表,均能在德国汉学期刊上看见相关的译文或书评。《许三观卖血记》德译本于2000年出版,同年,汉学家沃尔夫·鲍斯(Wolf Baus)在《东亚文学杂志》上发表书评讨论余华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两部作品在主题、写作风格上的延续关系。《第七天》德译本于2017年出版,但早在两年前,高立希已在《东亚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中文原著读书报告。
二、专业且多元的内容
德国汉学期刊致力于追求学术的纯粹性,其核心使命在于密切关注中国文学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通过发表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来推动学科的进步。
相较于其他载体,德国汉学期刊对余华的译介内容更多样化,包括汉学家撰写的作品推介与批评、中短篇小说译文、传记译文、余华在欧活动报道等,满足了专业读者想要更深入细致地了解和研究这位中国当代作家的需求。《东亚文学杂志》于2010年刊发了余华短篇小说《鲜血梅花》完整的德语译文,主要译者为科隆大学东亚学系的汉学家吕福克(Volker )及其学生。吕福克在2009年夏季学期开设了一门文学翻译课并把翻译余华的这部短篇小说当作一次练习。该译文虽不是技巧圆熟的杰作,但对文学译介或翻译教学的研究来说是极具价值的案例。为了满足德国专业读者阅读或科研的需要,高立希于2001年在《东亚文学杂志》刊登了对余华《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古典爱情》及《在细雨中呼喊》的简介,同年又在《取向》刊发余华自传的完整德语译文。由此可见,余华研究在德国汉学界受到重视且已有一定的文献基础。
德国汉学期刊呈现出愈来愈多的中德互动交流的发展趋势。在第29期《东亚文学杂志》上,高立希发表了一篇通讯稿,详述了2000年余华到德奥两国参加作品巡回朗读会的整个活动细节。朗读会活动的高潮在施瓦布明兴站,高立希激动地描述道:“乡公所的大厅被异常兴奋的年轻或年老的读者挤得水泄不通。”[1]读者被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深深打动,向作者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例如,余华是如何成为一位作家的;他的写作动机、写作技巧;作品在中国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接受情况等。由此可以推断出,余华作品在德语区不仅受众人数较多,且拥有一定数量的忠实读者。该篇文章是在其他载体上很难见到的内容,对研究余华以及中德学界、文艺界的互动来说是颇具价值的文献。
三、复杂和多维的阐释
学者的审美倾向在德国汉学期刊译介的影响因素中居主导地位。根据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翻译与文评均可视为一种改写,而改写本身受诗学观的制约与影响,这种诗学观包括改写人所处时代的主流诗学观、所属的诗学群体的文学观念及自身基于个人教育经历所构建的文学理念[2]。由于撰稿人各自持有不同的诗学理念,德国汉学期刊对余华作品的诠释表现出非模式化、非表面化、非单一化的特征。如何看待余华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汉学家鲍斯和顾彬发表在德国汉学期刊上的相关文评分歧较为明显。
鲍斯给予《许三观卖血记》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部作品与之前已译成德语的《活着》之间在主旨和艺术风格上具有延续关系,在主题上同样关切小人物的命运与社会变迁的联系,在风格上亦存在许多共同点。鲍斯将余华的艺术特质概括为“幽默、精确与冷静的混合物”,两个故事皆由一种“简洁而温暖”的语调进行讲述。在余华的作品中没有心理描写,也未夹杂作者的议论,只有对人物语言和动作的记录,鲍斯将这种方式视作“与传统现实主义方法的断裂”。但两部作品在形式上的差异也不容忽视,《许三观卖血记》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极具创新性,整个故事由大量的短场景和直接对话组成,且没有讲述者。鲍斯对《许三观卖血记》中频繁使用的重复手法大加赞赏,认为其能让人联想到民间故事,且加强了喜剧效果。鲍斯还指出,作者和译者的“深度捆绑”具有明显优势:“就像电影明星拥有固定的配音演员,余华的德译风格也不宜变来变去。”他称高立希的译文真实再现了小人物的声音,赋予作品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3]。
但顾彬在《取向》上发文说,余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更具价值,《许三观卖血记》却走入了一种不合适的“史诗般的宽度”,叙述“遵循年代顺序”,“重复技巧的使用是没有必要的”。顾彬对叙述中“突兀的跳跃、碎片化的结构及非必要的四字成语的使用”感到不满。但他表示非常喜欢阅读这本书,原因有三:一是“译者卓越的德语水平”;二是“逐页递增的人道主义”;三是“主人公能够从狭隘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不断地超越与成长”[4]。
细致分析上述文评后可以得出:两位批评家对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时,并未遵循统一的批评模式,而是根据各自的理论框架和批评视角,采用了多样化的分析方法,不追求全面性。根据个人的审美取向和批评目的,选择性地关注作品的某些方面。尽管两位批评家的文评具有鲜明的个性,但在深入剖析后,笔者发现其背后存在两处共性。其一,余华作品得到两位汉学家的一致喜爱。余华作品的主题深度和艺术表现力引起鲍斯的强烈共鸣,而其主人公身上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亦获得顾彬认可。其二,两位学者都高度称赞高立希的翻译水平。翻译实质上是一种改写,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母语驾驭水平等因素对作品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影响甚大。德国汉学期刊的撰文者往往兼具汉学家和译者两种身份,具备德汉双语阅读能力,因此他们能够对作品中文原著和德文译本进行比较阅读,能够敏锐地察觉到改写的特点。将对翻译的分析有机地融入文评中,这也只有在德国汉学期刊上才能见到。
两位学者最大的差异来自对作品结构和重复技巧的理解。鲍斯展现出一种更开放、包容的态度。而顾彬以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为中心来审视余华的长篇小说,忽略了作品的诸多特质。西方现代主义叙事依据的是写作主体的心理时间,打乱了传统叙事的线性时间关系,“现在”“过去”“将来”的界限可以是模糊的,这与余华想要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展现的意趣大相径庭。而20世纪80年代的余华,处于对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等西方文学巨匠的借鉴阶段,其中短篇小说虽已显露出独特的艺术特质,但仍有对西方作家的模仿痕迹,这个时期的作品被顾彬视为佳作,亦不难理解。
在对余华作品《兄弟》进行解读时,高立希与顾彬的文评也有较大差异。高立希在文章中援引《福布斯》杂志曾报道过的一个案例: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位收废纸的女性飞速成为富豪,以此来反驳一些批判家认为余华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不可信的观点。此外,高立希对余华这部作品中粗鄙、滑稽的叙事风格十分肯定[5]。而顾彬却指出,余华小说过度重视对故事情节的构建[6]。顾彬对中国诗歌情有独钟,并对一些当代诗人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然而,他对中国小说持有保留态度,并不完全认可中国小说家在叙事技巧上所取得的成就。因此,余华这位在叙事技巧上颇具造诣且惯常运用透明语言的作家,也未能免于顾彬的批评。
与顾彬从西方文学批评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审视的做法不同,鲍斯与高立希专注于文本和创作分析,并充分考虑了中德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通过对德国汉学期刊上登载的关于余华作品的批评与研究的文章进行考察,可以推断出德国汉学期刊构建了一个多声部的批评话语空间,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阐释是复杂而多元化的。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德国汉学期刊对余华作品的译介起步较早、持续性强;译介者群体相对固定、专业素养高,因此译作及文评水平很高;译介内容注重时效性、多元化。德国学者丰富了对余华作品的学术探讨,奠定了德国对余华作品译介的学术性框架,促进了余华作品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余华的作品获得德国汉学界高度认可,间接地反馈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通过深入研究余华作品在德国汉学期刊上的译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学作品在国际传播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因此,实现文化“走出去”战略不仅要从多维度努力,更需要相关部门及国内外学术界、译者的积极参与和持续支持。
参考文献:
[1]Kautz,Ulrich. Begegnung mit Yu Hua [J]. In: Hefte für ostasiatische Literatur,2000(29):149-154.
[2]Lefevere,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10.
[3]Baus,Wolf. Yu Hua-Der Mann, der sein Blut verkaufte [J]. In:Hefte für ostasiatische Literatur,2000(29): 160-164.
[4]Kubin,Wolfgang. Der Mann, der sein Blut verkaufte [J]. In: Orientierungen. Zeitschrift zur Kultur Asiens,2005,17(2):160.
[5]Kautz,Ulrich. Chinas andere Seite [J]. In: Hefte für ostasiatische Literatur,2006(41):126-128.
[6]Kubin,Wolfgang. Yu Hua: Brüder [J]. In:Orientierungen. Zeitschrift zur Kultur Asiens, 2012,24(1):138-139.
作者单位: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德国汉学期刊《袖珍汉学》《取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项目编号:2023SJYB0620)。
作者简介:李莉娜(1986—),女,汉族,重庆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德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