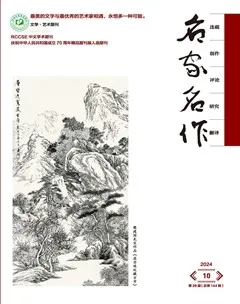丹纳“三要素”下的悲剧意识探析
[摘 要] 基于丹纳“三要素”的相关理论,对《活着》一书中的悲剧意识进行深入探究。从故事主人公福贵的坎坷生活经历入手,结合当时社会环境的状况与变迁,采用丹纳“三要素”中的种族、环境和时代进行分点论证,进一步探究贯穿于福贵生活经历中的悲剧意识。研究发现,福贵的生活受到了各方面的因素影响而跌宕起伏,悲剧意识始终贯穿全书。
[关 键 词] 丹纳“三要素”;悲剧意识;《活着》
一、引言
丹纳在其代表作《艺术哲学》中深入探讨了文学现象,并提出了著名的“三要素”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联性[1]。丹纳的“三要素”理论不仅在文艺理论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其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意义也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尽管许多学者对这一理论给予了高度关注,但他们往往只关注其在文艺理论方面的应用,而忽略了它在社会理论方面的广泛意义[2]。在中国当代文学界,作家余华深受丹纳“三要素”理论的影响,在其作品中巧妙地将苦难事件置于现实的历史背景之中,使得他笔下的悲剧人物更具人性的光辉。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活着》,充分体现了丹纳理论的精髓。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充满了无尽的苦难和挑战。他的生活经历不仅是个人悲剧的写照,更是当时社会中“卑微群体”生存状态的真实缩影。福贵的故事全面展现了那个时代底层人民所面临的残酷现实和艰难困境。本文通过丹纳的“三要素”理论,深入分析福贵悲剧生活背后的社会根源。细致探讨种族、环境和时代如何影响个体命运,揭示其悲剧意识。
二、悲剧意识探讨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意识最早出现在屈原笔下的《离骚》中。对于余华而言,悲剧的核心并非英雄的痛苦与死亡,而是一个无法与周围社会断裂的个体的荒谬与孤独[3]。这种对悲剧讽刺的意识往往表现为沉默、没有言语或无言的状态。人类被不由自主地投掷进这个世界,如同没有实体的影子,被束缚在“被黑暗吞噬”的现实中。
余华对孤独的理解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共鸣,与王国维的悲剧观有着显著差异。王国维认为悲剧源于人物间的痛苦关系;而余华则揭示了日常中的悲剧沉默,探讨了孤独与人性的深层联系,这种联系超越了社会关系。他的故事常在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痛苦,与道家哲学有着相通之处,强调孤独与悲剧的微妙存在。余华更关注个体面对生活压力的无声抗争与自我救赎,认为孤独促使人们内省,寻找生命的意义。在他的作品中,孤独是成长的催化剂,让角色在沉默中学会坚强。此外,在《活着》中,余华还巧妙地将孤独与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相结合,指出在信息爆炸、人际疏离的当下,人们虽然身处人群之中,却往往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与空虚。他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幅现代人心灵的荒原图景,呼吁读者正视并反思这种社会现象,寻找重建精神家园的途径。
三、种族要素影响下产生的悲剧意识
《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到,“我们所谓的种族,是指先天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4]。由此,不难看出,丹纳的“三要素”理论中的种族要素可以分为先天和遗传两个部分。先天可以理解为生来便具有、独特于他人的特性,而遗传则不妨理解为延续了家族、长辈性质的特性。《活着》中福贵跌宕起伏的生活经历中的各式悲剧意识,与其种族要素的影响是息息相关的[5]。
(一)先天影响下形成的个性
福贵从幼小的时候开始,就展现出了非常顽劣和纨绔的性格特点。在他童年时期,有一次在私塾里,当他拿起《千字文》这本书时,竟然对教书的先生出言不逊,毫不尊重。结果,这位先生严厉地批评了他,甚至预言他长大后肯定会成为一个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先生用“朽木不可雕也”来形容福贵,表示他已经无可救药。福贵的父亲也认为他从小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孩子,对他的顽劣行为感到非常失望。福贵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经常一连几天都泡在城里玩耍,完全不顾家里的事务。他的顽劣性格也让他染上了嫖娼和赌博等恶习,尤其是赌博,成为他悲剧命运的开端。尽管他是徐家唯一的儿子,父亲并没有完全放任他的放荡行为,仍然希望他能够走上正道。从父亲为他请私塾先生这一举动中,可以看出父亲对他的期望和关心。然而,福贵本人对学习却毫不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反而越来越沉迷于各种恶习之中。面对这样的福贵,父亲也感到无计可施,尽管他尝试过各种方法来纠正儿子的错误,但最终还是无法阻止福贵继续胡作非为。福贵的顽劣性格和恶习最终导致家产败光,使得整个家庭陷入了悲剧的结局。由此可见,福贵的顽劣性格与他的先天影响密不可分,尽管父亲尝试纠正他的错误,但却无法将他从这条不归之路上挽救回来。
(二)遗传影响下带来的个性影响
福贵不幸地染上了赌博的恶习,频繁地参与城内的赌博活动。这种行为不仅仅是因为他天生就具有某种倾向,更是由于遗传因素的影响。他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同样沉迷于赌博的诱惑,将祖辈传下来的两百多亩土地几乎全部输掉,只剩下一百多亩。福贵年轻时的行为举止,与他父亲年轻时的状态如出一辙,极其相似。福贵的父亲在年轻时,不务正业,反而对福贵的爷爷说:“你别担心,我儿子将来一定会光耀我们家族的。”然而,几十年后,福贵竟然也说出了同样的话,仿佛是一个轮回,这充分证明了遗传对个性的深远影响。因此,福贵不断地沉迷于赌博,输得越来越多,最终导致家产全部输光,迎来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巨大的悲剧。
不仅如此,福贵与他的父亲在心路历程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年轻时,福贵的父亲沉迷于赌博,将祖上传下来的土地输得只剩下一百多亩,直到后来才幡然悔悟。而福贵在年轻时也将自己的身心全部投入赌博中,最终导致家里破产,直到那时他才开始悔悟。由此可见,遗传因素在悲剧意识的产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四、环境要素影响下产生的悲剧意识
丹纳在他的著作《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到,“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的倾向,并且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他指出,环境可以细分为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部分。物质环境大致上可以理解为自然界中存在的诸多因素,例如动物、植物、地理等,而社会环境则主要指向有关人文因素的社会系统。对于福贵的生活来说,后者对其产生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从而间接地影响到了前者,为福贵的悲剧埋下浓厚一笔。
在《活着》中,人们盲目热血,队长带领村民砸锅炼钢,结果只得到废铁。为了炼钢,队长请风水先生选地,被选中的人家房屋难保。福贵家因妻子与风水先生相识而幸免,但其他家庭仍遭受损失。这不仅是小说的悲剧,也反映了政治影响下的悲剧。此外,天气导致稻子被淹,人们只能喝稀粥度日。饥荒时,一小袋米都变得极其珍贵。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为填饱肚子而挣扎,社会发展停滞。余华通过细节描绘了天灾下人性的恶。
五、时代要素影响下产生的悲剧意识
(一)新旧更替而充满悲剧的时代
《活着》的故事背景主要设定在20世纪40—80年代的中国。这一时期中国正经历着新旧交替的重大变革。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福贵一家作为一个已经落魄的平民家庭,只能被动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方针。为了应对新时代的挑战,福贵及其家人被迫参与各种活动。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福贵一家的命运如同浮萍,在历史的洪流中摇曳生姿,却又坚韧不拔。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土地改革的春风拂过了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给予了像福贵这样的农民家庭一线生机。他们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田地,虽然土地贫瘠,但那份踏实感却如同久旱逢甘霖,让福贵的心头燃起了希望的火种。
然而,生活的艰辛并未因此减少。为了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出希望的果实,福贵起早贪黑,用汗水浇灌着每一寸土地。他的双手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却也因劳动而显得异常有力。家中的妻子家珍更是以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的坚韧与乐观,成为福贵最坚实的后盾。
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深入,农村的生活条件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合作社的成立,让福贵和乡亲们能够团结一心,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提高粮食产量。虽然过程中不乏困难与挑战,但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每个人都充满了干劲。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更是吹遍了大江南北,也为福贵一家带来了新的机遇。福贵凭借着勤劳与智慧,开始尝试新的农作物种植,甚至小心翼翼地涉足了一些简单的副业。虽然起步艰难,但每一步都走得异常坚定。他的孩子们也在这样的环境下茁壮成长,他们接受着新时代的教育,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准备在未来的道路上大展拳脚。
岁月如梭,转眼间几十年过去,福贵一家已从那个落魄的平民家庭成长为新时代下的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一户人家。他们见证了国家的巨变,也亲身经历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坚持始终如一。福贵常常坐在门槛上,望着远方的田野,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满足。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活着的意义所在——在时代的洪流中,勇敢地活下去,用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
(二)时代选择下难以抹去的阶层差异
福贵的儿子有庆的献血经历,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阶层差异的显著性。在这个故事中,有庆是一个善良、充满热血的男孩,他怀着对社会的热爱和对生命的尊重,积极地参与了献血活动。然而,令人痛心的是,那些负责抽血的医生却对有庆的身体状况视而不见,不顾他已经开始出现脸色发白、头晕目眩的现象,仍然坚持继续抽血。他们冷漠无情地将有庆的健康和生命置之度外,直到有庆因为失血过多,当场倒下,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些人才停止了抽血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医生们的表现更是令人寒心。面对有庆的悲剧,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同情和责任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真是胡闹”,然后便急忙去为县长的女人进行治疗。这种冷漠的态度充分暴露了当时社会中阶层差异的严重性。医生们似乎只关心那些地位高、权力大的人,而对像有庆这样家境贫寒的小男孩的生命漠不关心。有庆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阶层意识固化的缩影。有庆的地位远远低于县长夫人,这使得他在那些冷漠的医生眼中,似乎只是一个可以随意牺牲的工具。这种对生命的轻视和对阶层差异的漠视,正是余华笔下所展示的“对人性残忍冷漠、凶暴疯狂”的社会现实。然而,有庆只是众多受阶层差异压迫的穷苦人中的一个。在那个时代,还有许多像有庆一样的人,他们的悲剧并没有被广泛地关注和报道,他们的生命在社会的冷漠中默默消逝。这些悲剧,正是那个时代社会矛盾和人性扭曲的真实写照,也是余华“对人性残忍冷漠、凶暴疯狂的展示”[6]。
六、结束语
本文以余华的作品《活着》为例,通过丹纳“三要素”的视角来分析悲剧意识的产生。从种族这一要素的角度进行分析,福贵不仅受到了自身基因的负面影响,还受到了家族遗传的负面影响,使得福贵踏上了和他父亲相同的错误道路,虽然在事后幡然悔悟,却终究不能扭转悲剧已然酿成的事实;从环境这一要素的角度进行分析,物质环境下天灾的影响固然让人心生绝望,连果腹都成为一种奢求,然而社会环境下普通人被迫随波逐流的生活状态更是令人深感无奈;从时代这一要素的角度进行分析,福贵一家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之中,身为家境已然落魄的普通家庭,他们为时代的洪流所裹挟而难以脱身,为了适应时代的变迁被迫走了不少弯路,也因此引发了不少悲剧的出现。而时代发展的局限性又注定了许多陋习依然存在于社会中,阶级歧视便是其中的典型之一。这样“看人下菜碟”式的区别对待直接导致了福贵之子有庆的丧命,也揭露了时代发展局限性的弊端。通过以上分析,将更加深切地从特殊的角度去了解悲剧诞生和悲剧意识产生的因素,也能以《活着》中的故事角色来映射作者对农民不公命运的思考,以及对农民生活的同情和悲悯[7]。余华在其作品中探讨了语言与现实、历史与道德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其悲剧意识的基础。他以绝望和黑暗的视角审视人类存在的意义,通过孤独个体的内心独白质疑人类价值。余华的悲剧意识与孤独个体的声音揭示了现代性的困境,并与欧洲思想家有相似之处[8]。他提出生命本质上是孤独的,并认为不朽只会加剧孤独感。余华认为,荒谬与孤独是人类存在的悲剧性的两面,强调个人价值,赋予角色丰富的历史维度。这些角色通常与社会隔绝,处于孤立状态。余华通过黑暗和虚无表达现代悲剧意识,深化孤独感。他还指出绝望和希望都是虚幻的,悲剧意识源于个体在社会中的孤立状态。社会的荒谬性、被未开化大众包围的处境以及语言的局限性,使得沟通变得不可能[6]。余华的悲剧意识建立在无出路的叙事结构之上。
参考文献:
[1]周均平.论泰纳美学的基本原理或轴心概念——三要素说[J].临沂师专学报,1991(2):24-28.
[2]谢建文.现实的悲悯:1990年代余华小说创作母题[J].名作欣赏,2010(23):119-121.
[3]孙卫华.《活着》悲剧叙事的嬗变:从小说文本到影视剧文本[J].电影文学,2008(11):135-136.
[4]泰纳.英国文学史[M].杨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51-155.
[5]俞冰.《活着》引发的思考[J].电影文学,2011(9):71-72.
[6]田敏.余华小说的悲剧意识与“活着”哲学[J].求索,2011(3):206-208.
[7]姚瑶.浅析《活着》里的生与死:品读《活着》,品读余华[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2(10):70.
[8]赵苓岑.象征、悲剧意识与“偶尔的疲惫”:关于余华的长篇小说《文城》[J].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5):107-112.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作者简介:章榜(2003—),男,汉族,浙江温州人,本科,研究方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