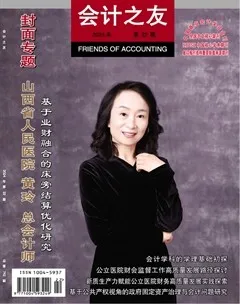国家审计能促进国有企业绿色转型吗
【摘 要】 文章以2011—2022年沪深A股工业行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检验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审计能够显著促进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环境信息披露在国家审计促进国有企业绿色转型中发挥中介作用,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调节效应,能够负向调节环境信息披露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审计促进中央国有企业、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及高管股权激励强的国有企业绿色转型更为显著。拓展性检验发现,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同一省份的溢出效应。结论丰富了国家审计监督治理效应的研究,拓展了企业绿色转型驱动因素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国家审计; 国有企业绿色转型; 环境信息披露; 融资约束
【中图分类号】 F239;F2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4)22-0113-1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9月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国家在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背景下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双碳”目标的提出不仅是我国绿色发展之路的里程碑,而且是未来数十年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这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此,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加快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刻不容缓。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新阶段,对国家审计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十四五”时期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提出,以加快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为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促进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推进乡村振兴与绿色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和重要保障,作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应发挥好绿色转型过程中的监督和保障作用。但是目前企业存在形式主义、资金缺乏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绿色转型。企业绿色转型的替代效应[ 1 ],使企业管理层出于短期业绩增长压力,可能以环境治理投入、环境税等方式进行“敷衍了事”的“绿化”,并没有以绿色创新的方式进行深刻变革。同时,由于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绿色创新[ 2 ],企业即使在外部压力下有较高的意愿进行绿色转型,但资金短缺也会导致企业没有能力进行研发投入,创新导向的绿色转型成为“无水之源”。此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顶梁柱”的国有企业,本应履行好社会责任,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中发挥较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但在实际“绿化”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特质[ 3 ],增加了企业负担,使其无暇进行绿色转型战略规划和根本性的绿色转型。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完全依赖内部利益驱动并不可靠,企业只有在一定外部环境和压力下,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绿色转型[ 4 ]。这就需要国家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对企业绿色转型施加外部约束。研究发现,政府环境监管[ 5 ]、利益相关者压力[ 6 ]等合法性压力与环境规制[ 7 ]可以推动企业绿色转型。而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机制及国有企业外部约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独立性,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监督职能和治理效应,从而为国有企业绿色创新转型提供监督保障。因此,本文以2011—2022年沪深A股工业行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以及环境信息披露的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的调节中介效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从国有企业绿色转型角度丰富了国家审计的微观治理效应研究。现有对国家审计的微观治理效应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提升内控质量和企业价值、促进国有企业创新等方面,鲜有考虑国家审计这一治理监督机制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第二,从国家审计视角拓展了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因素研究。对企业绿色转型影响机制的研究,鲜有从国家审计治理效应这一视角进行研究。本文探究了国家审计治理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拓展了企业绿色转型驱动因素的研究视角。第三,从政府和企业两个维度提出管理启示。本文研究结论对政府部门完善审计监督制度,发挥国家审计的治理效应和反馈机制,制定绿色转型相关政策具有实践意义。同时,研究国家审计促进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为企业完善内部监督治理、推进企业绿色转型赋能提供了现实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绿色转型
内部动机和外部压力可以影响企业绿色转型。一方面,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导致其进行绿色转型主要受自身利益的驱动,而国家审计可以增强企业绿色转型的内部动机,推动企业进行绿色转型。根据“波特假说”,严格、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创新,从而形成“创新抵消”效应,部分甚至完全对冲因遵循环境规制增加的成本,改善环境和商业业绩,使得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更具优势[ 5,8 ]。国家审计的监督机制,能够确保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等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节能减排等命令型环境规制的落实,发挥“创新抵消”效应,降低企业绿色转型的成本压力,使企业出于自身业绩增长、竞争力提高的需求,自觉实施绿色转型。另一方面,在外部压力缺乏的情况下,一旦绿色创新的经济利益在短时间内不足以抵消其创新投入,企业很可能不会进行绿色转型。因此仅仅依靠利益驱动等内在动机是不可靠的,实施适当的外部激励手段和外部压力机制同样重要。相关研究也发现环境规制等外部手段可以有效倒逼企业绿色转型[ 9 ]。国家审计可以基于其权威性和强制性,实施命令型环境规制、施加合法性压力,迫使企业实施“绿化”行为。
另外,国有企业的绿色转型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更高,制造环境问题而地方政府无法制约[ 4 ];另一方面,“政企分开”落实不到位,使得部分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互相依赖,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企业绿色转型。国家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可以有效发挥监督治理效应和免疫系统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厘清政府和企业责任,促进国有企业加强环境治理,推动国有企业绿色转型。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国家审计能够促进国有企业绿色转型。
(二)环境信息披露的中介效应
国家审计能够发挥揭示、预防、抵御功能,通过监督和治理机制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10 ],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一方面,基于国家审计的监督机制,国家审计可以基于其权威性和威慑力,惩罚企业隐瞒信息的行为,施加合法性压力,确保企业行为符合环境制度的要求,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提供合理保证。另一方面,基于国家审计的治理机制,国家审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企业内部环境,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源头,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国家审计在审计过程中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障碍,通过治理机制和反馈机制,在政策制定中,有针对性地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提供支持,克服企业绿色创新的信息披露难题[ 11 ],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激励机制和合法性压力,推动企业实施根本性、长期性、主动性的绿色转型。一方面,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为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从而使企业获得长远利益,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可以向利益相关者证明其履行了环境责任,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从而获得更多资金、信息和技术支持[ 12 ]。这些短期利益又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声誉[ 13 ]、企业价值[ 14 ]和竞争力[ 15 ],部分抵消当前较高研发投入使企业面临的风险和压力,提升企业绿色转型意愿,从而进行绿色转型。另一方面,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合法性压力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环境信息披露受到政府执法部门和资本市场的双重监督。如果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显示企业有较多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那么企业很可能面临高额的环保处罚、缴纳排污费、减少环保补贴,这可以使企业的环境外部性内部化,迫使企业的绿色转型战略从被动治理转向主动防治[ 16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环境信息披露在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绿色转型中发挥中介效应。
(三)融资约束调节的中介效应
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激励机制和合法性压力,促进国有企业绿色转型。但是如果企业外部筹集资金的能力受到限制,那么投资支出可能会对现金流的波动表现出“过度的敏感性”[ 17 ],从而限制企业的投资行为。一方面,融资约束会通过抑制未来短期业绩而弱化技术创新对环境治理投入的替代行为,使企业与管理层为了满足短期利润目标,采取短视行为,宁愿以支付环境税等环保投入方式,维持形式上“绿化”的短期繁荣,也不会增加长期投入以绿色创新方式进行根本转型。另一方面,由于绿色创新投入的收益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在企业负债率较高、外部融资约束较高的情况下,企业无法获得稳定的现金流,倾向于“守成”,即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确定性相对较高的生产经营领域。因此,缓解融资约束、增加资金供给能够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资金支持,与环境信息披露的激励机制发挥协同效应,从而使企业抛弃成本包袱,加大研发投入,更快进行绿色转型。
即使企业具有较高的绿色创新转型意愿,但企业是否有能力进行绿色转型也是值得考虑的。融资约束作为抑制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即使国有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的合法性压力下,希望通过绿色创新投入实施绿色转型以获得长期收益,但是由于创新投入的不确定性高等风险,企业很难通过外部来源获得研发资金。即2n0l5WQ0ViFGHKCNtxThpg==使获得外部资金也通常有较高的融资成本,因而缺乏研发资金的企业无法进行大量创新投入以实施创新导向的绿色转型。因此,高融资约束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绿色创新转型意愿,削弱环境信息披露的合法性压力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使企业缺乏资金来源进行创新投入,而无法实施彻底的绿色转型。国有企业具有公益特征,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需要为调节国民经济做出贡献,因此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难免受到政府的干预。如果财政压力较大,地方政府可能为了完成政治目标,对地方国有企业施压[ 3 ],进一步挤占企业研发资金,阻碍国有企业实施绿色转型。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融资约束对中介效应模型中环境信息披露与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本文的研究假设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22年除西藏外30个省份的沪深A股工业行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就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在数据整理中,剔除缺失数据的企业和ST、*ST的企业,最终获得了6 669个数据样本,并借助Stata16和Excel等工具对数据进行了相应处理。本文所使用的国家审计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审计年鉴》,其他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测度与指标选取
1.被解释变量
绿色创新是企业绿色转型的核心和关键,本文基于杨波等[ 18 ]的研究,选取当年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作为测度企业绿色转型的基础,选取指标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加1取对数(Lngreen)来衡量国有企业绿色转型。
2.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郑国洪等[ 19 ]的研究,采用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国家审计政策(PostAudit)。首先依据《中国审计年鉴》中被审计企业的名单,将样本划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即当上市公司所属中央企业被审计过时Audit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其次,当上市公司所属中央企业受到审计署审计,被审计当年及以后年度Post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国家审计政策虚拟变量(PostAudit)以Post和Audit二者的交乘项Post×Audit度量。
3.中介变量
环境信息披露是指环境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本文参照蔡春等[ 20 ]的做法,选取包括环境管理、政府监管与环境认证、环境信息披露载体、环境负债、环境业绩及环境治理5个准则层、共计30个指标,赋值后将指标加总,按百分制计算得分,度量环境责任披露情况(CER)。
4.调节变量
本文以WW指数度量融资约束。WW指数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WW数值越大表示融资约束程度越高。
5.控制变量
结合程军等[ 21 ]建立的模型,本文采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两职合一(Dual)、高管持股(MHS)、股权集中度(TOP1)、股权制衡(EBD)、独立董事比例(Indep)、董事会规模(Board)、机构投资者持股(Instholding)、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报酬率(ROA)、现金资产比率(Cash)、公司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成长性(Growth)。各变量指标选取与度量方法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为了考察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控制行业效应和时间效应。采用双重差分法模型验证解释变量国家审计(PostAudit)与被解释变量国有企业绿色转型(Lngreen)的关系,验证H1。
检验环境信息披露(CER)在国家审计(PostAudit)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Lngreen)的影响中是否发挥中介效应,即验证H2。
检验融资约束(WW)对国家审计(Audit)与国有企业绿色转型(Lngreen)关系的调节中介效应,验证H3。
四、实证分析
(一)回归结果分析
1.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
通过Stata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回归结果如表2列(1)所示,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回归系数为0.278,在1%水平显著,说明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绿色转型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国家审计可以促进国有企业绿色转型,验证了H1。
2.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中介效应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2列(2)、列(3)所示。列(2)中国家审计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回归系数为4.976,在1%水平显著,表示国家审计可以促进国有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列(3)中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回归系数为0.256,在1%水平显著;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回归系数为0.004,在1%水平显著。以上结果表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国家审计可以通过推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间接促进国有企业绿色转型,进一步验证了H2。
3.融资约束调节的中介效应
融资约束对国家审计、环境信息披露与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2列(4)所示。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回归系数为0.251,在1%水平显著;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回归系数为-0.122,在1%水平显著;环境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交乘项的系数为-0.004,在5%水平显著。以上表明国家审计通过推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间接促进作用受到融资约束的调节。具体而言,融资约束能够对中介效应模型中环境信息披露与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验证了H3。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1.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为了缓解样本选择偏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黄俊等[ 22 ]的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样本进行一比三的最邻近匹配,利用PSM-DID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依然支持上述结论。
2.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借鉴郑国洪等[ 19 ]的研究,利用跨期动态模型回归检验处理组与对照组是否满足连续多期DID的平行趋势假定。根据国家审计实施时间分别设置如下政策时点哑变量:before3,国家审计发生之前的第三个年度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before2,国家审计发生之前的第二个年度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before1,国家审计发生之前的第一个年度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current,国家审计发生当年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除国家审计发生之前的第三个年度国家审计对环境信息披露具有促进作用外,只有国家审计发生当年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融资约束的调节中介效应在5%水平显著。参考窦炜等[ 23 ]的研究,可能是由于国家审计的预期效应导致的。因此,可以认为回归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平行趋势检验,上述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3.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其他未知因素的影响,确保本文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由国家审计实施所引致的,需要进行安慰剂检验。参考任胜钢等[ 24 ]的研究,对Post与Audit的交乘项进行随机抽样,重复500次,按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图2。其中,x轴表示500次抽样中PostAudit的系数值,y轴表示估计值为该系数的频数。通过系数分布图可知,PostAudit的随机抽样系数始终以0为均值,并呈正态分布,这说明基准回归的结果不太可能为其他不可观测因素所导致,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4.替换变量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将国有企业绿色转型以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加1取对数度量,检验结果仍然支持H1、H2、H3和H4①。
5.增加控制变量
考虑到企业市值和企业价值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增加控制变量企业市值和企业价值以提高上述回归模型的可靠性。企业市值(CAP)以当日收盘价与股本总额的乘积度量,企业价值(TobinQ)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回归结果(略)同样证明了国家审计能够促进国有企业绿色转型,也验证了环境信息披露的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对中介效应模型中环境信息披露与国有企业绿色转型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
6.被解释变量滞后一年
前述模型仅考虑了国家审计的作用滞后两年的情况,为增加实证结果的可靠性,考虑国家审计的作用滞后一年的情况,即国家审计(PostAudit)选取2010—2019年的数据,其他变量选取2011—2021年的数据,回归结果(略)主要变量在1%水平显著,证明上述假设成立。
(三)异质性分析
1.国有资产管理权限、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绿色转型
由于国家审计主要针对央企,虽然审计过程中央企控股的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国家审计的影响,但该影响是间接的,因此本文进一步细化国家审计的治理效应研究,探究国家审计对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治理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按国有资产管理权限,国有企业分为中央与地方国有企业。在中央或地方国有企业分组检验中,国家审计对企业绿色转型不同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5列(1)、列(2)所示。在中央国有企业中,国家审计(PostAudit)与国有企业绿色转型(Lngreen)的回归系数为0.110,在1%水平显著。在地方国有企业中,国家审计(PostAudit)与国有企业绿色转型(Lngreen)的回归系数为0.099,不具有显著性。表明与地方国有企业相比,国家审计对促进中央国有企业绿色转型更为显著。经过分析后发现,中央国有企业受到国家审计监督作用更强,且其负责人的考核往往会与国家政策落实情况、环境责任承担情况相挂钩,致使中央国有企业绿色转型效应得以有效发挥。
2.地区差异、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绿色转型
为了验证在不同地区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根据国有企业所在省份,划分为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研究各地区差异是否影响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回归结果如表5列(3)、列(4)、列(5)所示。在中东部地区,国家审计(PostAudit)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Lngreen)的回归系数为0.224,在1%水平显著;在西部地区,国家审计(PostAudit)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Lngreen)的回归系数为0.538,在1%水平显著。采用Chow检验进行进一步验证,引入地区差异(Region),国有企业属于中东部地区为1,其他为0。回归结果显示PostAudit与Region的交乘项系数为-0.197,在5%水平显著。结果表明,国家审计更显著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经分析后发现,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更依赖资源消耗型增长,国家审计的监督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种“饮鸩止渴”的行为,从而更能显著地促进该地区国有企业绿色转型。
3.高管激励差异、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绿色转型
通常认为,高管股权激励可以提高企业发明专利创新绩效[ 25 ]。为了验证在不同水平的高管持股比例下,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引入高管持股(MHS),将高管持股(MHS)大于等于或者小于中位数的企业划分为管理层持股比例高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低的企业,回归结果如表5列(6)、列(7)所示。在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的企业,国家审计(PostAudit)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Lngreen)的回归系数为0.450,在1%水平显著;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低的企业,国家审计(PostAudit)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Lngreen)的回归系数为0.205,在1%水平显著。采用Chow检验进行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显示,PostAudit与MHS的交乘项系数为15.889,在10%水平显著。结果表明,国家审计更显著地促进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的企业的绿色转型。经分析后发现,这可能是由于给予管理层更多的股权激励,可以分享绿色转型带来的企业价值提高和股票增值的长期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管的短视行为,能与国家审计发挥协同效应,更显著地促进该国有企业的绿色转型。
(四)拓展性检验
国家审计除了能促进被审计国有企业的绿色转型外,是否可以发挥溢出效应,促进本地区其他国有企业的绿色转型?本文引入国家审计的区域介入程度(PostAudit_Region),检验国家审计在同一省份中的溢出效应。国家审计的区域介入程度以同一年度同一省份的国家审计(PostAudidxMD2wO3RhAhDHfb6Wr6E4GWl2Kqb+quGIMpdt5qduw=t)度量,该指标越大,说明该年该市接受国家审计的国有企业越多,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国家审计的区域介入程度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回归系数为0.026,在1%水平显著,表明同一年度同一省份被审计的国有企业越多,未被审计的国有企业的绿色转型水平越低,说明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同一省份的溢出效应。国家审计作为一种环境规制手段,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环境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进行处罚并督促企业整改,可以发挥震慑作用,不仅约束了被审计企业的短视行为,而且通过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健康运行,推动了同一地区未被审计的国有企业的绿色转型。
五、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审计监督是国家治理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2011—2022年间沪深A股工业行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以及环境信息披露的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调节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国家审计可以显著促进国有企业绿色转型。国家审计可以通过内部激励机制、外部震慑机制和对政府、国有企业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促进国有企业的绿色转型。第二,环境信息披露在国家审计促进国有企业绿色转型中具有中介作用,即国家审计可以通过促使企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绿色转型。国家审计可以通过奖惩机制,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激励机制、利益相关者和合法性压力,推动国有企业实施根本性、长期性、主动性的绿色转型。第三,融资约束对环境信息披露的中介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融资约束可以抑制环境信息披露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缓解融资约束既可以解决具有绿色转型意愿的国有企业在资金方面的后顾之忧,又可以削弱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研发活动所需资金的挤占,与环境信息披露的激励机制和合法性压力发挥协同作用,以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第四,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央国有企业、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及高管股权激励强的国有企业。这也为不同情境下国有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第五,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同一省份的溢出效应。国家审计可以发挥震慑作用,不仅约束了被审计企业的短视行为,而且通过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健康运行,推动了同一地区未被审计的国有企业的绿色转型。
本文的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丰富了国家审计监督微观治理效应研究和企业绿色转型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文献,在实践中为完善国家审计监督治理体系和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从企业方面看,不仅要完善企业管理层激励机制,发挥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的示范带动作用,而且需要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切实解决企业绿色转型中的资金难题。从国家审计方面看,应进一步健全国家审计的监督机制和治理机制,充分履行国家审计在生态文明审计中的预防、揭示和抵御职能。此外,要充分认识国家审计的溢出效应,保障国家审计充分发挥监督治理效应,推动整个地区国有企业主动实施长期性、根本性的绿色转型。
【参考文献】
[1] 覃予,王翼虹.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化投资路径选择[J].财经论丛,2020(10):75-84.
[2] 叶翠红.融资约束、政府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J].统计与决策,2021,37(21):184-188.
[3] 陈茹,张金若,王成龙.国家审计改革提高了地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J].经济管理,2020,42(11):5-22.
[4] 刘学敏,张生玲.中国企业绿色转型:目标模式、面临障碍与对策[J].中国人口·资源和环境,2015,25(6):1-4.
[5] JAFFE A B,PALMER K.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a panel data study[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7,79(4):610-619.
[6] 邵利敏,高雅琪,王森.环境规制与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选择:“倒逼转型”还是“规制俘获”[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0(6):62-68.
[7] 韩国文,甘雨田.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40(8):89-98.
[8] WEISS J F,ANISIMOVA T.The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effects of well-design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evidence from Sweden[J].Industry and Innovation,2019,26(5):534-567.
[9] 于连超,张卫国,毕茜.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和环境,2019,29(7):112-120.
[10] 吴红军,徐寅寅,江怡.企业漂绿研究综述[J].会计之友,2023(22):53-60.
[11] 李春发,卢娜娜,李冬冬,等.企业绿色创新:政府规制、信息披露及投资策略演化[J].科学学研究,2021,39(1):180-192.
[12] 熊国保,罗元大,赵建彬.企业环境责任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0,36(21):172-175.
[13] 田虹,姜雨峰.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声誉影响的实证研究:利益相关者压力和道德滑坡的调节效应[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55(2):71-79.
[14] MACKEY A,MACKEY T B,BARNEY J B.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rm performance:investor preferences and corporate strategie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7,32(3):817- 835.
[15] MAYA S R D,MARN L,ROBIO A.Competitiveness as a strategic outcom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2,19(6):364-376.
[16] 郭进.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J].财贸经济,2019,40(3):147-160.
[17] FAZZARI S,GLENN R,BRUCE H.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88,1988(1):141-195.
[18] 杨波,李波.“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绿色转型升级[J].国际经贸探索,2021,37(6):20-36.
[19] 郑国洪,肖忠意,陈海涛.国家审计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创新质量[J].审计研究,2022(5):25-36.
[20] 蔡春,郑开放,陈晔,等.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基于“三河三湖”环境审计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19(6):3-12.
[21] 程军,刘玉玉.国家审计与地方国有企业创新:基于经济责任审计的视角[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8,30(2):82-92.
[22] 黄俊,殷海锋.资本市场国际融合与公司审计收费:来自A股纳入MSCI指数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23(2):136-147.
[23] 窦炜,张书敏.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22,19(3):453-462.
[24] 任胜钢,郑晶晶,刘东华,等.排污权交易机制是否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9(5):5-23.
[25] 刘冠辰,李元祯,李萌.私募股权投资、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专利异质性视角的考察[J].经济管理,2022,44(8):116-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