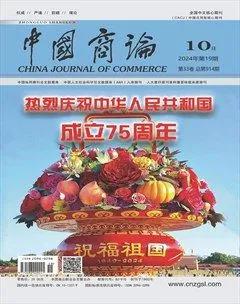业绩期望落差对商誉泡沫的影响研究
摘 要:巨额商誉泡沫是上市公司稳健经营和资本市场平稳运行的潜在风险,而业绩期望落差会对商誉泡沫产生影响并引导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研究企业业绩期望落差对商誉泡沫的影响机制十分重要。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及权变理论,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剖析了业绩期望落差如何扭曲企业并购决策,催生出商誉泡沫这一潜在隐患。研究发现,随着业绩期望落差的扩大,企业商誉泡沫先降后升,呈正U型关系;高管过度自信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起正向调节作用,而财务冗余起反向调节作用。本文旨在丰富业绩期望落差和企业商誉领域的研究,以期为企业风险管理和监管部门化解商誉泡沫提供新思路和新范式。
关键词:业绩期望落差;商誉泡沫;高管过度自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财务冗余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4)10(a)--05
1 引言
近年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次数和规模增多,商誉迅速扩张,随之超额商誉及潜在的减值风险问题也凸显出来[1]。如2022年我国资本市场商誉总额同比暴涨82%,导致大额商誉减值及业绩“爆雷”事件。从理论上说,商誉泡沫源于企业对并购后业绩的过度乐观预期和短视行为[2],当这种预期未能转化为实际价值收益时,企业便陷入了由期望落差引发的商誉泡沫陷阱。当并购后的实际业绩未能达到预期水平时,商誉泡沫便迅速破裂,加剧了业绩期望落差与商誉泡沫之间的恶性循环。那么,当管理层面临业绩期望差距的压力时,会产生何种商誉决策?随着业绩与期望差距的扩大,企业是否会做出不同的商誉决策?这些问题尚缺乏经验证据 。
当前学术界集中于讨论商誉如何影响企业审计、融资、投资、创新等方面[2-3],对商誉的前因变量的探讨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4]。商誉确认过程中包括代理问题、估值差异等非理性因素会导致商誉往往虚高。现实中频发的大额计提商誉减值等现象也揭示出由于标的公司选择、并购方案制定、价值评估等非理性因素产生过高并购商誉。然而,这些非理性因素亦是治理商誉泡沫的关键。企业行为理论指出决策者在组织层面决策过程中的主要参考点体现为企业的业绩期望水平[5]。管理层是企业并购行为的决策主体,而商誉又是并购方自主评估决定的产物,高管过度自信作为内部心理偏差的特性,反映管理层认知如何影响决策质量。此外,权变理论指出组织应根据其内部特性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来灵活调整其策略[6]。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外部环境的动态因素,揭示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并购策略和财务风险的塑造作用;财务冗余作为内部资源缓冲,表明企业内部资源如何帮助企业应对外部冲击和业绩压力,共同构成了理解业绩期望落差与商誉泡沫关系的多维视角。
基于此,本文拟从企业行为理论和权变理论出发,以我国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业绩期望差距对超额商誉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本文将业绩期望差距与商誉泡沫相联系,填补了该领域实证研究的空白,将商誉泡沫纳入企业行为理论的研究框架,丰富了商誉泡沫的前因研究。第二,通过区分业绩略低于期望与远低于期望的不同情况,本文daffcf3b47b6fecfd75a4f8210250ed80fea1572372a94ae389b3f4fb1685cf4突破了线性影响效应的局限,证实了业绩期望差距对商誉泡沫的非线性影响,并提供了高管“孤注一掷”行为的理论阐释,为理解不同绩效水平下的后果发展提供了更细粒度的理论支持。
2 理论假设
2.1 负向绩效反馈对商誉泡沫的影响
企业行为理论指出,仅用绝对值衡量绩效难以反映企业决策的真实依据,因组织行为者追求一定绩效水平,并据实际与期望的差距决策[5]。这种差距会激励战略搜索活动与冒险行为,但可能带来高风险或不必要变化,甚至会危及企业绩效乃至生存。据此,本文提出负向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商誉泡沫之间关系非线性,呈正U型曲线。
2.1.1 在企业业绩略低于期望水平的负向业绩期望差距情形中
企业在运营中,负向业绩期望差距常反映资源配置、管理及市场策略问题。为弥补此差距,决策者可能采取高风险策略,但易导致高管支付过高并购溢价,形成商誉泡沫。商誉泡沫在危机时可能限制企业的现金流,加剧融资约束,增加业绩下滑和股价崩盘风险。对此,企业需灵活调整战略,优化资源配置,在并购决策中仔细权衡风险与收益。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与质疑则可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经营困境可能减少资源积累,进而抑制管理者的私利行为。由于商誉影响非即时效应[7],管理者或偏好短期见效策略以快速改善业绩,从而减少商誉泡沫产生。
2.1.2 在企业业绩远低于期望水平的负向业绩期望差距情形中
尽管Staw(1981)的威胁僵化理论提出企业在重大损失下会因生存威胁而倾向于风险规避,但该理论难以全面解释企业在危机中的自救行为[8]。实际上,面对业绩压力,企业决策者会积极寻求恢复机会[7]。一方面,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商誉泡沫作为积极信号吸引投资,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摆脱危机提供机会。另一方面,并购能带来协同效应和改善市场需求管理能力,增加企业并购需求。但在生存危机和业绩压力下,企业可能因急于求成而忽视并购资产的公允价值评估,产生商誉泡沫。因此,商誉泡沫与业绩期望差距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特征。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1:负向业绩期望差距与商誉泡沫之间呈显著的正U型关系。
2.2 高管过度自信的调节作用
高层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高管的个人特质会深刻影响其对情境的认知和决策过程[9]。在企业行为理论中,高管的决策和行为受到其心理特质的影响,过度自信便是其中之一[5]。在商誉积累上,过度自信的高管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并购、扩大市场份额等方式来快速提升公司的业绩和商誉,忽视潜在风险,抬高并购溢价。
面临较小负向期望差距时,本文认为过度自信高管抑制形成商誉泡沫。一方面,过度自信使得管理者对企业经营和财务状况保持乐观态度,更倾向于投入资源于高风险、高回报的研发和创新领域,并减少并购溢价的支付。另一方面,当企业面临较小的业绩压力时,过度自信的管理层可能更相信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非依赖并购获取外部资源,从而降低商誉泡沫的产生。
然而,面临较大的负向期望差距时,过度自信高管更可能寻求外部支持。由于存在“自我归因”现象,过度自信的高管常常将成功归因于自身,而将失败归咎于外部环境。因此,当公司业绩大幅低于期望时,他们更可能采取进攻性战略。此外,根据Roll(1986)的“管理者自负假说”,过度自信的高管在并购过程中可能支付过高的溢价,这种非理性的价格上升自然导致商誉泡沫的出现。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高管过度自信增强了负向业绩期望差距与商誉泡沫之间的U型关系。
2.3 财务冗余的调节作用
在企业行为理论框架下,财务冗余是应对环境变化与风险的关键策略。在业绩期望有落差时,其提供资源调整战略和优化运营。鉴于财务冗余在大型企业中占据核心地位,能够支持企业同时追求多个可能相互冲突的目标,因此本文试图探讨当企业存在业绩期望差距时,财务冗余是否会调节企业行为。
面临较小负向期望差距时,高财务冗余易导致商誉泡沫。冗余资源过多使决策者风险偏好发生变化(忽视风险),倾向推进并购而非积极恢复业绩。此外,财务冗余增强了风险承受能力,增加机会主义倾向,高估目标价值,形成商誉泡沫。同时,高冗余降低了搜索成本和资源约束,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缓冲空间。但也可能减弱外部监督,诱发高管机会主义和自利行为,加剧商誉泡沫。
然而,面临较大负向期望差距时,高财务冗余可能抑制商誉泡沫。高财务冗余提供更多战略选择和灵活性,减少了对并购的依赖,有助于探索新项目和市场机会。同时,财务冗余增强了决策者信心,减少并购焦虑,有助于审慎评估并购价值,抑制商誉泡沫。因此,在不同程度的负向期望差距下,高财务冗余对商誉泡沫的影响复杂且动态。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3:财务冗余削弱了负向业绩期望差距与商誉泡沫之间的U型关系。
2.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经济主体难以准确预测政府经济政策变动的状态,涉及政策预期、实施及后果等多个层面[10]。从信号理论视角看,这种不确定性影响企业传递的信息和信号,深刻影响企业外部经营环境,使其行为高度依赖政府政策导向。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负向绩效反馈对商誉泡沫的影响中起重要调节作用。
面临较小的负向期望差距时,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倾向于抑制商誉泡沫。高不确定性下,决策者会更积极寻求新信息,灵活调整战略,将资源分散至新领域。同时,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市场需求频繁调整,增加企业风险和业绩波动,促使企业并购时更谨慎,进行充分调研分析,抑制并购溢价。然而,面对较大的负向期望差距,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推动商誉泡沫。企业面临生存压力,决策者倾向采取激进措施以挽救企业。在企业行为理论的框架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的战略制定和决策过程。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可能采取保守策略或寻求新机遇。决策者因担心错失市场机遇而急于并购,导致误判并购价值和商誉泡沫。此外,不确定性加剧并购双方信息不对称,增加目标方信息披露选择空间,提高主并方评估难度[11],更易发生高估现象,扩大商誉规模。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了负向业绩期望差距与商誉泡沫之间的U型关系。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本文所用数据来c96f4da317215e461082edbdc76a9fed自CSMAR数据库,并按以下标准筛选样本:(1)排除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2)排除金融保险行业;(3)排除ST、*ST公司。最终获得27751个样本。
3.2 变量选择与度量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魏志华和朱彩云(2019)的研究方法,利用模型(1)对样本公司进行回归分析,预测公司商誉的期望值。通过计算实际商誉与预测值之差,度量商誉泡沫的程度 [1]:
GWi,t=a0+a1Cashi,t+a2Buyeri,t+a3Gw_ingi,t+a4Sizei,t+a5ROAi,t+a6Growthi,t+a7Mholdi,t+a8Duali,t+Yeart+Indt+εi,t(1)
式中,GWi,t代表公司i在年度t的商誉金额,经年末总资产调整;Cashi,t为哑变量;Buyeri,t表示买方支出价值,即并购对价总和;Gw_indi,t为同行业年度商誉均值;Sizei,t为公司规模;ROAi,t为盈利能力;Growthi,t为成长能力;Mholdi,t为管理层持股水平;Duali,t为两职合一哑变量。此外,Year和Ind分别控制年份和行业的影响。
3.2.2 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Chen(2008)的方法,选用总资产回报率作为衡量企业业绩的指标。基于业绩反馈理论,文章区分了历史业绩预期差距和行业业绩预期差距。其中,历史业绩预期差距APG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而行业业绩预期差距则用于稳健性检验。APG指企业当年实际业绩低于当年历史预期业绩的差值。参照Chen(2008)的递归度量公式,自变量相对于因变量滞后一期进行测量[11]:
Ai,t-1=a1Pi,t-2+(1-a1)Ai,t-2(2)
式中,Ai,t-1是公司i在第t年的历史预期业绩,而Pi,t-2在第t-2年的实际业绩。a1前期实际业绩与预期业绩的相对重要性,取值介于[0,1],本文遵循Chen(2008)的研究,取a1=0.6。需明确的是,Ai,0是公司i初始预期业绩,以第0期实际业绩替代。此外,参照王菁等(2014)的研究,对历史业绩预期差距进行截尾处理[12]。
3.2.3 调节变量
(1) 高管过度自信
本文参考魏哲海(2018)的方法,构建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标(OC),通过对性别、年龄、学历以及两职合一情况进行打分[13]。
(2) 财务冗余
本文参考Vanacker(2013)的定义,将财务冗余(Slack)定义为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与总资产比值与行业均值之比[14]。
(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本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的衡量,参考Baker (2016)构建的政策不确定指数,将月度指数取12个月的算术平均并除以100转换为年度指数[15]。
3.2.4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钟熙等(2022)的研究,将企业的公司规模(Size)、公司成立年限(FirmAge)、资产负债率(Lev)、现金流比率(Cashflow)、两职合一(Dual)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作为控制变量[16]。
3.2.5 模型建立
为检验提出的假说1,本文建立公式:
GW_excessi,t=α0+β1APGi,t+β2APG2i,t+βi∑Controlsi,t+Yeari+Industryi+εi,t(3)
其中,GW_excessi,t代表企业i第t年的商誉泡沫;APGi,t代表企业i第t年的业绩期望差距;APG2i,t代表企业i第t年的业绩期望差距的平方项;Controlsi,t为控制变量组,式(1)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的公司规模、公司成立年限、资产负债率、现金流比例、双职合一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εi,t为随机扰动项;另外,还控制年份Yeari行业(Industryi)固定效应。
进一步地,本文通过加入交互项建立式(2)、式(3)和式(4),分别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管过度自信和财务冗余分别对企业业绩期望差距影响商誉泡沫的调节情况:
GWexcessi,t=a0+β1APGi,t+β2APG2i,t+β3Zi,t×APGi,t+β5Zi,t×APG2i,t+βi∑Controlsi,t+Yeari+Industryi+εi,t(4)
其中,Zi,t调节变量,包括高管过度自信(OC财务冗余)Slack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此外,其他变量与式(1)中的设定一致,该模型同样控制了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
4 实证分析
4.1 主效应检验
为了深入探讨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商誉泡沫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增加控制变量,负向业绩期望差距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无控制变量时,β=-0.0938, p<0.01;引入控制变量后,β=-0.0639,p<0.01)。同时,负向业绩期望差距平方项的回归系数亦呈现显著为正的特征(无控制变量时,β=0.0192,p<0.01;加入控制变量后,β=0.0136,p<0.01)。这一发现揭示了负向业绩期望差距与商誉泡沫之间的复杂关系:适度的负向业绩期望差距有助于降低企业商誉泡沫的风险,然而,当这种差距过大时,可能引发“孤注一掷”效应等不利因素,进而增加企业商誉泡沫的可能性。简而言之,负向业绩期望差距与商誉泡沫之间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正U型关系,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1。
4.2 调节作用检验
4.2.1 高管过度自信
通过模型(1)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高管过度自信与负向业绩期望差距平方项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1461,p<0.01)表明在相同的负向业绩期望差距下,自信程度较高的高管所在企业,其负向业绩期望差距与商誉泡沫之间的正U型关系更显著。这一发现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2,并揭示了高管过度自信在两者关系中的强化作用。
4.2.2 财务冗余
模型(2)实证结果显示,财务冗余与负向业绩期望差距平方项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β=-0.0345,p<0.01),表明在面临业绩落差时,财务冗余充足的企业商誉泡沫风险较低。这验证了假设H3,并强调了财务冗余在缓解商誉泡沫风险中作用。在负向业绩期望差距的情境下,财务冗余支持企业采取稳健决策,减少冒险行为,抑制商誉泡沫形成。同时,财务冗余还为企业提供风险缓冲,保持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降低商誉泡沫风险。
4.2.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模型(3)的实证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负向业绩期望差距平方项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0.0208, p<0.01),验证了假设H3,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从信号理论视角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市场判断,增加决策复杂性,可能导致企业采取激进或保守策略。企业可能通过调整并购或商誉管理传递积极信号,但也可能加剧商誉泡沫,因过度依赖商誉而忽视实际绩效改善。一方面,企业可能因担忧政策变化而谨慎投资,加剧业绩下滑与商誉泡沫的正U型关系;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可能冒险投资以应对不确定性,增加商誉泡沫风险。
综上所述,高管过度自信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誉泡沫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财务冗余则发挥反向调节作用。这些发现既体现了企业行为理论中管理者心理特质和行为倾向对企业决策的影响,也揭示了信号理论在解释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决策和商誉泡沫形成中的作用。
4.3 内生性检验
本文运用以下方法展开内生性检验,所得结论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1)为了避免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本文参考杜勇等的研究方法,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技术对样本进行处理。(2)为处理业绩预期差距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连燕玲等(2014)的研究方法,选择企业规模与存续期作为工具变量,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模型进行内生性处理。(3)借鉴Lemmon和Lins(2003)的研究思路,本文采用自变量滞后两期的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这种处理方式有助于更准确地估计变量之间的关系,降低内生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4)为缓解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控制了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4.4 稳健性检验的深化
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1)将行业业绩差距作为历史业绩差距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其余步骤保持不变。(2)参考魏志华和朱彩云(2019)的研究,本文分别采用上市公司标准化商誉减同年度同行业企业标准化商誉的中位数和均值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3)鉴于我国并购规模在2016年达到峰值后逐步回落并趋于稳定,本文调整了回归年份范围,采用2016—202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5 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我国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果发现,企业的业绩期望差距对商誉泡沫并非呈现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随着企业业绩期望差距的增大,商誉泡沫呈现正“U型”变化。进一步地,本文发现高管过度自信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起正向调节作用,而财务冗余起反向调节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对企业而言,首先应理性对待业绩期望差距,避免策略过于激进或保守。面对较大差距,应深入分析原因,通过提升内部运营效率与产品结构等逐步缩小差距,而非过度依赖外部扩张。同时,设立合理业绩目标,减少商誉泡沫风险。其次,注重高管团队建设,并加强决策监督。最后,密切关注政策变化,预判风险,及时调整策略,并合理利用财务冗余资源,提升企业财务稳健性。
政府应首先加强金融监管,建立商誉泡沫预警机制,定期监测上市公司商誉状况,及时预警风险[17]。同时,严格监管可能导致商誉泡沫的交易,防止企业过度扩张或高风险投资。其次,完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上市公司充分披露商誉情况,提高透明度,助力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最后,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企业树立理性发展观念,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时考虑行业竞争态势和企业实际情况,避免盲目追求规模和速度,同时支持创新和技术改造,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魏志华,朱彩云.超额商誉是否成为企业经营负担: 基于产品市场竞争能力视角的解释[J].中国工业经济, 2019(11):19.
王雪,杨志国.超额商誉与债务融资成本[J].会计与经济研究,2023,37(2):84-98.
赵彦锋.超额商誉、高管激励与审计收费[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1(1):62-69.
张欣,董竹.超额商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22(5):16-30.
JOHNSON L T, PETRONE K R. Commentary: is goodwill an asset?[J]. Available at SSRN, 1999: 143839.
李丹蒙, 叶建芳, 卢思绮,等. 管理层过度自信, 产权性质与并购商誉[J]. 会计研究, 2018 (10): 50-57.
GU F, LEV B. Investor Sentiments, Ill-Advised Acquisitions and Goodwill Impairment[J]. 2008.
STAW B M. The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to a course of ac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1, 6(4): 577-587.
CHATTERJEE A, HAMBRICK D C. It’s all about me: Narcissistic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 and their effects on company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7, 52(3): 351-386.
陈艳艳,程六兵.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管背景与现金持有[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8,20(6): 94-108.
CHEN F, HOPE O K, LI Q, et al. Flight to 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investors’ demand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during political uncertainty event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8, 35(1): 117-155.
王菁,程博,孙元欣.期望绩效反馈效果对企业研发和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J].管理世界, 2014(8):19.
魏哲海.管理者过度自信,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J].工业技术经济, 2018, 37(6):10.
VANACKER T, COLLEWAERT V, PAELEMAN 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ack resourc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 The role of venture capital and angel investor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3, 50(6): 1070-1096.
BAKER S R, BLOOM N, DAVIS S J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4) :1593-1636.
钟熙, 宋铁波, 陈伟宏, 等. 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战略导向: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管理评论, 2022, 34(1): 242.
魏山,李玉菊,李凡,等.A股上市公司并购商誉确认与减值状况分析[J].中国商论,2022(23):119-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