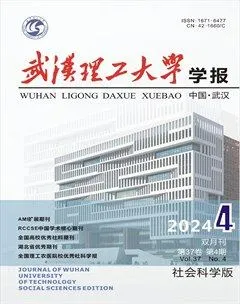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价值、风险与优化路径
摘 要: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和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引发思维方式和教育方式的新变革。面对技术革命的时代浪潮,应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对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赋权增能,通过打造“以数提质”“以数增效”“以数聚能”的发展方案,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内容的优化升级、育人方法的改革创新,育人效果的精准提升。同时,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发展的过程中,也会滋生“技术依赖”“去中心化”“信息茧房”等不良现象,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育人主体自觉性、淡化了育人价值引导力、分化了育人叙事的整体性,严重阻碍了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稳定高效开展。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应该注重价值引领、完善制度建设、提高数字修养,不断夯实数字赋能基础、完善数字赋能保障、增强数字赋能动力,坚决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奋力打造高校数字化红色文化育人新样态。
关键词: 数字技术;红色文化育人;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1; D6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4.04.016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先进文化总和[1]。高校作为培育青年人才的教育主阵地,承担着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使命,是推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力量和责任主体,要不断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育人优势,感召和引领大学生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近年来,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技术正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与交往方式,面对新的历史发展契机,我们应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深度融合,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对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赋权增能,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把科技创新“优势变量”转化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助推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多元化、精准化、智能化发展。但同时,由于受自身逻辑属性和操作程序的规定,数字技术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其中之风险可能会危及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因此,在数字技术泛在的社会环境下,全面剖析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优势和风险,深入探索应对变局、破解困局、开拓新局的因应之策,对于提升高校红色文化育人质量,推动高校育人高质量、数字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价值意蕴
数字技术是一种能将图、文、声、像等信息转化为计算机可以识别的语言以便进行再次表达、计算分析、加工存储以及快速传输的技术[2]。近年来,以大数据、元宇宙、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和5G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成为引领社会进步与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3]数字技术与教育发展的相向而行、合谋共生是时代大势所趋,也是现实发展所向。高校红色文化育人作为新时代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住数字技术赋能发展的时代机遇,打造“以数提质”“以数增效”“以数聚能”的发展方案,实现高校红色文化育人资源、育人方式、育人效果的全面提升,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系统化提升和范式性转换。
(一)以数提质: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内容的优化升级
内容是指构成事物的一切要素的总和,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承载,事物的质的提升往往是内容上量的积累的作用结果。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内容是高校教育工作者在红色文化育人实践活动中,为了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依靠红色文化资源历史遗产,根据教育具体实际情况,为育人对象提供的带有价值引导性的信息总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深度参与,打破了传统模式下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内容开发力度不足、时空传递受限、呈现形式单一的局限,能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内容全方位、深层次、多维度优化升级。
1.运用数字技术激活红色文化资源,推动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型,提升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内容的丰富性。红色文化资源作为红色文化的具象载体,是党带领人民探索发展道路、开创伟大事业的历史印证,也是一种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具有价值引领、道德培养、精神激励等多重价值。但同时,红色文化资源也有时间跨度大、地域分布广、留存形式多样、保存状况复杂的特点,阻碍了其教育价值的高效率转化和普及性应用。利用数字技术海量数据储存、庞大算力处理、全息影像映现的技术优势,虚拟建构红色革命遗址、博物馆、纪念馆、文档、物品等红色物质文化资源,收集整理红色方针、政策、路线、制度、革命精神、理想信念、音乐、诗歌、戏剧、小说等红色非物质文化资源,数字化修复一些损坏的、流失的珍贵历史文物,模拟化再现一些具有重大教育价值的历史事件和经典战斗场景。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革新与升级,使红色文化以更加准确、生动、多元的形式展现出来,丰富了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内容,让广大高校师生能够跨越时空阻隔、克服不利条件影响,真实、便捷、深刻地感受到红色文化的历史魅力和教育价值。
2.搭建数字化信息平台,促进信息交流与资源整合,增强育人内容的共享性。传统的高校红色文化育人过程中,育人内容一般来自上级部门配发的辅助教材、读本和老师个人的备课经验体会,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高校之间甚至是同一高校不同教师之间,获取教育资源的方式以及把握同一教育内容的深刻程度都存在多种差异,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传播衰减的过程中存在被弱化的风险。随着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以来,数字平台或网络平台日益成为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数据繁殖的规模爆炸性增长,信息交换的频率指数级加剧,新型的“互通共享”模式替代了传统的传递渠道。各地区、各类型的红色文化育人信息汇聚在数字平台,经过算法技术的再次挖掘整理,形成资源供给数字矩阵,为全国高校红色文化教学提供全面、系统、及时的教学资源。依靠数字化信息平台,不同教师群体可以相互交流备课经验、借鉴教学成果、共享教学信息,实现教学课程内容供给的科学全面、新鲜及时性。同时,大学生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爱好和需求,从海量的教学资源、课程资源中选择合适的课程内容开展学习,构建“时时可学、处处能学、人人皆学”的学习环境。
(二)以数聚能: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方法的改革创新
所谓红色文化育人方法,是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为了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在红色文化育人活动中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是一个过程性育人实践活动,科学的方法是保障高校有效开展红色文化育人的重要支撑。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方法的确立与变革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来自教育者对各教育要素的深刻把握,反映了教育者对教育客观规律的自觉应用。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加速演进,为适应新形势下实践发展和改革的需要,高校红色文化育人要主动拥抱数字技术的赋能做功,克服传统育人方法中单向灌输、说服教育的局限,将数字技术的理念和思维运用于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方法改革创新的全过程,打造“交互参与”和“具身体验”红色文化育人方法的新样态。
1.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发展构建了虚实相融的交互空间。数字技术的出现弥合了现实场景下教学互动不足、形式结构固化的缺憾,通过对教学空间场域的深度形塑,消弭了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对立冲突,将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发生场域由现实世界复刻、孪生至虚拟场域,将虚拟场域的学习体验即时准确地反馈到现实世界,构建了全景化虚实相融的交互空间。在虚实相融的交互空间中展开红色文化育人,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可以获得“亲历在场”的实践感受,“实现思想创构、情感宣达、行为指向的同步与拟真”[4],一方面有利于推动红色文化育人的创新性表达和场景化叙述,另一方面有利于教育者深刻把握教育对象,在学习过程中的思想观念、价值立场和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动态和状况,充分体现高校红色文化行为规范和价值引领的育人优势。
2.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发展创设了具身沉浸的学习模式。传统高校红色文化育人主要依靠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载体,通过课堂知识教育与校园文化熏陶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进行,受主客体条件所限,育人过程往往呈现出重课堂教授、轻身体感知的现象。与“教”“知”相分离的传统方式不同,“具身沉浸”式的学习模式主张通过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使教育对象的意识、情感、触觉被充分调动起来全方位沉浸在教育场景中,育人形式从原有的“看到”“听到”跃升为“感受到”“体验到”,教育对象摆脱被单向灌输、被重复说教的消极状态,以具身沉浸式“第一人称”视角主动探索学习,积极互动交流,自觉地完成对红色文化知识的信息接收和行为转化。
(三)以数增效: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效果的精准提升
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效果反映了高校开展红色文化育人活动的具体结果及其实际效应,效果的好坏不仅是衡量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得失的标准,而且关系着如何“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5]。正是在这种效用尺度支配下,追求良好的育人效果,不断提升育人质量就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必然。数字技术的精准化特性,高度适配了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提质增效。通过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综合构建,推动育人过程可视性把控、教育问题即时性反馈,实现学情信息的精准化匹配和教学管理的精准化施策,促进红色文化数字化育人效能持续增强。
1.运用数字技术精准把握教育对象学情,满足个性化发展需求。让高校红色文化教育做到“因材施教”,可提升红色文化育人发展的个性化水平。当今时代,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趋凸显,个性突出、价值多元、追求多样等现实特征更加明显,把握人们思想动态的难度也越来越大[6]。传统的“以老师为中心”“大水漫灌”式教学思维,已经难以适应现今的实际情况,高校红色文化育人要真正取得成效,应该实现向“以学生为中心”“精准滴灌”的教学思维转变。通过数字技术收集分析教育对象在学习、工作、生活过程中生成的数字信息,搭建起多维度、全景式“数字画像”模型,深入了解教育对象的思想规律、行为动态、生活习惯和现实需求,秉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教育原则,对教育对象进行针对性指导和帮助,真正做到“因材施教”“量体裁衣”。
2.运用数字技术精准创设育人评价模式,提升育人决策的智能化水平。数字技术凭借强大的信息抓取、运算、分析能力,对教学过程进行全过程把控,精准创设育人评价模式,实现高校红色文化育人评价科学化和多样化发展。“人们的活动信息作为数据被收集起来,经过整合、计算、优化,重新反馈到现实世界,为未来更为有效的决策提供信息基础。”[7]育人评价是单次育人活动循环的终结点,同时也是新的育人活动循环的发起点,在此环节中,教育者对教学过程进行复盘总结、教育对象对教学问题进行集中反馈,深刻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优化流程,为下一次育人活动的开展作好准备,如此交替循环,从整体上提升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效能。
二、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潜在风险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8]数字技术亦是如此,其在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变革结构要素、重构内在关系带来全新发展动力和机遇的同时,也会滋生“数字依赖”“去中心化”“信息茧房”等顽症痼疾,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育人主体自觉性、淡化了育人价值引导力、分化了育人叙事的整体性,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稳定高效开展带来了风险和挑战。
(一)陷入“数字依赖”误区,弱化了师生主体自觉性
主体自觉体现了人内在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解放,是人对自身能动性和实践行为的自我意识[9]。高校红色文化育人作为一种塑造人、成就人的实践活动,教师是发起者、推进者和实施者,主导把控着育人教学的各个环节,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导主体;学生是参与者、经历者和受教者,制约、影响、反作用于育人实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体。在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活动中,师生主体自觉性是激发系统内生动力的关键要素,是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充分发挥师生双方的主体自觉性,才能最大限度发挥红色文化的育人功效。数字技术深度介入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发展,有效提升了育人过程的流畅性和实效性,使师生双方的实践诉求能在一定程度上高效、便捷地得到满足。师生双方容易对数字技术建立信任,并将所有问题的解决诉诸数字技术,由此陷入“数字依赖”的漩涡之中。在“数字依赖”漩涡的拖拽下,师生双方不再进行人文思考和实践探索,丧失了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主体自觉性特征,有沦为数字技术依附者的风险。
“数字依赖”下的“数字在场”“自觉意识缺场”,导致原本充满思想碰撞、精神交流、情感互动的红色文化育人活动,化约为一连串数字代码间的机械性流动。在数字代码构筑的“数字浪潮”中,师生双方的主体性逐渐迷失,主体地位逐渐让渡给“数字技术”,致使“教育活动本该有的意义和价值在大量数据符号交互的过程中被过滤和解构,师生也被视为缺乏自我意识和情感温度的个体存在”[10]。具体来说,一方面数字技术遮蔽了教师的自我意识。在数字技术的宰制下,教师往往会把复杂的育人过程简单化、把多元的育人要素片面化,将数字技术作为推动教学工作的唯一途径,形成了单向度的“技术合理”思维。渐渐养成“潜心教研不如算法推荐”“勤于探索不如网络搜索”的思维惯性,并进一步衍生出重情景构建、轻价值引领的“形式主义”,重信息收集、轻辩证否定的“拿来主义”,重数字指标、轻内涵积淀的“投机主义”等不良风气,无形之中消解了教师主体的自我意识,弱化了教师主体的教学自觉性。另一方面,数字技术遮蔽了学生的自我意识。作为“网络原住民”的大学生群体,数字空间适应能力较强,但价值分辨能力、自我约束能力较弱。如果过度依赖数字技术接受红色文化育人,深度沉迷于数字系统搭建的虚拟空间,那么数字浪潮将会侵吞人的理性认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分割边界被模糊化、扭曲化。伴随着大学生“数字人”特征的不断凸显,“现实人”身份日益淡化,致使他们原有的独立思考、自主决策、开拓创新的能力逐渐退化,导致大学生主体自我意识被遮蔽,主体学习自觉性弱化。
(二)引发“去中心化”现象,淡化了育人价值引导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11]由此可见,红色文化育人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这促使高校在开展红色文化育人时,更加关注大学生群体的理想信念、道德观念建设,彰显出强大的价值引导力。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每个人都拥有了“麦克风”,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制造者和发布者,信息流转样态呈现交互化、扁平化特征,原有的信息集约化生产和由内向外、自上而下的传输模式被解构,引发了信息传收的“去中心化”现象,严重冲淡了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价值引导力。
在数字社会交往日益“去中心化”的趋势下,碎片化叙事消解了宏大叙事的效力,追求“即时满足”取代了对思想的深度体验,各种思想潮流在数字空间中交织蔓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受到威胁,导致红色文化育人价值出现偏航。促生这种异相乱象的根源,首先在于资本裹挟下流量经济的盲目狂奔。“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12]在资本链条的驱使下,流量作为数字社会最为显著的产物,被资本赋予了实现价值增殖和扩张的使命任务。资本与流量的媾和,助推了流量经济的肆意狂奔,也催生了“流量为王”的时代观念。于是,“流量就是金钱”“一切为了流量”等观点大行其道,在这种喧嚣的氛围中,部分媒体为了“抓人眼球”博取流量,以“娱乐至死”的态度,把庄重严肃的红色文化变成商业价值的工具和空虚低俗的消遣,恶意抹黑英雄人物,亵渎红色文化场所,过度消费红色文化情怀,以及创作传播一些高级黑、低级红的影视作品,严重干扰了大学生的思维成长和价值塑造,弱化了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实际效果。其次是国内外敌对势力阴谋利用数字技术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近年来,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数字技术逐渐成为一些国内外敌对势力操纵舆论、进行价值观渗透的重要工具。这种以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推荐为依托的价值观渗透新手段,采取分众对待、精准投喂、柔性宣传等隐秘方式,有组织、有预谋地设置议题、制造负面舆情,企图动摇社会认同基础、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我国社会进行西化、分化。尤其是针对青年大学生的“洗脑”宣传,别有用心者利用算法推荐来散播谣言、扭曲事实、煽动矛盾、刺激情绪等,使其视野窄化、思想僵化、观点极化的风险悄然增加,这也使得高校在开展红色文化育人时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现实考验。
(三)衍生“信息茧房”效应,分化了育人叙事的整体性
高校在开展红色文化育人实践时,要想把道理讲深入、讲透彻、讲鲜活,需要连贯严密的整体性叙事作为保障。只有坚持全员在场、视角全面、逻辑严谨的整体性叙事方式,才能将红色文化的历史脉络、理论特色、精神旨归、未来道路阐述清楚,才能真正让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数字技术衍生的“信息茧房”效应,给红色文化育人XNMA7oMdH33WDyQchICxcw==的整体性叙事带来了风险。所谓“信息茧房”效应是指在网络社会,人们是以自己的兴趣为导向,去选择摄取信息的内容和方式,“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13]长此以往,人们仿佛像受困于“茧房”般,桎梏于单一化、同质化的信息之中。在信息茧房效应的作用下,人们接收的都是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投喂,从而形成了思维习惯的自我圈养和认知维度的自以为是,隔绝了不同信息资源间的交汇作用,阻断了不同用户群体间的相互影响,从主体结构和作用形式上严重分化了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叙事的完整性。
在具体育人实践中,“信息茧房”分化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叙事完整性的具体表现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信息茧房”的“过度适配性”造成了认知视野的窄化。“信息茧房”效应是数字技术与用户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产生逻辑来自数字系统通过信息收集和分析,实现对目标用户的身份特征、行为习惯、兴趣爱好、现实需求等方面的精准画像,从而实现资源供给的靶向适配。一定的适配性是数字技术实现智能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显现,可以让用户感受贴心和暖心的数字化服务,可以使用户在纵向上加深对某一方面信息的印象。但过度的适配性意味着用户过分沉浸于同质化的信息,阻绝了异质信息的摄取,久而久之,将会导致人的认知视野的窄化。青年大学生群体正处在人生的“拔节孕穗期”,需要接触不同领域的知识和信息,积极拓宽自己的认知视野,培养多元全面的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如果数字化实践中,只接收特定信息的主体发布的信息,只接受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内容,那么将逐渐陷入闭塞、局限的认知境地,消融大学生们探索未知、开拓创新的能力。其二,“信息茧房”的“信息割据性”造成了网络社群的极化。随着“信息茧房”效应的蔓延,互联网用户很容易因兴趣相投、观点一致结合在一起形成固定圈层,导致了网络社交生活的圈层化现象。在圈层化的社会生活中,信息的流转出现了“割据性”特征,即每个圈层内部拥有共同的关注焦点和话语体系,信息交互较为频繁,但不同圈层之间处于相互隔绝、彼此疏离、不相往来的状态,信息资源不再是“过点成线,连线结网”的立体化流转,而是被割据在一个个圈层化的“孤岛”中。圈层内充斥着同质化的立场和观点,成员所持有的单一性认知被相互间自我确认和自我强化,在缺少纠偏机制和合理建议的情况下,逐渐发生非理性偏转,最终有引起整个网络社群价值立场极端化的风险,正如哲学家凯斯·桑斯坦所说,“如果互联网上的人们主要是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进行讨论,他们的观点就会仅仅得到加强,因而朝着更为极端的方向转移”[14]。
三、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红色文化育人的优化路径
在新的历史方位下,运用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既是持续推进育人数字化发展的积极探索,也是拓展红色文化育人渠道、提升红色文化育人效果的现实需要。加快推进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有效化解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是一项动态、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立足实际情况,坚持问题导向,在实践中注重价值引领、完善制度建设、提高数字修养,不断夯实数字赋能基础、完善数字赋能保障、增强数字赋能动力,奋力打造高校红色文化数字化育人新样态。
(一)注重价值引领,夯实数字赋能基础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发展的过程,不是两者之间的机械式叠加、静态型复合,而是数字技术在“育人为本”的主导思想引领下,对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结构、方法、过程等方面进行的全方位升级和整体性重塑。这一过程是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共同制约下进行的,其中,工具理性关乎方法、效率问题;价值理性关乎方向、意义问题。要想使整个过程取得圆满效果,就必须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这就要求高校红色文化育人不能被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导向所绑架和统率,而是要让数字技术在价值理性的统摄下为其服务和增能。因此,只有注重价值引领,才能为数字赋能实践明确目的和追求,才能夯实整个数字赋能过程的开展基础。
一是要坚持育人为本原则,发挥数字技术的正面效应。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绝不是为了展示现代数字技术的“无所不能”,也不是为了追求育人发展的“领异标新”,其使命任务在于运用红色文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其目标指向依然是为党和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这个角度上看,数字技术是工具,是手段,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和行为规范育人是本质,是核心。因此,无论数字技术如何变化发展,教育都应该坚守育人为本的原则,紧紧围绕学生,关心学生,服务学生。在育人为本原则的统摄下,工具理性促进价值理性的发扬,价值理性指引工具理性的发展,技术逻辑与育人规律之间的矛盾不断被解决,个体沉浸在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信念之中,逐渐挣脱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思维束缚,全面提升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彰显人的自觉性、能动性和自为性。围绕“现实人”构建由实到虚、由虚返实、虚实结合的实践进路,有效抑制信息科技的异化现象和技术主义的僭越行为,促进了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数字化转型中形式与内容、本质与现象的和谐发展。
二是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哈贝马斯提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揭示了当代西方科学技术这种工具理性已经变为价值理性统治人、奴役人的方便的工具或者‘一大帮凶’”[15]。当今时代,国际国内利益格局深刻变革,各种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数字空间中的高校场域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最前沿,能否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6]因此,这要求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政治清醒,敏锐洞悉敌对势力“借助数字技术不断盘剥、腐蚀和侵占网络空间,意在对我国的意识形态进行‘殖民’”[17]的险恶用心。在实践中,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主流价值、主流文化占据数字空间话语高地,用红色文化中镌刻着的红色基因、映现着的英雄气概、饱含着的奋斗精神吸引人、感染人、引领人。主动设置议题,加强舆论引导,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由“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模式转变,不断提升斗争意识和斗争策略,与各类错误思潮和敌对行为作斗争,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二)加强制度80dda5f1a87d54fa2ec562b384c534316c03f513ad1a576f3abb5d8c0ae76779建设,完善数字赋能保障
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是确保系统运行并充分发挥效能的必要条件和保障措施。数字技术与高校红色文化育人之间的融合互动是一项复杂系统,且正处于起步探索时期,因此要特别重视制度机制的规划和建设。只有在良好制度体系的引导规制下,才能使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在数字化发展中,突破理念固化的思维藩篱,汇聚多方能量,充分激活红色文化资源的创新活力、要素潜能、发展空间,消解数字歧视、数字黑箱、数据滥用等异化现象,努力弥合各种因素导致的数字鸿沟,营造风清气正、规范有序的数字生态环境,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提升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效果。推动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道德观念、准则与规范,克服由于技术黑箱、数据泄露、算法歧视等所带来的数字社会风险,引导受教育者形成良好的行为品性、法律意识、道德责任,化解交往过程中的“信任”危机,助推建设和谐社会。
一是要坚持全局谋划,强化顶层设计。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发展是一项需久久为功、持续用力的事业,面对新的形势和现实挑战,应该站在全局角度进行战略谋划,强化顶层一体化设计,绘就科学发展蓝图,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实现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要紧紧围绕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追求、实施方法等方面进行前瞻性思考和整体性规划,明确发展方向、任务举措、关键要素、难点关隘,统筹好保障支持、组织协作、职权责任,筑牢系统性推进的“四梁八柱”;要积极争取项目发展和专项资金支持,强化数字化技术供给,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开放共享的红色文化育人数字化平台,加强数字资源的整合互通,既要进一步扩大数字化覆盖的区域广度,也要兼顾不同主体、不同要素的实际状况,最大限度弥合赋能过程中横向上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和纵向上某些环节、某些地区发展不充分的现象。
二是要完善制度法规,促进规范管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加强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18]数字网络空间的隐匿性、多元性、复杂性等特性,导致行为溯源困难、安全漏洞频出、风险难以确定和管辖权分散等固有缺陷。但是,数字空间终究不是法外之地。坚持底线思维,不断完善制度法规是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确保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红色文化育人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关键要素。从整体出发,一方面,要着力完善数字运行管理制度。通过完善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操作流程、技术应用、平台运营、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制度化建设,加强对信息生产、信息推荐、信息流转过程的宏观调控和价值引导,建立全链条多层次立体化的治理体系,坚持源头防范、防控结合、标本兼治,着力净化网络环境,倡导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另一方面,要着力完善数字安全防范制度。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保障数字安全不仅关乎国家整体安全,也关乎各项事业的兴衰成败。有效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数字化发展,必须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构建纵深呼应、上下联动、人技协同的一体化安全防护体系。压实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网络安全技术设备建设,加强重点领域的数据安全管理。规范各数字平台采集使用学生和教师个人信息行为,严厉打击各类盗取、侵犯个人隐私的违法犯罪活动,打造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的工作格局,切实形成保护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的工作合力。
(三)提高数字素养,增强数字赋能动力
马克思指出:“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9]具有实践能力的人是社会生产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类所具备的素养能力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在数字技术发展持续迈向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提升人的数字素养,促使个体能够深刻认识、熟练掌握并能自觉运用数字技术优化工作逻辑、创新育人场景、重塑育人秩序,为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发展注入新动能。切实提升个体的数字素养,需要聚焦现实情况中的机遇和挑战,依据不同的群体特征分众施策,不断增强个体在数字化育人环境中的适应性和创造性。
一是要着力提升大学生的数字素养。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信部、人社部联合印发的《2024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明确要求,“我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20]高等教育承载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使命任务,是青年人才培养和提升数字素养的主阵地,也是一个社会数字发展能力和潜力的关键标志。高校红色文化育人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要素,加强大学生数字素养建设,不仅可以实现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发展的效益最大化,而且能够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打好底层基座。因此,高校应该从价值、思维、技术、实践等多个维度入手,通过打破专业、学科壁垒,丰富数字资源供给;加大原理剖析和案例复盘力度,提升数字思维能力;加强基础建设投入和专业课程引导,创设良好的数字实践环境等方式不断提高大学生数字素养。随着数字技术与红色文化资源的融合交汇愈加深刻,大学生只有具备坚持科技伦理底线,适应数字化环境与发展、深刻理解数字运行逻辑、积极应用数字技术解决现实问题、自觉锻造理性思维和发展胜任力的数字素养,才能够在数字环境下将红色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够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审慎辨析资本主义的当代形态,形成对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力。
二是要着力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教师作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目标的执行者、育人内容的实践者、育人质量的捍卫者,是整个高校红色文化教学的主导力量,教师自身的数字素养情况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成长。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是育人数字化发展进程中提高教学效率、改善育人效果、增强教育软实力的坚实支撑。所谓“教师的数字素养”,是指“教师适当利用数字技术获取、加工、使用、管理和评价数字信息和资源,发现、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优化、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活动而具有的意识、能力和责任。”[21]因此,在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发展的过程中提升教师数字素养,首先,要坚持辩证思维,提升数字化意识。通过集体培训或者专题学习等方式,一方面使教师群体能够突破传统教学的思维定势,以一种更为积极、自信的态度拥抱数字技术;另一方面,也要培养他们时刻保持自主思考,随时可抽身于数字世界之外的思维意识,避免陷入数字钳制和驯服漩涡。其次,要突出目标指引,提升数字化能力。紧紧围绕增强高校红色文化教学实效性这一目标,加强教师群体对数字技术性能、特点、应用以及发展趋势的理解,系统掌握数字育人必备技能。最后,要坚持价值导向,提升数字化责任。引导广大教师进一步系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为准则,牢固树立法律意识和思想道德观念,持续提升数字社会法律素养与思想道德修养。同时,引导大学生群体正确参与数字社会生活,培养健康向上的数字生活习惯,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数字技术赋能行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忠家.红色文化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5.
[2]傅维利,傅博.把握数字技术融入教育实践的积极方式[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02-07(07).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
[4]冉莹雪,王建红.元宇宙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场语境、运用空间及理性审思[J].理论导刊,2023(08):123-128.
[5]习近平.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奋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22-08-19(01).
[6]骆郁廷,肖天乐.算法推荐视域下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J].思想理论教育刊,2023(10):109-107.
[7]王天夫.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21(12):73-88,200-201.
[8]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
[9]王淑娉,李艳.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体自觉[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35(05):111-114.
[10]陈薪旭,叶飞.教育数字乌托邦的风险及其防范[J].大学教育科学,2024(02):59-66.
[11]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J].共产党员,2021(22):4-6.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9.
[13]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
[14]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M].尹弘毅,郭彬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03.
[15]张志丹.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63.
[16]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93.
[17]徐丽燕.数字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21):76-79.
[18]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52.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0.
[20]金歆.2024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N].人民日报,2024-02-23(01).
[21]中华人民共和共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的通知[EB/OL].(2023-02-14)[2024-03-06].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302/t20230214_1044634.html,2023-02-14.
(责任编辑 文 格)
Value,Risk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Red Culture
Education Enabl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FAN Yu-bo1, FAN Lian-sheng2
(1.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0,Hubei,China;
2.School of Marxism,Sanming University,Sanming 365004,Fujian,China)
Abstract:Digital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big data,artificial intelligence,blockchain,and cloud computing are triggering new changes in ways of thinking and education.In the face of the tide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digital technology should be fully used to empower the red culture education work in universities,and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ontent of red culture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methods,and the accurat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effects by creating development programs of “improving quality with numbers”,“increasing efficiency with numbers” and “gathering energy with numbers”.At the same time,in the process of enabl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d culture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digital technology will also breed undesirable phenomena such as “technology dependence”,“decentr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cocoon”,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weaken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education subject,weakens the value guidance of education,and diverges the integrity of the education narrative,seriously hindering the stable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red culture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Therefore,in practice,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value guidance,improve system construction,and digital cultivation,constantly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digital empowerment,improve digital empowerment guarantee,and enhance digital empowerment motivation,resolutely prevent and resolve various challenges,and strive to create a new pattern of digital education of red culture in universities.
Key words:digital technology; red culture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