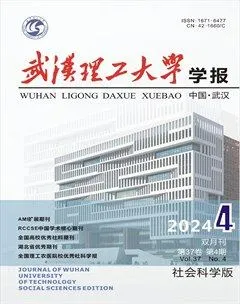英国诗人拜伦在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形象演变
摘 要: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形象在中国先后经历晚清民初革命思潮、个体本位启蒙思潮、群体本位左翼思潮等阶段,显现出“豪侠”“摩罗”“浪漫战士”的鲜明形象意涵。从“豪侠”拜伦之重侠义内涵的形象特质征用,到“摩罗”拜伦之情感主体性高扬的启蒙立场开拓,再到“浪漫战士”拜伦之兼具情感主体个性与革命精神认同的现实遭际,拜伦承担了介入中国社会现实的形象符号功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作为精神界战士的人格想象,其代表的社会叛逆者情感主体的形象,深深根植于20世纪中国启蒙、革命诗学的历史土壤之中。
关键词: 拜伦;豪侠;摩罗;浪漫战士;多维形象
中图分类号: I209;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4.04.013
出身于英国伦敦没落贵族家庭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勋爵(Lord Byron,1788-1824年),自小跛脚的身体疾病和备受欺辱的成长氛围,让他善于洞察虚伪欺诈,也培养了他勇于反抗的精神品质。而暴戾黑暗的成长体验,也使拜伦更加向往“罗曼”(romantic)情调的自为诗意情感境界。他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异教徒》(The Giaour)、《唐璜》(Don Juan)等浪漫主义诗作,更是具有深远世界影响的经典之作。受众通过诗中浪漫主义诗歌语言形式的艺术表现力、社会叛逆者群像的情感力量、反抗专制及歌颂爱和自由的呐喊高歌等,深刻感受到拜伦其人其诗可贵的战士形象魅力。反过来,拜伦身份与其诗歌间颇具反差感的艺术张力,具有强烈的形象符号意义,这也促进了拜伦及其诗歌形象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接受。
20世纪初,处于严重民族存亡危机中的晚清中国,政治革命潮流正盛。拜伦因其精神界战士的人格形象与抗争精神、民族革命的政治意识与传奇色彩,以及其诗浪漫主义的诗歌品质与情感主体,深深吸引着中国文坛。换句话说,苦难深重的中国语境迫切地需要革命,需要具有强力精神的、近乎浪漫魔力色彩的革命英雄形象鼓舞自身,而拜伦其人其诗散发出的浪漫主义诗人英雄气质,则恰好契合了这一需要。有学者称:“中国文坛对拜伦感兴趣的不是诗人拜伦而是反抗斗士拜伦,感兴趣的不是拜伦诗歌而是拜伦本人。”[1]这意味着,拜伦形象在20世纪中国革命语境中的传播接受之旅,并非是简单的浪漫主义诗人诗艺的再现,而是夹杂着中国本位的革命英雄形象想象的再创造之旅。
一、豪侠:晚清民初革命思潮中的拜伦诗人形象
甲午战后“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民族危机,尤为迫使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掀起政治改良、政体革命的思潮。英国贵族诗人拜伦为希腊独立而战,不惜牺牲自我的英雄魅力,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豪侠形象、晚清民初革命呼唤的英雄形象之间,产生了古今交汇、中西调和的精神遇合。基于革命思潮的动员目的,晚清民初知识分子对于拜伦其人其诗的推介与形象塑造多为豪侠形象,具有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况味。
晚清“诗界革命”以黄遵宪“要不失为我之诗”的诗体改革为标识,诗人之“我”的个人本位视野,开始从日益僵化、教条的古典诗歌传统中高扬起来。尤其是晚清“诗界革命”中“少年革命者‘狂狷’的人格、反叛意识及暴力复仇”[2]的革命诗歌书写,凸显了诗歌思潮语境对于诗人革命者强力形象的渴盼。作为“诗界革命”之组织者与理论家的梁启超,1902年在《饮冰室诗话》中提出“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的个人革命思想。同一年,他在《新小说》第2号上推介英国诗人拜伦,称赞拜伦是“英国近世第一诗家也,其所长专在写情。所作曲本极多。至今曲界之最盛行者,尤为拜伦派云。每读其著作,如亲接其热情,感化力最大矣。拜伦不特为文家也,实为一大豪侠者。”[3]这是诗人拜伦形象首次在中国的塑造与传播。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当革精神”的理念中,援引域外“拜伦派”(英国浪漫派)诗人群体中拜伦之“感化力最大”的精神形象力量,并将其放置在“豪侠”这一中国文学传统的浪漫想象之中。
诗人拜伦豪侠形象在中国的传播接受,是在具体的诗歌翻译环节中进行的。梁启超在1902—1903年连载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插叙了拜伦《异教徒》《哀希腊》中的两部分诗歌节选,其中的《哀希腊》更是引起了诗人拜伦在中国的接受热潮。《哀希腊》是拜伦长诗《唐璜》中的插曲,作于他奔赴希腊参与民族独立战争之前,全诗慷慨激越,充满着鼓励希腊人奋起的诗意情感。《新中国未来记》以主人公李君、黄君归国后,在旅顺旅馆旁听隔壁陈君吟诗的情节,插叙了拜伦诗歌的译介活动。小说以原诗、译诗列举的方式,将拜伦“The isles of Greece”(《哀希腊》)译出:
(沈醉东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娇。“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神名)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如梦忆桃源)玛拉顿后啊山容缥缈,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如此好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4]5
梁启超以“沈醉东风”“如梦忆桃源”的传统曲牌,对拜伦《哀希腊》的诗歌声音进行歌诗传统改造。就译诗语言而言,梁启超本着“以曲本体裁译之,非难也”[4]5的翻译理念,在大体用韵的“古风格”白话歌诗语言上,融入大量音译西化名词(“撒芷波”“德罗士”“菲波士”)和白话虚词(“咳”“啊”“了”)等,译诗语体显现出欧化与改良白话的演进趋向。而这种歌诗传统声音框架内的译诗语言革新,插叙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整体形成了互文的文本语境。与其说拜伦“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毋宁说其潜叙事亦存有一层拜伦向“新中国未来记”的召唤结构。此时拜伦“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的肯定语气,便不仅在显叙事层面,指向他投身希腊民族解放与抗争奴隶境遇的英雄气概,还在潜叙事层面暗涵中国革命语境中的救国求存之志。这也意味着,诗人拜伦在与中国切身的革命精神需求相结合的形象接受之旅中,如他所咏的“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的豪言,如同文中问号向感叹号的转进,犹如中国化豪侠精神诸如侠义、尚勇、牺牲等。
《哀希腊》成为早期拜伦诗人形象在中国塑造的诗歌桥梁。梁启超之后,南社诗人马君武在风雨如晦的幽夜,以“裴伦哀希腊,今吾方自哀之不暇”[5]的迫切意绪,首次完整译介了拜伦《哀希腊》全诗。“吁嗟乎!闲立试向波斯冢,宁思身为奴隶种”的七言诗体,其间英雄长叹、为民请命的文学意味,呼应着马君武对拜伦“英伦之大豪也,而有大侠士也,大军人也,哲学家也,慷慨家也”[6]的豪侠形象想象。其后苏曼殊的五言诗体,胡适的离骚体译诗,都在中国诗歌传统的表意系统中强化了拜伦的豪侠形象。
诗人拜伦的豪侠形象不仅表现在译诗的文学表达上,更在介入中国政治现实的能动作用中激活。1913年7月21日,苏曼殊在《民立报》发表《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他以“昔者,希腊独立战争时,英吉利诗人拜伦投身戎行以助之,为诗以励之,复从而吊之曰:Greece!Change thy lords,thy state is still the same;Thy glorious day is o’er,but not the years of shame……”[7]在“讨袁檄文”的政治言说中,“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谋人家国且功成不居的“侠义”品质,介入了以“希腊”自况今日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可以说,纸墨中的豪侠拜伦形象开始介入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现场,具有了具体的历史的形象活力,获得了较广泛的传播与接受。
1916年,刘半农在与苏曼殊关于“豪侠”拜伦的通信往来中,传记式地赞誉拜伦“中年清温而明洁,妍妙而深远,是富于美情也。其末年则庄严而劲烈,雄奇而伟俊,是富于侠魂也。”[8]兼具“美情”与“侠魂”的拜伦豪侠形象,在辞采华丽的文学语言修饰中定形,在语言的想象空间中获得符号意蕴的无限延伸。相较于拜伦诗人豪侠形象为民请命、投身民族革命的宏大想象,苏曼殊等少数知识分子亦将这一豪侠诗人形象,与其具体、真实的人生足迹贴合。“拜轮生长教养于繁华,富庶,自由的生活中。他是个热情真诚的自由信仰者;——他敢于要求每件事物的自由——大的小的,社会的政治的。……他一生的生活、境遇与创作,都缠结在自由与恋爱之中。”[9]不同于中国近代多数知识分子出于塑造“革命”拜伦形象的需要,而有意遮蔽拜伦之于传统道德具有惊世骇俗影响的抗争行为,“情僧”苏曼殊予以正面推介[10]。在他的笔触中拜伦贵族的出身、自由信仰的文化政治信条、坦诚内心的恋爱追求,使得豪侠特征变得生动形象、形神兼备。
在晚清民初政治革命思潮中,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等看到了拜伦身上鲜明的诗人“豪侠”气概。他们认识到拜伦的贵族出身,和他跨越国界的、不惜牺牲自我的民族独立政治意识,及其《哀希腊》等诗歌文本中豪侠形象魅力,这些都负载着中国式“豪侠之气”的想象与“大豪侠”革命者的现实呼唤。进言之,晚清民初“豪侠”的拜伦诗人形象塑造,实质上指向中国文学传统的接受心理与政治革命的现实需求。知识分子对于拜伦形象的想象与塑造,更多的是基于拜伦个人精神气概,具有某种程度的“革命征用”色彩。
二、摩罗:个体本位启蒙思潮中的拜伦诗人形象
“摩罗”一词“系梵文译音,指佛教传说中专事破坏的恶魔。”[11]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将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海盗》等诗歌作品中具有反抗精神的社会叛逆者群像誉为“摩罗”,其“恶魔”般力量譬喻的“摩罗精神”,指向欧洲诗坛的积极浪漫主义思潮。同时,鲁迅在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奇、裴多菲等“摩罗诗派”的群体中,突出拜伦“诗宗”的地位。究其根底,基于启蒙立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穿过拜伦革命诗歌的话语资源,更青睐拜伦及其诗歌形象折射的“精神界战士”与叛逆者形象对于个体启蒙的形象意义。
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对于拜伦“摩罗诗人”形象的叙述逻辑看,他先从拜伦“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抗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己”[12]68出发,揭示被御用文人讽为“恶魔”的拜伦之抗争精神的启蒙影响。继而,鲁迅在哲学思索层面指出中国老子哲学的“无为而治”在进化论世界的不适,他推崇摩罗诗人的“强者”哲学。由是在诗学层面,“迨有裴伦,乃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之声。平和之人,能无俱乎?于是谓之撒旦。”[12]75鲁迅希冀以拜伦“刚健抗拒破坏之声”,改造惯于“平和”的国民性。他详细介绍了拜伦的一众诗作,尤其是《曼弗雷德》《该隐》《天与地》,使“精神界战士”的拜伦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裴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盗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也。”[12]81在鲁迅心中,拜伦是兼具反抗上帝的自由追求与压制民众的专制基因的,这也是其复杂形象的写照。最后,鲁迅也赞扬了拜伦投身希腊独立运动的抗争行为,且其对世界范围内普希金、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摩罗诗人的诗学影响。
质言之,鲁迅肯定拜伦反抗天帝行为背后的“精神界战士”的强者形象意蕴,也警惕其强力所带来的压制民众的反面形象。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鲁迅笔下的拜伦,则是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统一的拜伦,但个性扩张导致对他人自由蹂躏时,鲁迅就止步了”[13]。这正反映了鲁迅对于“摩罗”形象的辩证思考,其“恶魔性”在开启民众“精神界战士”之智时,也许会走向自由的对立面。因而,鲁迅笔下开启的“摩罗诗人”拜伦形象,突破了豪侠拜伦形象单向度的侠义内蕴,更添益了“强力”精神对于个体启蒙的辩证反思,意即摩罗精神既有可能增强个人的主体能动性,也有可能让人为“强力”所异化,继而成为专制者的危险。此后,在鲁迅开辟的个体本位的启蒙立场上,“摩罗诗人”拜伦形象迎来了在近代中国的接受高潮。
1924年4月22日,拜伦逝世一百周年祭,掀起了拜伦在中国的第二次译介热潮。不同于晚清民初以《哀希腊》为中心的译介热潮,《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所刊载的拜伦专号,拓宽了拜伦诗人、诗歌、诗论的系统译介,丰富了诗歌镜像中拜伦的多元形象。《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四期推出的“诗人拜伦的百年祭”专号上,署名“西谛”(郑振铎)在“卷头语”中,以诗的错落分行形式赞叹道:“我们爱天才的作家,尤其爱伟大的反抗者。/所以我们之赞颂拜伦,/不仅仅赞颂他的超卓的天才而已。/他的反抗的热情的行动,其足以使我们感动实较他的诗歌为尤甚。/他实是一个近代极伟大的反抗者!/反抗压迫自由的恶魔,/反抗一切虚伪的假道德的社会。/诗人的不朽,都在他们的作品,而拜伦则独破此例。”[14]郑振铎开首以诗歌的形式为拜伦的形象定调,即“反抗压迫自由的恶魔”诗人,也即摩罗诗人形象意义的重申与强化。他在其后的《诗人拜伦的百年祭》一文中,将对于伟大诗人潜隐在作品中的全人格,和由伟大人物的事迹(行动)牵引的热情感受,融为对于拜伦的崇慕之感。质言之,郑振铎肯定了摩罗诗人拜伦在诗歌精神与现实行动上的强力性。
相较于百年祭系列文章对拜伦摩罗诗人强力形象的积极塑造,沈雁冰(茅盾)则在《拜伦百年纪念》中,开篇点明“两个拜伦”现象:“一个是狂纵的,自私的,偏于肉欲的;一个是慷慨的,豪侠的,高贵的。”在介绍拜伦的诗学转变旅程后,文末茅盾评价道:
中国现在正需要拜伦那样的富有反抗精神的震雷暴风般的文学,以挽救垂死的人心,但是同时又最忌那狂纵的,自私的,偏于肉欲的拜伦式的生活;而不幸我们这冷酷虚伪的社会又很像是制造这种生活的工厂。我但愿盲目的“拜伦热”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现在纪念他,因为他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诗人,是一个攻击旧习惯道德的诗人,是一个从事革命的诗人;放纵自私的生活,我们,青年是不肯做的,正像拜伦早年本不肯做,而晚年——虽然他的生活是那样短促——是追悔的。[15]
茅盾一方面赓续了拜伦之“富有反抗精神的震雷暴风般的文学”,对于中国“垂死的人心”抑或说国民性的疗救效用;另一方面,他也警惕青年拜伦摩罗性形象中的消极面,即“狂纵的,自私的,偏于肉欲的”恶魔性质。他担忧中国“冷JIxOVSgolwmy5fFr66gYQg==酷虚伪”的社会环境,与拜伦热泥沙俱下的接受热潮遇合,会走向摩罗精神启蒙的对立面,即过度高扬情感主体的能动性,而陷入“放纵自私的生活”。实际上,从鲁迅开辟的摩罗拜伦诗人形象论,正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唤醒铁屋沉睡国人的呐喊声。他们从拜伦诗歌话语中探析到了其“恶魔性”的双刃性,怀抱着“猛药沉疴”的心态,既高扬其反抗精神的强力形象,增强国人的主体能动意识,又如茅盾般警惕个体启蒙进程中“非理性”的异化。
从情感主体的召唤视角来看,基于个体启蒙本位的知识分子,希冀通过摩罗诗人拜伦形象的塑造,最大程度激发国人的反抗主体意识。而从摩罗诗人拜伦形象呈现的积极浪漫主义土壤来看,梁实秋也于1926年的《拜伦与浪漫主义》一文中,塑造了浪漫主义视野的摩罗拜伦形象。他认为浪漫主义的精髓,便是“解放”二字,而拜伦就代表了一种极端的反抗精神,“拜伦的一生可以说是除了争自由没做别的事,他的诗歌是代表全人类至圣至神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呐喊。浪漫诗人全是注重自我的表现,而自我范围之广,没有再比拜伦加甚的。”[16]在浪漫主义文学表现与情感主体“解放”的延长线上,梁实秋将摩罗诗人拜伦的形象拟声为“一声惊天动地的呐喊”,以唤醒国人沉睡的主体意识。
在个体本位的启蒙思潮中,鲁迅、茅盾等知识分子接续了豪侠拜伦诗人形象的侠义内涵,但将其知识结构放置于现代积极浪漫主义的视域中加以理解。他们青睐拜伦心理结构与诗歌表现之间的摩罗性,其恶魔般的极端的反抗精神,在国民性改造的启蒙立场中具有积极作用。然而,作为猛药治沉疴的方式,他们也认识到情感主体能动作用的极度泛滥,会使恶魔性的消极面泛滥无涯。因而,在他们基于个人本位的启蒙探照中,拜伦作为摩罗诗人的驳杂形象得以构建。
三、浪漫战士:群体本位左翼思潮中的拜伦诗人形象
1927年大革命失败,旧中国阴暗恐怖的政治空气使得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陷入低谷。作为西方积极浪漫主义“诗宗”的拜伦形象,在中国接受语境中也遭遇冷遇。1928年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兴起,1930年代阶级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等左翼思潮的兴盛,均与出身贵族,高扬浪漫主义情感主体大纛的拜伦勋爵形象滋生龃龉。然而我们细究1930年代出版的译诗集、新诗集现场,有关拜伦译诗的数量仍蔚为大观。“这些译作不仅远离了前一时期人们有意将拜伦及其作品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更呈现出一种媚俗倾向”[17],拜伦大量的私人性情感得到充分译介、言说与消费。由此观之,1927—1949年在中国的拜伦形象,因译介与读者群的关注点、趣味及爱好不同,进入了多元化形象塑造的阶段。
1929年11月,左翼诗人殷夫曾以诗歌宣言:“Romantic的时代逝了,/和着他的拜伦,/他的贵妇人和夜莺……/现在,我们要唱一只新歌,/或许是“正月里来是新春”,/只要,管他的,/只要合得上我们的喉音。”[18]其后,殷夫以工厂、童子团的群体视野结束诗篇。可以说,殷夫创作的这首《Romantic的时代》具有时代典型意义,围绕“Romantic的时代”“贵妇人”“夜莺”等意象展开的诗人拜伦,使得此前时代塑造的“豪侠”“摩罗”等形象意涵瞬间消解。而“我们的喉音”本位视野中对立的“他的拜伦”,诗歌言语间泾渭分明的阶级界线,使得工厂、童子团等无产阶级群体本位立场,彻底以断裂姿态与拜伦形象进行了切割。这也预示了此后基于群体本位的左翼思潮,对拜伦“反抗战士”基本形象的解构和弱视。如1944年任访秋所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章第三节有关浪漫主义派的论述中,他赞同穆木天对王独清的诗歌批评,即王独清“受拜伦的影响最深”,仅在内容上便显露出“(一)对过去没落的贵族世界的凭吊;(二)对现在都市生活之颓废的享乐的悲哀”[19]128。总之,王独清“在过去同贵族的浪漫诗人相结合(缪塞、拜伦)而在现在同颓废派象征派诗人起了亲密的联系”[19]128。再如1948年7月,史美钧的诗人论《衍华集》中,分析前述王独清因出身破落之家,“所以特别追恋于往昔,叹息,吟哦,随时随地暴露出这种倾向,渐次形成极度病态的人生态度”,而这也“很受拜伦、缪塞等贵族的浪漫派的影响”[20]。在这些诗论背后,诗人拜伦所联结的“贵族的浪漫”勾连着“病态的人生态度”,构成负面的形象符号。
然而,诗人拜伦在中国的传播,固然与特定的社会政治思潮、文化启蒙思潮的助推有关,但归根究底是因其内在的浪漫主义诗人品格与诗歌意蕴。20世纪30年代以降的群体本位的左翼思潮主潮,尽管从主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看,高扬“我”的情感主体能动性的诗人拜伦,已与中国语境中强调“我们”的集体本位现实主义文学话语意志产生裂隙。但在具体诗人的实践进程中,“我”与“我们”的情感主体所指并非决然对立。
1930年张竞生译拜伦的《多惹情歌》,今译为《唐璜》。拜伦以西班牙贵族青年唐璜为主人公,其冒险、艳遇和各种经历,尤其是与海盗女儿海蒂的牧歌式的真诚爱情颇令人动容。后历经波折与变故,唐璜又成为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的宠臣,在出使英国后便周旋于伦敦上流社会的名士淑媛间。其后的诗歌叙事因拜伦的辞世而中断,但按拜伦的设想,唐璜将在漫游欧洲中参与法国大革命,以巴黎街头战斗而亡的方式结束,让唐璜成长为一名“战士”。对此,张竞生从数年前他在广州与人辩论“恋爱与革命”问题谈起,他认为“这两事可以一致并进的。恋爱是情义的表示,革命也是情义的表示”:
他好革命,尤富于爱情。他爱妻、爱女、爱友人、爱一切的妇人,他推广其情爱以至于爱山水、爱明月、爱一切的自然,以至于爱狗、爱马、爱泅水,与爱一切有意义的战争。
人类幸而是情感的动物,因其情感大小不相同,所以其所作的文章功业遂而多寡有差异。凡富于情感者,其发挥为诗文的必极繁丽,而建设为功业的也必极宏大[21]。
在张竞生眼中,“恋爱”与“革命”皆是“情义的表示”,二者并无矛盾。而拜伦之于爱情、革命、有意义的战争背后,是他“情感”丰满的形象写照。拜伦在实现博爱的过程中,充满了情感的扩张与反抗的功业,也是其“浪漫战士”诗人形象的有力证明。不独张竞生对于调和个人爱欲与革命情义于一体的战士拜伦形象的理解,左翼浪漫主义诗人蒋光慈更是用自身的诗学信念与实践,演绎了“浪漫战士”拜伦形象在中国之真实境遇。
拜伦是19世纪英国积极浪漫主义“诗宗”,蒋光慈是20世纪中国左翼浪漫主义的标识人物。有研究者比喻:“蒋光慈则是在寻求民族前途的时代旋律里和革命文学的开拓探索中发现了拜伦的价值,从而立志成为另一个中国的拜伦。”[22]这言明了拜伦与蒋光慈在精神内蕴与诗人气质层面跨越时空的形影相惜。
早在1924年旅俄归来后入党的蒋光慈,热情地写就《怀拜轮》一诗,“拜轮啊!/你是黑暗的反抗者,/你iq0gjFc00saebhMVquMYoSjK8yZL00t7R9rKN6HzBtM=是上帝的不肖子,/你是自由的歌者,/你是强暴的劲敌”,“拜轮啊,/十九世纪的你,/二十世纪的我”[23]362-363。言语间写满了蒋光慈对拜伦“黑暗反抗者”“上帝不肖子”“自由歌者”“强暴劲敌”的浪漫战士形象之认同,并以告白的形式自况。最典型的如该时期蒋光慈仿照拜伦《哀希腊》所写的《哀中国》,他以“我不过是一个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口吻,情感激越地表达了“我今枉为一诗人,/不能报国当愧死!/拜伦曾为希腊羞,/我今更为中国泣”[23]393的意绪。枉为诗人、报国痛泣的抒情主人公语言背后,是蒋光慈对于如拜伦般诗人英雄功绩的浪漫战士形象之召唤。换言之,“多情的拜伦啊!/我听见你的歌声了,/自由的希腊——/永留着你千古的侠魂!”[23]309蒋光慈眼中的“侠魂”拜伦,是超越政治主题“纯化”的拜伦形象,也即蒋光慈正视了一个“多情”而又为“自由”抗争的“侠魂”战士拜伦,他视野中的拜伦是血肉丰满、满含人欲与革命情义的浪漫战士拜伦。
蒋光慈是先以“侠魂”的情感与浪漫精神认同拜伦,继而再顺理成章地领悟到自由、反抗的战士诗人拜伦。因此,蒋光慈与拜伦一道,演绎着浪漫理念第一性的战士诗人形象。随着1930年代以降左翼现实主义话语的日盛,集体本位的现实主义话语成为左翼诗人的金科玉律。“蒋光慈作为中国现代左翼浪漫主义诗歌的首发者,无论是他的文学理论,还是居核心位置的诗歌创作,都显示出个人主体性始终如一的坚守”,“蒋光慈始终站在革命运动之外围言说革命的个体性革命话语立场”[24]。之所以造成如此现象,恐怕是与上述蒋光慈认同拜伦“浪漫战士”形象的内在理路密切有关。而我们观照“浪漫战士”蒋光慈的现实遭遇,因其内在精神结构的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蒋光慈也成为了“浪漫战士”拜伦的形象缩影。
总而言之,“豪侠”拜伦、“摩罗”拜伦、“浪漫战士”拜伦,较典型地譬喻着诗人拜伦在近现代中国的形象接受史状况。从“豪侠”拜伦之重侠义内涵的形象特质征用,到“摩罗”拜伦之情感主体性高扬的启蒙立场开拓,再到“浪漫战士”拜伦之兼具情感主体个性与革命精神认同的现实遭际,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拜伦作为一种介入现实的形象符号,其传播接受之旅与20世纪中国启蒙、革命思潮史的涨落、迭代密切相关。如何进一步发掘革命战士拜伦形象在不同时代中国语境中的变迁及其精神内核的深度解读,仍期待学界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296.
[2]周旻.“新声”与“怀古”:晚清“诗界革命”中的少年意气[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06):82-99.
[3]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120.
[4]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M]//谢冕,赵振江.中国新诗总论:翻译卷.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
[5]马君武.哀希腊歌序[M]//莫世祥.马君武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439.
[6]马君武.欧学之片影:十九世纪二大文豪[J].新民丛报,1903(28):90-93.
[7]苏曼殊.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M]//王学庄,杨天石.南社史长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337.
[8]刘半侬(刘半农).灵霞馆笔记·拜轮遗事[J].新青年,1916(04):26-35.
[9]柳无忌.译苏曼殊潮音自序[M]//柳亚子.苏曼殊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书店,1985:35-36.
[10]倪正芳.拜伦与中国[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57.
[11]游光中,黄代燮.中外诗学大辞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20:682.
[1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3]高旭东.鲁迅与英国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33.
[14]西谛(郑振铎).卷头语[J].小说月报,1924(04):13.
[15]沈雁冰(茅盾).拜伦百年纪念[J].小说月报,1924(04):183-184.
[16]梁实秋.拜伦与浪漫主义(续)[J].创造月刊,1926(04):100-106.
[17]倪正芳.徘徊在主流话语的边缘:20世纪30—70年代拜伦在中国之命运[J].作家杂志,2008(01):82-84,160.
[18]殷夫.殷夫:我是时代的尖刺[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21:111.
[19]任访秋.任访秋文集:现代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128.
[20]史美钧.衍华集:下[M].现代社,1948:13-14.
[21]张竞生.多惹情歌·序[M].上海:世界书局,1930:1-2.
[22]倪正芳.拜伦与中国[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147.
[23]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3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24]韦良.中国现代左翼浪漫主义诗歌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
(责任编辑 文 格)
Image Evolution of British Poet Byron in Modern China
CHEN Yong-lin1, WANG Xiao2
(1.College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Hubei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
Wuhan 436032,Hubei,China;
2.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Hubei,China)
Abstract:The imaginative personality of the 19th century British romantic poet Byron,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ocial rebel and the emotional subject in his poetry,is deeply rooted in the historical soil of 20th century Chinese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ary poetics.Previous studies have been somewhat weak in study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image of Byr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revolution.The Byron image in China has undergone stages such as the revolutionary trend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the individualistic enlightenment trend,and the mass-oriented leftist trend,and has manifested distinct image connotations of “gallant man”, “amala”, and “romantic warrior”. From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 narrow connotations of the “gallant man” Byron image to the pioneering of the enlightenment stance with high-flying emotional subjectivity of the “amala” Byron image,to the real-life experiences of the emotional subject with individuality and revolutionary identity of the “romantic warrior” Byron image,has been assumed the function of an image symbol that intervenes in Chinese social reality.This study thus provides an insight into the multidimensional image of Byron in China,which is helpful in recreating the complex scen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Byron’s image and Chinese poetry modernity.
Key words:Byron; gallant man; amala; romantic warrior; multi-dimensional 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