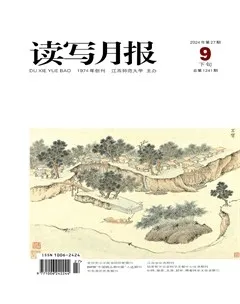《项脊轩志》空间建构中的情志书写
在《项脊轩志》中,归有光作为家族振兴重任的承担者,见证了百年祖宅的变迁,也见证了家族的分崩离析与家风的日益沦丧。在责任重压下,归有光将项脊轩视为心灵与精神的归处,借以表露自己对母亲、祖母以及妻子的思念与浓重的爱意。项脊轩在,亲人的期许与爱便不会消失,情感记忆便永恒不败。
一、自然空间:场景还原心境
加勒东巴什《空间的诗学》提到:“因为家宅是我们在世界中的一角。我们常说,它是我们最初的宇宙。它确实是个宇宙。它包括了宇宙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从内心角度来看,最简陋的居所不也是美好的吗?”[1]对于居住者而言,家宅不仅仅作为物理建筑而存在,更是宅中人内在心境的映射。
在《项脊轩志》中,归有光详述了修缮前后的项脊轩。修缮前的项脊轩“仅方丈”,空间极小;“百年老屋”外设陈旧破败;“又北向,不能得日”昏暗无光。经过归有光的修葺,项脊轩承载宅中人心境的意义被重启了。先是稍稍修葺,解决“尘泥渗漉”的现实问题,而后开辟四窗、修建墙体,使日光映射屋内。直至“兰桂竹木”入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项脊轩才又进一步成为作者心境、情趣的外化。多样繁复的植被均指向作者超然的内在心境。《孔子家语》有言,“芝兰生于深处,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兰道出了淡然的君子品性,也暗示着归有光作为少年士子的内在心境。除了兰花,桂花与竹子同样蕴藏了作者的君子风范与儒家心境。南宋刘学箕在《木犀赋》中指出:“木犀为花,高雅出类。馨发而不淫,清扬而不媚,有隐君子之德。”桂花彰显着儒家君子的坚贞;竹子更是历来文人表达心向的重要媒介,“满堂皆君子之风,万古对青苍翠色”,诉说着文人自强不息的君子气概。这些植被对于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归有光来说,具有激励、代言的价值意义。因而,在修葺项脊轩时,作者选择“兰桂竹”点缀祖宅,使其成为内在心境的言说者。应当说,这些植被赋予了项脊轩人格意义,即使是简陋的南阁子,也能凭借兰桂竹激发出作者的超然心绪。
如果说植被是归有光心境的显现,那么“借书满架,偃仰啸歌”的读书生活则是他颜渊之乐、自得心境的正面言说。尽管作者修葺了项脊轩,但细究语句“余稍为修葺”,“稍”点明修葺之力度并不大。修葺后的项脊轩仍然无法与宽敞明亮的家宅相比,作者居住其间,没有看到阁子的狭小老旧,只感受到轩中读书生活的丰富充实,只体会到夜晚的寂静闲适,只看到动物的有趣与活泼。他无法发出“陋室”的哀愁,惟叹其“珊珊可爱”,彰显“何陋之有”的闲意心境。这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儒士自得精神相契合。可以说,简陋的外在环境被作者诗意、脱俗的心境遮蔽了。至此,项脊轩完全转化成了作者儒士心境与心性的承载物。
对于归有光来说,修缮前的项脊轩更像是物理意义上的家宅,而修缮后的项脊轩则从物理建筑跳出,作为其心志的传递者而存在。
二、伦理空间:家族激发心志
所谓家族,不只是指具有直系血缘关系的小家,而是由夫妇、兄弟伯叔组成的以血缘关系为代表的大家,即氏族之家。这种家还拥有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某些行政和司法的职能。“与‘国’颇相类似……个人与家发生的各种联系,亦可以视为与国发生的联系,甚至亦可视为个人的生活世界本身。”[2]也就是说,家族具有凝聚族人,引导族人在交流中传承家族文化与精神的功能价值。一旦族人脱离家族,不接受家族的凝结与号召,那么赋之于家族的功能便消失了,家族不再具有社会职能。
归有光在《项脊轩志》中用富有特征的笔法描绘了归氏家族内部空间的变化,以此展现族人脱离家族、家族功能消失的发展历程。开始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而后“诸父异爨”“多置小门墙”直接消散了家族的凝聚功能,分解空间的材料由“篱”变为“墙”,更是在解构空间的同时,屏蔽了轩中人可视化的交流,或许族中人还能透过“篱”进行眼神、语言上的交流,而“墙”出现后,人与人的交流便荡然无存了。这种由“逐渐隔阂”到“完全封闭”的交流历程展示出归氏家族的分崩离析。
一个家族真正的颓败不囿于家族人心的涣散与家境的困顿,以礼仪规范为代表的家族精神与家族文化的沦丧才是导致一个氏族衰落的根源。“客逾庖而宴”不仅折射出家族空间的混乱,还暗示着归家礼仪尽失。“庖厨”自古便与君子之说有着密切的联系,贾谊在《新书·礼》有言,“故远庖厨,仁之至也”,将“远离庖厨”提到了“仁”的高度,朱熹同样继承了孟子以及前人对“君子与庖厨”的关系认知,指出“其所以必远庖厨者,亦以预养是心,而广为仁之术也”。远离庖厨本为君子之约,但此时客人参加归家的宴席却要逾越庖厨,对于君子应当具备的“仁”性置之不顾。更甚者,作为祭祀场所的厅堂沦为了鸡犬栖息之所。大约从周代开始,我国的厅堂就具备了接客、议事的基础功能,随着古人对文化、仪礼的重视,厅堂逐渐成为了供奉先祖、祭祀神灵以及组织婚丧活动的场所。当然,对于氏族来说,家族还承载着执行家族法规的职责。简言之,厅堂是氏族精神、风气的凝聚之地。但此刻归家“鸡栖于厅”,直接打破了儒家祭祀的神圣性与庄严性,解析了厅堂作为家族精神象征的文化意义,使其成为了世俗性的普通场所。种种违背儒家仪礼的行为,均是致使归家伦理秩序失常、人心日益相隔乃至家族风气沦丧,最终崩解归家伦理空间的决定因素。
尽管此刻的归氏家族已支离破碎,但在归有光父亲归正之前,归氏家族也有过盛大的家族荣耀。据记载,“归氏世著吴,自唐天宝迄于同光,以文学仕宦者不绝于世……至今吾县人犹传‘县家一令,不如归氏一信’”[3]。为了延续家族的荣光,归氏先祖直言“为吾子孙,而私其妻子求析生者,以为不孝,不可以列于归氏”,强制凝聚族人,以期传递累世家族文化与精神信念。家族往昔的荣光决定了归家的家风、精神传承的必要与重要。但此刻“诸父异爨”,后人违背先人遗愿,归氏家族仅仅存留一屋躯壳。面对这样悬殊的落差,从小接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归有光发出了振兴家族的豪言壮语:
“项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4]
面对家族伦理失序的现实,归有光自命“项脊生”,主动担负起振兴家族的重任。将自己与诸葛亮等人相比,诉说其不畏处于败屋的困境,期待功成名就,光耀门楣的心志。对于归有光而言,“家族”的意义尤为重大。家族是他修身齐家的起点,更是与他个人命运紧密相连的共同体,个人的荣辱与家族休戚与共。正因此,他愿意承担重任,对科考之苦甘之若饴,发出传承、弘扬家族荣光的高昂宣言。
伦理空间的分解总能刺激中国古代士子,使其为接力先辈精神而奋斗,这也是中国古代各氏族能够不断传承繁衍的原因。反之,一旦族人人心涣散,不再将个人短暂的生命融入家族传承的长河,必然会影响家族文化的传承,进而导致氏族精神、传统的断裂。
三、精神空间:细节凸显情感
“精神空间”是文学地理场景的价值旨归,是作家建构文学地理空间的最终指向。精神空间立足于现实空间,并与伦理空间相映照,意指由作家的经历、感受构成的文学空间。
《项脊轩志》中,作者利用长维度的时空,讲述了在项脊轩中,祖母、母亲以及妻子与自己的动人往事。时过境迁,项脊轩已然成为归有光的情感原点,也成为了支撑归有光在科举之路上承压突围的情感支点。
亲人的离去是人们永恒的伤痛,母亲的早逝对于归有光来说是生命的一次抽离。在《项脊轩志》中,他摒弃直接言说自己与母亲的情感交流,而借老妪之口隐藏失母之痛,这是一种“常”与“变”的叙事逻辑。“常”即符合常理,母子之间的情感交流止于归有光八岁,对于十八岁的归有光来说,母亲的疼爱与身影似乎已逐渐模糊。因而,母子之间的亲情必然要借助某一中介——老妪。“变”则指寻常中反寻常,尽管作者借老妪之口以表达亲情的皈依,但他又使老妪放弃言说自己幼时与母亲的往事,转而讲述母亲“以指扣门扉”询问其姐姐“儿寒乎?欲食乎”。在“变”与“常”中,以母亲对姐姐的关爱映射其对自己的疼惜,作者在委婉曲折中完成了失去母亲的悲述。其实,在“变”中,还涉及一处细节值得考究。母亲为何在“室西连于中闺”的现实下仅“扣门”而不“入门”?有明一代,主仆之间的关系界限仍然严格,母亲与老妪的身份地位决定了母亲难以逾越礼法,入门而视。而“扣门扉”这一动作及时消解了阶级身份下无意识导致的亲情隔阂,并由此表现母亲的急切与对幼儿的关心。“变”与“常”这一细节使项脊轩有了情感的加持,见证着作者与母亲的情感跨越时空再次联结在一起。甚至在多年以后,归有光仍能喊出“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5]的哀嚎。
项脊轩不仅见证了母子间的亲情,也承载着祖母对归有光的期许与疼惜。“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祖母关切孙儿之深意可见,见孙苦读而“阖门”,为其创设安静的读书环境,更见祖母之温柔与怜爱。阖门后的“自语”以及“儿之成,则可待乎”则是对孙辈勤苦读书的赞许以及对其考取功名的期待。祖母的话语中也有值得关注的一处细节,“吾家读书久不效”表明归家往昔“自工部尚书以下,累叶荣贵”的荣光不再,而祖母为名门之后、明太常卿夏昶孙女,身份的特殊性使她在见证家族由盛而衰后,尤为关注族人是否能重振家族、光耀门楣。目睹孙辈有心求学,祖母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顷之”,“持一象笏”交于归有光,肯定其“他日汝当用之”,祖母托付给归有光的是整个家族,交予的是家族的未来荣光。项脊轩见证着十八岁的归有光接过振兴家族的重任,成为了十八岁的归有光安放深情怀念的载体。直至而立之年的归有光再次落笔时,项脊轩仍然是他心灵情感的归处。
《项脊轩志》的末尾两段,是归有光在而立之年作的补记。项脊轩迎来了归有光的妻子魏氏,魏氏“少长富贵家,及来归,甘淡泊,亲自操作”,从富贵之家下嫁到潦倒之家,却未有嫌弃之姿。在轩中,询问作者古事,回娘家后谈论得最多的仍然是丈夫的小阁子,引得姊妹好奇“何谓阁子也”。魏氏不仅是归有光的妻子,更成为了归有光精神上的共鸣者,心灵上的陪伴者。尽管此时的归有光已经多次乡试不就,仅有秀才之名,但魏氏仍然鼓励他:“吾日观君,殆非今世人。丈夫当自立,何忧目前贫困乎。”直至重病,妻子仍满怀期望种下枇杷树,祈祷丈夫能功成名就。早在《周礼》便有枇杷树入祀庙堂的记载,象征着读书人科考功名之志向。枇杷树的存在扩充了项脊轩的情感空间,使其成为见证夫妻伉俪情深的爱情空间,妻死后,枇杷树旺盛生长,而人已不再。强烈的落差致使情感空间被撕裂,项脊轩成为了悲与喜交织的残缺空间。尽管其后二年,他复葺了南阁子,但内在的情感空间缺失终无法修复。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轩中的几位女性,在勉励归有光读书科考这一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尽管人到中年,有功名难就、思念先人、愧对先人的复杂心绪,但只要项脊轩在,精神空间就不会消逝,爱与期许便会在。
《项脊轩志》言浅意深,蕴含着归有光的情与志。归有光借助轩中人、轩中事以及轩中景表露出复杂多元的情感要素与士子心志,种种情绪仅透过只言片语的勾勒与铺叙便足够打动人心,引起世人的情感共鸣。
注释:
[1][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页。
[2]李大博、王莹:《论<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3期,第95页。
[3](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周本淳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36页。
[4]李卫东、张玉霞:《文学鉴赏》,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7页。
[5]陈振鹏、章培恒:《古文鉴赏辞典(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1589页。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