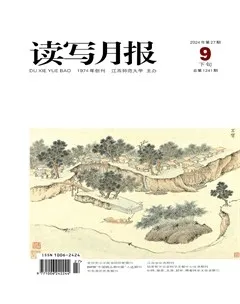背景·要素·逻辑:阿Q精神胜利法运行模式透视
《阿Q正传(节选)》是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二单元的课文,隶属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教材节选了小说第二、三章,主要讲述了阿Q在现实生活中频繁受辱和不断启用“精神胜利法”御辱的故事。精神胜利法是阿Q荒诞行为表征的内在机制。理解精神胜利法,是解读阿Q人物形象的关键,也是读懂《阿Q正传(节选)》的一把锁钥。
一、缝隙与补白:还原精神胜利法的发明背景
陈思和教授说,文本细读的过程就是心灵与心灵相互碰撞与交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阅读者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直面作品,寻找“经典”,发现缝隙,实现对作品的主体参与。所谓缝隙,就是作家遗漏或者错误的地方,也是作品所展现出来的世界与作品背后完整世界之间的差距。[1]作品的缝隙里隐藏着解读作品的密码,能够帮助阅读者完善故事,实现深度阅读。
(一)耐人寻味的文本缝隙
小说《阿Q正传》中,精神胜利法第一次出现,是在阿Q被撩拨他的闲人打了之后。“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这个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在心里想自己被儿子打,是他启用精神胜利法的时刻,然而,在此之前,还有一句非常重要但又容易被忽略的话,那就是“阿Q站了一刻”。这“一刻”阿Q在想什么,鲁迅没有说,只简略地概述了阿Q被打后“站”的动作,留下一个文本缝隙,引人遐思。
无独有偶,当得知阿Q有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后,闲人们主动撩拨挑衅阿Q,阿Q自贬为虫豸也无济于事,“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这里还有一个文本缝隙,那就是“不到十秒钟”。在这“不到十秒钟”里,阿Q在想什么,鲁迅依然没有说,只交代了“不到十秒钟”后,阿Q再次启用精神胜利法,心满意足的得胜走了。
(二)合乎情理的心理补白
在此,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地想象阿Q被打后的心理,还原这“一刻”阿Q的心理活动。光天化日下,自视甚高的阿Q被他瞧不上的未庄闲人打,还被众人围观取笑,这对于极端自尊且爱面子的阿Q来说,绝对是一件屈辱的事。阿Q先是被闲人揪住黄辫子,再在壁上碰了响头。整个被打的过程,阿Q都很被动,也无力摆脱困境。接连被碰了四五个响头,阿Q可能会因为猛然撞击而大脑断片,也可能会因为不断碰撞而感到疼痛。此外,阿Q被打的原因也很荒唐,起因是闲人“玩笑他”、“撩”他,“终而至于打”。因此,被打后那一刻,阿Q可能会感到屈辱、愤怒、痛苦、尴尬、难过、委屈、迷茫……种种复杂的情感交织,阿Q的内心应该充满了悲愤。“阿Q站了一刻”,那一刻无比漫长,他可能想到反抗,要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地报复回去。然而,或许是想到以往反抗失败的惨痛经历,或许是仔细掂量了自身瘦弱且营养不良的身体条件以及寡不敌众的tVEkdGqcLg/nR+/pMJ+1GQ==现实处境,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阿Q的脑海中,阿Q明白了自己终究是无力反抗也无法反抗的,那一刻的阿Q可能会感到气愤,却又无可奈何,最终选择了放弃反抗,以精神胜利法逃避现实。可以想见阿Q当时的神情与状态,无所适从地站着,脸上的表情变化不定,又孤单又可怜。
对比第一次被闲人碰头,第二次阿Q被碰头的个数多了,由“四五个”增长为“五六个”,但是阿Q反应的时间却大大缩短,说明阿Q已经习惯了莫名被打、被当众欺侮的悲惨处境,并且已经熟练掌握了应对欺辱的方法——精神胜利法,有了受辱和御辱的经验,阿Q的反应时间大大缩短。在这“不到十秒钟”里,阿Q可能快速回顾了以往受辱的经历,再次强化了反抗无效的认知,找到了对他来说最便捷、最可行也是最有效的路径,精神胜利法在不断运用中得到巩固和强化。
从“一刻”到“不到十秒钟”,补白文本的缝隙,可以还原精神胜利法的发明背景,不断遭受身体上的失败,无力反抗现实中的悲惨处境,是阿Q发明与运用精神胜利法的重要背景。精神胜利法是阿Q经历了由反抗到反抗失败后的无奈选择,也是阿Q的消极平衡术。
二、压抑与消失:透视精神胜利法的感觉失能
精神胜利法的运用,伴随着阿Q的感觉失能。在一次次地启用精神胜利法的过程中,阿Q的羞耻感受到压抑、屈辱感转移、疼痛感消失,只剩下“得意”“飘飘然”这两种精神状态。对精神胜利法运用得越纯熟,阿Q的感觉失能程度也就越高。
(一)压抑羞耻感
阿Q的感觉失能首要表现为羞耻感被压抑。第一次阿Q被闲人打,阿Q站了一刻后,启用精神胜利法,心想自己被儿子打了,“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这里的矛盾在于,阿Q是一个很自尊的人,自认自己“先前阔”、见识高、“真能做”,未庄的所有居民他都不放在眼里,觉得他们是不见世面的可笑乡下人。对于自己头上的癞疮疤,阿Q一直很忌讳说,他的禁忌逐渐由同音字(癞、赖)扩大到同义字(光、亮、灯、烛),同时也不许别人说。但凡别人犯讳,阿Q就要全疤通红发起怒来。小小的癞疮疤被人取笑,阿Q就感到羞耻,觉得自尊折损,生气发怒,或骂或打或怒目而视。然而,启用了精神胜利法后,大庭广众下被打,阿Q的羞耻感却被压抑了。
又一次,当阿Q被闲人再次揪住黄辫子,让他说是“人打畜生”时,面对明目张胆的欺辱,阿Q却做出了与他先前认知反差极大的举动,他自己扭住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从自认自己是品行优秀且毫无缺点的“完人”到自轻自贱当众宣称自己是“虫豸”,阿Q的羞耻感完全被压抑。
(二)转移屈辱感
除了羞耻感被压抑外,屈辱感的转移也是值得关注的。当第一次被闲人打时,阿Q通过幻想,以儿子打老子转移自己的屈辱感,心满意足地走了。第二次被打,阿Q以自己是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与状元强行建立联系,“便愉快的跑到酒店喝酒”,和别人调笑,“又愉快的回到土谷祠”,倒头睡着。两个“愉快的”,凸显了阿Q精神上的愉悦。愉悦感的显扬意味着屈辱感的转移。当被赵太爷打嘴巴,阿Q刚开始有些愤愤,随即启用精神胜利法,把赵太爷想成自己的儿子,渐渐得意起来,还唱起了《小孤孀上坟》,这种得意持续了许多年。屈辱感被得意转移。
例外的是被王胡和假洋鬼子打。阿Q觉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是他瞧不上且常常奚落的王胡,竟然敢动手打他。然而这种屈辱感被阿Q关于科考取消、赵家失势的胡思乱想冲淡。“阿Q无所适从的站着”。蕴积的屈辱感本可转化为反抗的力量,却因为阿Q深恶痛绝的假洋鬼子到来而被转移。等到挨了假洋鬼子打后,阿Q再次感到屈辱。但这一次阿Q“抽紧筋骨,耸了肩膀”,主动等候被打的降临,领受被打的屈辱。又因为被打的完成,而在心态上觉得轻松,屈辱感再次被转移。
(三)消除疼痛感
疼痛感的消失也是阿Q感觉失能的重要表征。小说中,不管是被闲人在壁上碰头、被赵太爷打嘴巴,还是被王胡连碰且用力推,抑或是被假洋鬼子用黄漆棍子打头,阿Q本该感到疼痛,或做出疼痛的表现。然而,启用了精神胜利法,阿Q的疼痛感竟然消失了,相应的,有关疼痛的表现以及自卫反击的举动也都付之阙如。唯一例外的是被赌徒打,阿Q不小心卷入赌徒的打架中,“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两个“似乎”别具意味,模糊不定的表述,昭示阿Q的感觉失能,头脑昏昏的阿Q分辨不清自己是否挨打,痛感也就若有若无随即消失。
痛感的消失,使阿Q在每每被打后,总能快速地摆脱狼狈、痛苦的现实处境,迅速切换到愉快、得意、心满意足的状态,以此来麻痹自己的神经,沉溺虚假的胜利中。
三、转移与转嫁:提炼精神胜利法的行为要素
现实中阿Q经常受辱被打,而幻想中阿Q总能通过精神胜利法获得胜利。精神胜利法是阿Q御辱制敌的重要妙法。细究阿Q启用精神胜利法的行为,可以提炼出转移、转化和转嫁三种要素,正是对这三种行为要素的运用,阿Q实现了对现实失败的超越。
(一)想象转移屈辱
阿Q被闲人当众揭伤疤取笑,又被揪住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阿Q都面临着极大的屈辱,遭遇严重的失败。对此,阿Q选择启用精神胜利法,以“我总算被儿子打了”来安慰自己,靠想象虚构父子叙事,颠倒现实秩序,转移屈辱,实现心理的平衡。同样,蒙赵太爷打了嘴巴,阿Q的心里愤愤不平,但他又以“儿子打老子”的话术来麻痹自己,转移屈辱。通过想象自己是赵太爷的老子,而威风如赵太爷不过是自己的儿子,替换现实中的尊卑地位,获得心理补偿。
相对于阿Q,闲人身强力壮,孔武有力,不管是从身体条件还是从战斗力来看,阿Q都不是闲人的对手。赵太爷未必在力量上有优势,但他在未庄地位尊贵且格外受到尊敬,阿Q在权势上比不过赵家,气焰上也低几分,自然也打不过。也就是说,当面对强大的敌人欺辱时,阿Q无力反抗,只能通过想象转移屈辱。
(二)自虐转化屈辱
阿Q在赶赛会的赌摊附近莫名挨了几拳几脚,引得旁人诧异的观看,这还没完,等到他若有所失地来到土谷祠,才发现自己好不容易赢得的一堆洋钱不见了!阿Q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这一次,他按照原来的路径启用精神胜利法,通过想象编织故事,说钱被儿子拿去了,但没用,“总还是忽忽不乐”;通过自贬转移屈辱,说自己是虫豸,但仍没用,“也还是忽忽不乐”。阿Q遭遇了现实和精神上的双重危机。面对危机,阿Q做出了惊人的举动,“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
如果说之前被闲人或赵太爷欺辱,还有一个对象可供阿Q想象发泄失败的情绪,转移现实的屈辱,但是这一次阿Q既无法确证自己是否被打,也无法找到拿走他“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的人。心中的怨恨、委屈、难过不断泛起,无法排遣的“忽忽不乐”,促使他将自己对象化,通过打自己借以想象自己在打别人,以自虐转化屈辱。
(三)凌弱转嫁屈辱
自打被赵太爷打后,阿Q声名鹊起,得意了许多年,直到他被王胡打。王胡和阿Q一样,都是未庄的下等人。但阿Q“非常渺视”王胡,觉得长着络腮胡子的王胡实在看不上眼。然而,正是王胡粉碎了阿Q的高傲与自信。阿Q被王胡扭住辫子,拉到墙上碰头,还被推跌出去很远。阿Q觉得屈辱难堪。这时,阿Q深恶痛绝的假洋鬼子来了,正气忿、要报仇的阿Q把内心对假洋鬼子的咒骂轻轻说出来。假洋鬼子拿着哭丧棒“拍!拍拍”地打在阿Q的头上。阿Q再次觉得屈辱难堪。倍感屈辱的阿Q,看到对面走来的小尼姑,“发生了回忆,又发生了敌忾”,迎上去吐唾沫,说着污秽的话,还伸手摩小尼姑的头皮,扭住她的面颊。在周围鉴赏家的哄笑中,阿Q“报了仇”,感到飘飘然。

面对厌恶且瞧不上的王胡和假洋鬼子,阿Q是有心理优势的,所以敢于骂出口,但心理优势无法转化为武力优势,在“打不过”的现实屈辱面前,阿Q恃强凌弱,通过欺负更弱小的小尼姑转嫁屈辱,实现精神胜利。
四、自欺与忘却:发现精神胜利法的运行逻辑
细看精神胜利法,充满了荒谬,滑稽感十足,不难识破和拆穿,但在小说中却被阿Q运用得炉火纯青,无往不胜。这其中固然有阿Q严峻的生存境遇、未庄和当时整个社会共谋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阿Q的自欺与忘却,使精神胜利法持续上演,反复运行,拥有顽强的生命力。
(一)自欺以摆脱现实失败
回看阿Q受辱的几次遭遇,被闲人挑衅碰头,被赌徒拳打脚踢,被赵太爷打嘴巴,被王胡碰头推倒,被假洋鬼子拿棍子打头。每一次被打,阿Q都启用精神胜利法帮助自己摆脱困境。被闲人打,阿Q心想自己被儿子打,感叹世界不像样。再次被闲人打,阿Q先是自轻自贱,说自己是“虫豸”,再断章取义、偷换概念,认定自己是和状元一样独占鳌头之人。被赌徒打,还丢失了赌赢的洋钱,阿Q感到失败的苦痛,用力的在自己的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明明是在自虐,却幻想自己打别人。被赵太爷打,阿Q想象赵太爷是自己的儿子,以此来安慰被打的自己,获得精神上的得意。被王胡打,阿Q却思索别人小觑他的原因,溯源到皇帝停考,赵家减了威风。被假洋鬼子打,阿Q既没逃跑,也没反抗,主动等候着被打的处分,还把一切的晦气归因为遇上小尼姑,因而欺辱小尼姑。
可以说,不管是想象代偿,编造父子故事,还是自贱自虐,把自己异化成卑微的他者,抑或是胡乱归因,轻率判断,把自身的处境与别人建立关联。本质上,阿Q都是靠自欺麻痹神经,以想象中的胜利置换现实中的失意。
(二)忘却以持续精神胜利
如果说自欺是阿Q摆脱当下现实失败的重要方式,那么忘却就是阿Q持续获得精神胜利的重要法宝。
忘却在小说中直接出现,是在阿Q被假洋鬼子打后。被打的刹那,阿Q便知道假洋鬼子大约要打了,他没有躲闪,提前做好被打的姿势,集中精神等候着,拍拍响如期而至,于阿Q似乎是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接下来,“‘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在忘却的作用下,阿Q忘记了被打的屈辱和悲愤,迅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慢慢变得高兴起来。同样,被闲人打、被赌徒打、被赵太爷打、被王胡打,每一次遭受凌辱后,阿Q总能以自欺获得心理平衡,迅速恢复到开心、得意的状态,不管是“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还是“愉快的回到土谷祠”“渐渐的得意起来”,抑或是“早已有些高兴了”“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忘却使阿Q一次又一次地踏入精神胜利法所营造的幻景之中,一次又一次地错失精神觉醒的契机。故态复萌,周而复始,精神胜利法成了循环生产的圆圈,把阿Q围困其中。
审思精神胜利法,可以建构一条精神胜利法的运行逻辑链。阿Q狭小的生存空间和悲惨的现实处境,是精神胜利法运行的背景和起点。在它运行的过程中,通过压抑羞耻感、转移屈辱感、消除疼痛感,造成阿Q的感觉失能,只剩下得意和飘飘然两种精神状态。在频繁被打的现实面前,阿Q通过想象、自虐、凌弱,实现屈辱的转移、转化和转嫁。以自欺来摆脱现实失败,以忘却持续获得精神胜利,是精神胜利法生生不息的关键。
注释:
[1]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本文系江苏省苏州市“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基于单元学历案的课堂重构校本研究”(编号:2022/LX/01/009/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吴县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