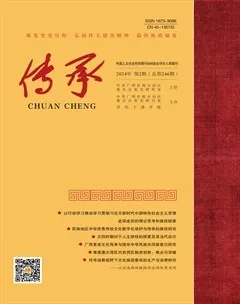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证研究
[摘 要]文章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和西林县各民族间的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现象,揭示了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远影响。具体而言,不同民族的共居共建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语言共学共用构建了新的社会条件,文化互学互鉴营造了新的社会环境,婚姻共事共乐则创造了新的社会生活。这些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行为不仅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还为其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路径、价值认同及内生动力。文章进一步提出了在隆林、西林两县实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包括强化政治基础、夯实经济基础、巩固思想基础、稳固社会基础以及健全法治基础,旨在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努力,全面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新时代广西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常态化机制研究”(23FMZ023)
[作者简介]杨登祥(1968—),广西隆林人,隆林各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研究方向:地方民族文化。
DOI:10.16743/j.cnki.cn45-1357/d.2024.02.006
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这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要顺应时代要求,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1]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如何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明了方向。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以共同文化、共同历史、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和协作的精神。当前,虽然有关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等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还需要更多来自民族地区基层田野调查等方面的实证性探讨。
一、不同民族的广泛接触丰富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不同民族经过长期的接触,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各民族在居住、语言、文化、婚姻等方面的共居共建、共学共用、互学互鉴、共事共乐,不断组成新的社会结构、构成新的社会条件、促成新的社会环境、形成新的社会生活,从而丰富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
(一)各民族村落共居共建组成新的社会结构
村落是指大的聚落或者多个聚落形成的群体居住地,常用作现代意义上的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包括自然传统村落、人工打造村落等。自然传统村落所蕴含的精神特质,传承着各民族几千年来的民族记忆,也是承载着各民族几千年来的灵魂栖息处,更是各个民族乡愁的集中体现。
在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隆林”)、西林县(以下简称“西林”)各民族村落中,有单一姓氏村落、亚血缘族居村落、多姓氏杂居村落、多个支系乃至多个民族杂居村落等类型。单一姓氏村落在广西隆林、西林苗族居住区较为普遍,它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结成的单一姓氏的大家庭,属于同宗共祖的叔伯兄弟子孙数代人所组成的宗族体系的村落。亚血缘族居村落是该地区以家族及其亲属以户联合组成的村落,该类型村落以地缘为纽带,通过相互联姻逐渐发展成为大村落。这种村落内部人们平时保持高度的团结。多姓氏杂居村落,即在村落中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宗室家族的人群居住。该类型村落的人们,尽管他们是不同宗室家族的人群,但是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他们仍然与单一姓氏村落和亚血缘族居村落一样,保持与自己不同宗室家族的人们友好相处、紧密团结。农忙季节劳力的帮工、换工和畜力的互通有无、交换使用等农村良好传统现象同样比较普遍,这充分体现了村落一贯团结互助的良好习惯。例如:广西隆林德峨镇八科村大长冲屯内杨氏和李氏、小长冲屯内杨氏和王氏以及打锣屯内杨氏、熬氏、丁氏、安氏的这些杂居村落中,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无论是哪一姓氏宗室的人家家中碰到红白喜事或其他困难,屯中异氏宗室的人家,都将其视为己出而积极伸出援手,参与帮助相关后勤保障等事务;主动与碰到困难人家的家庭户主,一起协商解决困难的对策与办法。充分体现了彼此“一家亲”的睦邻友好、团结互助关系。
此外,还有一种是多个支系乃至多个民族杂居村落,即在村落中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支系,或苗族与汉族、彝族、壮族、仡佬族等两个以上民族家庭杂居的人群居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他们在友好相处、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和谐进步的关系等方面与单一姓氏村落、亚血缘族居村落和多姓氏杂居村落相比,不仅不逊色,而且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不同支系的苗族、不同民族家庭的村落,人们彼此共居共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广西隆林、西林各民族建立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作了生动的诠释。例如:广西隆林革步乡向阳村懒石抗屯和蛇场乡马场村六路冲屯、新民村同共屯、蛇场村下对、新立村关塘屯等是汉族、苗族2个民族共同居住的村落;德峨镇岩头村岩头屯、弄保屯,保上村阿稿屯、峨托屯等是苗族、彝族两个民族共同居住的村落;广西西林普合苗族乡文雅村亨沙屯、者底村下伟徕屯等是苗族、仡佬族两个民族共同居住的村落;隆林克长乡新华村海子、仁上屯、德峨镇常么村更芭屯和西林普合苗族乡岩腊村岩腊屯等是汉族、壮族、苗族、彝族、仡佬族5个民族共同居住的村落。以克长乡新华村仁上屯为例,20世纪60年代该屯已共同居住着2户汉族、4户壮族、5户苗族、7户彝族、5户仡佬族,共23户。1969年起5个民族群众在郭卜寿、黄顺昌等几位老队长的带领下,团结和睦,共同劳动,勤劳持家,共建家园。队长郭卜寿带领各族群众经过4年的努力,在该村落后面的石崖上凿通了一条800多米长的水渠,解决了该村落23户人畜饮水难的问题,并扩大该村落水田的灌溉面积。他们还主动将修通水利渠道的水让给海子、干坝、垭口等相邻村落的苗族群众灌溉农田[2]。
不同类型村落的居民,尽管日常彼此共同居住、共同建设着各自的村落,但由于村落内居民的姓氏、宗室、支系、民族不同,因此,其观念、认知度也就各有不同。而在一个观念众多、认知度参差不齐的村落中,其居民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更多的是崭新观念和认知度高的姓氏、宗室、支系、民族在影响着那些观念陈旧和认知度低的姓氏、宗室、支系、民族,从而促成彼此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增进共同性,形成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追求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结构。
(二)各民族语言共学共用构成新的社会条件
广西隆林、西林居住着汉族、壮族、苗族、瑶族、彝族、仡佬族等6个民族,20世纪90年代末出生的各民族人员都能讲当地汉语。当地汉语属于西南官话,在广西被称为“桂柳话”,与国家通用语言只是口语声调上的差别。在该地区,部分汉族人能听得懂苗族的一些日常用语,对外交流也是使用汉语。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居住在广西隆林、西林壮族所操壮语属壮语北部方言桂边土语,该土语隆林又分为南面和北面,西林称为东面和西面,在语言上有声调的差别,词汇上差别较小。“不丢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是广西隆林、西林壮族坚定使用本民族语言的真实写照,这也使得壮语得以代代相传。该地区壮族内部多年来一直使用自己的母语作为交流语言。如今,壮族中老年男子和大部分中年女子都能使用当地汉语,对外交流使用当地汉语。
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广西隆林、西林苗族使用的苗语属于川黔滇次方言(也称西部方言苗语)第一土语。在偏苗、白苗、红头苗、花苗、清水苗、素苗六个支系中,除素苗支系外,其他五个支系语言大同小异。20世纪70年代前,广西隆林、西林苗族鲜有与其他杂居族群通婚,其生产生活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彼此交流用语均使用苗族母语,因而苗语得到很好的发展。改革开放后,随着时代发展和电视普及率提高以及外出务工人员增多,许多苗族大人在与小孩或孙子或外孙进行日常语言交流时,都刻意引导其讲当地汉语。如今,大人之间彼此交流的语言还是苗语,而小孩之间的交流则一半是本民族母语,另一半是汉语。部分50岁左右的妇女只懂得本民族母语,绝大部分白苗、红头苗、花苗、清水苗的成年男女都能够使用偏苗支系的语言。与彝族、壮族、仡佬族杂居或村落为邻的苗族,有部分男子能使用简单的彝语、壮语和仡佬语。如今,苗族中老年男子和大部分中年女子都能使用当地汉语,对外交流都使用当地汉语。
瑶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有部分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家把瑶族语言分为四大语言八大方言,即勉语(勉方言、金门方言、标敏方言、邀敏方言)、布努语(布努方言、包瑙方言、巴哼方言、炯奈方言、优诺方言、唔奈方言)、拉珈语、汉语。”[3]广西西林瑶族使用勉语的金门方言和布努语的布努方言。虽然瑶族大部分以本民族独居村落为主,但是大多与壮族、苗族村落为邻,所以有部分男子能够简单使用壮族、苗族语言与之交流。现在,绝大部分瑶族男子和中年女子都会使用当地汉语,对外交流都使用当地汉语。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广西隆林、西林彝族交流使用的是彝语东部方言。20世纪80年代,该地区的彝族男女老少都已能够使用当地汉语。随着迁入时间久远、人口数量不多、与其他民族通婚率和电视普及率的增加等,目前在部分彝族家庭内部,大人与小孩日常生活交流语言,不再是彝语,而是汉语。广西隆林、西林彝族一般都通晓当地汉语和偏苗支系语言,彝族中老年男女同偏苗支系交流语言所使用的是偏苗支系语言,对外交流使用当地汉语。
仡佬语是汉藏语系中古老的语种之一,仡佬语分为多罗、哈给、稿、阿欧或黔中、黔中北、黔西、黔西南四种方言。居住在广西隆林、西林仡佬族分为多罗、哈给和布流3个支系,其语言属黔中、黔中北方言的第一土语。其方言土语差异较大,3个支系之间基本不用本民族语言交流。据调查,广西隆林德峨镇三冲村弄麻屯等仡佬族约300人,还能使用仡佬族母语交流[4]58。但是该县德峨镇么基村大水井屯和岩茶乡弯桃村约500人中,能够掌握仡佬族母语的已不足30人,他们日常生产生活用语是当地汉语[4]52。仡佬族大部分中老年人能听得懂小部分偏苗支系日常用语,对外交流使用当地汉语。
20世纪50年代开始,广西隆林、西林各民族干部为便于开展工作,就边工作边与当地群众共学共用其语言。由此,在该地区出现了苗族干部除了能使用汉语,也知晓彝语、壮语等,而一些汉族、壮族、彝族、仡佬族也能说苗语。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该地区族际通婚的不断增加,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施行后,各民族共学共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便成为常态。不同民族之间这些语言共学共用的要件,构成各民族以语言为基础的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条件。
(三)各民族文化互学互鉴促成新的社会环境
我国各民族的饮食不仅反映各民族日常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由此而产生、传承、保留着许多名食小吃。以广西隆林、西林苗族的名食小吃为例,主要有辣椒骨、羊瘪汤、豆腐乳、涟渣涝、糯米肠、活血、狗红肠、素菜汤、鸡爪菜、魔芋糕和饭豆酸菜等。辣椒骨是广西隆林、西林苗族的一道风味独特、极负盛名的美食,也是该地区苗族传统的优等调味品。一坛辣椒骨,其所承载的不仅是广西隆林、西林苗族一个家庭一年的味道,而且是一生的记忆。隆林辣椒骨制作技艺已于2018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列入第七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再如羊瘪汤,该小吃是广西隆林、西林苗族的上乘佳肴之一,经常食用羊瘪汤,有助于驱寒消暑、消除疲劳。再以广西隆林、西林壮族为例,他们则擅长制作甘蔗糖片、黑粽子、五色糯米饭等名食小吃。
历史上,广西隆林、西林苗族在与其杂居各民族的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彼此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苗族辣椒骨、羊瘪汤、豆腐乳、涟渣涝、素菜汤等的制作技艺早已经被当地汉族、壮族、瑶族、彝族、仡佬族所掌握。而壮族擅长制作的甘蔗糖片、黑粽子、五色糯米饭等技艺,也先后被当地汉族、苗族、瑶族、彝族、仡佬族所接受和掌握。由此,现在广西隆林、西林各民族日常喜欢清淡甚至素淡汤的食俗、就餐必须配有蘸水的风尚、宰杀年猪后制作辣椒骨等的习俗、节庆活动精心准备的黑粽子、五色糯米饭等的特色食品,都是广西隆林、西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互学互鉴的结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饮食文化,这既是普通饮食温暖的交流,又是各民族文化爱的传递。该地区各民族的饮食习惯便由此逐渐养成,从而使各民族的饮食更加丰富多彩。时至今日,广西隆林、西林过年前宰杀年猪之后仍保留着一种习俗,该地区汉族、壮族、苗族、瑶族、彝族、仡佬族这6 个民族都必须制作腊肉与腊肠,并掌握其技艺,且各民族所制作的质量差别也不大。
广西隆林、西林汉族、壮族、苗族、瑶族、彝族、仡佬族6个民族是我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6名成员,虽然广西隆林、西林各民族饮食文化反映的仅是我国少数民族在缔造中华文化中伟大贡献的其中一部分,但是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华文化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互相影响、相互促进的结果这一真谛。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加深和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该地区各民族饮食越来越丰富,吃法也是越来越多样化,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正是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长期“和睦相处、唇齿相依、和衷共济、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才得以共建彼此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社会环境。
(四)各民族婚姻共事共乐形成新的社会生活
广西隆林、西林苗族族际通婚“破冰”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德峨镇八科村上巴角屯苗族姑娘杨志林与该村团石屯彝族教师黄子辉成婚,到1983年德峨镇保上村阿稿屯彝族干部王文林与猪场乡岩圩村狼丫二队苗族姑娘古彦丽完婚后,隆林苗族姑娘或小伙子与自己有缘的汉族、壮族、瑶族、彝族、仡佬族的小伙子或姑娘通婚的现象逐步增多。地域上也由广西隆林德峨镇辐射至隆林全县乃至西林,甚至整个桂西北,进而辐射全广西乃至全国各地。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广大农村各民族交往和人口流动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社会务工环境,加上年轻一代视野的拓宽和婚姻观念的更新,广西隆林、西林各民族族际通婚更是呈现上升趋势。族际通婚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表现形式,使不同民族群体的生理性融合成为可能,成为其他文化融合的基础,从而有效地促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最好诠释,因而在广西隆林、西林现代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格局和社会生活。
二、深刻认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
“交往交流交融”是既密切相关又互为递进联系的三个层面,交往是基础和前提,交流是过程和递进,交融是核心和目标。而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若忽略“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联系,或没有起到奠定基石和提供方法路径、价值认同、内生动力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都可能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目标的实现。
(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基石
以广西隆林、西林苗族为例,受过去统治王朝实行“分而治之”和一些陈旧观念的影响,苗族内部日常语言交流大多使用本民族母语,族际交往交流交融更谈不上使用汉语。20世纪90年代前,除广西隆林、西林的彝族、仡佬族2个民族因人口较少,他们偶有与汉族互相通婚外,苗族各支系大多数只在族(支系)内通婚,其母语作为日常生活交流的语言使用比较稳固。所以该地区苗族等一些民族群众,尤其妇女在与其他民族交往时,在语言交流方面还存在着一定难度。在该地区,偏苗支系老人常常教育子女要加强文化知识和汉语的学习。
一方面,在各级党委、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下,加之在当下电视、网络日益普及下,现在广西隆林、西林县广大城乡各民族青年和小孩已完全通晓当地汉语,各族群众在语言交流方面已经有了明显改善。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后,随着广西隆林、西林各民族族际通婚率的迅速提高和广大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当地汉语已逐渐取代一部分各民族的母语而成为其家庭日常交流用语。同时,不同民族间流畅的语言交流,既能拉近双方的距离,又能知道对方表达的意思,还能消除双方语言上的障碍,更容易增进双方的感情和彼此之间的团结,有效地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这对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语言相通、情感相融的基石。
(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方法路径
我国各民族都有各自一套完整的日常生产生活习俗,其包括社会交往、农业生产、生活饮食、婚丧嫁娶、岁时节庆等。以岁时节庆习俗为例,在我国,不同的民族,其节庆既有相同又各有不同,例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国庆节等;形成了我国种类繁多的节庆,不同的节庆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历史、生活、经济、文化、习俗、服饰、风情等情况。
广西隆林、西林6个民族节庆,除上述共同的节庆外,各民族每年比较隆重而又盛大的节庆还有汉族“泡汤节”、壮族“排歌节”、苗族“跳坡节”、瑶族“盘王节”、彝族“火把节”、仡佬族“尝新节”等。以苗族“跳坡节”为例,因它是广西隆林、西林苗族历史悠久的盛大节日,至今传承着灿烂的苗族文化而蜚声海内外。每年正月初三至十六,苗族同胞按惯例从四面八方汇集各个坡场,开展喊坡、赶坡、祭坡杆、爬坡杆、吹芦笙、弹月弦、服饰文化展演等丰富多彩、独具浓郁民族风情的文化活动。广西隆林、西林苗族“跳坡节”是规模大、容量多、影响深、族群性和区域性的重大节庆活动,随着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和各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如今,参加苗族“跳坡节”的人员越来越多、场面越来越隆重、规模也越来越大,它已经不仅仅是桂滇黔三省(区)苗族自己的节日,而且还发展成为汉族、壮族、瑶族、彝族、仡佬族等多个民族和区内外民族、民俗专家学者以及各级媒体人士等共同交流、彼此欢庆、平等和谐的重大盛会。时至今日,随着各民族长期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彼此节气文化的互学互鉴,广西隆林、西林“跳坡节”等各民族节庆已被赋予新的文化元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价值认同
“十三五”初期,广西隆林结合该县实际,把全县16个乡镇居住于自然条件恶劣的部分各民族贫困户,通过搬迁形式,统一安置到隆林县城城西易地扶贫安置点——鹤城新区。由此,该安置点成为目前广西隆林、西林最大的人工村落。为加强该新区的建设和管理,该县按照“搬得出、稳得住、快融入、能致富”的要求,通过强化“三就近三变三交”,着力推动新区各民族转变思想观念、就业方式和生活习惯,构建管理有序、就业充分、保障到位、和谐宜居、民族团结的新居住区。
在“三就近”方面。一是就近就业,解决了各族群众搬迁后就业创业难问题。该新区依托隆林脱贫奔康产业(就业)园方便搬迁各族群众就业的优势,首先安排搬迁各族群众1000人以上在脱贫奔康产业(就业)园的17家企业就业;其次是开发并安排100个公益性岗位;最后是实施技能培训,促进技能型就业1。二是就近入学,解决了各族群众搬迁后子女入学难问题。在该新区的规划、建设中,同步配套建设了罗湖幼儿园、罗湖小学、隆林第五初级中学,并于2020年9月全部投入使用,3所学校(园)共安排搬迁各族群众子女就学将近2000人2。三是就近就医,解决了各族群众搬迁后看病就医难问题。隆林党委、政府把新州镇卫生院搬迁建设在该新区的附近,开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急诊科、公共卫生科等科室,辅助科室有检验科、B超、DR等。同时,还在该新区内设立居民卫生室,有效解决了各民族搬迁户的看病就医难问题。
在“三变”方面。一是村民变市民。首先是党员带头树新风;其次是群众自觉讲规范。该新区注重充分发挥党委成员先锋模范作用,逐楼逐户上门发放宣传单和告知注意事项,各族群众日常居家和出行也都注意遵守城市文明公约;再次是党员巡视常态化。采取有效措施转变新区居民过去在农村的生活陋习,促进该新区各族群众的移风易俗。二是分散变集中。建立“党委+管委会+楼栋长”分片联系机制,实现新区管理从“被动式”向“参与式”转变。三是生人变熟人。首先抓好全方位服务。从家庭信息到纠纷处置,从解决家庭困难到提供就业信息等,为各族群众提供全方位服务。其次抓好全天候服务。搭建各民族充分交往交流服务平台,推行新区管委会24小时值班服务制度。最后抓好全域性服务。自治县有关部门开展“一条龙、一站式”便民服务,实现各民族充分交往交流交融和便民服务的零距离。
在“三交”方面。一是各族群众广泛交往,相互关照,和睦共处。注重抓好各栋楼、各单元、各楼层之间各民族住户的日常交往的礼貌问候和彼此关照等,充分发扬“一家有难、大家关心”的好传统、好习惯,有效促进新区各族群众广泛交往,相互关照,和睦共处。二是各族群众全面交流,相互学习,彼此连心。充分利用元旦、春节、五一劳动节、中秋节等节假日,引导各族群众积极参与各种定期或不定期在新区内举办健康、向上的各种文娱活动等,积极搭建新区各族群众思想文化交流平台。三是各族群众深度交融,相互亲近,追逐梦想。在新区内建设一座民族乡愁记忆馆,既能有效增强各族群众全面交流,相互学习,彼此连心,又能促使各族群众在回望自己来时的路、眺望今后的路时,时刻不忘并更加坚定地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随着该新区5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的不断深入,各族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做得了和睦邻居、交得了知心朋友、结得了美满婚姻、搭得了团结大局。目前,该新区各族群众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共同谱写新时代“五个认同”“团结跟党走、建设新隆林”“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新篇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价值认同。
(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内生动力
时至今日,在广西隆林、西林,每年正月初二、初三这两天,还有一种象征着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的“拜老庚”习俗,苗语称“Pyia ga caag tsaiv”(谐音“别嘎江斋”),意思是给“老庚”拜年。即在该地区,汉族、壮族、苗族、瑶族、彝族、仡佬族等各民族青少年男女之间,只要彼此兴趣相当、年龄相仿、性格相近,双方都有意向,而且不仅局限于族内,都有结拜为“老庚”的习惯,俗称“打老庚”,即“嘎江”。“嘎江”苗语是“老树的根”,意思是“如树根般牢固可靠的关系”。结拜为“老庚”之后,从此,双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由此,就有情趣相投“打老庚”、春节期间“拜老庚”、平时大事“想老庚”和困难时候“帮老庚”等一系列活动。
庚亲绵延,代代交往。结为“老庚”的双方儿女,互相认对方父母和兄弟姐妹为“庚爹”“庚妈”“庚哥”“庚妹”。“庚爹”“庚妈”又认自己“老庚”的儿女为“庚儿”“庚女”。同一辈的“庚亲”既是兄弟姐妹同等的身份,又是民族之间的友谊。特殊的民族关系,更容易在处理民族纠纷中起到特殊的作用。
广西隆林、西林各民族“打老庚”这一民族团结进步的特殊传统习俗,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所接受。各民族间不仅父辈们结拜为“老庚”,而且为了延续各民族间这一民族团结进步的特殊传统习俗,到儿子这一代,同时也出现延续结拜为“老庚”的现象。广西隆林、西林各民族间不仅在县内结拜为“老庚”,而且在与毗邻的贵州省黔西南州一带的布依族、汉族人民的往来中,也有结拜为“老庚”的,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使两省(区)相邻的各族人民更加团结友好相处,有效推动区域各民族团结与全社会和谐的构建。
“五个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动力,而广西隆林、西林各民族间结拜“老庚”习俗,具有增进民族团结、提升民族自信、增强民族凝聚、推动民族发展、促进民族融合的功能。在汉族、壮族、苗族、瑶族、彝族、仡佬族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契合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使他们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稳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来,这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内生动力。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实践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当前,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做到“五抓”。
(一)抓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
100 多年前,广西各族群众还处于“苗民聚族腹地。原非化外之民。今犹榛榛狉狉。曾与鹿豕无异。旅行苗地者。如游上古部落之社会。又若置身异国焉”[5]1的贫穷落后的社会。他们严冬时节“天寒雨雪。屋檐冰冻数尺许。参差下垂如贯珠。银粟万山。云雾迷蒙。飞鸟无声。交通断绝。苗民焚薪取暖。终夜劈拍不绝。举家男女。环炉灶而眠”[5]3却无御寒的衣被。他们一日三餐“煮法。先注水于釜。扭菜使断。投诸釜。加米少许。以代油脂。淡食。不加盐。因盐不易购也”[5]6,却无生活必需的油盐。他们为解决日常温饱“故苗地之闹饥荒。殆如司空见惯。以苗民之勤苦俭啬而顑颔不饱。鬻卖子女。以求升斗之食者。盖常见之。近数年来。此风尤甚。童稚数百。船载远贩。评值论价。如牛马然。有时其价之贱。更弗牛马若也”[5]4。
随着统治阶级于清朝中后期到民国初年对广西隆林、西林各民族的歧视压迫更甚,使该地区各民族尤其苗族的生活处境是“活动之面积日狭,活动之能力日低,而其生计,更属不堪闻问矣”[6]265。又如:“家君之出巡日记中有如左(下)一段,吾人读之,盖可见所谓好乱之苗人,未尝不是安分,而数千年之闭塞与压迫,实造成彼辈之销沉之意气,而绳以物极必反之理,于感情十分激荡之时,此种人之挺而走险,未尝固又越乎人情也。”[6]302“外人对彼辈压迫至若何程度,编者虽不甚了了;试举某苗酋门首所粘之对联如次,则彼辈好勇斗狠之习之所由养成,及其表现,可见一班矣。联曰:一旦祸起非常,欲携老幼孤寡,东奔西逃,何处能觅藏身地?顷刻计生方寸,呼父兄子弟,上撑下杀,方得今日残安家。”[6]300正是因为自身所处恶劣和艰苦的环境,加之遭受各种歧视和压迫,这也激起了各民族的不断反抗。
与广西隆林、西林各民族350年前“教化不行,版图不入”[6]7,“不事诗书,礼义罔闻,彝伦攸斁,动辄操戈,不知三尺。历代以来,屏居化外”[6]11,到100多年前“而无衣无食,则比比皆是,赤贫者亦极众,穿褴褛之麻衣,吃南瓜终生者,实大有人在”[6]266。“偏苗中之富裕者,百无一二,其外之九十八九,多以樵与佣为生;沦为农奴者,亦大不乏人。”[6]274“怪来家无主,国无王,连年地方撩乱,刀兵不息,水旱瘟疫,死亡枕籍,百物腾贵k3T0d91jtY0knOobQlKxmg==,捐税繁重,兵差横行,均昔所罕见”[6]303的悲惨生活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笼罩在广西隆林、西林六个民族头顶上长达上千年的乌云消散了,各民族人民看到了太阳,迎来了光明。如今的广西隆林、西林,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社会和谐,该地区各民族人民安居乐业。由此,当我们回望广西隆林、西林各民族历史,只有了解广西隆林、西林各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才能深刻体会到: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脱贫攻坚战取得的巨大成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绩等,都已一一惠及了各族群众。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因此,欣逢盛世的各民族干部群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从这个层面说,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抓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
(二)抓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其根本目的就是让各族群众过上好日子。以广西隆林为例,全县辖16个乡镇180个村(社区),总人口42万人。“十三五”期间,该县作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远山区、水库移民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和连片特困地区“六区合一”的贫困县。首先,贫困人口规模大,经2015年精准识别后,全县有97个贫困村,共19699户86712人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23.57%;其次,贫困程度深,该县克长乡苗族聚居的后寨村贫困发生率高达61.68%,该县德峨镇苗族、彝族、仡佬族三个民族聚居的么基村贫困发生率也高达49.54%;最后,贫困面很广,全县2185个屯中贫困发生率在50%以上的有222个,占比达10.16%;1013个屯贫困发生率在20%以上的,占比达46.36%1。
面对如此贫困状况,广西隆林党委、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牢固树立“不等不靠、主动摘帽”理念,以实现全县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为目标,以产业发展、转移就业、移民搬迁、生态补偿、教育扶智、低保兜底、医疗救助等“七个精准脱贫一批”为路径,共选派自治区、百色市、自治县、乡镇四级脱贫攻坚工作队员472名和全县7835名在职领导干部职工结对帮扶27770户贫困户(含2014年退出户3236户与2015年退出户4835户),整合资金投入59.31亿元,全面拉开了全县脱贫攻坚战序幕。在国家农发行、深圳罗湖区等有关对口帮扶部门的大力帮扶下,2020年,全县19699户贫困户86712名贫困人口全部如期脱贫摘帽2。在市县党委、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实现“三连好”成绩。实践证明,抓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有利于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有效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三)抓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近年来,广西隆林、西林党委、政府以争创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为契机,注重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尤其青少年要牢固树立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员的意识,让他们知道自己所属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注重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各民族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充分挖掘各民族文化的精神和价值,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多文化养分。同时,自200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以来,注重在各幼儿园、中小学和职业高中普及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有效解决了不同族群因语言不通而导致的隔阂问题。另外,基于“五个认同”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其具有增进民族团结、提升民族自信、增强民族凝聚、提振民族精气神、推动民族发展、促进民族融合的功能。广西隆林、西林党委、政府在推动争创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具体工作中,注重加强对各民族“五个认同”等的宣传,使汉族、壮族、苗族、瑶族、彝族、仡佬族等各民族在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中,树牢各民族间“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密切关系,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切实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抓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上来。
(四)抓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平等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广西隆林、西林各民族在居住生活、饮食习惯、劳动用具、互助帮工、岁时节庆、族际通婚等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团结和谐的社会关系,让各族群众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施行以来,广西隆林、西林历届党委、政府注重创新工作方式和载体,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深入持久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工作。广西隆林首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于1988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县城召开,大会共表彰了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22个;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130名,其中苗族34名、彝族6名、仡佬族5名、徕人(后来识别为仡佬族)3名、壮族61名、汉族21名[7]61。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仅广西隆林,先后有汉族陈隆生,苗族马绍英、杨光富、杨明福、王雪娇,彝族黄登林和仡佬族张恺婧7人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荣誉,有隆林各族自治县民委(即现民宗局)、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两个单位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荣誉[8]。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隆林、西林各民族干部群众倍加珍惜今天民族团结来之不易的机会,注重发扬民族团结、友爱互助的良好品质,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民族团结。由此,在广西隆林、西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外在形式中,随处都是“各民族饮用于同一口水井水、同捡一山柴,相互关照,彼此连心;居住于同一个村落中、同住一座屋檐下,相互依存,和衷共济;劳作于同一丘田地上、同耕一片热土地,相互帮助,和睦共处;就读于同一所学校中、同在一个班级里,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庆祝着同一个节日、同唱一首《欢乐满山坡》,相互包容,兼收并蓄;就职于同一个单位里、同朝一个方向干,相互亲近,共同追梦”的景况。全县5个民族都相互通婚,各民族密切交往交流交融,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分别娶或嫁不同民族的情况日益普遍,“四代同堂、情融五族”的家庭比比皆是,成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写照,促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得到牢牢夯实。
(五)抓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基础
一是广西隆林走出一条民族区域自治的法治化道路。1950年3月1日,解放军解放了隆林县城,隆林各族人民获得解放。1952年7月中旬,由队长莫虚光、副队长韦日高、兰昌法带领的中共广西省委民族工作队60人和中共百色地委统战部部长、百色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赵树同带领的百色民族工作队255人,先后来到隆林,吸收隆林各民族中的积极分子19人,组建了百色民族区域自治工作队。7月18日至29日,县人民政府在县城召开民族区域自治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各族群众代表和县、区、乡干部、工作队共696人[7]64。会议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中央、省有关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制定了《隆林县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初步计划》,决定在以苗族为主的五区(德峨)保上乡开展试点,建立乡(村)级自治区政权。在中央民族工作视察组的具体指导下,草拟了隆林县建立壮苗民族联合自治区工作计划、隆林县实行壮苗联合自治区宣传提纲[7]65。1953年1月1日,隆林在县城召开万人大会,正式宣告隆林各族联合自治区人民政府(县级)成立,1955年改称隆林各族自治县。二是隆林利用自身立法权优势,制定与修订地方性法规。如:1990年以来,发布了《隆林各族自治县自治条例》《隆林各族自治县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补充规定》《隆林各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目前,《隆林各族自治县野生茶树保护条例(草案)》正在征求意见和修订之中。隆林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进一步推动了其辖区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和地方经济发展,完善了不同时期民族区域自治法治体系,丰富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经验。三是开展法治宣传和执法检查等。隆林人大常委会和司法机关充分利用“国家宪法日”等时间节点,以分发宣传单等方式,开展法治进机关、进校园、进乡镇、进企业、进村屯等宣传活动,使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同时,隆林人大常委会还开展了执法检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等工作,要求地方自治机关保证宪法和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在本地方得到正确遵守和执行。以上做法,既为推进隆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提供良好的法治支撑,也在不断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立法、执法实践,有效地抓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基础。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10.
[2] 隆林各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隆林各族自治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853.
[3] 韦树关,黄如猛.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21:23.
[4] 《隆林仡佬族》编撰委员会.隆林仡佬族[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3.
[5] 刘介.苗荒小纪[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
[6] 王誉命,雷雨,杨登祥,等.西隆州志:广西西隆县苗冲纪闻[M].新加坡:浩宇出版社,2023.
[7] 隆林各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隆林各族自治县民族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8] 隆林各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隆林各族自治县概况修订本编写组.隆林各族自治县概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77.
[责任编辑:廖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