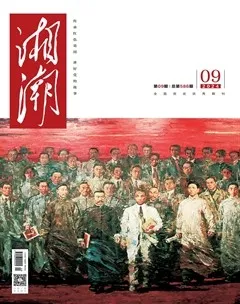心明眼亮意志坚,拨开云雾见青天
邓中夏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1923年二七惨案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陈独秀写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认为中国产业工人太幼稚,公开否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有的领导地位。与此相对的,则是某些“左”的思想,以为中国革命立刻就能取得胜利。二者都不能认清当时的革命形势,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也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上正确的道路。为此,邓中夏撰写了《我们的力量》等一系列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比较科学的分析。
阐明革命的前途和复兴革命的领导力量,是邓中夏1923年至1925年间撰写《我们的力量》等一系列文章的重要目的。五四运动后,邓中夏开始以主要精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说。1920年3月,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的有关著作。同时,邓中夏在蔡元培倡导学生走向社会、李大钊号召青年到民众中进行民主主义宣传的影响下,也明确了在大变革的时代必须投身火热的斗争才能寻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1918年,邓中夏就曾利用假期到唐山矿区接触工人,了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后于1919年3月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团多次赴城市、乡村、工场讲演,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并通过开办夜校、创办工会等方式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因此,邓中夏对中国革命前途和领导力量的分析,既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又立足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不迷失于一时一地的困难状况,不拘泥于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为中共四大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如何看待京港大罢工后的革命形势?
邓中夏在文中首先指出,中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当时社会心理趋向革命,但不少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人有着盲目急躁的“左”的想法和行动。邓中夏批评了“左”倾思想对革命阶段的混淆,指出中国革命尚且处于民主革命阶段,也批评了革命低潮中的右倾情绪。针对所谓工人数量少、实力弱的论调,他指出,工人“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实在比任何群众尤为重要”。因为经济所依赖的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实际上都由工人承担,“新式工业下的工人只有日益增多,终归有长成壮大之一日”。针对革命的长期性和光明性的辩证关系,他判断不是一日两日甚至一年两年的事,可如果因此而对革命胜利的前途发生动摇,那么“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即便“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
如何认识和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地位?
邓中夏指出,中国的革命尚处于民主革命阶段,之所以工人“革命的精神格外富足格外坚决”,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是格外比人厉害”的。邓中夏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当时的状况,对中国工人的行业分布、组织情况进行了仔细的调查统计。基于此,邓中夏回应了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两种怀疑:一是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构成出发,驳斥了“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无产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的观点;二是从中国工人的罢工历史和成就出发,阐明工人的觉悟“是由它被压迫被掠夺的地位反应出来的”“是随它的反抗的争斗之经验而发展的”,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必然产物,必然随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进行的活动的变化而变化。
邓中夏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强调了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从主观上看,“资产阶级固然是我们的仇敌”,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尤其是我们目前最厉害的两个仇敌”,工人阶级必须从谋求本阶级利益出发,独立地参加民族民主革命,巩固和发展经济斗争中已取得的自由和利益,通过先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这两个仇敌,得到初步的解放,再进而实行社会革命,打倒资产阶级,以得到全部的解放;从客观上看,因为工人阶级参加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工人运动的发展是推动革命目标实现和革命阶段进步的重要因素,邓中夏鲜明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因而“是任何革命方式之下应该特别重视而不可变更的”。
如何正确认识社会其他阶级?
对于资产阶级,邓中夏分析了中国资本构成及其社会关系,其中商业资本不可能脱离帝国主义关系而独立存在;银行资本与本国官僚和军阀势力交情深厚,并受到外国资本的操纵;工业资本虽然因为外资外货的不公平竞争和军阀混战的侵扰,具有革命动机,但是最终会因为利益而陷入调和妥协。因此,在中国资产阶级中,官僚买办资本的性质必然是反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因外资打击和军阀压迫而发展困难,但对于通过推动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以保全和增长其利益有所期待,也正是这种狭隘,它们变得软弱、妥协,最终“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对于小资产阶级,邓中夏指出其“有革命要求和倾向”,并且“比大资产阶级为猛进为坚决”。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他们的压迫更为深重,使得他们在生存发展上的境遇更为艰难。外国货物在质量上和价格上的优势使小资产阶级的产品滞销,实力雄厚的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组织起生产管理先进和机械应用普遍的大企业,在市场中占有率高,进一步挤压了小资产阶级的生存空间。但小资产阶级有着“资本微小”“组织亦甚为纷歧”“不能集中其势力”的特性,这是其生存境遇日益艰难的根源,也是其遇到顺境时急躁冒进、遇到逆境时左右摇摆的原因,因而邓中夏指出,小资产阶级“只能为革命的助手”。对于农民,邓中夏指出,中国的经济基础“差不多完全是农业”,农民人数“至少要占全国人三分之二”。他们“因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甚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种种原因亦驱使他们有加入革命之可能”,并已经通过当时发生在多省的抗税罢租运动等“痛快淋漓的把他们潜在的革命性倾泄出来”。但是农民存在的问题是“居处散漫,安土重迁,不易集中其势力”,因而要实现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重要的就是领导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一方面“尽可行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领导和帮助农民建立农会,“把散漫的群众都集中在一个组织与指挥之下”;另一方面进行教育宣传,针对中国自耕农佃农多于雇工、农民私有观念较深的现实,以“限租”“限田”“推翻贪官劣绅”“打倒军阀”“抵制洋货”“实行国民革命”等为口号鼓舞农民。
在《我们的力量》一文最后,邓中夏指出,通过分析革命的形势和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可以看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无产阶级需要一方面通过组织建设和斗争实践不断加强团结增强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积极团结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克服各革命力量微弱散漫的状况,领导联合起来的革命力量承担起实现“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两种伟大事业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