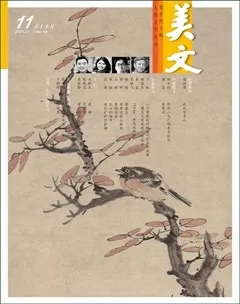又来“拿铁”
刘荒田 广东省台山人。出版散文随笔集、诗集多部。《刘荒田美国笔记》获首届“中山杯”全球华侨文学奖散文类“最佳作品奖”;另获“2012年度世界华文成就奖”、2015年“新移民文学笔会·创作成就奖”。
一
又来“拿铁”——老地方,旧金山格利大道和第16街交界处的“皮特”咖啡店。多少年了,不来这里则已,来必“拿铁”。是因为这店有炮制“拿铁”的独门功夫,还是因为家里的咖啡机打不出牛奶泡沫?我不加理会,习惯而已。拿铁的价格涨了几次,此前不到3美元,现在是4.35美元,外加小费。下单时服务员问我的名字,因为要等。
午后三点多,阳光凶猛,在常年雾气称霸的太平洋海滨,它因稀罕而讨人喜欢。外面的光明把店内衬得更阴暗。坐于室外最宜,风恰到好处,上有遮阳棚,但椅子都坐了人。里面,才七八个客人,一人占一张小圆桌,多数打开手提电脑,一副安居乐业的作派。靠窗的长桌只在头尾有人。我在中间落座,翻看报纸。柜台那边有人叫一个耳熟的英文名字,迟疑一下,悟出是区区,连忙走过去。
“拿铁”在手。侠士仗剑,扫视人间,问谁有不平事。我只嫌纸杯有点儿烫手。长桌前坐下,瞥一眼左边的芳邻,她比我先到一分钟,口罩把小脸遮蔽三分之二,无法知道其族裔和模样,正埋首于手机。我放心了。如今疫情依然肆虐,全美国已被新冠病毒收拾了70万人,保持社交距离是要务,我要确切地保证她没有把我视为威胁。
拿起杯子来呷,怎么进不了口腔?原来忘记拿下口罩。口罩湿了一片,有碍观瞻,拿下来,从口袋掏出备用的换上。这时发现,我没全错,桌上有店方的通告:“逗留店内须戴口罩,需要使用嘴唇方可除下。”
落地玻璃窗外,是号称全美交通最繁忙的格利大道。记起来了,这个位置已坐多次,贪图它和周作人所喜欢的“十字街头的塔”近似。他从小就是十字街头的人,位于华东的西朋坊口的故里,“十字街的拐角有四家店铺,一个麻花摊。一爿矮癞胡所开的泰山堂药店,一家德兴酒店,一间水果店”。这塔好就好在是“喧闹中得安全地”,一方面,便于和引车卖浆之流混在一起,“吸尽了街头的空气”。另一方面,有便于跳出来。毕竟,“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胸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
深一层品味,所谓“十字街头的塔”,用白居易的说法,是“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出仕也好,退隐也好,都有缓冲的空间。知堂老人此说,放到今天,未必切题。街上一点也不摩肩接踵,过分明朗的阳光下,空疏,虽然行人比闭户抗疫的去年多了。隔壁的墨西哥餐馆,搭在街旁的临时餐厅,十多张桌子,只有两个客人。车和人,都是过眼云烟。偶尔被“为牟”公司的车子吸引,一律是豪华车“捷豹”,顶上都带塔型转盘,左右前后带感应设备,街上游弋最勤,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驶过。这家新兴企业,近年接了各大汽车制造商的订单,承包自动驾驶试验。但看多就腻了。
好在有自然的眷顾。对面的罗西服装店门外的花坛,素馨花羞怯地开,看着心疼。功用与围栏近似的石楠,低矮的灌木丛而已,无花可开,枝梢的叶子却红得整齐而浓烈,分明在宣告:在枫叶怎么也红不起来的旧金山,秋季当令的是我们。
店里的看头多一些。暗处小圆桌,一个比我老的白人独坐,跷腿的姿势没变过,雕像似的。一个比我年轻的老头,三番五次从店里走出,往街心洒水,仿佛是施行一种祭祀仪式。各干各的,没有互动。
二
在奶泡沫的安抚和咖啡因的刺激下,思路清晰起来。为什么爱来这里?只因为这是我的“十字街头的塔”。然而,知堂老人所描绘的,和当下的出世入世没大的关联。我的私密之“塔”,方位在往昔和现实的交界。因为我和家小从故土连根拔起,首先落脚于此。
我喜爱的诗人向明先生,93岁写了一首《熬夜》,其中有这样的妙句:
这夜
浓浊如用力碾磨出的墨汁
有得让笔力煎熬的了!
且从这里眺望。如果时间是水,41年,于个人而言,说不浩瀚是假的。移民岁月的开端,近一万三千页日历,最先一沓页码从这里撕下。它纷繁多姿,跌宕迂回,岂不是“有得让‘脑力’煎熬的了”!然而,煎熬并非酷刑,相反,它可誉为最可口的食物,又容易咀嚼和消化,只嫌其少,亦如除夕夜的乡愁,亦如神定气足的早晨外出散步,为“前面还有多少里”而快意。如果你对此予以否定,请回过头去问通宵写诗的诗人:以夜色这浓浊的墨汁“煎熬”笔力,你会不会嫌夜太长?
……一个中国后生向我走来。那是1980年的秋天,一家四口搬到对面的第十六街355号。一身柳条纹黑蓝色西装,是在九龙弥顿道的洋服店买的,花了港币450元,系领带学了多次依然不上手,干脆省掉。他刚刚去下城拉肯街拜访早年在乡间因写诗而缔交,先我一年移民的诗人。进门后,诗人半开玩笑半正经地告诫新乡里:穿装不宜太“正式”,除非喝喜酒和参加葬礼。后生反问:上个月,我刚抵达金山大埠,你来看我,不是穿齐“三件套”吗?他搔头笑了,是的,第一次,让你见识一下金山客的派头,下不为例。相对大笑。
那后生就是我,32岁,浓黑的卷发,路上总是好奇地东张西望。中午,在诗人家饱餐了鲍鱼汤和牛排,饱嗝连连。席间,诗人腆着可观的肚子给我夹菜。他知道我为了他才分别一年多就增重30磅而惊讶,自豪地说:“没有这气势,岂不白来?”从诗人的家出来,乘38路巴士回家,下了车,看时间还早,到处走走,见识新环境。
那年,这家“皮特”咖啡店,是“万年实业公司”的办公室。“万年”的正对面,是一栋两层高,占地广大的商业大楼。门外贴着关张大平卖的英文广告。我按路标的指引,走上二楼,这儿是麦迪逊百货公司,因租约期满,清货走人。我在货架前,一如大观园里的同姓姥姥,一路发出惊叹。出国前只在高级宾馆见过的天鹅绒面长沙发,席梦思弹簧床,拿起价目牌看,标价有三四个,最高是一千,一路递减到跳楼价——一百多美元。在“奇货”前停伫稍久,笑眯眯的白种小姐就走近,问能帮什么忙吗?你再提问,她更热情,不厌其烦地解释,不喜欢这一种,好,请看这一种,可惜英语只听懂小半,虽然从当知青起自学了近十年。为了不辜负人家的盛意,我买了一套西装(因为诗人朋友暗示,我的柳条西装吊丧时穿较合适),花了20美元。一张八角形矮桌,模样别致,想不出放在哪里,也买下,冲着四块五的标价。花一美元给只有一辆旧自行车的女儿买了洋娃娃,当爸爸以来的第一次。回到家,精于购物的太太居然没予以恶评。
一口一口地喝“拿铁”,把回忆再逆推一个月。那天,全家从旧金山国际机场的海关走出,在岳父母家借住一个月后,便定居在第16街355号地下,由车库改建的小住所,装修简陋,地毯破旧,但在我眼里,档次高过家乡县城的华侨宾馆。工作也找到了,在离家八个街区的“海运”中餐馆当帮厨,月薪600美元,每天从上午11点干到夜晚10点,上工前去附近的教堂所开设的英文班上课。儿子上小学一年级,女儿在家由太太带。带家拉口的男人,不感到担子多重。以税后500美元算,扣除房租200,300美元足够日常开销,何况在国内时已是熟练车衣工的太太可接活,报酬够付房租。大体说来,生活远比国内轻松和富足。
如果有人问及:全新的人生可有乡愁?有,但不强烈。眼前的日子,谋生加上英语加上全新的人情、文化,已把思维填满,树梢的明月,冬至日的汤圆,都没激发特别的牵扯。比家乡好得多,这一由现实综合出来的结论,击退所有大而无当的思念。当然,给彼岸的父母和友人的信,是不间断地写的。低头弯腰在矮八角桌上写信太辛苦,跑了一趟下城,买下一张书桌和带扶手的椅子,花了80美元,即月工资的八分之一。16岁起就做的文学梦,暂时隐没了。
三
回忆真好,如果一口“拿铁”带起一桩有头有尾的往事,那么,别说小号杯,大号杯也嫌太快见底。奇怪的是,新移民年代的不适应、忧虑、意外、纠纷,一概未被记忆纳入,栩栩地活现于心间的,全是阳光下的好事。我体谅自家不得已的狡猾,老年难以承受太多的不快乐,记忆由本能选择。
哲人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然而,生命之川有回流,河床遗下鹅卵石。诗人洛夫有句:“咖啡是黄昏回家的一条小路。”我刻意放缓速度,让拿铁停留在杯子里,一如向明诗里的诗人,以诗笔将夜色化入形而上的永恒。脑际的影像,和照片一样,瞬息定格永久,还可以随意修改。
此刻所坐之处,即当年的“万年实业”,昔年无缘进入,只远远地瞻仰过门前上下车的瘦小的老板和高胖的太太,偶尔看到他们两个体积巨大的公子,肩膀阔得几乎和门扇相同。但它的贴邻——美新杂货店,是常常进去的,首先是看新奇,一个铺位的店,比家乡供销社的门市部小一半,可是货物丰盛到令人咋舌。其次是买酱油、豆豉、腐乳之类,尤其是家乡出产的。去多了,常常谈天。老板姓谭,香港来的,原籍开平,和我家乡相邻。他一家、岳母、内兄一家住处又在16街。他内兄在奥林匹克俱乐部餐厅当练习生,女儿和我儿子同班。这么一来,与远在天涯的亲人比,近邻倍感亲切。
拿起杯子,低吟洛夫的诗“一仰而尽/然后对着墙壁呼喊/杯底传来她隔世的回应”。诗里的“她”,我得换为“此处”。多情岁月,化为无数生动的意象,跃动在视线可及的四周。
……我走向16街355号,门前依旧,房东那从旧金山大学修满汽车维修学分的儿子,依然把开不动的旧车停在车道。40年前是两辆“保时捷”,此时是一辆“傲世无比”。从前地下只有滚轴式大门,颇重,开合都要伸手用力拉,六岁多的儿子从中练了臂力,一岁多的女儿只能靠妈妈。我们搬走后,加开了侧门。可是,我的回忆还得拉高滚轴门以进入。
里面,是经济紧巴而性情和乐的一家。缝纫机前,妻子低头赶工的身影映在墙壁上。破地毯上,女儿在骑亲戚送的二手三轮车。晚上,我在西餐馆当清洁工,酒吧的客人离开后才能开吸尘机,每天上班晚,9时才离家。此前埋在太软的二手沙发里小睡。两岁多的女儿在旁边嚷嚷,她妈妈低声说:“爸爸过一会要上工呢,很辛苦,你自己玩,乖。”这一幕我无数次地记起,连带记起女儿对妈妈说的悄悄话。那时她三岁半,够格进幼儿园。进园第二天,妈妈去接她回家,路上,妈妈说:“刚刚进去,一定不习惯,慢慢就好了,不要动不动就哭。”女儿神秘地说:“我不让人家知道,躲进洗手间才哭。”幼儿园也在16街,儿女的童年,在这里留下无数脚步和笑语。
我的36岁生日,也在这里度过。早上,我在书桌前写家信,客厅的电视机前坐着的儿子和女儿,激烈地争吵,为了过一会唱“生日快乐歌”时,是祝“爸爸”还是“爹地”。已读四年级的儿子洋化了,说要叫“爹地”。女儿反对。我隔着窗口做和事佬,说,都行,我喜欢。眼前,依稀冒起袅袅热汽,那是妻子做的长寿面。
然后,女儿从幼儿园毕业,和哥哥一起就读苏特咯小学。妻子进了车衣厂。我早上要送孩子上学。总是被把读书放在第一位的儿子叫醒。和儿女,数这一段路程最亲密,朝阳在金门大桥的橘黄色铁墩上方射下,带着灼眼的芒。路旁的三角梅和美人蕉滴着露水。雨天,我有了女儿不能抗拒的理由,让我抱起她,跳过水洼,可是,一旦看到行人,她就要挣脱,非要自己走。这是后代为自立做的最初演习。
古人云:靡不有初。有什么比得上“初”。73岁的男人,最放肆的梦想,就是再“初”一回,都来吧!新移民的苦难。患坐骨神经痛的帮厨,中餐馆厨房的洗碗槽前一站就是十个小时,从屁股到脚跟的酸麻,迫得我不断地变换站姿,却不敢停下剖石斑鱼和鲍鱼的手。那时,钟走得太慢太慢,一天有如与天地比寿的长。好极了,打包还给我,为了它的长,我接受这难忍的疼。
都回来吧!新移民的野心。梦想当诗人,不敢指望靠稿费养活一家,可是,变为铅字真难。同道者老南,这位在家乡结交的诗人,爱在半夜来电,喂,刚刚写好的,题目叫《献给圣诞树》,念给你听听。我明白,他的得意是必须脱颖而出的,管你的呵欠让话筒震颤。我听着听着,歪头睡了,醒来,听筒响着豪迈的朗诵声,啊,白胡子圣诞老人……
都回来吧!花三千美元买的八缸雪佛兰,哪怕这老爷车长了锈,破了几个大洞。深夜在归家巴士上邂逅的黑人,两人热络地聊天,我用较结巴的英语,他用更结巴的广东话。到了站,他随我下车,我不敢径直回家,在这一带徘徊了两个小时。大街上,仿佛留下我和他被路灯拉长的影子。“皮特”斜对面的铺子,如今是银行,从前是多米诺披萨店。儿女缠着妈妈去点一块。刚刚出炉的披萨,面上的阿莎啦啦乳酪雪一般白,那是岁月的温柔。
拿着太轻的空杯,忽然感到空虚,因为无法调出更多的记忆。环顾店内,人也走得差不多了。柜台内传来搅拌器的声音,但不见人进来,可见是用手机下单的,该也是“拿铁”。我要不要续杯?算了。
走出“皮特”,向16街355号旧居回眸,怀深沉的歉意,因为与早年记忆联系最紧密的房东阿婶,已成故人。搬出后三十多年间,不知和妻子念叨了多少回,要去看看阿婶。去年中秋买了月饼,下了决心,即使无法以电话预约,也要当不速之客,但临行前,从阿婶的同村乡亲那里得知她几年前辞世。下次来“拿铁”,要祭奠这位恩人。
关于这里,还有的是回忆。以后仍喜欢回应向明的诗,让“往事”这浓墨继续煎熬脑力。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