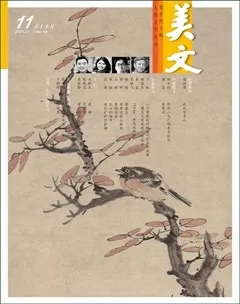退休
黄宗之 湖南衡阳人,医学硕士。曾在南加大做访问学者,从事肝癌分子生物学研究,后转入欧洲一家生物制药公司美国分公司研发部任职,工作至2022年初。在《北京文学》《小说月报》等杂志和美国华文报纸上发表小说、散文等多篇,另出版长篇小说多部。现任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北美华人作家协会理事,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常务理事,《世界华人周报》文学版和综合版主编。
2022年2月底的一天,分公司副总裁召集我们研究部门开会。人事部门经理来到会场,她突然向我们宣布总公司决定:由于疫情的影响,以及洛杉矶地区的运营成本过高,公司进行机构调整,洛杉矶分公司出厂的相关制品将陆续转移到成本低的北卡州生产。洛杉矶分公司研究部门关闭,所有研究人员在2周后被裁员,公司将给予每人6个月工资和1年医疗保险补偿。
这个突然而至的变故,让我心里咯噔一下,十分错愕。公司没有任何经营不善的迹象,却突然间决定解雇我们,这让我一时难以接受。同事们都处在巨大的震惊与不安中。
会议简短,一结束,人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心情各异,无奈、激动、沮丧、焦虑各种表情全写在脸上。我们研究部门十几个人被安排与人事部经理单独面谈。离开会议室,我迫不及待给妻子雪梅打电话,告诉她这不幸的消息。
她先一愣,很快镇静了下来对我说:“你刚好到了退休年龄。”随即安慰我,“没关系,公司付给6个月工资补偿,你以后可以拿社安福利,就好好安心在家里休息吧。”
她的语调平静,甚至还有一点欣幸,我原本紧绷的心情放松了下来。我同实验室的同事埃薇琳与我同龄,她在公司工作了40年,一个月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她亏大了,离开公司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埃薇琳的上司肯(Ken)早说过打算明年退休,想匀出更多时间好好享受人生,可年龄还不够领取社安福利。与他们相比,我却幸运很多,随即,我的心里油然而生出一种因祸得福的窃喜。
在此之前,我并没有现在退休的打算。我实在是太热爱我的工作了,信誓旦旦地对雪梅说过,我想工作到干不动的那一天为止。
可自从朝夕相处、和睦得犹如家人的工作伙伴一个个先后退出职场,雪梅和两个女儿也希望我从繁忙的工作中退下来歇息。我不打算退休的决心动摇了,犹豫不定,心绪难安,很挣扎,左思右想,难以决定是不是真该选择退出职场?
回到办公室,我独自坐在已经待惯了的熟悉环境里,想到很快就要离开这儿,心里感慨万千。
一晃,来美国已经27年。我曾在大学实验室做研究,后在这家生物制药公司技术部门工作至今。这个当初只有2000多人的小公司经过21年的成长,发展成为了拥有2.5万人大公司,名列世界三大生物制品公司之一的国际100强科技创新企业。我也由普通技术人员一直升任到资深科学家。20多年的相依为伴,我深深地爱上了基立福。它拥有令人舒适宽松的文化氛围,我们部门研究人员来自不同族裔,大家彼此互助,和睦相处,每人都潜心于自己的研究,工作让我的日子过得充实而富有成效。几乎每一个工作日的清晨,我开车离开家门,都是满怀喜悦,兴冲冲地奔往公司,期盼着崭新一天的开始。我常常是在忙碌中度过的,从不同的研究课题的实施中获得新的启迪、新的发现,得到新的结论。当公司请来患者讲述我们研究的药品让他们重获新生时,我倍感到工作的意义,以及生命的价值。在一个随时可能遇到变故、没有安全感的异国他乡,我安安稳稳地过了20多年相对平静而优裕的生活。正因为此,工作让我感到快乐和幸福,所以我不打算退休,想继续在公司里工作。我不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快乐,希望这一份幸福更加长久。我更是希望自己尽其所能地把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加倍地回报给公司,回馈给社会。
现在好了,用不着我纠结。我安慰自己,既然公司替我作了决定,我就安心退休吧。
离开公司的最后一天,我们部门在餐馆里举行告别聚餐。曾经与我们共事过、早已离开的研究人员全都赶了回来,大家相聚在一起,同我们说再见。10年前曾与我一同工作的同事凯蕾也来了,这位白人女博士毕业后就被副总裁史蒂文招聘到我们研究小组,与我共事了七八年,现在希望城研究所里担任实验室主任,她买来两大束鲜花送给Ty和我。获悉我们部门裁员消息的新朋旧友,纷纷来到我家探望,或请我去餐馆聚餐,庆祝我即将开始崭新的人生。
可是,在真正退出职场的第一天,我的心情相当地乱。早晨起来,不用再开车去公司上班,自己莫名其妙地不知所措。一整天里,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掉这富裕的时光。不做研究了,我还能干什么呢?突然离开了周而复始的忙碌,我感觉自己成了一个被轰轰烈烈社会抛弃了的人,我的人生价值不再有了,变成了一个对社会不再有意义的人。我的心情特别地沮丧,曾经家中唯一的男人,不再是一家人的顶梁柱,按月拿回的优厚薪金也不再有了,支撑了我几十年的男人自尊骤然遭贬,对社会和家庭都不再有实质的贡献,我很失落,心情特别难受。我有一种被人为地拉下了曾经光彩夺目人生舞台的惆怅,好似骤然陷入了一片昏暗之中,看不清前路。接下来的日子我还能做什么?想到这,我不禁伤心起来,独自闷在家中,抑郁得直想痛哭。
就在那天,与我一起打网球小我十多岁的朋友戴峻打来电话问候我,见我心情不好,赶来我家。
“人生不仅只有工作呀!你现在有了更多的时间,为什么不好好去做一些曾经想做但没有时间做的事情?你完全可以把退休后的生活过得比以前更加丰富和精彩!”他鼓励我开始全新的自己,为新的一段人生重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提出来陪我去社区大学一同选修文学课程;第二天邀我去公园散步;周末,他与妻子开车拉上我和雪梅一块去野外春游,请我们在餐馆吃饭。此后的一个周末,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管云彬博士和他的妻子葆茹又设宴邀请我们网球队几对夫妻到他们家聚餐,庆祝我退休。
在妻子雪梅和朋友的悉心关怀下,几天过去了,我的心情渐渐地好了起来。
是的,我们的人生总会有一段一段不同的里程,生命的每一段路程都有它的价值,我们应该主动去寻找和发掘,有意识地赋予它新的意义。只要认真想一想,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做好规划,我们是能够把握住该如何好好地度过下一段人生路程的。
我从消极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变得积极主动了,打开电脑,替自己制作了一个表格,规划整年、整月,甚至每一天可能做的事情。我为早晨、中午、下午、晚上列出了好些项目,写小说、写家族史、写自传;读文学经典、看影视名作;打网球,去健身房锻炼;研究健康饮食、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出游世界,亲近大自然;主编文学刊物,替他人做嫁衣搭舞台;为中美文化交流、人民和睦友好做桥梁;在社区当义工,为社会进步作奉献。
离开工作至今,我退休马上就要到一年了。回头看,这一年我究竟干了些什么?真的,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远比过去过得丰盛。
在一年里,我出国旅游4次。3月份与妻子和两个女儿乘飞机到佛罗里达,坐游轮一周,在加勒比海三个国家旅游。5月9日到19日,我去了在法国南部靠近地中海的美丽古城Narbonne,参加在那儿召开的欧iHDW/nEBcDpBFu5xU6BdK37c9hAnEUFBcRqnQTkc6Ao=美作家笔会。接下来马上又与雪梅到埃及,与老乡杨福生、平平夫妻俩乘坐游轮在尼罗河上旅游。7月份,应加拿大出版公司友人张辉先生之邀,由他出资,到温哥华参加“温哥华文学周”,在华人作家协会冯玉会长家为我举行了一场新书《艰难抉择》研讨会。
我利用洛杉矶作家协会原有资源,与《世界华人周刊》合作,协同欧洲、澳洲、北美、东南亚、日本等地华文团体共同创办和主编了海外华文文学专版,于每周定期刊登在《中国日报》副刊上。自2022年3月创刊,10月再与欧美影视协会合作,增加了综合版,刊出影视、人物等专辑,各板块共出版了76期专版,有效地展示了各地华文创作成果。此全球协同共谋一刊之举在海外华文界尚属首次,旨在推动各地区华文文学的均衡发展,促进海外华文文学共同进步。我与这些团队的编辑人员不遗余力,以推动海外华文界的合力发展为宗旨,得到《中国日报》社长江启光先生的大力支持,形成了一个国际化的海纳百川的媒体强强联手的良性局面,为海外华文界搭建了一方巨大的国际舞台。作为《世界华人周刊》的主办合作单位,由协会王伟副会长领导的洛杉矶专版编辑团队,我出钱给美编为华文作家叶周排版专辑,推出该平台的第1期,为之后的世界各地专版树立一个可以借鉴学习的范式。
我完成了一年内的文学创作规划,主编了一部我们家族的家史文集《寻根——我们家的共同回忆》,由女儿安琦出资2500美元,在2023年初完成了编辑工作,交由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影视集团印刷100本精装本,分发给国内的家人保存。邮寄了20本给浙江传媒学院朱文斌院长,请他代为转交给国内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教授学者。与此同时,撰写了30多万字长篇纪实作品自传《风雨兼程》初稿,目前正在修改完善,在2月底退休整整一年时封笔。
没想到,我干的事情还真不少。时间充裕了,安排自由了,我竟然有远比在公司里做了更多更广的事情。的确,那些曾经想做而没有实施的计划,现在可以好好地进行了。我比过去活得更加潇洒、更加自由,过得更加充实和富有意义。
如今,在生命已经开始的另一个驿站里,我寻找到了重塑生活的崭新意义。也许我们并不需要有特别的意义,只要好好地健康地活着。但,我还是想赋予另一段人生新的价值和内涵,让生活尽可能地丰富多彩,在最后与世界告别时,我能够安心地告慰自己,我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尽其所能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为之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奉献。
我没有辜负生命,没有辜负有幸来到过人世间。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