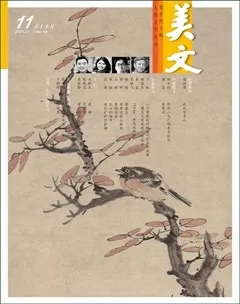在北美,兼议游戏
张 华 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出版《伯明翰文化学派领军人物述评》《生态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构》《阅读哈佛》《全球伦理读本》《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诠释》《对外汉语:理论与实践》《人文学术:东方与西方》《东学西传:国学与汉学》《文化与全球化》《国际中文教育散论》等著作。
“汉风专刊”《百期絮语》(2024年第8期)曾言:在前100期中,我们也曾尝试以“栏中栏”的方式发表一些传记散文,比如“汉风人物”等。今后,我们仍会根据实际情况设立“栏中栏”,并会做一些机动调整,以满足更多读者的阅读需求。
当写下这段话时,其实思考更多的是当初创办该栏目的一些设想。比如,除了修改编辑栏目稿件并写作导语或评论文章,是不是也应该写一写散文作品?作为对专刊稿件有先睹为快优势的主持人,在阅读本期“北美华人散文小辑”的3篇佳作后,又勾起我对北美时光的回忆,以及将其记录下来的冲动和愿望。同时,又联想到对近期火爆的网络游戏话题的一些看法,随即就有了这篇主持人语的题目。
之所以未能在创办该栏目之初就着手实现这一初衷,主要还是因为多数外国本土作者的中文写作水平还达不到发表要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中文普通话讲得非常流利,甚至可以讲地道的中文方言,说相声,绕口令,开各种玩笑,但真正让他们写作,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不少外国本土作者都是先用自己的母语写作,然后再翻译成中文。即便如此,实事求是地讲,有些作品仍很难称得上“美文”。这就需要栏目主持花费大量时间亲自上手做调整、编辑、修改和完善甚至补充翻译工作。如此,也就没有时间写自己想写的散文了。其实,这些外国作者的文稿不能满足杂志要求也很正常,因为并不是每一位口语流利、讲话生动的人都可以写作同样美丽动人的文学作品,不少外国作者可以用中文口语讲述动听故事,但让其创作就成为难事;而事实上,对于中国作者也是一样的,他们可以用口语把故事讲述得生龙活虎,但一到让其落诸文字,就变得相当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都有从小学到大学的本国语文教育的原因。与此同时,对外国人进行国际中文教育教学的重要性也在此意义上得以进一步彰显。在过去,很多国人并不认为教外国人学中文是什么难事,更不会把它视作一个专业或一门学科、学问,认为只要自己会说中文,就能教外国人学好中文。有些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在报考专业时,也多少会有这样的认识,觉得国际中文教育应该是一个容易学不会挂科的专业。前段时间坐出租车去学校,司机师傅问道: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有什么区别?你们都教什么语言?答曰:“北语”和“北外”虽然都教外国语,只是“北语”教的外语语种比北外少很多。然而,这并非“北语”和“北外”最大的区别。通俗地讲,“北语”和“北外”最大的区别在于,“北语”以教外国人学习中文为主,“北外”以教中国人学习外语为主。司机师傅听到回答,笑道:那我也能到“北语”教外国人。于是,这话题立刻变得没办法再聊下去了。
事实上,如果建议对方换位思考并进行反问,也许可以较好地理解和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可以问与司机师傅有同样想法的人这样一个问题:你如果是一位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是愿意随便找一个会说中文的中国人(比如出租车司机)教你,还是找一位受过专业训练和教育的职业中文教师?或者:你如果是一位到外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是愿意随便找一位会说外语的人(比如出租车司机)教你,还是找一位受过专业训练和教育的职业外文教师?
写到这里,突然发现我的“张氏飞鸽体”又来了。“张氏飞鸽体”这一称谓,来自在香港城市大学担任过11年校长的张信刚先生。他在为《阅读哈佛》作序时写道:虽然这本书的题材很广,时间和空间跨度都很大,但它有一个非常明晰的脉络,更有一个十分突出的主题——哈佛。不论是《写给高中儿子的赴美建议》中的谆谆教诲,《呼唤哲普》中的反学究态度,还是《盖茨、星巴克、FACEBOOK 及其他》中的消费漫谈,它们的出发点都是哈佛。好似一个传信飞鸽的主人,从哈佛这个基站放出一只又一只飞鸽,每只鸽子都会依照主人的指令飞往不同的目的地。所以,我想我可以将这本书的风格称为“张氏飞鸽体”……到哈佛大学读书,是我第一次到达北美,这一次在北美住了一年多,一些经历记录在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阅读哈佛》一书中。该书第一次印刷后供不应求,次年又第二次印刷,第二次印刷大约3000册,有2000册被当时的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现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购得,主要用于向公派出国人员行前培训时赠阅。有位外派至美国洛杉矶领事馆工作的北语教授在受训前曾得到过签名版,所以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就向同行的公派出国同事“炫耀”,据他后来回国后所述,当时的同事都还很羡慕。
再次到北美也是在《阅读哈佛》出版的2009年。不过,这次不是到美国,而是到加拿大的温哥华。为期一个多月的活动,是由当时的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组织的首届(后来居然成为了唯一一届)“第二语言习得研修班”,来自全国首批24所有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院校的24位代表,由国家汉办的领导带队,在温哥华U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全天候密集课程培训。这一年,我从美国回国已满两年,即从哈佛大学回国的第三年。在这两年内,也还是有不少再次赴美的机会,但若持J1签证再次赴美,就必须距上次离开美国满两年,这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外交协定。当然,持商务或旅游签证(B1/B2)再次入境美国是不受此限制的。在UBC研修和在美国使馆办签证所经历的故事,我会在今后的散文当中讲述。
我曾经翻着旧护照计算过,自第一次从北美回国后至疫情之前的十年间,我曾有26次踏上北美土地的经历,感觉当时“去趟北美就如同去了趟北京郊区”,而这话是当年我在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读书时,我的老师在波士顿的UMASS(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参加学术活动并进行讲座时说过的。这十年,仅仅是发生在赴北美航班上的故事,也可以讲个“三天三夜”。然而,三年疫情之后,尽管我年届70的老师还马不停蹄地为欧洲中心的各种事务奔波于中欧、中美和中非之间,我也有多次再赴北美的邀请,但是,在我心中却感觉那里成了一片陌生的土地,一想到要乘飞机航行那么远的距离,那么长的时间,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不安甚至恐惧,也不再想对人讲述在航班上的经历和故事了。不过,我会把这些经历和故事记录下来。如今,虽然日常穿梭往来各大洲的人非常多,但每个人的个体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每次的经历也都是不可复制的,这就如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执教北京语言大学 20 余年来,我已指导和培养了 100 多位来自世界各地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硕博研究生,推荐至海外读书的中国学生学者更是不计其数,他们也有着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旅行、求学和生活经历,所以,我也常鼓励他们要讲述和记录。
许多经常往返于中国和北美之间的学者,大多都会有出行前对乘机的不安甚至恐惧,特别是单独行动和到一定年龄的学者。曾有一年内 10 次往返中美之间经历的UCF(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英文系主任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Murphy)教授就曾几次跟我说,每次制定来华计划时都信誓旦旦,期待中常常兴奋不已,但临近动身的头一天却常常有“打退堂鼓”的想法,每次都要“再下决心”,直到登上航班,准时、安全起飞才会稍稍安心,而平安到达看到前来接机的人才能彻底放松。回程的时候,大致也有同样的焦虑。所以,他说他似乎得了“乘机焦虑症”。我与墨菲教授是有20年交情的学术朋友或曰同事,我的学生在10年前写了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并出了书。如今,我居然在每次长途旅行前也有了与他同样的“焦虑症”,又成了同病相怜的病友,对他当年的感受就又有了更深更进一步的理解。
对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游戏的人》(Homo Ludens)的首次阅读,也是在飞机上进行的。作者在自序中曾说: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人类学及其姐妹学科迄今为止在游戏这个概念上花的力气实在是太少,它们对游戏这个因素对文明的极端重要性下的功夫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在第一章“作为文化现象的游戏”中,他说道: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人类文明并没有给游戏的概念追加任何基本的意义。动物和人类一样游戏。只需要观察小狗就可以明白,人类游戏的一切要素在它们的嬉戏中已然存在。它们用认真的态度和体姿,邀请对方一道玩耍。它们谨守规矩:谁也不许咬,至少是不能使劲咬,同胞兄弟的耳朵是不能咬的。它们会假装极其愤怒。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切嬉戏中,它们感到无比的快乐,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样的喧闹打斗仅仅是动物游戏的比较简单的形式。还有更加复杂而高度发达的形式:正规的竞赛和美丽的表演,在场的观众则以钦佩的态度仔细观摩。
这不由得让我想对目前市场上流行的“两大类游戏”作些个人评价。需要说明的是,这纯粹是把游戏作为一种文艺或娱乐形式来评判的个人看法,“两大类游戏”也是我的个人分类而已。在我看来,评价目前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游戏,仍可用评判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的视角来展开,即仍可用“战争”“武打”“暴力”“豪放”与“爱情”“唯美”“言情”“婉约”两大主题进行分类,或可用美国好莱坞大片与法国细腻片进行分类。前者以最近火爆市场的深圳游科公司产品《黑神话:悟空》为代表,后者以祖龙娱乐产品《以闪亮之名》为代表。而前者之所以能够突然冒出水面、激起浪花,后者却总是默默地潜行于水底,乃是由其主题的性质决定的:战争的勇猛必然制造出喧嚣轰动的大动静,爱情的美丽必然表现出安然温婉的小姿态。而且,从人类历史来看,前者也基本总是占据上风。美国好莱坞取材于中国文化元素拍摄的动画片《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均具有扣人心弦的战斗场面,而我们至今也还没有看到大片制作公司,将被视作东方“罗密欧与茱丽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制作成动画片或游戏。我曾与游戏界的权威业内人士探讨过这个话题,他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理解成本太高,曲高和寡;而战争主题就是凭技能拼杀和“你死我活”,它迎合了很多人的隐形需求。“理解成本太高”,说得太好了。在我看来,“梁山伯与祝英台”哪怕与“黑神话”同样进行3A制作,也难以获得与“黑神话”同样的市场和效果。另外,这些也必然与人类的现实处境有关。当今的世界并不太平,战争正在发生,人们渴望正义战胜邪恶,渴望除暴安良与定海神针的力量。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