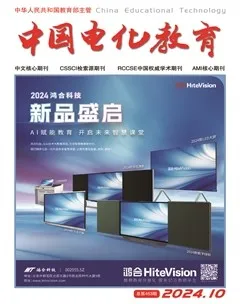知识如何通达素养
摘要:厘清知识与素养之间的关系,是推动素养教育落地的关键所在,而该关系的“厘清”,不在于两者间关系的有和无,而在于解释清楚如何从知识通达素养,即说明其关系的必然性与内在关联机制。对此,该文基于胡塞尔现象学并结合皮亚杰认识论思考中的“两个范畴说”进行系统分析,得到如下认识:知识的发生同样是素养的发生,知识可以通达素养且必然由知识通达素养;知识的发生同时也是思维的发生,由知识通达素养的途径是“我”的思维过程;主体性发展即是素养的发展,在认识发生的立场上,完整的主体性可以由个性化、身体在场、感性理性协调以及他者在场来保证。最后,该文简单回应了在当前数字化时代,应该如何看待知识和素养之间的这种关系。
关键词:知识;素养;思维;认识论;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受2022年度安徽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混合学习环境下高校教师评价素养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AHSKQ2022D095)资助。
素养教育既是国际潮流,也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如何实现素养教育,特别是知识与素养的关系究竟是何,大家一直在探索。新课改伊始便发生了一场关于素养教育要不要从知识开始的著名争论但悬而未决[1];国家课程标准以给出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方式来诠释专家们对知识与素养关系的理解但备受质疑[2];近年伴随“核心素养”dVA+TosfzISTyuCHuiTHyw==概念的引进,国家层面推出《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3],各学科课标均给出自己的学科核心素养,将其作为课程落地过程中引领素养教育实践的直接指针,此时似乎是认为三维目标与核心素养相冲突,比如在推出的新版课程标准中将三维目标隐去[4],显现出对知识与素养之间关系的彷徨,针对这种现象有学者指出,三维目标与核心素养并不冲突,应该是互相支持,有了核心素养不再谈三维目标是个误解[5]。由此可知,学界对于知识与素养之间的关系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此种状况既是理论上的不足,也必定不利于素养教育的落地,需要通过不断思考尝试寻找新的答案。本文的做法是:从理论源头出发,梳理知识与素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与关联机制,从理论层面论证知识为什么能通达素养,并设法给出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系统回答知识应该如何通达素养。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知识与素养的关系问题在胡塞尔发生现象学中有系统性贯通,尤其是胡塞尔在认识发生立场上关于“我”与“对象”关系的解释,是理清知识与素养关系的起点;胡塞尔现象学成就中的个性化构造、具身、感性发生以及交互主体性思想,还可以进一步解释走向一个完整的“人”的主体性发展问题,也即素养发展问题;另外,本文还倾向将以皮亚杰“两个范畴说”为核心的发生建构哲学思想融入胡塞尔认识论框架中进行系统讨论,以充分展开对认识发生细节的关切。皮亚杰与胡塞尔的认识论研究本质上都是对康德先验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将皮亚杰的认识论成就纳入胡塞尔思想体系中相互补缺一并把握是合理的思考方式[6]。
一、知识与素养之内在关联
回答“知识如何通达素养”这一问题,不仅要弄清楚知识与素养之间的内在关联,还要率先说明两者间关系的必然性,这在胡塞尔现象学成就中可以找到依据。
(一)胡塞尔认识论现象学中我与对象的关系:“它-我”结构
哲学的根本任务是通过对“真理是什么”的追问不断追求世界的“真”,而其中认识论是研究人类认识的起源、本质与基本规律的哲学分支。胡塞尔的认识论成就亦可称为发生现象学,它通过在认识发生视角中对现象与本质之关系的重新考察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变革。在传统哲学那里,现象与本质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不管是古希腊的“本质居于现象之先”,还是康德时期的“本质居于现象之后”,都没有将“我”(认识主体)、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解释清楚[7]。胡塞尔开启了“现象寓于本质之中”的逻辑研究进路,认为本质(真理)是由认识主体在“看向”现象时当场构成的认识成就。也即,本质(真理)是认识主体在与现象相遇的过程中当场被构造出来的,认识主体每一次“看向”现象,都会直接与本质(46O518HWFgF8inZxJeDSUA==真理)相遇。胡塞尔用认识主体主动的意向性详细解释了这一过程。意向性,即意识的指向性,是指认识主体的意识总是朝向某物的意识[8],比如,“我”听到一首歌,看到一棵树,爱我所爱,念我所念……不管意识活动的对象是否真实存在,“我”的每一个意识经验都是意向性的。因此,意向对象既不是外在对象的映射,也不是原本内在于认识主体的,而是在当下发生的认识活动过程中由认识主体内部活动构造而来[9],是认识主体意识本身的意义构造。随着关于发生细节的不断揭示,胡塞尔最终走向了发生现象学,实乃建构了基于发生思想的系统的认识论逻辑体系。
进一步,在胡塞尔看来,认识主体在构造对象的同时也在构造自身。也即,在“我”构造对象的那个当下,“我”获得了对世界的了解,与此同时,“我”自身也在同步发生发展。在这里,认识主体的构造行为中含有一个“对象-自身”结构,在人称转换上,可以将认识主体构造的对象视为“它”,将认识主体自身视为“我”,由此可以得到一种基于“它(对象)-我(自身)”关系展开的“它-我”结构。我们可以在胡塞尔的时间与发生思想中进一步对“它-我”结构展开分析。在“它”的方面,认识的发生和意向对象的构造,描述的都是那个当下的认识活动,也即,构造对象(它)更注重当下构造,在那个当下,“我”构造了什么。在“我”的方面,即对构造自身(我)而言,既要看当下发生,更要看历史发生,这就涉及到胡塞尔所言认识主体自身的历史构造问题。从认识论视角来看,历史构造是指发生在过去但是被留存下来且能够为以后的认识发生奠定基础的认识结构[10],由于每个认识主体的历史构造都是不同的,这就导致当下构造的对象的差异性,同时也导致构造自身的差异性。概言之,时间性分析进一步对“它-我”给出说明:虽然构造对象发生在当下,但也必定和自身的历史构造相关,和“我”自身的构造相关,因此也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且构造对象和构造自身是同时发生同时完成的,是相辅相成内在一致的。
(二)从“它-我”结构到“知识-素养”结构
在教育场域中,认识发生过程即为学习发生过程,这时“我”的意识所意向到的那个对象“它”,即是“我”在与现象相遇的过程中构造出来的知识,因此,“我”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转换为“我”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得到的启示是,知识作为对象是由“我”在学习发生的当场构造而来,这与当前流行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知识观有着很好的一致性。“我”作为一个学习者当下构造了知识,获得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受历史性视角中“发生-构造”的认识的支配,“我”构造的认识成就不会立即消失,而是“作为非反思的‘背景’存在于此”[11],即在“我”的心灵深处积淀为个人的“习性”,这种“习性”包括稟好、个性、能力、气质、性情、品格、素质等所有后天获得的习惯或属性[12],构成了“我”的人格之具体内涵,在作为部门科学的教育学意义上,便是素养的直接体现。在学界已有研究中,将素养指向人的内在品质基本达成共识[13]。因此,认识主体在历史性视角中通过构造自身积淀而成的“习性”即是素养,也即,“它-我”结构映射到教育语境中可以转换为“知识-素养”结构。这说明了知识与素养之间的必然关系:“它”是对象,是认识主体构造的知识;“我”是认识主体,“我”在构造知识的过程中自身也在发生变化并因此促进了自身素养的积淀与发展,在先验哲学的立场上,也是为“我”未来再次构造知识准备好新的前提。“它-我”结构解释了对象与主体一同构造的过程,“知识-素养”结构也就解释了作为对象的知识的构造与“我”自身素养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知识-素养”结构为当前学界坚持素养教育要以知识为起点的这类观点提供了直接的学理依据,也即:从知识构造的严格逻辑的立场看,素养教育必须也只能从知识开始,伴随知识的构造发生,学习者的素养发展才能得以实现。
从当下和历史的视角再次审视“知识-素养”结构,可以得到更多内涵。从当下的视角思考学习发生过程,可以更准确地描述学习者的学习结果[14]。相对而言,学习者自身素养的积淀是一个历史性过程,是在无数个当下知识构造的前后勾连中完成的,是经过一个长期且足够广泛的自知识构造开始的学习过程。因此,构造对象和构造自身虽然是同时完成且内在一致的,但是必须坚持站在当下和历史两个视角分别审视它们。即时间性包括两个分析侧面,一是当下发生,二是历史发生,对两个侧面进行分析,才能获得时间性的全貌,对本文而言,才能获得学习者的知识构造与素养发展之关系的全貌。
二、知识通达素养的途径:“我”的思维过程
由“它-我”结构演绎而来的“知识-素养”结构解释了知识与素养之间的必然关联,那么,在“它-我”结构的发生与发展中,知识与素养之间是如何实现关联的?其关联的内在机制是何?这一问题还要借助皮亚杰的“两个范畴说”展开分析。
(一)“两个范畴说”与“它-我”结构的发生发展
在本文的立场上,皮亚杰的首要身份不是儿童心理学家,而是热衷认识论研究的哲学家,因此需要越过那个为我们所熟悉的作为心理学家的皮亚杰而看到作为哲学家的皮亚杰[15]。皮亚杰的哲学认识论思考的突出成就是在范畴研究中创造性地引入发生学思想,借此对康德那里一成不变的范畴是如何发生发展的进行了解释,给出了新的知识观。皮亚杰继承了康德的先验范畴思想,认为范畴的内核就是主体所具有的结构性7RpcKdHucqvdsJ3Ira2zFD4A+aiu4h0mCEvosxG6bSU=先验认识条件,但需要进一步将其一分为二用于刻画范畴的发生发展:其中一种认识条件是主体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使用,称之为“物理范畴”;另外一种认识条件是主体在内部协调时发挥作用,称之为“逻辑数学范畴”。物理范畴所指是一种由概念所说明的先验结构,在认识发生的过程中,认识主体必须用概念来综合感觉材料。被物理范畴统整的概念性内容,还需具体的逻辑判断才能实现意义,这一逻辑判断即是在逻辑数学范畴相配合的作用下实现的。例如,“我”看到一颗苹果树并在大脑中当下构造了一颗苹果树,得到“这是一颗苹果树”的判断,在这个认识中,不仅有概念(苹果树),还有判断逻辑(这是……),该判断是物理范畴与逻辑数学范畴一并运动的结果。在“我”作出“这是一颗苹果树”的判断的那个当下,大脑中原本空的概念被填充了内涵,逻辑便成为有意义的逻辑,“我”的认识也随即发生。这个过程在胡塞尔那里被称为“述谓判断”的过程[16],“述”即指逻辑过程,其逻辑便对应皮亚杰的逻辑数学范畴;“谓”乃“称谓”,指概念被填充意义的过程,对应皮亚杰的物理范畴,可见胡塞尔和皮亚杰二人的思考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且相辅相成。皮亚杰以与胡塞尔不同的方式继承并发展了康德思想,最终在认识发生的视野中与胡塞尔殊途同归。
可以看到,“我”在知识发生的每一个当下积累的新的经验,同时会导致“我”的先验范畴的发生发展,新的先验范畴又会在下一次知识发生中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说,在这个循环迭代的认识发生过程中,“我”不仅构造了对象(知识),自身的先验范畴得到发生发展,自身的习性在不断积淀,“我”的素养也在发生发展,这是一个由“它”转向“我”的过程。由康德首次发现但未能揭示其发生特质的先验范畴,正是“我”在历史参与的认识活动中塑造自我、构造自身中发展而来,是在不断的构造对象与构造自身中实现的。
(二)知识与素养通过“我”的思维过程实现关联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皮亚杰以发生学视角论证了认识主体构造对象的过程也是构造自身的过程,与胡塞尔的构造思想不谋而合。进一步可以看到,皮亚杰所指物理范畴与逻辑数学范畴的内在一致性,实际上可以转化解释知识与思维的内在一致性[17]。一个真实的认识发生过程,必然是物理范畴和逻辑数学范畴一并运动的过程,是一个真实的知识发生过程,这个过程也正是大家所熟悉的思维过程。如此,借皮亚杰的两个范畴说,可以将对象发生也即知识发生与思维发生相关联,认识发生的过程也即思维发生的过程,认识发生与思维发生是同一事件的两个不同侧面;也正是在知识发生与思维发生中,主体性得以发展,也即素养得以发展。在此基础上,自然而然可以在知识发生、思维发生与素养发展之间建立起关联。本团队在前期相关研究中曾指出:“一个具有学科核心素养的人,应表现出形成了关于学科思维和方法的习惯,这种习惯是由长期训练而来的,它富有底蕴且自然显露……”[18],因此,思维的培养并不是最终目的,是为了在长期与知识相互转换的认识活动中,丰富学习者的人格与内涵。在长期积累与内化中,学习者逐渐由刻意走向习惯自然[19],并在稟好、个性、能力、气质、性情、品格、素质等个人习性方面不断积淀,由此个人素养也得到发展。
融入皮亚杰两个范畴说的思想内涵,可以进一步将由胡塞尔而来的“它-我”结构细化,将思维这个过程性要素融入进去,得到“它-思维(过程)-我”结构。在本文话题下,也即得到一个由知识通达素养的“知识-思维(过程)-素养”逻辑框架:要经历一个自知识开始的并与思维相伴随的学习过程,才能形成日趋成熟的思维习惯与思维能力,最终形成素养发展。概括而言,皮亚杰的知识观以思维这个过程性要素为桥梁连接了知识与素养,也即,素养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要从思维能力的培养逼近或通达素养,这显然与流行全球的对思维教育的重视相呼应[20]。在对教学活动指导的意义上,团队前期基于皮亚杰的两个范畴说演绎了一个“面向学科的全人教育目标描述模型”[21],该模型从两个范畴说中提取了三个核心要素,即“知识”“过程”与“思维”,结合教育教学实践,构建出“学科知识-问题解决过程-学科思维”的三层教育目标描述模型,与之前的三维目标相比,该模型意识到了知识与思维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不仅关注了学科知识的培养,更关注了学科思维的培养,为教师在教学中开展思维培养搭起了脚手架[22]。该模型实际上就是“知识-思维(过程)-素养”结构针对实际教学实践进行指导的一种落实方式。
三、知识通达素养的表现:走向完整的人之主体性发展
“知识-思维(过程)-素养”这一由知识通达素养的逻辑框架,可以帮助我们从理论上认识知识与素养的内在关联。但从教学实践的立场来看,要想实现真正完整的素养教育,还要结合学习者自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主体性发展来考虑如何由知识通达素养。素养是“我”之素养,是“我”的内在品质,且这种品质必然由发展而来,那么,对素养的把握应该从人的主体性28edcc454d71d25ee17ea153721ab9303ca163f25c4117d6ced0a33b979358a7发展开始追问[23]。在此回望胡塞尔认识论思考成就,其个性化构造、具身、感性发生以及交互主体性思想对“我”的主体性发展问题给出了系统解释,因此也为本文主题的展开与理解提供了更为完整的理论依据:客观而真实的主体性由个性化、身体在场、感性理性协调发展以及他者在场来说明,因此,在由知识通达素养的教学中,要充分注重“我”的个性化构造、“我”的身体、“我”的感性与理性的贯通以及他者的作用。
(一)通达素养的过程中要尊重“我”的个性化构造
胡塞尔思想体系说明,虽然认识发生的过程规律是一般性的,都是认识主体的本质直观过程,但每个认识主体却是个性化的。即不同于康德那里“抽象的、观念的、一般的或者超越个人的主体”,胡塞尔所言先验主体性“是我的具体的和个人的主体性”[24]。在他看来,只有从具体主体开始观察,才能够洞察认识发生的真相。在此立场上,所有的学习发生及素养发生,都是从“我”作为一个具体的真实的学习主体出发的具体的个性化的学习发生及素养发生。如前所说,“我”有着个性化的发生历史,因之有着个性化的先验认识条件,也因此会导致当下认识发生的个性化,同时构造了具体的个性化认识成就,构造了具体的个性化的“我”,这便为教育层面确认个性化构造以及学习者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逻辑合法性。
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25],个性化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去发展的重要问题,同时也与“我”的主体性发展直接相关,与“我”的素养发展直接相关。在胡塞尔具体主体思想的关照下,学习的本质是个性化的学习者当下发生的个性化的对象构造与自我构造,这种个性化构造是合理且合法的,因此,无论是学习者的构造结果还是构造过程,必须给予充分尊重。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在尊重每位学习者不同认识出发条件的立场上,充分理解每位学习者自己的认识发生逻辑,不能简单粗暴地将学习者的构造结果指为对或错,要尝试以代入学习者的方式从第一人称的视角理解他们构造的个性化结果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再行思考其与教学目标之间的差距,并分析出现不同差距的原因。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充分理解每个学习者内部的知识构造过程及其底层机制,才能理解不同学习者的个性化构造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习者健康发展自身素养,引导学习者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主体人去发展。反思当前的教育实践,虽然各种场合都在强调要注重学习者的个性化发展,但在真实的教学中又是站在统一的一般性教学目标的意义上对学习者进行评价。关于该问题,本团队前期已经从胡塞尔和皮亚杰的认识论框架出发,试图为促进学习者个性化发展评价寻找一个根本性的理论依据,借此可以重新认识学习者个性化发展与一般性教学目标之间的关系[26]。
(二)通达素养的过程中身体始终在场
胡塞尔在其认识论思考中提出了具身思想,他从意识的先验性出发论述了身体理论,通过分析感知的功能提出了身体具有构造性特征[27],并指出世界经验是通过我们的身体而被中介并成为可能,身体是其他客体的可能性条件[28]。在胡塞尔的影响下,梅洛·庞蒂更为系统地完成了身体哲学研究,在他看来,人类所有的理性形式都建筑于通过身体知觉获得的体验,这种体验是一切理性的基础,是最原初、最真实的体验。具身思想在皮亚杰的发生建构论中也有体现[29]。在皮亚杰看来,初生婴儿与外界打交道的唯一方式就是基于身体的“动作”,这种“动作”也是成人须臾不离的基本活动形式,这即是皮亚杰所言范畴之“动作起源论”。在这种视角下,人的“主体性”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即完整的主体人应该是身体与心灵(思维)同时在场的人。从主体性角度考虑,完整的主体人是一切发展的前提,因此,素养形成过程也是身体和心灵统整参与的过程,“我”的思维能力与身体能力本质而言是同一个整体,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
具身思想告诉我们,“我”的身体和基于身体的动作是所有认识活动的起点,也是我所有“积淀”的必然。在“我”的一切构造活动中,身体始终在场,具身乃主体性之真,具身是“我”之主体性最根本的特征,无论是感性发生还是理性发生,无论是当下发生还是历史发生,身体都参与其中。教育界当前有很多关于具身与教育的研究或思考,认为只有当下学习中有身体动作参与才是具身[30],这种认识有一定意义,但归根结底是狭隘的。主体性视角中的具身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一方面,认识主体的当下发生是具身的,任何一次当下发生其身体都是在场的,认识的发生要基于身体才得以展开;另一方面,认识主体的历史构造与历史积淀也是具身的,身体始终作为最基本的要素参与到认识主体过往的历史中。这种认识要求:首先,要注重学习者的身体在当下认识发生中的重要作用,要秉持学习者的身体始终在场并在当下参与学习活动的理念;其次,要深刻认识到,学习者在历史积淀中发展而来的个人习性、品行和习惯等都是具身的,要关注学习者在历史构造中积淀而来的各类具身性经验,并能理解不同学习者具身性经验的个性化,如此才能对学习者构造的个性化成就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三)通达素养的过程中要注重感性与理性互动
感性发生与理性发生之间的关系问题,亦是既有教育理论中未曾给出很好解释的问题,本文依然从胡塞尔和皮亚杰的思考成就中寻找依据。首先,感性发生必然以身体为基础,所有感性材料的发生都是自身体开始的。因此感性发生与具身思想有严格的关联关系。单从感性发生的视角看,在胡塞尔,于概念形成和做判断之前,必然有感性材料进入“我”的感官,经过一个综合过程之后才能将其概念化。因此,概念得以合法的基础是前期感性经验活动,这种感性经验活动就是认识发生当下在概念化之先的那个前概念经验活动。比如,在“我”得到“这是一棵苹果树”的判断之前,必然会有一些感性材料(苹果树的外形、树叶或者果实的样貌、颜色等等)进入“我”的感官,正因为在“苹果树”概念形成之先的前概念经验,才让“我”作出上述判断。因此可以获得一个重要的认识:概念(也即理性活动成就)内涵的丰富性是由前概念经验保证的。同时,最初的价值意义必定来源于感性,例如幼儿用手抓火被灼烧感到痛疼、品尝美味的水果获得愉悦感等感性活动,都是价值意义的最初也是奠基性来源。为了进一步说明感性理性的相互作用,胡塞尔的第二感性分析对此给出了进一步解释,他将感性分为第一感性和第二感性[31]:第一感性为基于身体欲求的“原感性”,是低级的、动物性的;原感性体验被理性认识活动(“我”的思维过程)所修正之后产生了第二感性体验,也即,第二感性是历史性视角中感性与理性交织交融的结果,表现出前概念经验的概念性[32],它具有充沛的情感动力,但却包涵了更多的认知因素,构成了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关键要素,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奠基性保证。这个过程是感性结构化的过程,该结构同样是由概念所说明的,该过程也可称为感性活动的理性化过程。再次回望皮亚杰两个范畴说中的物理范畴,是在认识主体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其实已经包含了感性发生层面的意义,由感性发生而概念发生,借助逻辑数学范畴走向理性发生,如此完整的认识才能发生[33]。概言之,在胡塞尔与皮亚杰的认识论框架下,认识发生不仅是理性认识的发生,还是感性与理性认识发生的交融,感性与理性相融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以此讨论素养教育问题,得到的重要启示是:感性为理性奠基,理性能力的价值来源是感性,理性内容的丰富意义来自感性;理性致感性结构化,感性水平得以提升,使感性亦具备了哲思品质;在感性水平提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理性水平,如此不断往复,最终实现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将这种感性与理性关系的分析与本文讨论的如何由知识通达素养进行关联,可以得到更加丰富的内涵:从知识经过思维,加上感性与理性的一并发展,才能通达素养。对教学活动的启示是:教学要从学习者的感性体验开始;要时刻注意学习者感性与理性的相互作用,强化学习者的感性体验与理性思维之间的交互作用;要在理性中发展感性,以感性为基础发展理性,最终获得素养的提升。
(四)通达素养的过程中他者始终在场
在前述视角下,知识是由“我”在与现象相遇的过程中被当场构造而来,既然如此,如何保证“我”构造出来的个人知识都能被其他人所理解并接受?或者说,“我”又是如何理解他人构造出来的知识的?倘若“我”构造的知识不能被他人理解或接受,“我”又如何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被社会所认可的素养的发展?因此,在讨论如何由“它”转向“我”,如何由知识通达素养时,上述问题也必须解释清楚。胡塞尔认为,世界是以交互主体性为开端,主体性只有在交互主体性中才是其所是[34]。因此,是交互主体性而非单个主体构造起了自然和世界,这就保证了不同主体对“同一个世界”的认识是先天可能的[35]。在交互主体性思想中,“自我”“他者”“他我”之间的关系问题也非常重要。“自我”是认识世界的起点;“他者”是“自我”的近似主体,只有自我经验到他者时,才有可能构造起客观的以及超越性实在;最终他者的意义表现为“他我”,这意味着“对于我而言的他人,对于本己的个体单子而言的其他异己单子”[36],其实是“我”的主体性得以最终实现的根本条件。
在教育场域中,假设“我”是一名学生,那么他者主要包括教师、家长、“我”的学习同伴也即其他学生等等,这几类主体对于“我”而言都是“他者”。在“我”的主体性视角中,便是他我之构成条件,“教师-学生”“家长-学生”“同伴-学生”等几种常见的组合即是“他我”的几种不同类型。不同的他者在学习活动中对于“我”而言也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比如一般而言:教师是知识权威的代表,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会参考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设置统一的教学目标,并引导“我”逼近那个目标;父母或长辈等作为家长是家庭教育中的灵魂,是“我”成长中的重要条件;其他同伴是“我”学习过程中的“同行者”,和“我”一起进行知识建构活动并在相互影响中走向共同的目标。作为学生的“我”的主体性的社会化,正是由这样的他我条件构造而成的。
面对不同他者的作用,教师应该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帮助学生协调不同的他我关系,且要引导学生正确面对不同他者在知识构造中的作用,进而促进其主体性的健康发展。当不同学习者构造的结果不一致且与统一的教学目标之间存在差距时,教师可以设计更多的小组或班级活动借此将作为学生的每个孤独的“我”置于群体之中使其体验到那个交互主体性的“我”,比如通过小组协商的方式对不同的构造结果进行讨论,使逐渐达成一致。当下流行全球的“知识建构”学习研究,就有着对小组协商的特别重视,是交互主体性得以体现的很好实例[37]。同时推荐一个与此相关的理论思考——现象图析学,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个性化构造与群体学习发生间的关联。现象图析学由马飞龙等人提出,它倡导教师要充分尊重不同学生的个性化构造结果,且不要用“有色眼镜”看待这些结果,每种结果都是平等且合理的。在此基础上,对这些“不同”的结果进行描述并分类,得到的即是一种结构化的基于学习群体的意识结构,这种意识结构即结果空间[38],可以从交互主体性的意义上描述学习者群体构造的结果。借助结果空间,教师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学习者当下的知识结构与思维结构所处的位置,从而更好地指引他们向同一个世界所对应的一般性教学目标逼近。
概言之,交互主体性是认识发生及学习发生过程中须臾不可离的要素,教育场域中的每一个“我”都因他者而真实存在。与此同时,在学习过程中,“我”也是借他者才能走向统一的教学目标,走向胡塞尔所言的那个共同的客观世界。在教学中如果不考虑交互主体性及他者与他我的作用,“我”即是在“孤独自我”或在交互主体性显现不充分的情况下构造知识,如此显然不利于“我”理解自己当前所处的位置以及与统一的教学目标之间的差距,更不利于“我”的自身能力或素养的发展。顺便提及,当前教育界认识交互主体性(主体间性)几乎都是从哈贝马斯社会学视角中的“交往”开始或将胡塞尔与哈贝马斯的交互主体性思想混为一谈,实则是一个误解。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思想从他者分析而来,本质上是主体性问题,与哈贝马斯的相关思考有本质区别。
四、结语
本文是一个遵循演绎推理范式的理论研究,以胡塞尔现象学为理论基础,结合皮亚杰的认识论思考,依次回应了知识与素养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知识应该如何通达素养的问题。因此,本文讨论的是作为奠基意义的逻辑问题,无论在何种时代背景下,知识与素养之间的这种基本逻辑关系是不变的。在教育实践中,我们应该在尊重知识和素养之间基本逻辑关系的基础上,结合不同时代背景的特定性展开对学生各种素养的培养,特别是在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技术的介入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理解知识应该如何通达素养的问题。比如,我们强调通达素养的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化构造,不仅要尊重其个性化构造的过程,还要尊重其构造的结果。在数字化时代,数据挖掘、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的嵌入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学生的课堂行为、言语动作表情或在学习过程中留下的其他学习痕迹,借助技术的使用和数据的表征可以更好地实现对学生个性化构造过程与结果的尊重。再比如,我们强调知识通达素养的过程中要保证身体在场,在数字化时代,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优势突破时空限制[39],创设虚拟逼真的场景,让学生融合具身的感官体验以实现身体“在场”的角色代入,充分发挥身体在通达素养过程中的作用。除此之外,我们强调通达素养的过程中他者是始终在场的,要充分发挥交互主体性的社会建构的作用。在数字化时代,技术支持下的各种小组协作平台和工具被开发并应用于课堂教学,这类工具的应用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分享、交流、协作并实现从个人建构到小组建构再到社会建构的转变。总的来说,本文提出的知识与素养之间的关系是在胡塞尔和皮亚杰认识论基础上演绎出来的,不受时代背景的限制,但是特定的时代背景可以为具体教学实践中学生知识的学习与素养的培养提供不同的途径和方法。
参考文献:
[1] 王策三.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再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3):5-23.
[2] 教基[2003]6号,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和语文等十五个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的通知[Z].
[3] 人民网.《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发布[EB/OL].http://edu.people.com. cn/n1/2016/0914/c1053-28714231.html,2023-11-20.
[4] 教材[2022]2号,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通知[Z].
[5] 杨九诠.三维目标,核心素养的分析框架[J].上海教育科研,2021,(1):1.
[6] 白倩,刘和海等.“胡塞尔—皮亚杰”认识论框架中的建构主义思想追溯[J].电化教育研究,2023,(10):11-17.
[7] 叶晓玲,李艺.现象学作为质性研究的哲学基础:本体论与认识论分析[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0,(1):11-19.
[8][16][24][28] [丹麦]D·扎哈维.李忠伟译.胡塞尔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9]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张延国译.笛卡尔式的沉思[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10][33] 侯家英,李艺.“胡塞尔—皮亚杰”视角中的康德知识学框架的改造[J].电化教育研究,2021,42(8):19-25.
[11][36]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修订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2] 倪梁康.胡塞尔的“发生”概念与“发生现象学”构想[J].学海,2018,(1): 134-146.
[13] 陈佑清.“核心素养”研究:新意及意义何在 ——基于与“素质教育”比较的分析[J].课程·教材·教法,2016,(12):3-8.
[14] 白倩,李艺.皮亚杰发生建构思想下的学习发生[J].电化教育研究,2022, (12):11-17.
[15] Gruber,H.,Voneche,J.The Essential Piaget [M].New York:Basic Books,1977.
[17] 白倩,冯友梅等.重识与重估:皮亚杰发生建构论及其视野中的学习理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3):106-116.
[18][23] 李艺,钟柏昌.谈“核心素养”[J].教育研究,2015,(9):17-23.
[19] 陈羽洁,张义兵,李艺.素养是什么 ——基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知识观的演绎[J].电化教育研究,2021,(1):35-41.
[20] 时龙.关于思维研究与思维教育若干问题的探讨[J].教育科学研究,2019,(1): 5-12.
[21] 李艺,冯友梅.支持素养教育的“全人发展”教育目标描述模型设计——基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哲学内核的演绎[J].电化教育研究,2018,(12):5-12.
[22] 冯友梅,李艺.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批判[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2):63-72.
[25] 蒋萍.论知识经济时代全面发展教育与个性化教育的统一[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6):72-74.
[26] 白倩,侯家英等.支持个性化发展的学习者评价之哲理溯源——基于胡塞尔现象学的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11):97-107.
[27] 丹·扎哈维,段超.胡塞尔的身体现象学[J].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2015,(2):273-293.
[29] 刘丽红.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中的具身认知思想[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1):51-55.
[30] 叶浩生.身体的教育价值:现象学的视角[J].教育研究,2019,(10):41-51.
[31] 李云飞.现象学的原初经验问题[J].学术研究,2013,(3): 26-31.
[32]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邓晓芒等译.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34] 朱刚.胡塞尔的“哥白尼式转向”[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92-105.
[35] 朱刚.交互主体性与他人——论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意义与界限[J].哲学动态,2008,(4):85-90.
[37] 张义兵,孙俊梅等.基于知识建构的同伴互评教学实践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8,39(7):108-113.
[38] 苏寅珊,徐晟等.现象图析学哲学基础及教育意义的再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21,42(7):12-18.
[39] 孙田琳子,金约楠等.跨学科视域下人工智能伦理教育重构:知识观、学生观与教学观[J].中国电化教育,2024,(4):45-51.
作者简介:
白倩: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哲学、认识论及教育应用。
刘和海: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信息化与媒介素养。
李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哲学、教育基本理论。
How does Knowledge Lead to Literacy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Epistemological Thought of “Husser-Piaget”
Bai Qian1, Liu Hehai1, Li Yi2
1.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2.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Jiangsu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how knowledge is connected to literacy is self-evident. Based on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Piaget’s “two-category theory”,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finally concludes that the occurrence of knowledge is also the occurrence of literacy, and knowledge can and must be accessible to literacy by knowledge; The occurrence of knowledge is also the occurrence of thinking, and the way to access literacy from knowledge is the thinking process of “I”. The development of subjectivity is the development of accomplishmen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ognition, a complete objective and real subjectivity can be guaranteed by individuation, the presence of the body,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erceptual reason and the presence of others. Finally, the article briefly responds to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literacy should be viewed in the current digital age.
Keywords: knowledge; literacy; thinking; epistemology; phenomenology
收稿日期:2024年1月17日
责任编辑:赵云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