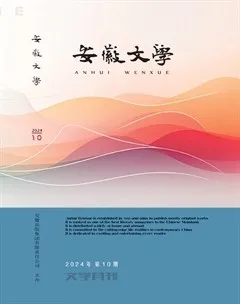血脉的回声
1
对于祖父而言,通往故乡的路是惊心动魄的。
1928年,深陷在贫困边缘的祖父带着一腔热血加入了红军赤卫队。革命的火焰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热腾腾的稀粥让他干瘪的身体慢慢恢复了生机和力量。彼时的祖父刚结婚。
1934年,参加红军炊事班的祖父跟随部队开始长征。彼时的村庄在炮火的侵袭下早已伤痕累累。祖母怀抱着年幼的孩子望着祖父的身影渐行渐远。直至祖父的身影消失在尽头,她才反身回到寂静的家里。
一年后,跟着队伍在行至广西的路上,祖父突然感染疟疾,他浑身发冷,高烧不退,头仿佛要炸裂开来。阵阵酸痛弥漫全身。疾病如一根无形的绳索束缚着祖父,他寸步难行,无法再跟上队伍,只得停下来养病。
一月有余,病好后,大部队已走远。祖父久久看着远方,转身踏上了回家的路。阵阵寒风呼啸着迎面吹来,迅疾离去。寒风在大地上四处游弋着,枯黄的落叶随风飘舞。祖父穿着一个破旧的裤衩子一步步往家的方向走去。阵阵寒风袭来,他浑身禁不住一阵儿颤抖。夜幕降临,他借住在破旧的寺庙里,揉着干枯的稻草取暖,看着温暖的灯火在不远处摇曳,一股浓郁的乡愁深深把他攫住。走走停停,几个月后,祖父终于回到故乡永新。故乡熟悉的风吹在他枯瘦的身上,他身子骨禁不住一阵痒痒。翠绿的小草在风中摇摆着腰肢,仿佛在向他起舞。步履渐渐变得缓慢起来。他细细打量着眼前熟悉而陌生的一切,僵硬的身体慢慢舒展,身体里的疲乏仿佛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个枯瘦的身影站在家门口,祖母起初没认出来。祖父开口说话的那一刻,祖母疾步奔至祖父面前。他们抱在一起,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回到故乡,租田种地远不能养活一家老小,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和家徒四壁的屋子,1943年12月,寒冷的冬季,屋外寒风阵阵,祖父携带妻儿迫不得已搬迁到几十里外的高桥楼镇大源村。在大源村种田三年,旱灾和蝗虫依旧不断,无奈之下,祖父带着妻儿又迁徙到几十里外的引泉村,在熟人的介绍和担保下,拥有了三间狭小的房屋,颠簸饥饿的生活总算结束,一切慢慢安定下来。引泉村人少地多,适合种田,一种就是几十年。频繁的搬迁,祖父祖母愈加深刻感受到世事的苍凉。
几年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祖父紧握锄头的手愈加有力,眼底的光愈加闪亮。
2
路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家徒四壁的情况下,父亲的求学之路异常艰难。
祖父祖母虽不认识字,却深知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祖父吃苦耐劳的精神深深影响着后辈。
每年年后,年味还未完全散去,开学的日子也跟着渐渐临近,祖母眉头紧蹙,不时走至猪圈里久久看一眼。转身,她拿着镰刀去了村里的池塘边,回来时右手挎着一竹篮子嫩绿的猪草。她急着再把猪养胖一点,这样就可以多卖点钱。薄暮里,看着猪吃得津津有味,不一会儿的工夫就把猪食一扫而光,她禁不住微微笑起来。半个月后,祖父祖母把家里仅有的这头猪抬出去卖掉,供父亲读书。当时父亲尚且在读小学初中。
祖父祖母早已做好了供父亲上学到底的准备。父亲自小就很懂事,他每天在一盏油灯下学习到很晚,昏黄的灯光把他的身影斜射在斑驳的墙壁上。清凉的晚风透过窗的缝隙跑进屋内,灯火在风的阵阵吹拂下微微摇曳着。
1959年,二十岁的父亲不负众望,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西省卫生学校,在当时那可不是一般的学校。父亲考取学校的消息仿佛一块巨石砸入寂静的村庄,顿时掀起阵阵涟漪。村里人纷纷前来道喜,母亲紧蹙的眉头舒展开来。
父亲去南昌读书后,孤身在异乡,思乡情更浓,他想回家却又不敢经常回家。
祖父多年前步行多日,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家的故事经常浮现在他脑海里。为了省下路费,父亲准备效仿祖父。
那次回家,他从南昌坐火车到分宜下车后,为了省钱,父亲决定从分宜县一路走回家。火车的轰鸣声渐行渐远,父亲独自走在寂静的小路上,耳边只剩下他的脚步声。饥饿慢慢吞噬着他的身体,他感到浑身无力,头昏脑涨。走至一口井边,他咕噜咕噜地喝下一肚子水,饱腹感暂时驱走了饥饿。继续往前走了几里路,适才隐退的饥饿感又反扑而来,变得愈加浓重起来。他伸手摸了摸口袋里的五钱,看了看不远处的店铺,唾液在喉咙口上下吞吐着,犹豫了片刻,他舍不得用,迈开步子继续赶路。继续走了几公里,走至山野前,他看到一亩红薯地。他顿时欣喜若狂,连根带藤拔出几个红薯,来不及洗净,就大口地咀嚼起来。暮色降临,不远处一只鸟飞入树丫上的鸟窝里,不时发出阵阵鸟鸣。走至深夜,他实在疲乏了,便借宿在陌生人家稻草铺就的床铺上。疲惫不堪的他一躺下就进入梦乡,半夜却又饿醒过来,窗外清凉的月光映射出他青涩的脸庞。
如此反反复复,走了九天九夜,父亲终于到家,此时的他已饿得头晕眼花浑身无力。祖母见状,赶紧拿出刚做的豆粉米果,端到父亲面前。父亲一口气吃了几十个,饥饿感顿时隐遁而去。祖父祖母一脸疑惑地看着父亲。父亲吞吞吐吐地说出自己一路从分宜走回来的真相后,祖父祖母满脸心疼。
父亲现在几十年的胃溃疡,应该就是那时饥一顿饱一顿落下的病根。
毕业后,父亲顺利分配到抚州东乡县人民医院化验科工作。父亲离家的路变得遥远起来。
白天,兢兢业业在化验岗位工作的父亲是忙碌的,当夜幕降临时,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宿舍,看着远处阑珊的灯火,父亲分外想家。他时刻牵挂着家里的妻儿老小。东乡距离永新高桥楼近四百公里,父亲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回家。刚参加工作时,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十块钱,微薄的收入难以支撑一整个家庭的开销,只能完全靠母亲挣工分来补贴家用开支。
父亲和母亲是经媒妁之言而结合在一起的。母亲年轻时很漂亮,她看中了父亲的才气和忠厚。那个弥漫着喜庆气息的日子,母亲是骑着毛驴嫁到我们龙家的。
婚后,家里四个孩子,开销很大,家庭的重担落在了母亲瘦弱的肩膀上。
深秋时节,空气中已有了些微凉意。经过近一年风雨的侵袭和烈日的暴晒,茅草变得枯黄干燥,是冬天烧饭取暖的首选燃料。午饭后安顿好年幼的我们,来不及休息,母亲便手持镰刀和绳子往山间走去。
秋日柔和的阳光洒落在山间大地上,母亲走至山半腰开阔处,躬身娴熟地忙碌起来。手起刀落处,枯黄的茅草应声倒地。半个小时后,母亲额头上布满细密的汗珠。一直到傍晚时分,母亲才肩背着一大捆茅草下山,晚风吹乱了她的发梢。
为了让回家的路近一点,在东乡县人民医院工作十年后,父亲终于从几百里外的东乡县人民医院调入乌石山铁矿职工医院。医院配套设施比较齐全,有铁矿子弟学校。父亲调入后,大哥和二哥随着他在铁矿子弟学校就读。
父亲在乌石山铁矿医院工作的第五年,祖父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祖父患病已久,那个清晨,他下床解手,却再也无法起来。
记忆中的祖父很喜欢赶集,家里到高桥乡镇上的集市有四五里路的距离,祖父不会骑车,每次都是步行前往集市购买家里的日常用品。快散墟时,年幼的我们总会不时跑到门口,踮起脚跟朝不远处的那条小路张望。小路上人来人往,我们四处搜索着祖父的身影。见人群中出现祖父的身影,我们顿时兴奋起来。祖父满载而归,提着一手东西往家的方向走来,祖父越来越近了,我们的心情也随之起伏。祖父每次赶集回来都不忘给我们买一些零食,一斤炒花生或是葵花子,让年幼的我们高兴好几天。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祖父也跟着笑起来。
祖父和祖母通往死亡彼岸的路因为亲人的陪伴而多了一丝温馨。祖父去世后,祖母的晚年变得愈加孤独起来。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祖母晚年卧床多年。
1988年的一个傍晚,正上初三的我踩着暮色回到家里,气息微弱的祖母忽然叫我名字。“小军,你快过来。”声音断断续续,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喊出来。“我快不行了。”祖母哽咽着说道,眼底闪着泪花。我疾步走过去,紧紧握住她的双手。八十年的光阴下来,祖母的双手枯瘦如柴,疾病如一把锋利无情的刀,剔除她身上的骨肉。
我看着她慢慢闭上双眼,走向时间的另一端。我能细微捕捉到她的双手的温度慢慢凉了下去。
祖父祖母虽然去世了,但他们的血脉长久地流淌在我们血管里,他们的谆谆教诲我一直铭记于心不敢忘记,因为那是我们为人处世的准则。
3
祖父祖母当初用尽浑身的力量支持父亲求学,最终是为了让整个家的命运之路越走越开阔。
家是温暖的港湾,房子是根,是栖息之地。家里的建房之路曲折而漫长。
记忆中的家是逼仄而潮湿的,家里仅有两间堂屋,一个长方形的房间摆着两张床,我们一家八口人挤在两间老屋里。这巴掌大的一片宅子,房子屋顶很薄,每逢暴雨来袭,雨水仿佛商量好一般,透过瓦片的缝隙连成雨线落进屋内。年幼的我们拿着脸盆放置在漏水的地方。雨水落在脸盆里,发出滴滴答答的清脆响声。雨水很快滴满了脸盆,我们成盆成碗地往外接。深夜,屋外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屋内密集的水珠落在脸盆发出的滴答响声不时在耳畔回荡。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记忆因为有了水仿佛也湿漉漉的。
母亲害怕刮大风下暴雨。在台风和暴雨的侵袭下,成片的瓦片容易吹落在地。每次遭遇暴风雨的侵袭时,父母亲总会一脸恐慌地带领着我们找来耙板、抓钩、木棍之类的东西,迅速爬上房顶去压住屋顶,唯恐瓦片被大风刮走了。肆无忌惮的风把一些瓦片吹得满地都是。风声、雨声和瓦片刮落在地的破碎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童年记忆的底色。
八口人挤在两间住房里。寒冬时节,屋外寒气逼人,我们兄妹四人挤在一张床铺上。我和妹妹、两个哥哥分别盖一床被子。静谧的夜里,我们兄妹四人躺在被窝里聊天。夜色渐深,我们很快滑入梦乡。半夜醒来,我们都歪歪扭扭地睡着,有的胳膊露在外面,有的大半个身子露在被褥外,有的则蜷缩着卷走了整条被子。
时光流逝,随着我们弟兄几个长大,巴掌大的老宅显得愈加逼仄起来,盖房子的事情迫在眉睫。
父母亲有着很深的房子情结。年幼时的频繁颠簸和年长时的寄人篱下,让父亲深刻体会到拥有一栋宽6AYaL53c8HNGFQbk9S9F8GENeTYX0zMijGfnuVjggBw=敞明亮的房子的重要性。他和母亲时刻渴望着一处宽敞温暖的房子。可家里捉襟见肘,父母挣来的钱大部分花在了我们兄妹四人读书上。彼时,我和妹妹正上初中,大哥和二哥正念高中。从祖父祖母这辈开始,祖母就把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希望他知识改变命运。到我们这辈,父亲更希望我们延续家族的传统,通过读书来改变贫寒的命运。
二哥会读书,不会干农活。记忆中盛夏农忙时节,插秧收割稻谷时,二哥总是站在田中间东张西望,半天不愿意弯腰。这种场景如今回忆起来总是让人忍俊不禁。父亲经常叮嘱年幼的我好好读书,我当着父母的面点头,出了门和小伙伴玩耍时,分分钟就把父母的话丢到了脑后。直到今天,我仍为没能认真读书考上大学感到遗憾。
父亲是医生,治病救人,看着眼前这些瘦弱的身躯深陷在深渊里,他总是眉头紧锁,在病历上飞速写下药方。直至他们摆脱疾病的折磨,他紧蹙的眉头才舒展开来。大哥跟着父亲在乌石山铁矿子弟学校读书时,日复一日的耳濡目染下,一颗种子在心底生根发芽,年幼的他便慢慢产生了做医生的梦想。
勤学苦读的他在书香气息日复一日的浸染下慢慢有了一副书生模样,但事与愿违,命运总是无情,命运的轨迹没有按照大哥预想的轨道行走。大哥高考落榜。消沉了一段时间后,在父亲的建议下,他开始跟着舅舅学木匠。大哥学木匠依旧是勤奋能吃苦,看不出他一点怨言。然而我们都未曾想到即使在学木匠,他内心那颗学医的火种依旧没有被残酷的现实浇灭。后来,大哥因视力问题,放弃了做木匠。
没做木匠后,聪明善良的大哥迅速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他买来各种书籍钻研种西瓜的技术,并开辟稻田开始种西瓜来维持家里的生计。长兄如父,大哥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快一步步把家带往开阔之地。
为了盖房,父母亲节衣缩食,大哥则带头种起了西瓜。经过一番商议,母亲选择了那亩土壤疏松、土层深厚和肥沃、排水良好、光照充足的地。开垄、松土、施肥、育苗、定植,瓜苗慢慢伸展开来。大哥有着过硬的种瓜技术。晨曦微露时,大哥就跑到田间地头给西瓜苗授粉。
经过悉心照料,三个多月后,一个个圆滚滚的绿皮西瓜出现在我们眼前,家里的西瓜产量在村里数一数二。
几日后,母亲踩着晨露,带着我和大哥来到瓜地里,一起采摘西瓜。交通不便,我们拉着一板车西瓜需要步行四十里路才能抵达县城。天未亮,我们就拉着西瓜出发了,一个在前面拉板车,后面几个人在推,路面坑坑洼洼,月光映射出我们单薄的身影。到县城,天已大亮。卖完西瓜,大哥又要急着回家给西瓜苗授粉。
1988年的盛夏,二哥不负众望,顺利考取江西大学的消息传遍了方圆十里,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龙家熬到头了,以后有福享了。”村里人议论纷纷,向父母亲投来羡慕的眼神。彼时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
这一年的下半年,我们举家从居住了几十年的引泉村迁回到了老家怀忠镇茶源村委夏南村。转了一圈,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夏南村是生命的根须所在。
二哥考上大学后,大哥继续埋头种西瓜,每天往返于田间地头,靠种西瓜来供二哥上大学。一家人靠着种西瓜,一股劲往一处拧,几年后,房子终于盖了起来。两层小楼,上下十二间,加上厨房、洗澡间、门楼等,有一百多平方米。站在新房前,父母亲久久地打量着,过往那些心酸和不堪的滋味不时涌上心头。
大哥成为医生的梦想没有被现实的重压熄灭,随着二哥大学毕业以及我步入社会参加工作,父母的生存压力得到了缓解。大哥没有再种西瓜,他开始踏上了自学之路。在追梦的路上,他像一个苦行僧,手持一盏微弱的灯火,孤独地行走在苍茫的夜色里。
在老家县人民医院工作期间,他刻苦学习,从不放弃任何一次学习的机会。
夜幕降临,喧嚣的医院变得安静下来,他常常独自在病房研究病理,努力提高自己的医学水平。他期待着早日像父亲一样治病救人,成为受人尊敬的医生。
多年后的今天,大哥早已是县老区医院内科主任。
4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条路,大哥成为医生之路虽艰辛,却最终还是看见了光明。
与大哥和二哥不一样,我很早就离开故乡,在异乡广东辗转漂泊十余年。当我行走在异乡的小路上,我脑海里就浮现出祖父1933年从广西步行回家的场景,还有父亲为了节省五毛钱,毅然步行九天九夜,从分宜走回永新老家的一幕幕也不时涌上我心头。没读大学成为我多年的遗憾,但祖辈父辈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却在我的血脉里哗哗流淌着。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刻激励着我。当我在异乡遭受饥饿、穷困、艰难等痛苦的侵袭,想起他们,一股无形的力量就在我心底弥漫开来。
薄暮里,合上父亲当年写下的家族回忆录,我陷入长久的思索中。父亲写下的每一个汉字里,一撇一捺都流淌着一股不服输的力量。
低头的刹那,一抹阳光透过窗棂斜射在我脸上,我仿佛听到了血脉深处的回声。
责任编辑 夏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