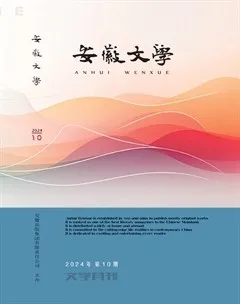质地的平庸与叙述者的僭越
评论家张学昕认为:“短篇小说写作常常是一种灵感触角延伸至生活纵深的一次闪耀,或者是,在一种经验、精神和感觉之间,故事、人物、语言、结构相约之后的不期而至。”由此观点出发,衡量张振的短篇小说《余晖落尽》,我觉得这篇创作无论从哪方面进行阅读、感受与分析,都无法抵近这一层面。小说没有灵感迸现,立意或思想浅显直白无法让人满意,更没有延伸至生活的纵深,提供独特的人生经验和人性深度。尽管从表面看,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环境、情节等几个要素比较完整,但在经验、语言、结构、感觉、氛围和精神之间,无法形成令人印象深刻的文本观感。那种“不期而至”、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付之阙如。若不能断言这是一个问题文本,其文笔的平庸也只能勉为其难地称为“创作”。
首先,主题立意的浅白与内在叙述逻辑的混乱。“乡下人进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当代小说重要的主题,诸多小说呈现了乡下人进城后的进取、拼搏、改变命运的不屈意志,也披露了他们在城市经历的苦难、挣扎甚或绝望。尤其是乡下人进城后的漂泊感所带来的精神痛苦以及身份认同的尴尬被小说揭示得颇有深度,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路遥的《人生》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框架下演绎了高加林的悲剧人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一方面接续了国民性批判的思想启蒙主题,另一方面揭示了改革开放对农民心理的冲击以及引起的诸多反应;贾平凹的《高兴》真实再现了刘高兴在城里生存的艰难和精神上的痛苦与迷惘;陈应松的《太平狗》,罗伟章的《我们的路》,尤凤伟的《泥鳅》,邵丽的《明惠的圣诞》,梁鸿的非虚构《出梁庄记》……一大批优秀的“乡下人进城”文本从多个维度深化了小说所携带的时代精神、文化内涵以及社会意义。当下的作家,如果再写类似的题材,只能另辟蹊径或写出不一样的风景,舍此,别无他路。从文学史或者“乡下人进城”的创作谱系看,这篇小说实在没有提供任何新鲜的经验,甚至连既往的主题深度也远未达到。《余晖落尽》无非就是一个励志的故事,稀松平常。米兰·昆德拉曾经将小说分为三个层次:讲述一个故事、叙述一个故事和思考一个故事。显然,这篇小说几乎只落在第一个层次:讲述乡下人李强进城的经历和体验。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读者很难读到溢出故事之外的深邃寓意、思考、哲理抑或其他,小说立意的浅显于文本叙述中肉眼可见。不仅如此,小说在叙述过程中也经常有内在逻辑混乱的地方。比如,李强一方面对放牧骑马生活的自由自在流连忘返,感到时间在不经意间过去,甚至忘记了时间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说他被故土生活所压抑和禁锢,一直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这先后的叙述就存在着叙事逻辑上的混乱和悖反。即便现实中的确如此,但在叙述上也要着意强调放牧生活的单调、乏味、枯燥,为后面的执意“出走”做足铺垫。还有,当李强登上远去的列车,远离了和父母的冷战、沉默、争吵,终于可以去远方(城市)实现心中的梦想时,虽对故土有不舍,有亲情的牵绊,但我想这时的李强更多的是释然、解脱和对未来的憧憬,而小说却叙述了他在车厢连接处的痛哭流涕,此情此景,却也和一颗放飞的心不太谐调。诸如此类的前后抵牾、矛盾、龃龉的叙述还有一些,这不能简单解释为人性的复杂性、性格内在的矛盾性,而只是一种没有尊重人物真实心理和没有遵守生活逻辑的想当然的书写。
其次,人物、情节、语言与结构的平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乏善可陈FyoU4sq/q3dePSzmm9oZhrJhyIHCjvGMQt74BIEJBUI=。从小说的叙述可知,李强有点儿桀骜不驯,“他认为自己有一颗闯荡的心,这点很不同于同龄人,以致于感到格格不入。”原本想着这样的性格特征,到城里会走出不一样的成长路径,做出迥异于常人的举动或者提供给读者别样的人生经验,然而,他走的路跟绝大多数的乡下人进城没什么两样。漂泊、吃苦、痛苦、失望,终于在城里硬撑着坚持下来,这样的人物在现实中比比皆是,无法给文学书写提供崭新的人物形象,更没有展现性格形象的独特性以满足审美诉求。小说的情节也无甚特点,只是简要地讲述李强到城里打拼的过程以及一些细节、人生感受,中间适当回溯自己在草原的生活。这是一种最普通的情节模式,谈不上情节的精心营构,更谈不上所谓的开场、伏脉、接榫、结穴、冲突、高潮等情节性的设置。情节的单薄、寻常无法体现小说情节艺术的特色。我们所熟悉的“横云断山”“横桥锁溪”“夹叙他事”“穿插藏闪”“添丝补锦”等创造性的情节艺术没有丝毫呈现。这里并非指摘作家没有采用类似于上述的这些技法,而是批评作家没有情节创生的意识,只是按照时间线索按部就班,因循守旧地去讲述李强的命运。除了情节的平庸,小说的语言也缺乏艺术的感染力和审美张力。小说即语言的艺术,叙述语言的面目可憎会导致小说的审美价值骤然下降。这篇小说的叙述语言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文学性、独特性,以致于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不到小说语言特殊的魅力。平铺直叙的语言、水波不兴的语言、过于常态化的语言,缺乏文学语言的诗意、幽微、纤敏和想象力。究其原因,主要是小说多数情况都是概略地讲述,缺乏对细部的描摹、场景的渲染、氛围的营造,从而导致语言的枯索,缺乏个性,更遑论风格。情节的平庸也导致了小说结构的寻常。按照R.L.史蒂文森的划分:“写小说有三种方法,第一,或者你先把情节定了,再去找人物。第二,或者你先有了人物,然后去找于这人物的性格开展上必要的事件和局面来。第三,或者你先有了一定的氛围气,然后再去找出可以表现或实现这氛围气的行为和人物来。”史蒂文森的结构三分法当然不是绝对的,实际的创作,小说的结构在三者的基础上可能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余晖落尽》结构上的平庸就是没有以其中的某一个点为中心,故事情节有(李强的进城遭遇),人物的性格心理有(李强的憋闷、坚韧),背景氛围也有(题目就是余晖落尽,带有很强的氛围感),但都没能得以凸显,形成主导性的线索,也就无法彰显结构上的特色。
再次,叙述者对小说中人物观念、心理的僭越。帕西·拉伯克曾言:“在小说技巧中,我把视角问题——叙事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看作最复杂的方法问题。”古典与传统小说多采用全知叙事,现代与后现代小说更偏向于限制叙事和纯客观叙事。当然,我们不能在叙事视角方面取进化论的观点,认为限制叙事或纯客观叙事就一定优于全知叙事,所谓叙事达尔文主义是荒谬的。从小说叙事本身来看,适合自己的叙事角度才是最好的。具体到《余晖落尽》的叙事视角,倒也不复杂,小说通篇采用的是全知视角,亦即“叙述者大于人物”的“零度焦点叙事”。小说中,叙述者不仅知晓主人公所有的行为、外面世界的纷繁复杂,也深谙小说中人物的心理和动机。虽然全知叙事中,叙述者(包括隐含作者)无所不能、无所不晓,自由出入天文、地理、历史、心理等诸多领域且游刃有余,其真实性会备受质疑,但如果运用合理,恰如其分,则这种“上帝视角”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可惜的是,这篇小说在很多地方,叙述者滥用了自己的权力,致使叙述者不仅仅是大于小说中的人物,而且直接替代人物说话和思考、表达观点,脱离了小说中人物的身份、处境、认知、地位以及教育背景,导致叙述者对人物的僭越。这里略举一例:“想到这里,李强心生悲悯。他想,科技成就了当下,却让一些行动蹒跚的人跟丢了方向……虽然生活在底层,虽然满是辛劳,但又有谁知道他们也拥有自己的幸福、人格,也在不断地建构自己的尊严。”读者一看这样的思想和认知,简直就是一个人文学者或知识分子的忧思,一个来自草原的牧马者,一个没多少文化的草根青年一般不会有这种思考与心理。作家试图提升小说思想深度的用心可以理解,但在这里假借李强的意念,严重背离了小说人物自身的身份与认知,从而形成了叙述者对人物的“越位”,其审美效果,只能适得其反。因之,一些用语也不符合所思者的身份,比如“悲悯”“建构”哪里是李强的话语?设若换成“心痛”“形成”等更为日常化的语言,或许才更贴合李强的实际生活。这也是叙述者的“越位”所不可避免地导致的语言“错位”。
当然,这篇小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还不止上述这些,有问题并不可怕,如果小说有不俗的品格、鲜明的个性也不失为值得一看的作品。遗憾的是,从整体上看,《余晖落尽》质地的平庸与叙述者的僭越,让这篇小说远离了优秀的行列。
责任编辑 王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