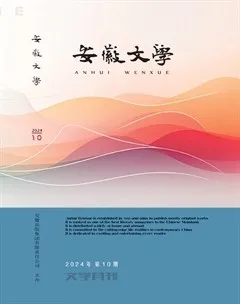青年的叛逆、困惑与单纯的热情
萨拉·格雷厄姆(Sarah Graham)在其编著的《成长小说史》序言里曾写道,任何一个读小说的人“终究会碰到一部成长小说——关于年轻人面对成长挑战的小说,因为它是文学史上最流行且最持久的体裁之一”。此言实在是不虚之论。不管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专业学者,还是仅以阅读来打发空闲时光的读者,都一定会在生命中某个或明亮或黯淡的时刻,相逢那些以年轻人为主人公,讲述他们初涉社会、追求理想、经历起伏、积累经验、获得启示的人生故事。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威廉·迈斯特》,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幻灭》,司汤达的《红与黑》,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鲁迅的《伤逝》,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庐隐的《海滨故人》,杨沫的《青春之歌》,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这些古今中外的成长小说经典,不仅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土壤上有关年轻人成长的文学想象,更是时代、社会和人的价值观念变化的真实镜像;它们不仅见证了一代又一代青年读者的成长,也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些伟大的文学经典与传统的现代遗产,我们的人生是被这些成长小说所指引、所造就的。
《余晖落尽》就是这样一篇以初涉社会的青年为对象,写年轻人成长的小说。小说主人公名叫李强,生在草原,长在草原,他的心却在外面的世界,梦想在城市创造自己的人生。小说的故事很简单,李强不安于在草原过安稳却平淡的生活,于是怀揣梦想辞别父母,离开故土,来到上海这个大都市寻梦、追梦。这是一个于连式的“外省人”的故事,也是一个祥子、高加林式的“乡下人”的故事。通常来说,如果一部(篇)小说里有一位不安于现状的年轻人,满载理想却涉世不深,在社会的熔炉里锤炼、挣扎与奋斗,那么它便具备了成长小说的基本要素,《余晖落尽》亦是如此。只是小说很小,短制,只讲述了青年李强的人生片段,也只描摹了当下社会的局部切片,既没有完整呈现主人公的生命图景,也未能深入抵达时代的核心地带,仅可谓一篇拟成长小说,或者说成长小说的浓缩版。
冲突是叙事文学推动故事的内在动力,也是成长小说情节设置的基本模式。成长小说的冲突,大致有内向性冲突与外向性冲突两种形式。内向性冲突,指的是主人公内心世界里灵与肉、情与理、欲望与伦理的冲突,它是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郁达夫的《沉沦》这类成长小说的主要情节推动力。外向性冲突,指的是主人公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因此,它通常存在一个与主人公构成矛盾关系的他者主体。其显性的文本表现形式是代际冲突,或为父/子辈冲突(胡适《终身大事》),或为祖/孙辈冲突(巴金《家》)。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成长小说代际冲突的焦点,是人生道路或恋爱对象选择上的分歧。《人生》里的高加林属于前者,他不愿意做像父亲那样的农民,从而选择逃离黄土地;《终身大事》里的田亚梅则是后者,她不赞同父母的包办婚姻,从而选择离家出走。因此,每一部(篇)成长小说,总会有一个叛逆的青年主人公形象,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于他们的父/祖辈,在父/祖辈的社会体系里格格不入。大体上来说,《余晖落尽》的情节结构合乎成长小说的外向性代际冲突模式,主人公李强是高加林式的叛逆青年形象,区别仅在于李强要告别的不是土地,而是草原。这个年轻人的父母,希望他“和周边人一样,找个工作,或种地、放牛,再或做点生意,开个饭馆”,过安稳且平静的日子;然而,这不是李强想要的生活,他“有一颗闯荡的心”,他不愿意终身守在草原。于是,他告别了草原,走进了城市。但是,李强却似乎没有高加林那种决绝的勇气与决心——未到城市,他向往城市;来到城市,他又留恋草原,他深陷于矛盾的情感。最终,《余晖落尽》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面目模糊、进退不决、摇摆不定的叛逆者形象。这个不彻底的、半吊子的叛逆者形象,究竟是小说的败笔,抑或他恰恰是这个时代青年的精神症候和典型形象呢?
这些成长中的叛逆年轻人,他们在社会熔炉里所经历的人生起伏,所体验的生活得失,所获得的生命启示,构成了成长小说的主要内容。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富有单纯的热情,却缺乏生存的经验。他们离开了旧的、熟悉的环境,主动进入或被抛入一个陌生的、新鲜的世界,习惯的生活已经不存在了,新的世界、新的生活又并非他们想象的样子,他们生活在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与鸿沟之间。于是,有的人陷入了退缩与犹疑的境地,《伤逝》里体味到“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涓生和子君便是如此;有的人陷入了迷茫和困惑,《海滨故人》里感叹“人生到底作什么”的露沙们便是如此;而有的人则不断地调适与改变,《青春之歌》里“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林道静便是如此……长成的代价,就是成长中必然要去经历疼痛与焦虑。应该说,就内容而言,《余晖落尽》是标准的青年成长小说。它既讲述了主人公李强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奋斗、拼搏的生活故事,写出了他经营生意过程中的顺境与逆境,也描摹了他在顺境与逆境中的心理状态,或满足,或挫败,或坚定,或犹疑。但是,《余晖落尽》毕竟只是短篇,因此它只能像《伤逝》《海滨故人》一样,选择主人公人生中的局部和横断面,详略有别地展开叙事,而无法像《青春之歌》那样,完整地叙述主人公跌宕起伏的生命史,全景式地呈现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同时,亦是因为短制,《余晖落尽》也无法像《青春之歌》那样,让主人公的性格在小说里得到充分的发育与发展,并精微细致地揭示人物的“心灵辩证法”,而只能相对直接与笼统地展示主人公内心纠结、矛盾的状态。
成长小说还有一条经典法则,那就是它通常会塑造一个青年主人公的引路人角色/形象,内嵌着引导/被引导、教育/被教育的人物结构。这个引路人,其功能是充当主人公的助手,是青年人的人生导师,帮助他了解与认识复杂的社会,甚至塑造年轻主人公的价值观。其可能是现实的、具有丰富社会阅历或人生经验的人,也可能是抽象的、具有启发性意义的观念与思想,或者兼而有之。在《高老头》里,伏脱冷就是这样的人,他让拉斯蒂涅认识巴黎社会的真相与本质,传授他征服上流社会的方法与秘密;在《伤逝》《家》里,承担引路人角色的则是恋爱自由、人格平等的现代思想与现代观念,青年人在这样的观念引导下冲破传统家庭与伦理的牢笼;而在《青春之歌》里,则是兼而有之,既有知识分子余永泽、革命者卢嘉川和江华这样具体的人,也有个性解放的启蒙价值观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同样,《余晖落尽》里也有这样一位引路人,那就是刘大爷。在李强初到上海、茫然无措的时候,他遇见了摆路边摊的刘大爷,“他请求老人带自己上路,他也想摆个路边摊。老人迟疑,末了,还是将自己的经验全讲给了他”。于是,在举目无亲的、陌生的城市里,刘大爷不仅让李强感到了人性的温暖,也传授了李强生存的技能,从而让他拥有了留在上海的勇气与底气。作者甚至不无夸张地、浪漫地写道,李强觉得他的“生活开始有了光”。然而,《余晖落尽》的结尾处却意外地改变了成长小说这个人物结构法则——刘大爷由主人公的引路人转变成了同情的对象。其实,姑且不论这么调整人物结构关系合理与否,它至少不符合小说的内在逻辑。其一,在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刘大爷又如何不知道淀粉肠配方出问题的消息?其二,刘大爷将路边摊看成“不饿着肚子就行”的“小本生意”,又怎会在生意清淡时变得那么“迷茫”?其三,被作者重点来写的路边摊,难道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它能否代表与象征上海这样的都市?主人公李强对刘大爷“心生悲悯”“心里愈加伤痛”的情感,实在令人疑惑。
(本评论为安徽省“江淮文化名家”引育工程领军人才项目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 王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