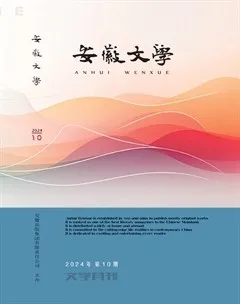甲壳
我考入邻县乡镇的公务员,我妈感慨:“成家”“立业”“生子”三块心里的大石头,最大的那块总算着地了。
她特意买回两只巴西龟,说我去报到后,家里得补充两个新成员,算是能量守恒。我总觉得这话有些不对,又不想和她理论,因为她肯定准备了一大箩筐的理由,等着我接招。我才不上当。
我妈喜欢热闹,常常人在院子里种花,室内的电视大音量开启着。我节约用电,关闭电视。她不乐意,还说,电视开着家里有声响,也就有了生机。她应该选择阿猫阿狗,或者聒噪的鸟类,整天制造多种声响,满足她对热闹的向往。关于养龟,我怀疑她已做好失败的思想准备,或许连煲汤的食材都备齐了。
巴西龟身形小巧,眼珠灵动,头尖没有任何色彩过渡,突然冒出两抹橘红,像是京剧里的净角脸谱。我妈给它们准备了半米长的玻璃缸,缸内盛着暴晒三天的自来水,缸底阶梯式铺放着珊瑚骨和火山石,还有几株水竹、狐尾、豆瓣菜、莲子草,喧宾夺主地存在着。我妈说,这是古法养龟,不需要物理过滤,也不需要过多打理,只利用植物和各种介质之间的微妙平衡,来达到一缸一景的生态养龟环境。我心想:这和自生自灭有区别吗?
乡镇分配了宿舍,是同事挑选剩下的。顶楼,漏雨,之前的住户在天花板上贴着塑料膜,形似一张倒扣的龟壳,让我在冬天产生住在温室大棚的错觉——棚外寒气未消,棚内温暖如春。宿舍用途单一,只能算是休息场所,洗漱、如厕、沐浴都要去公共区域。这是意料之中,我并没有心理上的落差感,从家里搬来床铺、衣柜、书桌,已然做好了长期居住的打算。
两个月后,我被县直机关抽去跟班学习,为期一个月。这是很多人都期待的机会,乡镇很多干部在县城都有房子,去县里跟班意味着可以和家人短暂的朝夕相处。我仿佛生出一口蛀牙,面对同事的羡慕,尴尬地笑不出来:才适应乡镇生活,又要在一处陌生之地寻找生活与工作的契合点。最头大的还是住宿问题,当时县直机关单位基本没有员工宿舍。我的分管领导姜主任和我爸年龄相仿,也是外地来的,对我格外关照。他考虑我是未婚女子,安排我暂住一所小学的教师宿舍。那里的硬件设施比乡镇好,有独立卫生间,不过没有热水器,得把加热棒支在水桶里加热,像《西游记》里耸立在东海的定海神针。我不是孙悟空,见到“定海神针”在水面闪现紫光,吓得腿软,不敢靠近,只好每周末以陪伴爸妈为由回家洗澡。
一个月后,“跟班”成了“借用”。姜主任和校长商量,反正就一间宿舍,平时也是空着,不如让我继续居住,他帮学校解决几笔经费问题。居住多久,谁也没有说清,这是个漏洞,我因此成为学校的“人质”。
保安老肖让我搬走,因为我长期居住,没有支付住宿费。这理由我接受,但住宿是姜主任安排的,得和他说一声。
“你是不是要结婚了?”
“才不是,连结婚对象在哪都不知道。”
“那你就安心住着,学校总比外面安全……估计这也不是保安的意思,是分管后勤的陈副校长让他说的。我去协调一下。”
我不想再给姜主任添麻烦。我对着镜子训练笑容,尽量让颧骨主肌和环绕眼睛的眼轮匝肌同时收缩,显得真心流露而又不谄媚,企图在见到陈副校长时展示这款笑容,赢得他的好感。然而,他只是借着咽口水,潦草地点了头。但我坚持,下一次他会用心地回应。每一次我都失望,在陈副校长离开的瞬间,立即收起笑容,为自己的小心思感到羞耻。
学校愈发过分。趁我上班时候,把我的私人物品堆放在值班室,说是中考期间,宿舍对外出租,让我克服两天。这小意思,就一个晚上,第二天是周五,下班后我可以回家。我盘算着,晚上在单位待着,单位有门岗,二十四小时值班,办公室四人一间,门可反锁,内有空调、饮水机、供临时休息的折叠躺椅……我居然燃起露营的兴奋。同事见我提着洗漱用品到单位,毫不留情拆穿:学校就差一间宿舍两个晚上的收入?
姜主任荣升到外单位任职。新来的主任火气大,喜欢对下属颐指气使,显摆官威,对我更为刻薄。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我找到问题的根源。他排外思想严重,谈吐时习惯夹杂着一股匪气和盲目的优越感,和我说话使用率最高的就是那句“你们外地人懂什么”。这反而让我越挫越勇。我从小在我妈骂声中长大的,脸皮早就达到菜墩子的厚度。我爸早前还会劝我妈,别为鸡毛蒜皮之事让孩子不痛快。我妈一句“我是她妈”,把我爸的话顶回去了。她的用意我懂,除了巩固家庭地位之外,还想提升我扛骂能力。我如她所料,在他乡遇到很多不痛快的事情,导致情绪沮丧、痛苦、失望,也算能够顺利抽身。我感激她对我心理韧性的培养。
我在摊前买水果,第一次发现喜欢的榴莲、山竹、椰子、菠萝、菠萝蜜、蛇皮果都带着硬壳从热带地区而来。是不是非要把自己包装成地雷,或者铁齿金锤,才能像这些水果一样,融入当地生活?
家里两辆“迷你”两栖坦克冬眠之后,每天持着中世纪简陋的盾牌在玻璃缸演练。见我靠近,立即停止作战,钻进“堡垒”,故意向我炫耀自己从一出生就拥有房车,不像我,身处他乡,始终没有归属感。
我妈的对策就是让我尽快在当地成家,融入当地社会。那阵子,巴西龟闹情绪,不吃饲料,她改喂活虾、生牛肉。见我在一旁,她自编自演:“真不懂你们这些小王八挑什么,好好的饲料不吃,非要挑三拣四的……现在还有我侍候你们吃喝拉撒,没有我,看你们怎么办。”
我假装听不懂,不做反应。她不甘心继续唱独角戏,把我拉到玻璃缸前:“看着这两只巴西龟,不想到什么?”
“王八对甲鱼——彼此彼此。”
我妈白了我一眼,走开了。她对我婚事的着急,并不在于我年龄增长所带来的苍老,而是恐惧我随着年龄的增长,仍然一无所有。
两只巴西龟吃饱之后,各自往相反的方向走开了。一只在珊瑚骨上攀爬。无论怎么爬,爪子一举高,身子和水平面接近垂直,很快就滑了下来,摔得四脚朝天,露出藏匿八卦阵图的淡黄色肚皮。尽管一次次失败,它仍不改初衷,为获得自由不断尝试。另一只潜在水中,划动四肢,悠然自得。我把它从水中拿到火山石上,它没有片刻迟疑,再次扑到水中。它们之间隔着半个玻璃缸,看起来并不像我妈单方面断定的:成双成对,亲密无间。
我并非不婚主义者,去参观清代古民居,大户人家门口摆放一对抱鼓石,像蜗牛,像海螺,像龟背,我都能想到“有了家,从此有了铠甲”。当我妈再次用假音对着巴西龟唱着:“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我打断那不专业的歌声:“你干脆就像买巴西龟一样,直接给我安排个结婚对象,我从此洗尽铅华,勤俭持家,相夫教子,恪守妇道。”
谁都没有料到,十个月后的春节刚过完不久,我结婚了。结婚那天是清明节,男方选的日子。我问爸妈,你们核对过这日子了吗?他们反倒“教育”我:核对什么?可怜天下父母心,相信他们是希望你们好的……结婚后,你要以对方家庭为重,不能再像婚前一样,大小姐脾气。我懒得为自己辩解,只能自诩:没有几个人有本事把清明节过成情人节。我的闪恋又闪婚,越发不确定和这个男人是否一见钟情,也不确定我们能否白头偕老。如爸妈所愿,在异地有了自己的小家,彻底搬离了学校宿舍。搬离那天,我感谢老肖这两年的关照,邀请他有空到我家坐坐。陈副校长即将退休了,他从我身边经过时,我第一次没有理睬他。我没有长出势利眼,自信的“披风”也并非温柔的爱人、强大的娘家,或者自大的灵魂藏着低水平的认知。我只因工作出彩,生出底气,笃定拥有独自前行的能力。
秋末,我妈把玻璃缸搬到院子里,让巴西龟晒着接下去为数不多的暖阳,准备过冬。等到她想起,已经是第二天了,一只巴西龟不见了。我估计是那只追求自由的巴西龟,以不懈努力终于梦想成真了。我妈不乐观。她担心巴西龟被院子的野猫叼去折腾了,凶多吉少。就算成功逃逸了,接下去饮食、冬眠、“龟”生安全,还是充满各种挑战。
我妈的院子集果园、花园、菜园、草地为一体,即使在深秋,依然绿意盎然。这增加了寻找巴西龟的难度。
第一天,我们搜寻平时较少行走的区域,破被褥似的落叶覆盖着即将休眠的土地,不见巴西龟的踪影。
第二天,我们在裸露的泥土、地面寻找。我一个后退,踩到柔韧、有弹性,又有些许坚硬的物体,顿时吓得大叫。我妈问,怎么了?我指了指脚底,头皮发麻,脸色发青。如果脚下的是巴西龟,我决定素食一周,为自己的暴行忏悔。还好虚惊一场,我踩到的是块橡皮。
第三天,我妈想上街找个懂占卜的师傅算一卦,问问巴西龟现在情况怎样。我爸打断她的念头,“龟”是“龟”,又不是“闺女”,它要去浪迹天涯,就由它去,不是还有只在家吗?我妈看着我,我摇摇头,指着玻璃缸。
“留守龟”没有独居的困扰,心思更为单纯,在仓促到来的冬阳静美中,享受独霸江湖的快乐。照常吃喝、游泳、晒太阳,也依旧不爱到珊瑚骨上攀爬。不知道那里是它的禁地,怕触景生情想起“出走龟”,还是“龟”各有志,它根本就瞧不上攀爬的苦力活。
时光竟也慢了下来。
一年后,儿子三个月大,才会翻身,就开始用小手撑起身子,小腿后蹬,试图将身子往前挪。脖子还没有习惯支撑脑袋重量,使潜望镜似的脑袋摇摇晃晃的。我拿婴儿枕摆放在他的后背,小小身子轻微一晃,很快适应负重。我看看他,又看看客厅摆放的玻璃缸,难怪有些眼熟。
我妈在院子里晾衣服,像中彩票般唤我,拳头大的深绿色“石头”上沾满灰尘和泥土——身披盔甲的“出走龟”凯旋归来。我们拿出无骨、无刺的软碎肉为它接风洗尘,它毫不客气狼吞虎咽,我儿子在一旁看呆了,还流下一串口水。我教儿子念龟,龟,乌龟,小乌龟。他朝我傻笑,口腔散发着若隐若现的奶香,我一时忘形,凑近闻,他顺势把手指塞入我的嘴中。我轻吮着,才发现小家伙的指甲壳,柔软、锋利,比出生时候变得坚硬了。
我一夜倒退到儿时,和儿子学着巴西龟爬行,和他一样用牙牙语交流,连审美风格都朝可爱类型的方向转变。我驮着儿子在客厅爬行,他仿如我后背的甲壳。我一时分不清我们俩到底谁像龟,也许我们都是龟类,玩着“叠罗汉”的游戏。
“小乌龟抓紧妈妈哦。”儿子的双臂环紧我的颈部,我让身子贴近地面,又轻微斜向一侧,他从我背上翻滚下,笑得咯咯咯的,如同珍珠项链脱线,一颗颗珍珠跃在地面的兴奋。孩子他爸在沙发上刷着手机,没有意识到我们娘俩都“变种”了。我不想孤立他,半开玩笑的让他负责遮风挡雨,娘俩放心快乐长大。他冲孩子一笑,点点头,目光又快速回归手机。
不知道是哪道程序出错了,孩子他爸开始和我洗脑,劝我“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我不懂他口中的“苦”和“乐”是什么,只想着老一辈人说的“平平淡淡才是真”“孩子是父母的天”。我和他分享儿子的成长,每天发生的趣事,模仿儿子各种表情说话,他微笑回应。直到他提出离婚,不再支付家用,只催着我早点办理手续。我如梦初醒,回忆那些过往。爸妈曾为我的婚姻进行分析、评估、提议,我始终视其为他们思想中的傲慢与偏见。那套忍辱负重、靠智取维持婚姻技巧,已肉眼可见地失效。时代早已不同,平衡一段婚姻更需要理智和情感。婚姻只是一张看似安稳的甲壳,没法成为真正无坚不摧的铠甲,试图通过它回归到舒适圈,或许炸个片甲不留,它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手雷。
孩子他爸提出离婚的那一刻,无穷的挫败和失望浇灭了我设想中的幸福火花。我还是盼着他能与我和好如初,对我微笑,告诉我,一切都是恶作剧。但他没有,甚至连家门也不进了。儿子每天早上一睁眼,哭着、念着爸爸,我心烦意乱,五味杂陈的情绪隐藏在心里。第一次居住在没有天花板的屋内,户外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我浑身沉乏,嗓子生痰,整夜难以入眠。半梦半醒时,也是噩梦连连,牙齿保持死死咬合的状态,持有警惕状态。短暂浅睡后,没有一点睡醒后该有的松弛舒爽,双手握拳,克制琐碎和无聊念想。我忽然明白,清明节终究过不成情人节,结局缘自起始。我不敢告诉任何人,包括爸妈:我身上没有积蓄,此前的所有收入都交给孩子他爸打理了。
乌龟,本该是壁虎的肉身,警惕性高,动作敏捷,随时可以断尾。只因在一地待久了,就住在壳子里了,习惯了松弛的状态,一旦面临与甲壳分离,才发现肉身已经和甲壳粘在一起,长在一起,嵌在一起了,难以脱离,丧失了壮士断腕的勇气。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虚荣的时代,精致的时代,沉默的时代,全民演戏的时代,我只在儿子面前卸下一切伪装。他还不足三周岁,我自认为任何泪水不会在这时候渗入他的记忆里。他意料之外地轻拍、抚触着我的后背,暖暖的身子扑到我怀里,为我擦泪,他的眼里写满焦急、关切、无措。我紧紧抱着他,他小小的脊梁骨直挺挺的。他已经把该背负的、不该背负的责任,一点一滴扛在肩上,越背越沉,每增加一点负担,他都显得束手无策,又是那么的心甘情愿。
终于有姐妹获知。一个摆出圆规似的站姿,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没有人有义务三天两头给你煲心灵鸡汤,自己不想振作,谁拉都没有用。”一个搂着我肩膀开导:“伤心改变不了事实,你把这些精力花在写作上,估计还能发表几篇作品。几年后回望,儿子健康,父母双全,工作顺心,创作颇丰。婚姻的缺口就像常见的月亏,只要肉身还在,还有机会在其他方面扭亏为盈。”
哭泣和倾诉都是对时间无效的消耗。人生没有真正的失败,每一次挫折都是下一次起飞的弹跳板。幸好还有写作。法国学者尚塔尔·托马在《被遮蔽的痛苦》写道:“使尽全力去拒绝痛苦,只允许自己受一点点苦,其实这样做,是投入注定失败的战争,还会因此在情绪上、想象上、肉欲上衰弱下去,从而不能做出重大发现。世界因我们过度的痛苦避开我们,而我们也会因吝啬眼泪而错过世界。”
儿子在幼儿园旁的小卖部驻足,目光停留在透明塑料盒里绚丽多彩的巴西龟身上。这些巴西龟出壳没多久,就要经历UV打印机的摧残,让龟壳、头部、鼻孔,甚至眼睛都被漆满颜料。我不知道它们经历这场酷刑后,怎样再次实现伸展、睁眼、呼吸。幸存者凶多吉少,颜料有毒,易使甲壳溃烂,患腐甲病和翘甲病,并且甲壳印上彩料,无法通过晒太阳进行钙质转换,它们的生命很难走向下一季,除非用小刀把彩料刮去,这又容易造成新的创伤。
甲壳并没有保护它们,它们却因“壳”被利用。
我把儿子放在爸妈身边,当起了“周末妈妈”,平日里所有心思投入工作和写作。那些委屈、欺骗、诋毁、背叛、伤害、抛弃化为石材、木材、红砖、青瓦、色料、玻璃,还有花花草草……在显示屏上建筑着自己的文学小屋和花园。写作支撑我走出生活的泥潭,使我在自卑和迷茫中看到亮光,获得苏醒。我一边敲打键盘,一边习惯性朝左侧扭头思考,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巴西龟从龟壳探出它厌世的脸,它不会哭泣、争吵和呐喊,对谁都不爱搭理的。我猜想它的内心曾被往事撕裂,如今永远是一副波澜不惊的神情。只有触及某个痛点,悲伤再次涌出,孤寂地缩在甲壳里,独自疗伤。
儿子见我用热水烫蟑螂,蟑螂逃之夭夭,也想试试龟壳能否在热水中保护住巴西龟的肉身。我还来不及制止,就闻到一股腥臭味,他立即意识到自己做错事了,眼圈一红,扑到我怀里。他的知识量和人生阅历,还不能理解因为有了甲壳,巴西龟行动一直谨小慎微,失去像蟑螂一样四处逃窜的能力。
我安抚着他,他依然沉浸在悲伤之中,后背轻微的抽搐,好像来自我子宫里的胎动,我感知自己的背部正在改变,愈发坚硬且厚重。
责任编辑 夏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