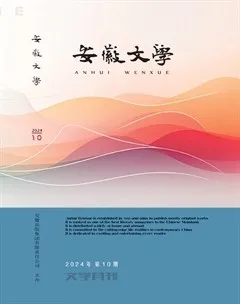棉蝗记
1
看到第一只蝗虫时我没太在意,径直走过去,片刻又看见一只,接着看见第三只、第四只。
这是立冬后天气转暖的日子,空气中有茶花香。虽置身山野,脚下的路面却是水泥浇筑,蝗虫停在路中间的太阳地里,寂然不动如老僧入定。
我拿出手机,打开镜头,凑到一只蝗虫跟前,“咔”,听到拍摄的声音,蝗虫撑起后足,片刻又趴下。
蝗虫的个头有一指长(约90mm),通体青绿,翅膀尾端枯黄,有磨损残破的痕迹。立冬后温度陡降,从二十多度降到零度,对山里尚未进入冬眠的昆虫可算是一场劫难。
还是不要打扰它了,让它继续晒太阳吧。起身,往前走,一小段路后又看见三只蝗虫。水泥路面隔个两米就有一道路缝,三只蝗虫待在路缝上,姿态一致——前半身抬起,尾部低垂。
我再次点开手机镜头,给它们各自拍了一张近照,发现它们的尾部插在路缝里。如同之前的蝗虫一样,它们对我的靠近无动于衷。
这究竟是个什么日子,怎么蝗虫都到路上来了。要说晒太阳,两边的草地也是有太阳的,在草地晒太阳还有个掩护,不容易被发现,饿了渴了顺便吃几口多汁的草叶。在这光裸裸的路上待着,简直就是把自己端上餐桌,请鸟儿来享用。
路边的杂木林里就有几只鸟儿蹦跳着呼朋唤友,发出类似“天气真好,快出来找食儿”的鸣叫声。抬头细看,是黑脸噪鹛,它生性活泼,一伙儿七八只,飞到哪里就把欢快的气氛带到哪里。
黑脸噪鹛的食谱中排列在首的就是蝗虫。也不只是黑脸噪鹛,几乎所有的林鸟都是蝗虫爱好者,蝗虫为它们提供了身体所必需的动物蛋白和脂肪,可以说,鸟儿的每一次歌唱与飞翔都有蝗虫供给的能量。
在山谷里走了一圈,看见二十多只蝗虫。快出山时,路中间的太阳地里又见到两只,它们身体叠在一起,一动不动——这是一对交尾的蝗虫。
原来立冬后仍有蝗虫在孕育后代,这简直颠覆了我此前的认知,以为生命短暂又脆弱的蝗虫入冬后早已销声匿迹。
回家后翻开昆虫图谱,比对图片,确定在路上看见的蝗虫学名叫棉蝗,也叫大青蝗。
棉蝗是直翅目昆虫家族中的一员。直翅目昆虫的基本特征是有前翅、后翅、复眼、口器和触角。前翅也叫gne0pjqHtoUp1kvff7A90etgnTPjBBebmrDufaW0Dio=鞘翅,质地坚韧,是保护后翅和身体的铠甲。后翅薄而透明,收拢在前翅之下,只在关键时刻——飞起来的时候才像扇子一样打开。
棉蝗是蝗虫界的“绿巨人”,体格健硕,力量强大,因此也有地方称之为“蹬山倒”。然而这家伙并没有外表看起来的那般强悍,对自己拥有翅膀这回事也不在意,很少飞行,甚至也懒得蹦跳,更愿意缓慢爬行,安静地发呆。
2
第二天,阳光不错,九点半出门,十点到达山谷。
山谷的路是环形的,出口即是入口。我选择逆时针的方向走进山道(昨天是顺时针),转一个弯,就见到路上侧卧着一只棉蝗,翅膀凌乱,腹部炸裂,有淡黄色呈膏状的东西流渗出来。在它不远处,另一只体型略小的棉蝗也以相同的,被碾压过的模样趴着。
想起昨天那对交尾的蝗虫,正是这里遇见的,看来在我离开之后,没多久它们就遭遇了不测。
这座山谷里有几片茶园。晚秋初冬正是种植茶树苗的时节,常有车子开进来运送肥料和树苗,当车子经过,路中间的棉蝗是无论如何也躲避不开的。
正当我叹惋之时,一只土褐色的小蚂蚱蹦了过来,停在压扁的棉蝗跟前。小蚂蚱体型极小,瑟缩着,呆立不动,仿佛陷入了一种失神,对近在身旁的我也毫不理会。
它为什么要停在死去的棉蝗跟前,难道……是来默哀的?
过去了三分钟,小蚂蚱这才移动身体,爬到那堆紧紧黏在地的“蛋黄”上,埋下脑袋,开始了颇有力度的咬嚼。
原来小蚂蚱是来进补的。
嚼食了一会儿“蛋黄”后,它开始进一步探索,爬上爬下搜寻了一阵儿,有点无处下口的样子。
我挪开脚步,继续往前走。想到之前竟然以为小蚂蚱是来默哀的,不禁感到好笑。
山谷里的路弯弯绕绕,有朝阳的一面,也有背阴的一面。背阴的路段看不见昆虫,进入朝阳的路段后,就见两只胡蜂喝醉了酒似的横冲直撞,之后又看见路边一只大腹便便的棉蝗。
棉蝗刚从草里爬出,仿佛承受不住身体的笨重,摇摇摆摆,走几步,便停下来歇一会儿。
使棉蝗不堪重负的是它的腹部,棉蝗几乎是拖着自己已然超载的腹部往前走,好不容易走到马路中间,在有路缝的地方停下,将腹部抬起,下弯,弯成直角,尾端探入缝中,开始了挖掘的动作。
为了看仔细些,我只得伏下身子,双膝着地,把头贴上去。此时如果走来一个人,肯定以为我在跪拜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从棉蝗的尾端内部伸出一对类似铲斗的器官,一张一合,将细沙泥土挖开,拱到边上,轻轻扭动腹尾,缓慢地钻下去。
三分钟后,棉蝗成功地将腹部插入缝中,只露出一小节上腹在地面。之后,棉蝗就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在阳光下安然不动。
这只大腹便便的棉蝗是雌性,将腹尾插入缝中,是为了在这阳光普照的宝地产卵。蝗虫大多是以卵的形态在地下过冬的,直到来年春天,青草钻出地面的时候,若虫也会从泥土下爬出来。
3
第三天,晨起大雾,楼下草坪覆了一层薄霜,空气里有冰凌的味道。
十点钟,把相机放进背包,又放了一个苹果,骑上自行车出门。心中挂念着山谷里的小家伙们,不知它们可经得住这场霜冻。
到达山谷,雾气早已散尽,阳光通透明亮,天空水洗过似的,呈现出水晶质地的蓝。进山谷,走五百米,见到坡上一株有些年头的银杏树,树身粗壮,够两人合抱。银杏树的叶子黄灿灿一片,逆光看,如同身披金袍的老神仙。银杏树下是茶园,茶树上爬满葛藤,路边灌木上也是葛藤,层层叠叠地缠绕,叶子在阳光下发出铁绿色的光。
初冬也是挖葛根的季节。往山谷里走,隔一段路就听到铲挖声,不见人影,只见路边停着电动车,车里放着一截截黄泥色粗壮如手臂的葛根。葛根是野生的豆科植物,生命力强大,任人刨地三尺挖之掘之,翻过一年,仍是漫山遍野到处蔓延。葛根洗净后切片晒干是药材,烀熟了切成段状又是能饱腹的点心。粗大的葛根捣碎洗粉,洗出的淀粉晒干,能储存很久,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煎葛粉饼,做葛粉圆子、葛粉羹。
本地人挖葛根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乡村生活延续下来的习俗,和春天挖野菜一样,是与山野亲近的方式。到了时节,就被一个声音提醒:是时候了,可以开挖了。
进山的车子多,对路上晒太阳的棉蝗来说可谓不妙,尤其在路缝里产卵的雌棉蝗,简直是灭顶之灾。
山谷里走了半小时,沿途已见四五只压扁的雌棉蝗,从腹部溢出的“蛋黄”引来黄胡蜂和蚂蚁,围着团团转。
“蛋黄”就是雌棉蝗的卵。蹲下来,观察一小团未被碾碎的卵,色如金黄琥珀,形如细长大米,一粒一粒黏在一起。
对黄胡蜂和蚂蚁来说,这可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美味,各选所需,先饱餐一顿,再挑那适合搬移的部分,运回各自的巢穴,作为冬天的储粮。
就在黄胡蜂和蚂蚁大快朵颐之际,一只小蚂蚱出现了。小蚂蚱的学名叫红褐斑腿蝗,这也是查询昆虫图谱得知的。认识昆虫的乐趣就在于此,先是看见它,然后知道它的名字、习性,再见时就不再陌生了。
小蚂蚱爬到雌棉蝗身侧,停下。直到黄胡蜂和蚂蚁心满意足地离开,这才爬到“蛋黄”处,享用起食物。
“大自然没有浪费的东西。”没头没脑的,我心里冒出这句话。
4
在看到棉蝗之前,有半年时间我的目光是失焦的,没有什么能吸引我的注意力,那部用了十多年的相机也被遗忘,在灰尘里待着,似乎再也派不上用场。
直到棉蝗不期而遇进入视野,我才重新拿起相机,擦去灰尘,对它说:老伙计,跟我一起出门吧。
得感谢棉蝗,它唤醒了我身体里住着的孩子。我身体1551517d99e490af90b5a9e1854b97a3里住着的孩子就是童年时的自己——孤单,怯懦,笨拙。然而只要进入山野,那个“自己”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灵敏如小兽,欢快似3fb2713d69775bdb4b4dd6b0f0cb07af鸟雀,日光的照耀下每一个毛孔都在载歌载舞。
或许我原本是山野的孩子,只是借了母亲的子宫来到这世上。当母亲把我生下,剪断脐带,我就成了惶恐不安的“流离失所”者。值得庆幸的是,我和山野之间的脐带未曾剪断过。年复一年,山野以她的方式庇护我,输送给我需要的能量,向我展示美之所在和生的奇迹。
也有一些时候——往往是我在俗世生活中消耗过多能量的时候,会突然陷入倦怠,被一团无名的惰性气体裹挟,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也丧失了快乐的能力。
早些年我会挣扎,然后陷入更深的沮丧和失语。后来——也就是这几年,当我再次被“惰性气体”围困,就对自己说,没关系,别为难自己,过段时间会好的。
我像观察一只昆虫那样观察着自己,安静地守着,看着。直到有一天,不经意间,一束光照过来,感官重新变得敏锐,目光又有了焦点。
5
雌棉蝗附近总有一两只雄棉蝗,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脑袋朝着雌棉蝗的方向观望。
雄棉蝗的体格比雌棉蝗小两号,翅膀没有磨损残破的痕迹,腹部隐藏在翅下,尾尖微微上翘,一副“清俊小生”的模样。
正午阳光强烈时,偶尔会见到飞翔的雄棉蝗,雄棉蝗飞起时露出红色后翅,逆光看过去如一朵凌空而起的火焰。
作为雄棉蝗,求偶的时候免不了要遭遇挑衅,与另一只雄棉蝗来场格斗。格斗之前会对峙,几分钟后,其中一只打破僵局,扑向对面,落在对手背上。
生性懒散的棉蝗,格斗起来也是懒洋洋的,撕咬两个回合就作罢,认输的一方向后退开。
获胜的雄棉蝗也不恋战,用前足捋了捋触角,后足摩了摩翅膀,整理好仪容,郑重其事地向雌棉蝗爬过去,每爬几步就玩起花样,抬起一只后足,伸长,举起,举到身体的极限,再收拢,放下。接着抬起另一只后足,伸长,举起,再收拢,放下,动作像有点卡顿的慢放镜头。
这是雄棉蝗的肢体语言,或者说求爱之舞,竭尽所能地展示自己体格的健美,以此吸引雌棉蝗的注目:看,我的大长腿,多壮实,多灵活。
对棉蝗来说,拥有一对健全结实的后足确实很重要,棉蝗的跳跃就靠后足发力,同类间格斗或面对天敌时,后足也用来当武器。造物主为了让这小小的昆虫在地球上得以生存,在它的后足装置了双排锯齿状的“暗器”,小时候我就被棉蝗的“暗器”划伤过——小心地俯下身,慢慢靠近它,就在我的手触碰到它背部时,谁知它后足抬起、一蹬,一股强大的力道将我的手弹开,在指尖留下细长血痕和针扎的锐痛。
拥有这样一对后足,棉蝗甚至敢跟人叫板。当我蹲下,想给那只向雌棉蝗献艺的家伙拍个近照,谁知它猛然转身,把脑袋抵过来,很霸气地撑起后足,深棕色的复眼盯着我,身子左右摇摆,作出一副随时要冲上来的威胁状。
你这个愣头青,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也罢,不跟你计较,还是我让开吧。我站起身,准备后退,拉长的影子刚好挡住了阳光,雄棉蝗在我的影子里有点慌神,那股子要挑战的劲头也不见了,转身,向着有阳光的地方爬去。
雄棉蝗爬出我的影子,重新进入阳光之地,停下来,似乎想在太阳地里歇会儿。这时我又移过去,挡住阳光,让影子遮住它。在影子覆盖到它身上的一刻,雄棉蝗显得很无奈,再次起身,向着影子外面的阳光地带爬行。
出于好奇,也出于“逗你玩”的心态,我走到另一只棉蝗跟前,遮住它的阳光,果然,原本一动不动的棉蝗撑起后足,开始爬行,爬出影子后,就停下,继续晒着太阳。
我把“影子游戏”和这段路上的每只棉蝗玩了一遍(除了正在产卵的雌棉蝗),无一例外地,棉蝗对我的影子避之唯恐不及,我几乎能听见它们的抗议:让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6
第四天,吃过简单的午餐,拎起相机骑车出门。刚进山谷就与木樨花香打了个照面,心头一荡,四下里寻找,并未见着花树。
放慢脚步,深呼吸,这时开的木樨花是季节额外的馈赠,经过霜气沉淀的香气,又温煦,又清冽。
山谷里有一段路从竹林穿过,阳光只在正午泼洒下来,在地面留下斑驳光影。竹蝗就是在这里看到的。
早前不知道它叫竹蝗,只惊异于它的鲜亮与轻盈,从眼前的光线里飞掠,似翡翠绿的叶子落入竹梢。落入竹梢的竹蝗匍匐不动,见我走过去,快要发现它了,就悄悄移动身体,移到一枚竹叶背面,过会儿又忍不住探出触角,再探出脑袋,拿乌溜溜的复眼看我。待我靠近,摁下快门之际,“嗖”的一下,它蹦开了,落在另一根竹枝,藏身叶后,又探出脑袋暗中窥视,那模样分明是一个顽皮孩童,引逗着人跟它玩捉迷藏呢。
我倒是很愿意和竹蝗玩这样的游戏,相互试探,彼此好奇,在这样的游戏中,一个人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面前的昆虫也不仅仅是一只昆虫。
这片竹林里的竹蝗有两种:黄脊竹蝗和青脊竹蝗——或许还有别的种类,只是我没有见到。两种竹蝗的区别不大,都穿着翡翠绿的“上衣”(头和胸腹),明黄色的“裤子”(后足),两翼也均是黑色,微小的区别在“上衣”的背脊上,黄脊竹蝗的背脊正中有道醒目的黄色竖条,青脊竹蝗则没有。
和大青蝗那种慢腾腾、懒洋洋比起来,竹蝗简直就是反面。竹蝗虽生得小巧,却有股子生猛劲儿,敏感且好动,根本不给人靠近的机会。当然,也不是完全无法靠近——当竹蝗交尾的时候,身体就没有那么轻盈了,这时可以稍微挪近一点,保持两步远的距离去观察(这是竹蝗容忍的极限)。如果我想再近一点,再往前挪动半步,竹蝗就会立马蹦开,一只驮着另一只,颇为吃力地蹦到安全区域。
7
来山谷的次数多了,发现总是能在相同的路段遇见同一只棉蝗。那是一只独足(后足)雌棉蝗,一根触角也断了半截——为了表达对它的敬意,不妨称它为蝗娘。
初见蝗娘,它在路中间艰难地爬行,缺了一条后足的支撑,腹尾总是倒向一边,趔趔趄趄。
蹲下来观察,蝗娘的腹部如同熟透了的浆果,隔着一层薄皮能看见腹内卵粒。不知这只蝗娘经历了什么,好在虽然丢失了一条后足,并不影响它此时的使命——为后代寻找过冬之地。
一刻钟后,蝗娘爬到一片长着细草的路缝,抬起腹尾,探测了一会,似乎很满意,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挖掘“地下室”,产卵。
真是个天才母亲,太了不起了。看着蝗娘撑着一只后足,用尾端的产卵器缓慢挖掘,直至把大半截腹尾安稳地埋进细草,心里止不住赞叹。
法布尔曾说“本能,其实就是动物的天才”。鸟儿在繁殖期会筑巢,昆虫在繁殖期会为后代寻找宜居之地,自然界的小生灵之所以能够生存,延续生命,都有它们与生俱来的天赋本领。
过了一天,同样的地方又见产卵的独足大青蝗,细看它的头部,一根触角断了半截——是头天见到的那只蝗娘。
想不到会再次遇见,如此说来,这片区域就是它的生活半径了。
后来的几天,路过这里就会下意识地寻找它,每次也都能找到,有时在路牙子上发呆,有时在路中间产卵。很奇怪,只要看见这只独足蝗娘,我的内心似乎也获得了某种慰藉,变得有力量了。活着真好啊,对这只蝗娘来说,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珍贵的,是幸存。
对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珍贵的,是幸存。
大约一周后,这只断了半截触角的独足蝗娘不见tz7zxZkojqVv2NVmtq+Lgx5W1BHwgStoJrlHkccm6mE=了,尽管知道它的消失是必然,心里还是有一小会儿失落。
8
小雪节气第二天,正午,去山谷里看棉蝗。
和刚立冬那阵子比起来,棉蝗的翅膀更为残破,衣衫褴褛的样子。有只棉蝗大概遭遇过袭击,半边翅膀不见了,好在它还活着,还能爬行。有两只雌棉蝗正在路中间的太阳地里安静产卵,蹲下来细看,发现它们各自失去一条后足。
也有失去两条后足的棉蝗,趴在地上匍匐而行。不远处,一只黄胡蜂正费力地拖拽着什么东西,走近了看,正是棉蝗的一条后足。
黄胡蜂扛着战利品飞起来,还没飞出一米远,就“迫降”了。棉蝗的后足比黄胡蜂长出两倍,又缀满锐刺,想要扛走可不那么容易。
这天还看见螳螂啃食棉蝗的场景。螳螂通身青绿,腹部粗壮,看样子也正处于产卵期。螳螂用前足将棉蝗横着摁在地上,埋头饕餮。棉蝗侧卧着,腹部几乎被噬空。螳螂用一种“唯有美食不可辜负”的专注享用它的猎物,即使我用手拨弄它的背部也不理会,此刻天塌下来似乎也不能让它停止进食。
9
小雪第九天,阴,温度比前段日子降了许多,天气预报显示白天8℃,夜里1℃。中午的时候想,去山谷看看吧,看看是否还能见着棉蝗。按说这样的天气是见不着的,也不一定,还是得眼见为实。
山谷入口处的银杏树已落光了叶子,就在前天,这棵树还披挂着黄袍。葛藤叶子已焦枯,茶花还在开着。松树林里听到长尾山雀的叫声,另一边山坡传来椋鸟的嬉闹声。
走了好一段路,没有见到棉蝗,也没有见到别的昆虫,那些在有阳光的正午随处可见的小家伙们都不见了,站定了听,也没听到那种窸窸萃萃的虫吟,草窠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看来昆虫的冬天是真的到来了。
快出山谷,总算见到一只棉蝗,磕头状趴着,前足已失去支撑,触须也耷拉下来。走到跟前,蹲下,用手触摸它,棉蝗已没有知觉。把它翻过身,腹部朝上,也没有丝毫动静。想着把它移到草丛里去,免得在路上又遭车轮碾压,弄得支离破碎。于是用手指捏住背部,刚起身,就感受到来自它躯体一股反抗的力量,接着,一对后足蹬了上来。
我的手一松,棉蝗“啪”的一声,摔在地上。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心里连声道歉,让它在奄奄一息时还这么重地摔一跤,真是罪过。
还是不想让它在路中间待着,又伸出手,捏住它的背部,棉蝗的后足又蹬上来,仿佛它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已死去,独这一对让它拥有“蹬山倒”之誉的后足还活着,本能地发着力。
我用极快的速度把它放进草丛,搁在一片阔大得犹如手掌的落叶上。
再见,棉蝗,就让落叶成为你安宁的归宿,让泥土成为你永久的故乡。
责任编辑 夏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