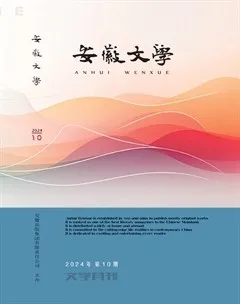吹奏者
七岁之前,他跟村里任何一个小男娃都没有区别。他们一群一伙,蹲在土里弹蛋儿,和尿泥,拿枝条不停抽打黄土,抠开蚁窝让无辜的蚂蚁到处乱窜,或者用谷秸棉芯做个手枪模型,小心翼翼端在手里,觑着一只眼,对着目标,嘴里还不停地“啪啪啪”。更多时候,他们像旋风一样穿过暖村的村巷,刮到饲养处的柰子树上,又刮向村口的阁洞下比谁跳得高。这股风也会刮到场院,效仿开小差的谷秸,在地上画一个圈,伸开双臂开始旋转,张着嘴,露出粉红的喉咙,大叫,大笑,或者大骂,晕头转向中跌倒。冬天,一场雪后,他们摇身变成了西北风的同僚,在温河冰面上不停奔跑,被惯性推着向前滑去,感受飞翔的速度和惬意。那时,他跟每个男娃子一样,棉袄袖子上布满擦过鼻涕的痕迹,油亮挺括的袖口中露出一截皴裂的黑红手臂。而唯一的区别在秋天,当男娃们把落叶一把一把地抛向天空时,他变成一块安静的石头,长时间抬着头,注视那些在空中飘落的树叶,试图通过意念中的咒语,将这些叶子固定于某个瞬间。
春天,温河迟缓的水流一夜之间变得清澈湍急,不几日,老柳枝上露出星星点点的嫩芽。作为风,男娃子们早已提前掌握了这一秘密讯息,撂下碗就奔向河边。老柳虬结的根一半裸在外面,一半斜插在土崖上,整个树身仿佛经受着某种压制,不得不痛苦地探向河面。虽然曾被大人们耳提面命,告诫此处危险,不得随便攀爬这株老柳,但油嫩嫩的枝条就像一只只明亮的小眼睛,一眨一眨召唤着他们。好胜心战胜了一切,他们选出身手最敏捷的小海,七手八脚扶着他爬上河边避雨房的房顶,用急切的催促声,用期盼的眼神,看着他手脚并用爬上了树。仿佛柳树抖了抖身子,一些细枝条便从树间落下来,有的直接掉到河里,有的掉到下面男娃们的手里。那时,他就站在小孩中央,仰着头,看着树上小海灵巧的身体,在长长短短的树枝间腾挪。
不用多久,整个暖村的上空都被柳笛声霸占了,飞来飞去的麻雀消隐不见,那些喜欢蹲在墙头的喜鹊也躲起来了。那几天,连我们这些刚被大人允准单独出门的小女娃,都开始掌握了在各种不同声线中分辨他们唇间柳笛形状的能力,如果声音急促而低沉,柳笛定然粗而短,相反尖锐而悠长的那只柳笛,多半细而长,最好听的柳笛声,来自树枝中上段的那个部位,柳管不长不短,匀称而柔软。柳笛从早到晚地吹着,逐渐覆盖了村庄原本的声音,即便最沙哑最低沉的柳笛声,也能盖过母亲们喊吃饭的声音,盖过父亲们责骂牲口的声音,更是将鸡叫和犬吠拿捏得死死的。当磨面房惊天动地的机器开始轰鸣,一管尖锐的柳笛声也能将震耳欲聋的幕布撕破,露出一个布满齿痕的空洞。
我跟伙伴禾苗手拉手站在那里,目光中饱含羡慕,看着那些男娃唇间的柳笛渐渐湿润,渐渐变软,渐渐哑掉。那时,他们的手里,包括上衣口袋,都藏着几支吹坏的,或者尚未做好的柳笛。柳笛吹一段时间后,柳管就会裂开,裂缝如果太长,柳笛就废了,但如果是短裂缝,只需用小刀切掉,重新将入唇部分的外层用指甲刮出一截白中泛绿的哨片,门牙轻轻咬几下,再去吹,它便又是一支完美的柳笛。可是,即使是同一支柳管,新柳笛的声音却再也无法跟旧柳笛的声音同频同声,似乎经过修缮的柳笛,是死去之后的重生。他们最终会将重生两次乃至三次之后彻底死亡的柳笛胡乱地扔到土里,那截泛着水汽、破损的柳笛,依然对我有强烈的吸引。
他也有一支柳笛在唇间,但显然没有其他人吹得轻松,他鼓起的双颊,通红的脸,还有额头的汗水,柳笛中断续的、沉闷的、不安的声音,以及被留在原地的孤单,让他看起来狼狈极了。尽管如此,禾苗还是跑了过去,拉了拉他的衣襟,以无比渴望的声音说:“哥哥,我也想要一支柳笛。”七岁的他正将身体中的全部力量聚集在口唇,笨拙地对付那支柳笛。而妹妹的手,就像拉开了他的气囊开关,他一下子就泄气了,先是鼓着的双颊瘪下来,之后是脸上的红晕渐渐散去,汗水凝固在额头。“小闺女们都不吹的。”这是他的托词。但这托词就像风里的尘粒,没有多久,就被妹妹禾苗的软磨硬泡吹没了。禾苗拉着我,转身向阁洞跑去,他已经进入阁洞。我们穿过阁洞下坡,拐弯,远远看见,小河口的老柳树上,他就像长在上面的一根长枝,随风向我们摇摆,招手,呼唤。
多年后的今天,我还在纳闷,是为了满足妹妹禾苗的愿望,他才在无人相助的情况下,勇敢爬上河边的老柳树,并阴差阳错地推开自己作为演奏者身份的门扉?还是一切都是某种不可逆的安排,必须得是那一天,那个下午,那一刻,由妹妹来按动他生命某部分的启动开关?时过境迁,我再也没有得到答案的可能。但不可否认,当他从树上小心地爬下来,又从避雨房的房顶处溜到一块不规则的石头上,而没有如我们担心的那样掉到温河里的时候,他已不是刚才上树的那个男娃子了。当时我们并未觉察,因为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保持原样,他捡起那根柳树枝,就像捡起了自己。我们回到禾苗家,看他将枝条上刚刚冒出来的小嫩叶摘去,轻轻揉搓着枝条,然后用剪刀将树枝剪成几段。第一个柳笛他做坏了,在把里面黄黄的树芯抽出来的时候,嫩绿的树皮被划了两个口子。下一个他就小心多了,适时加长了揉搓时间,在确保树芯跟树皮之间毫无粘连的时候,再小心将它抽出来。抽出来的柳笛放在盛了凉水的碗里,浸泡了好久,才将其中一支拿出来,用指甲在顶端刮出一道浅浅的哨片,然后放在嘴唇间。
并没有清脆嘹亮的笛声响起,只有噗噗的吹气声,好像他胸腔里的气,变成了一股风,被他用力吹出来,但没有任何声响。于是,他用牙齿嚼嚼“哨片”,再放到唇里吹,如此反复几次,哨片被他嚼烂了,不得不用剪刀将哨片剪去,再刮出一个新的哨片,如此几次,那支柳笛变成短短一截,根本无法承受声音的重量,从他的唇间箭矢一般射出去。直到第三支柳笛,他才吹响它。那一刻,禾苗高兴得从地上蹦了起来。
我也沾了禾苗的光,口唇间第一次感受到一支柳笛的存在,口腔里又涩又苦。但我们只能像其他小孩那样,吹响它,呜呜声,或者嗯嗯声,而不是像他那样,突然掌握通向未知领域的窍门,将柳笛吹出完全不同的声音。那个下午过后,他像一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突然就变得技艺超群,高大而威严,收获无数羡慕的目光。有时他就站在他们中间,嘴唇里甚至看不见柳笛,但那种忽而高过云层,忽而跌落悬崖,忽收忽放,忽喜忽悲的哔哔声,会从他的身体里传出来,让众人目瞪口呆,直到他张开嘴,舌尖上躺着一支筷子头粗细,短短的柳笛。
那是一个属于他的春天,是他人生的分水岭,我们只是柳笛的初级吹奏者,而他已掌握柳笛吹奏的中级技能。有一次,他的笛声吸引了月亮大爷。那段时间村里的大人们正没日没夜在地里劳作,赶着牛耙地,扛着坷垃锤用力敲碎那些坚硬的土坷垃,为即将来临的播种日做着准备,除去不出门的老人,村里只有饲养处喂牲口的月亮大爷最闲在。这是他第一次在一个大人面前施展他的技艺,那应该是柳枝最好的部分做成的柳笛,他通过轻重不一,长短不同的吹气,让那支柳笛之中,布满温和的、婉转的、急促的、悠长起伏的声音,渐渐地,我们面前出现炎夏的画面:苍蝇到处飞舞,惹得一个婴儿号啕不止,后来,婴儿的哭声渐渐止住,应该是被抱在怀里。窗外,一只麻雀叽叽叽叽地叫,树下,一个被责骂的女娃正嘤嘤嗡嗡地哭,猪在圈里吭哧吭哧地吃食,一只小狗发出呜呜声,羊羔咩咩地叫起来,公鸡开始打鸣,圈里的骡子也嗯啊嗯啊个不停,突然从街门外传来咳嗽声……月亮大爷刚开始还在一口接一口地吃烟,后来,烟袋锅离开了嘴唇,嘴大张着,两个金牙就像把门的哨兵,也从他嘴里探出头来,一直到吹奏者停止了吹奏。好半晌月亮大爷才想起手里的烟袋时,烟袋锅里的烟丝已变成灰,他将烟袋锅翻过来,在石头上磕几下:“这娃子日能,把这玩意儿吹得赶上早年的口戏了。”
“口戏是什么啊?”
喜欢叨古话的月亮大爷的话匣子便打开了。他说古时候啊,有会口戏之人,口戏口戏,就是用嘴来演戏,怎么演呢,既不用定脸子,也不用穿戏袍,全凭一张嘴,就能让人们听出风云变色,万马奔腾。听戏的人,要坐到屏风后面。这种口戏,多在茶馆酒肆,边喝茶边听口戏,想当年那可是人们最大的享受啊。我这古话,也是听我奶奶叨的。我们哄的一下笑成一团,月亮大爷的奶奶,那得有多老啊。你们不要笑,再老的人,也是有来处的,爹妈祖宗就是每个人的来处。话说我爷爷当年在京城一家裁缝店当伙计,有一回跟着东家去了一个茶馆,就见识了一回口戏。其实,你们的爹妈都会口戏呢。他笑眯眯地盯着我们看了一圈,见我们纳闷,便噘起嘴,吁吁地吹起来,这不就是口哨声吗?婴孩半夜从被子里抱出来,迷迷糊糊蹬腿抵抗,那时妈妈们的嘴唇就会噘起,吁吁地吹起来,婴孩就乖乖地尿了。我们又是一阵大笑。这口哨,是最粗浅的口戏,好的口戏,是学什么像什么,难辨真假。我爷爷当时不过十五六岁,他站在东家身后,猛听到马蹄声响,刚开始是一匹马,渐渐就是两匹,后来就多了,分不清几匹马,战鼓擂响,人喊马嘶,金戈相击,一场声势浩大的战势吓得我爷爷脸色苍白。半个时辰之后,一声脆响,口戏结束,人们面前的屏风被收起来,但见台上还是一个人,而这么混乱的声音,无疑都是他那张嘴的杰作。说着月亮大爷的目光盯住禾苗七岁的哥哥:“这小子能用小小柳笛学出这么多声音,倒是有点能耐了。”
月亮大爷的话,似乎点醒了他,他对吹奏之事愈发上心。柳树是春天长得最快的树,没过几天,河边柳枝就粗壮硬朗起来,一场雨后,柳叶全部冒出来,村里房前屋后的柳树也在一夜之间变得茂盛。那段时间,他试着用杨树枝做笛子,吹出同样千奇百怪的声线。但随着树木逐日森郁,再没有一根嫩枝提供给他,他不得不放弃用树枝做笛子的打算,而转身对所有管状物产生了兴趣,看到种在院子里的小葱,他摘下一根葱叶,不久也有了声音,但似乎葱叶吹几下就失去水分,变得软塌塌的,根本无法达到他预想的效果。后来他喜欢爬到树上摘阔大的树叶,杨树叶,柳树叶,榆树叶,柰子树叶,桑叶,每片叶子都要放在唇间试试,臭椿树的叶子终于被吹出了响声,并经过无数次尝试,两片椭圆形的椿树叶在他唇间,发出了比柳笛相似好几倍的鸟鸣,乃至在黄昏时分,招来了许多麻雀和火燕,它们停在禾苗家门前的苹果树上。那时,村庄正缓慢地被黑暗吞噬,禾苗哥哥的脸庞在朦胧的暗色中褪去白日里的黝黑,呈现出一种幽暗的光泽。看不见无数鸟雀从他唇间飞出来,但真的有无数只鸟,啾啾着,扑棱着翅膀,在傍晚的空中横冲直撞。
那几年,所有绿色的带着水分的叶子,都成为他的演奏工具,树叶,庄稼的叶子,甚至河边的草叶。他和叶子之间似乎有某种默契,只要找到彼此,便会合力出声。他的吹奏水平日渐娴熟后,当初的鸟鸣,婴儿的哭声,和大人们的咳嗽声渐渐变成了婉转的音乐,刚开始能断断续续吹奏《东方红》,到后来能将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吹得悠扬动听。
当庄稼成熟,万物褪去了绿色,他又将目光转向了秸秆。禾苗跟我说,她哥哥要制作一支笛子。将秸秆里面的棉棉一点一点用小刀抠出来,是件不容易的事,他的工具从小刀,到小剪刀,后来又从妈妈的针线笸箩里找到了针锥子,但长度依然不够,他不得不去小海家,向在铁厂上班的小海爹借来一把长长的改锥。但即便工具趁手了,技艺还不熟练,大约一个星期以后,他才成功得到一截挖空了内芯的完整秸秆。他将小火柱在火里烧红,然后小心地将火柱头在秸秆的一边烫出两个孔,之后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铁皮,插在秸秆的顶端,放入唇间。那是一种又闷又细又低的声音,他通过用手指按压那两个孔,试图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显然秸秆并非最好的乐器。
城里来的男娃,穿着白色的球鞋,戴着电影里特务们的灰色鸭舌帽出现在我们中间。手里拿着一个扁长的金属物件,他炫耀似的将它横放在唇里。于是我们的耳朵里传来从未听见过的声音,仿佛河流奔腾,又像是众鸟齐鸣。他说,这叫口琴,于是,口琴从他嘴唇快速一抹,音节从高到低,又从低到高,虽然不成曲调,却很是好听。此时的吹奏者跟我们一样,突然看见了暖村之外的世界,有种类更多更繁复的吹奏乐器,即便他的树叶能为我们引来鸟群,甚至在某次吹出的狼嚎声,让村里的狗全体出动,但在这管口琴面前,所有这些都是廉价甚至是低级的。那段时间,他停止了吹奏,任我们央求,任那群男娃子以孤立来威胁他。
瞎婆婆是暖村最会养花的人,她家院子里开满各色各样的花,有一种小黄花的叶子很好看,禾苗悄悄掐了两片,装在兜里,站在学校门口等哥哥。或许是那叶子太稀罕,也或许是哥哥不忍禾苗失望,总之在那个下午放学的时候,他坐在了磨面房的台阶上,吹响了那两片花叶,刚开始只是吱吱的试吹声,后来渐渐高亢,悠扬而细致的声音传得很远。学校新来的毕老师出门担水,竟被他吸引过来,将扁担放在两只水桶上,双手撑着横坐下来。
第二天放学,他被留下,站在毕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的坑洼不平的砖石地上。毕老师把一支磨得油光发亮的笛子送给他,之后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传授他演奏技巧,比如认识简谱,辨别音阶,如何运气。有段时间,他被老师要求照镜子吹奏,据说那是为了学会吸气,以保持气息的精准,直到那支笛子被黑色的胶布缠了两圈,他的《公社社员送粮忙》出现在正月里暖村社火戏台上,跟村里唯一的女大学生的《洪湖水》清唱和年轻矿工的三句半,一起成为那几年暖村春节的保留节目,甚至在六一儿童节代表学校去公社联校表演过。
二年级的我们跟着毕老师学习拳术和剑术,作为一个吹奏者的他,已经是一个高大壮实的五年级学生了,因为笛子,他受到毕老师的青睐。毕老师把自己最擅长的棍术传授给他,不几日他就学会了打、揭、劈、盖、压、扫、穿等技法,挥舞起来勇猛快速,他把那根缠着红缨子的棍子叫作金箍棒,跟他的笛子一样,从不离身,或许它真的能变大变小也不一定。
毕老师要调走了,临走那天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好好吹,将来有机会也许能被剧团要走呢。
春天夜里,在嗞嗞作响的放映机转动的声响中,我们观看了一部叫《红日》的电影,第二天中午,我们就听到了笛子断断续续的吹奏声,那时,小哑巴的妈妈正扛着镢头出门,听到笛子声,竟站在那里随着笛声唱了起来:一座座青山唵紧相连唵,一朵朵白云绕嗷山唵唵间……刚开始,笛声跌跌绊绊的,像水被石头挡住,它不得不绕个弯才能流下去。后来笛声逐渐流畅,与歌声相辅相成,神流气畅。我们一群小女娃急吼吼地从各家跑出来,不知该去看那个唱歌的人,gCKD26Ps2pps8ugkoyIkKQ==还是去听吹笛子的人。
我们悄悄从家里偷出镰刀,在房后的小柳树上砍下一根树枝来,很熟练地做长短、粗细不一的柳笛,扔掉做坏的,只留下声音圆润的。我们想尽办法去吹,却谁也吹不出像他那样任何一种形象而熟悉的声音,麻雀和燕子飞来飞去,猪和鸡低着头寻食,而狗和骡子们对我们不理不睬。风吹在我们的脸上,加重了我们的懊恼。我们围着禾苗,央求她去学艺,但几天后她无比灰心地说,即便哥哥教她,她也根本学不会。我们注视着入村的阁洞,幻想从中能走来几个陌生人,并打听禾苗的哥哥住在哪里。一阵风过,我们擦擦被沙土迷了的眼睛,阁洞里空荡荡的。邻村过庙会起戏,我们跟着大人在戏场看戏,目光紧盯着戏台两侧的文武场,似乎笛子从未出现在那里,倒是唢呐在每场戏的结尾处都会随着铿锵的锣鼓裂石流云。禾苗说,你们看错了,笛子在文场出现过,就是那个吹唢呐的人演奏的,那个人不只吹笛子,吹唢呐,还吹一种像小柜子一样的乐器,月黑风高,小姐在绣楼唉声叹气,那人吹的是比笛子长很多的乐器。后来我们知道,她说的那两种我们不认识的乐器是笙和箫,也就是说,如果禾苗哥哥被剧团要走,他得学会吹奏其他乐器,在我们心里,这对于他来说,也不是难事。
午后,有人推开了禾苗家的家门,进来的是有成大爷,他要给在铁厂上班的儿子娶媳妇,媳妇是城里人,为了烘托气氛,他想让禾苗哥哥到时在喜篷下吹一曲。禾苗爹没有犹豫,一口就应下了。禾苗悄悄跟我说,她哥哥不是很愿意,爹妈又是责骂又是哀求,他才勉强应下。此时他在离暖村八里地的公社上初中,婚礼那天,他把笛子用毛巾擦了又擦,后来他妈从柜子里找出一件他爹的新衣服,他出现在喜篷下的时候,新郎新娘正在举行典礼,挂在树上的电石灯让整个院子亮堂堂的,喜篷下的新娘,被人推攘着,鼻头渗出微微的汗珠。那天,演奏者吹的是《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虽然所有暖村人的耳朵曾参与了这首曲子在笛管由生涩至熟练的全过程,但在今天这个场合它却又明显地不同,仿佛小鸟婉转的鸣叫通过他的嘴唇,经由笛管欢唱,更悠扬,更喜悦,更令人陶醉。人们后来承认,那是他吹得最动人、最暖心的一次。而他似乎也对这次临场发挥很满意,他微笑着接过有成大爷递过来的一块喜糕和糖果时,黑脸在电石灯下呈现出猪肝色,额头跟新娘的鼻尖一样沁出了汗珠。
我们并没有盼来剧团招工的人,即便我们无数次埋怨,也注定是要失望的。几天后,我们眼里出现一个绷带人,一圈一圈,从头一直缠到脚。他躺在简易的担架上被抬回暖村。禾苗后来跟我说,是公社学校勤工俭学,拉电线的时候出的事故,电线从他的脸上划过,削去了半边耳朵和半个下巴。那段时间,我们这群小闺女向禾苗不停打听着关于他的消息,并在学校送锦旗和奖状的热闹中,想象那根看起来细细的电线如何变成一把刀,无情地劈向他,并暗自祈求当绷带去掉,老天还原一个跟以前一模一样的他。
树木逐日茂盛,草叶到处疯长,随着气温升高,田里的庄稼一天比一天高大。夜里,撕心裂肺的号啕盖过一切声响,猫头鹰的,老鼠的,黑渣坡野狼的,哭声让人揪心,让人害怕。很明显,我们失去了那个皮肤黝黑,高大壮实的吹奏者,那些树叶和草叶,再没有任何用处,而暖村春节起社火,吹笛子的节目也彻底消失。这事让村里人唏嘘了很多年。我再也没有去过禾苗家,听说她哥哥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拒绝见任何人,而那支毕老师送给他的笛子,也被他用力扔出门外,摔成两半。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