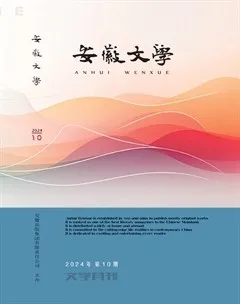玄鹄:叙述与可能
陆地:木叶老师您好,前不久您在端午前后写的长诗《玄鹄》在实验诗平台发布,受到关注。此诗结构营造独特,宏观与微观、历史与当下、真实与混沌兼容,对历史文化和人类文明作了跨越时空的描述和终极探究。您的诗在诗句排列上采用长短句,您怎么看诗歌形式的经营?
木叶:恰恰正是形式,把艺术的各门类,或者艺术某一门类内部的亚类之间,彼此分开,让它们自我确立,比如,这是散文,这是小说,而那才是诗;或者说,这是自由体诗(Blank Verse),这是十四行诗,那是排律,那是词(即所谓的“诗余”),等等。
陆地:能否谈谈您的诗歌宣言《广义叙述学》?
木叶:除了前述形式上的探究外,另一方面,我高度关注诗歌中的叙述问题。一般而言,古典文学学者爱强调的是“诗缘情”“诗言志”,强调其中的“抒情”,认为抒情是诗歌作为文体的特质与核心。应该说,它在包括当代诗在内的诗歌鉴赏上,仍是主流。
陆地:您一直在探索木叶体,当下的任何一个细节及情景与历史的任何一段之间的关系,是很奇妙的结合,广泛而深入,叙述而概括。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用这种形式来写诗的?
木叶:你这里所说的,其实是具体的叙述方式问题。应该说,这种你说的“很奇妙的结合”,只是我的文本当中众多叙述方式的一种,当然也是比较显眼的一种。
这涉及我个人的历史观与运命观,以及其他诸如时空观念、物质观念、宇宙观念等。我很久以来就有着强烈的主观认定:一人其实就是一切人,一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之间本质上互相翻滚着铆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变体”,都是“幻象”,用佛家的话来说,“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具体的、无从更改的命运将一人与另一人、一时代与另一时代划开,让我们误以为人与人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有着某种明确界限。正是这看似明确的界限,既让我们感受此在的踏实,又在更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感受、呼应与体验。
本体何在?诗人的工作应运而生,他要弥合这种认知惯性,因此你看到了所谓的奇妙的结合,也许表现出来的是某种“混搭”。“混搭”的目的是叙述出人类历史当中比比皆是暗通款曲的暧昧与吊诡,打破存在的迷障。或者说,叙述出某种“本质”,解构并重新结构它的常与变。写作是一门技术活,如果流于刻意,为奇妙而奇妙,文本当中必然新茧旧痂、裂痕累累,充斥无法抹去的虚假感与破碎感。
有意识地“广义叙述”,也即你说的“木叶体”实践应该有些年头了。
陆地:能不能说一下您不同时期诗歌的特点?也就是您在不同时期诗歌探索的历程,直到现在这个形式。对现在这样的表达您觉得满意吗?您想进一步探索的是什么?
木叶:对于所谓的“木叶体”,我个人肯定是不够满意的,主要问题,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叙述者问题”外,如何在一首诗的内部,既宏观又微观地,整体调谐出“一二一”的微妙节奏与韵律——微妙节奏与韵律既体现在具体诗句当中,又体现在上下诗行与诗节当中,更体现在整首诗上——尚在探索中。
陆地:《玄鹄》这首长诗把您平时在短诗中的积累得以井喷式地表现。您试图通过一个故事性的网状结构讲述历史及文化的变迁,构思很奇妙。您是怎么想到用这样的形式写一首长诗,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写出,带着一种屈原似的悲愤,冷眼看历史,对历史的戏谑?
木叶:长诗《玄鹄》很偶然,真正写作不过三天多一点的时间。它的创作契机,和正在发掘的安徽省淮南市疑似战国时期的楚烈王墓有关。诗中,Professor Wang、小王、考烈王,我作了某种三位一体式的散点叙述,由此纠集出所谓的《混沌史》这一若有若无的历史文本的探寻。 “混沌”本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概念,用于描绘对于智慧的独特的理解。
在我的拟想中,《玄鹄》是一个开放性的1710a99d788008e2632fa69f100f6859文本,而不是简单的对于王陵发掘过程、对于东方智慧(混沌)的寻找过程的添附。我期待读者会喜欢这首长诗。
陆地:您觉得诗歌最重要的是什么?不同诗人对诗歌语言和内容的探索都有不同的侧重点,而您的侧重点是什么?
木叶:诗最重要的是诗本身,它当然由语言和内容有机合成,即语言是诗性的语言,内容是诗性的内容。
就对于诗的语言和内容的执拗与探索而言,我的关注点始终在于它们的诗性,也即诗中语言能否葆有诗性,诗所承载的内容,无论它在可注释的现实当中怎样活泼泼地存在,一旦落实到诗当中,那么就要苛求它在诗的意义上的成立。否则,那就是记叙文,是说明文,哪怕它外观上仍然有一个“诗”的形式。请注意,记叙文、说明文这些文体,都是实用文体,而诗,恰恰是非实用的,属于形而上。
此外,诗是浑然的整体,侧重语言和侧重内容,都属偏颇。很难想象,一首形神俱足的诗,语言是诗性的,整体上看内容却有这里那里的瑕疵甚至明显的匮乏。反之亦然。
当然,我们也得承认“时代局限性”,虽然那往往不过意味着后世的审视。包括此刻的我们,也不会例外。
陆地:您觉得写诗寂寞吗?一些探索性的诗可能属于小众,您觉得遗憾吗?您怎么看广受欢迎的诗和少数人喜欢的诗?
木叶:情到深处人孤独,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人,做任何事。至于小众、大众,那是相对而言。
我能明白你所提出的“广受欢迎的诗”与“少数人喜欢的诗”的界限所在,乃是在提醒我作为一个诗歌的探索者,要有甘于“少数人喜欢”的决心与勇气。
陆地:确实,大众和小众是个模糊的概念。因为没有一种量化。我们习惯于用“大约”。不管怎样大众和小众都是他者,创作者和他者虽然可以有视角上的交互,即胡塞尔的主体间性,主体既是以主体间的方式存在,其本质又是个体性的,表现为个体与个体间的凝视。无论是大众还是小众,作为独立个体允许他们存在,创作者可以不关心,自我沉溺,当然需要足够强大。
诗人们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路,您比较喜欢国外哪些诗人的诗呢?特别喜欢的一两个诗人是谁?他们给您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木叶:如果刻意强调国外诗人的话,喜欢的诗人也多、也不多,可以点出名字的,例如里尔克、特朗斯特罗姆等。当然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延长,看我在何种意义上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给我的最重要的启示,是世界上只有一种诗(这样说肯定不准确,但我想不到更好的表达),优秀的诗人应答的姿势各个不同。
诗人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通往诗之路。这条路,我至少知道荷尔德林走过,那是一条热烈的浪漫主义之路。今日再来走的话,诗人们会发现,这条路已经辛辣很多,充满了电气、AI、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种种优雅的刻板。
陆地:诗歌在您的生命中居于怎样的位置,生命存在的方式?是作为一种爱好,还是像爱一个心爱的人那样爱它?
木叶:智力和情感力的操练及其产品吧。对于我来说,它的位置没有“生命存在的方式”那么重要,但也不能简单说它只是一种“爱好”。
陆地:您怎样看诗的节奏?您的诗时而长8c27c5ed0282ccac8a9cdfa7915c6cb099844de3c3c2ea875ec2c26469b6a1f2句时而短句,似乎有点散文化倾向。您觉得诗与散文在形式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木叶:散文是和韵文相对而言;诗天然地属于韵文。因此,诗必然要有节奏。问题可能在于,怎么去理解现代诗的节奏,并把它在现有的语言上运用得恰到好处。
我的诗中,确实可以看到大量的、长短句相间的有意调度,我个人的目的,是想制造出一种可能与别人不太一样的,同时又真正是诗的节奏。当然我得承认,这种节奏的调制实验,还远远没有完成。
陆地:诗渐渐达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走得深远,也是诗人思想体系不断建构的过程。这过程其实是混沌的,无意识的,有时甚至是昏昏沉沉地走出来的。很难用努力这个词来形容。当然有些方面也可以有意而为之,比如读书,行走,冥想等,在具体的生活中停顿回头以及忽有所悟?
木叶:任何的刻意都提升不了自我。对于写作者而言,提升自我肯定包含但远不限于“读书、行走、冥想在具体的生活中停顿回头以及忽有所悟”。我想起了苏联有“七部半作品”称誉的电影导演塔可夫斯基,他的一部电影,好像叫《安德烈·卢布烈夫》吧,曾给我巨大的黑白震撼,和无穷的启示。
诗是“糟蹋”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语言和思想同样如此。
陆地:您读古诗吗?有人觉得现代诗的表达方式与古诗完全不同,所以不需要再读。您觉得呢?
木叶:当然会读。如果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那么蕴含在古诗当中的,必然是我们的旧家,形变而质不变;一个写作者,如果不去做存在的溯源,又何以看清微茫的此在,及至不可知的将来?
单就语言本身来说,不读古诗,不精通我们的母语,又何以将自己的母语整体都作为书写工具,在写作当中充分调用?
现代诗因其“现代汉语转向”,已经在节奏、韵律等诗歌构成元素上,制造了种种障碍,引起一般读者的种种不适,有鉴于此,我觉得写作者更应当到古诗所提供的汉语母语当中去寻找调整的某种可能。
陆地:您怎样看诗人的禀赋?您觉得诗人的一生中必须有一首长诗还是让一生中所有的诗成为一首长诗?
木叶:好像有一种说法,诗人们终其一生,其实写的不过是不断增补、不断添附同时又不断恢宏的一首诗。比如,惠特曼终其一生,都在不断扩充他的《草叶集》(《草叶集》完全可以作为一首诗来看待)。我想这句话里面,大有讲究,对于天赋异禀的诗人来说,这首诗是无穷回旋往复中的一首诗,其中有可能会包括长诗;对于庸常的诗人,或者深陷在程式当中的诗人,他这一生可能真只写了一首形式上的诗,比如清代的乾隆。
至于“让一生中所有的诗成为一首长诗”,是指这“所有的诗”最终会合成为“一首长诗”,还是“这一生中所有的诗”到最后,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写作者创作的每一首其实都是长诗?
这种浪漫,当然值得期待。但是无论如何,诗人断不可刻意地去写作据说是他这一生中必须有的“一首长诗”。
陆地:呵呵,那就让一生成为一首长诗吧。
2024年6月27日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