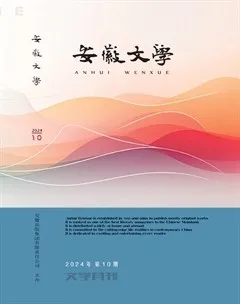放生
1
肖伯琴路过张玲红的鱼摊时,故意把身子一挺,头向上扬了一个角度,高跟鞋踢踏得震天响。张玲红搜寻肖伯琴的目光,想来个硬碰硬的撞击,却没有遇着。肖伯琴并没有迎接张玲红的目光,她将目光投放到了别处。张玲红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对着肖伯琴的后背高声地骂道:“跩得跟在国宾馆钓鱼台工作似的,只不过是给人家做饭,说到底就是帮佣,以为自己高人一等,打扮得乔模乔样,这样装扮给谁看,勾引谁?有本事被人包养在家里,不抛头露面上菜市场买菜才叫本事!”肖伯琴的肩膀稍微晃动了一下,像是要站下来应战似的。张玲红刚想把昨天一夜在床上串联好的骂词演绎一下,肖伯琴却又若无其事地朝另一家鱼摊走去。
几个买菜的邻居听见张玲红叫骂,都停下来,盯着肖伯琴的背影朝张玲红挤眉弄眼。魏水生沉下脸连忙叫张玲红搭把手,把四轮车上的鱼按品种、大小倒进各个盆子里,“什么事都有个了结,还抱着嚷嚷不休,赶快做生意。”众人见魏水生有杵他们的意思在里面,也就买鱼的买鱼,买菜的买菜,兀自散去。
张玲红是发了心想和肖伯琴骂上一仗的,这个女人昨天和她婆婆居然骂到她门上去了,她和魏水生去运河里收网,傍晚河上起了一点风,回来迟了一点,尽管回家听到婆婆讲,这对婆媳并没有占到一点上风,她婆婆一路用骂声把她们婆媳护送回家,左邻右舍也帮腔说这对婆媳毫无道理,居然到人家门上兴师问罪。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事,这个地方有种说法,除非是“红人”,即坐小月子的,故意登别人的门,找别人家晦气,或者男人带别的女人回家,被家里的女人发现,才可以到对方门上吵骂。两个孩子在学校坐一条板凳,肖伯琴的女儿穆小小在班上经常取笑张玲红的女儿身上有鱼腥味,在课堂上捏着鼻子要求老师给她调换位置。张玲红的女儿魏苗苗下课给了穆小小一巴掌,穆小小找老师告状,老师批评穆小小太娇气,同学之间应该互敬互爱。穆小小回家一哭诉,肖伯琴立刻拉着婆婆骂上门去,兴师问罪,小小不能白挨了一巴掌,谁知竟被狠狠地骂了回来。肖伯琴低估了老太婆的战斗力,她没有考虑后果,她和她婆婆两个人被张玲红婆婆骂得张不开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包括婆婆年轻时的荒唐事,都被张玲红的婆婆像把箱底里的衣服拿到大太阳下,晒伏一样暴晒在众人面前,肖伯琴婆婆的眼睛里全是羞愧。
肖伯琴和张玲红以前在一个厂上班,在一个车间,又在一个巷子住着,既是同事,也是街坊。巷子北边居民大都在城镇企业单位工作,肖伯琴的老公穆强林顶替了他爸爸的工作,在煤炭库工作。张玲红住在巷子南面,叫太平庄,原先大都是渔民。魏水生没有工作,继承父亲衣钵,打鱼为生。现在提倡河里围养,野生的杂鱼逐渐珍稀了,魏水生在巷口的菜场租个摊位卖鱼。每年的禁捕季节,他就卖围养的鱼,开捕的季节,魏水生就和渔民一起去河里捕鱼。魏水生网撒得好,地方和省里的电视台,来拍地方志之类的节目,都是叫来魏水生表演。魏水生每一次的撒网镜头,都赢得满堂喝彩,他倒不是在乎那三百块钱,网被他抡起的时候,就好像憋在胸腔里的力量得到释放,整张网天女散花似的,浑圆地落在水面上。张玲红下班也帮着老公看看摊位,一年到头没有好衣服穿。后来厂里体制改革,张玲红干脆停薪留职,和魏水生一起打理鱼摊,前一天就去河里把网收好,养殖在河里的水箱里,第二天一大早四五点开着电动四轮车去河里取鱼,拿到市场上卖,帮着买家剔除鱼鳞。夏天还好,冬天顶风冒雪,不是一般人能够吃得了的苦。人虽然辛苦,但是花花绿绿的钞票让张玲红感到踏实安稳。没一年,肖伯琴也下岗了,单位照例发了一点钱打发工人回家。
刚刚下岗那阵,有次逛街,在一家服装店里,张玲红和肖伯琴两人正好碰着,张玲红左挑右选只舍得买一件裙子,肖伯琴一下子就入手三件。服装店老板娘对肖伯琴的热情立刻就高涨起来,围着她打转,把张玲红晾在一边。后来,张玲红经常在阳台上听到肖伯琴和穆强林的对骂声,肖伯琴渐渐在吃上有点缩手缩脚,买菜总是抠抠搜搜的,一般都是拣小的刚刚死了的鱼虾买,说自己喜欢吃小鱼小虾。张玲红一般不串门,实在是替肖伯琴着急,就去肖伯琴家给她指道,说可以在菜场附近摆个面摊,早上卖菜的、买菜的、取鱼贩肉的,来不及吃早饭,也不高兴做,开个面店生意肯定好。肖伯琴把嘴一撇,我才不要做这些事情,整天风吹日晒,热锅上跑来跑去,皮肤吹都吹老了。我这个样子给人家站个服装店,或者站个超市,总比站在锅门口没有一点清爽气强,说着用眼睛的余光瞄了一下张玲红。张玲红这才注意到自己穿着半腿高的胶鞋,底部厚厚的一层黄泥,套在膀子上的塑胶护袖沾满了鱼鳞,就像脱了釉彩的塑料珍珠,发出惨淡的光影。肖伯琴并没有让张玲红家里面坐坐的意思,就这样把她堵在房门口说话。要开,我就开大饭店,做老板娘。肖伯琴对着转身离开的张玲红递上了这么一句话。
张玲红很后悔这次的登门,发誓以后再也不登肖伯琴的门。牛拴在树桩上,不耕田也还是老,人怎么可能永远年轻花哨,自己为自己的懒找借口罢了。
本来昨晚上张玲红就想气冲冲地骂上门去,给魏水生拦住了:“家边邻居的,小孩不懂事,大人还不懂事?过两天,两个孩子好了,你们以后见面还说不说话?”
“那她为什么这样做,还婆媳两个人吵上门,还要你妈带话,让我教育苗苗。我看她教育教育自己女儿才是正经,这么小小年纪,手上脚上全涂了指甲油。上次听苗苗说,穆小小上课玩手机,罚站,老师让她把家长叫来,穆强林居然去学校恐吓老师!”
“你不要听孩子乱说,他穆强林再怎么不知好歹,敢去和老师吵?现在巴结老师还巴结不过来。虽说他有点不着边际,还不至于这么不知天高地厚!”
“我说话你总不信,难道你也看上他那个婆娘?我是没人家会打扮,我脱了这身衣服,三月不出门,一天一张面膜,再涂脂抹粉,比比看,到底是你老婆好看还是人家老婆好看?”
“说说就不上槽道了!”魏水生笑了起来,“快去把锅里的鱼盛上来,我要喝一杯。明天卖过早市,还要去河里撒网,居委会来通知,说省电视台要来拍我们这段运河宣传纪录片,明天好多大人物来,不要拖后腿。”
2
肖伯琴没有敢接茬,她是领教了张玲红婆婆的厉害了,渔船上的人,狗脸上栽毛,说翻脸就翻脸。亏你张玲红以前还和我在一个厂子,一大早在菜市场指桑骂槐。肖伯琴有点心虚,她知道如果停下脚步,和张玲红恋战,她是骂不过她的,她得赶紧把菜买齐去主家那里。女主人昨晚上就把拟好的菜单交给她,说今天要在家里请客。尽管主家一再叮嘱,只要新鲜,价格贵一点没有什么,但一想到每次回去报菜价,女主人来来回回地询问,她就担不到底,生怕自己没有算计好,说漏了嘴。这个主家开的工资还可以,比普通人家的都高,她和另一个专门带小孩的外地女子一桌吃饭,据说这个女子持有育婴师资格证书,专门培训过的,工资是她的两倍,什么事都不做,包括小孩的衣服,都是肖伯琴洗,那个女人就只带一个孩子。
如果说一点不揩油,也不见得,肖伯琴家里的那份菜金全部打包在里面。虽不至于主家吃什么,她家就可以吃什么,至少比以前丰盛了许多,所以早上这一段时间一点也不得歇。事先把留出来的菜送回家,让婆婆帮着择菜、洗菜,她在主家吃过午饭还要急匆匆地往回赶,她一顿不烧,小小一顿不吃,丫头嘴巴刁钻,不吃奶奶做的饭,不吃葱姜,不吃隔夜饭。穆强林下岗后,零散地打打零工,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睡觉看手机,人好像和床板粘起来了一样。中午等肖伯琴回来做饭,吃过饭,就去棋牌室打小麻将。夫妻吵得狠了,婆婆出来说,她和老头可以把儿子养去,养到老。主要的倒是你要养活你自己和女儿,“三世修得皇城边住”,若不是我儿子,你能到城里享福?
也是同一个厂出来的工友,以前是他们车间的“四朵金花”之一,现在在家做阔太,她老公开了家灯具厂,做城市亮化工程,赚了钱。当然,现在“四朵金花”之一的张玲红被排除在外了,邋里邋遢得不成样子。这个阔太念及旧情,给肖伯琴介绍了这个活儿,这个工友的老公和这个主家有来往。主家的女儿在澳大利亚生下孩子,取得外国国籍后,又把孩子扔回国内让父母照看。“这个人家,不要说两个保姆,十个保姆都请得起!”阔太对肖伯琴说,“正常只有女主人和孩子在家,男主人自家企业有食堂,一般不怎么在家吃,说白了,就是做饭给你们自己吃。人家主要是想找个年轻一点的,手脚麻利的,据说这样对婴幼儿成长有好处,小孩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
肖伯琴几天做下来,并不只是他们主佣几个人吃饭,女主人的弟兄姐妹、七姑八姨喜欢来这里,陪女主人说话逗乐,每天一大桌,都围着小孩转。同人不同命!她很羡慕嫉妒和她一个桌上吃饭不做事的保姆小吴,小孩哪个不会带,小小不是就这么被自己带大了?那个资格证书也就糊弄有钱的人家罢了。
肖伯琴把菜一一摆放在厨房里,等女主人过目,她在厨房里换了衣服,省得衣服上沾染了油烟味。一开始她是在专门看护孩子的保姆小吴房里换衣服,后来小吴说,油烟味对孩子的嗅觉发育不好,就改在厨房里换了。她本来洗菜做饭也带来了一副塑胶手套,女主人有一次说菜里有塑胶的味道,肖伯琴就不敢再戴了。
中午,肖伯琴把前一天放在冰箱里的剩菜热了热,吃了饭。小吴嘴噘得老高,她用开水泡了饭,撕开一袋榨菜。肖伯琴单独为女主人炒了一个菜,烧了一碗素汤。中午难得清净,老板娘关照她的亲戚,老谢今天要请重要的客人,不希望家里有很多人。
3
魏水生把船开进了河里,这是条木制的舢板船,只不过船改装过了,船尾装置了电瓶,可以不用划桨。太阳像鸭蛋黄,从黄色渐变成橘色、红色,悬在河面上,紫霞满天。也许是为了渲染“晚上回来鱼满舱”的意境,本来说好的摄制时间由晌午改在了午后。张玲红扮成了渔婆的样子,其实也就是在头上包了块花头巾,在腰间扎了个花围裙,都是她婆婆年轻时用过的老物件,压在箱底好多年,这次特地翻了出来。张玲红坐在船头,魏水生有了水的沾染,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张玲红当初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他,嫁给没有工作,打鱼为生的魏水生,也就是看上了他手里的那张网。
张玲红看着魏水生对着水面发呆,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穿着保安制服的管理人员一再清场,虽是开捕季节,今天相关部门明令禁止渔民捕鱼,魏水生的渔船孤零零地飘在河面上。张玲红把头巾摘下来又扎上,一遍又一遍地抹头上的汗水。这个三百元钱不要了!张玲红从船头站起身,船身跟着晃动了一下,魏水生坐在船尾一动不动,张玲红只得又坐下来。
终于,河面上起了很大的波澜,游艇在水面犁出滚滚浪花,鸣锣开道似的呼啸而来。魏水生急速把船驶离浪花击打的范围以外,游艇在河中央打了个转,停了下来。
居委会主任用喇叭站在岸上喊话,示意魏水生去湖中央,靠近游艇。魏水生没有搭腔,自顾自把船开到既定位置,这个位置无论是取景还是打鱼,都是绝佳的地带。张玲红很欣赏魏水生这一点牛脾气,在这处河面上,就是他说了算。
游艇后面拴着的小船被解了下来,从游艇下来三四个人,小心翼翼地爬下悬梯,手把手把拍摄器材传递到船舱里,小船慢慢地靠近魏水生的船。
网在魏水生的手里就好像有了生命,整张网鼓得像一张帆,风灌满了每个角落,饱满圆润,像蒙古包似的盛开的云铺在了河面,慢慢地落进湖里。
“淮昂!”小船上的一个人兴奋地叫了起来,犹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个声音盖过了张玲红头顶像蜜蜂“嗡嗡”作响的飞行器。魏水生不抬头,听声音就知道此人是谁,他是谢长利,现经营着全市最大的强力混凝土搅拌厂,当地有名的富豪。显然,这声音也感染了魏水生,当浑圆的网被魏水生拖曳起来的时候,魏水生的脸和湖水在余晖的照耀下熠熠发光。
每次录制这类节目,除了三百元的劳务费,这网鱼也归魏水生所有,算是额外收益。谢长利兴奋地对魏水生说,这网鱼他全兜底,让魏水生出个价钱。
魏水生伸手从网里抄出一条白银银的鱼扔进船舱,掬起的水花像水银倾注而下。张玲红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一条昂嗤鱼,但是这条鱼又不同于普通的昂嗤鱼。内河的昂嗤鱼黄灿灿的,身量也小,再怎么长,也不会超过半斤重。而这条鱼通体莹白,足有五斤多重,鳃下的两根胡须有尺把长,大嘴一张一合喘着粗气,颌下支棱着的两根鱼翅让人想起垓下的项羽。
谢长利笑了起来,“我所以包你这一网鱼,说老实话,单单看中的也就是这么一条鱼!也是为你着想,省得你一条条地零卖。”谢长利不紧不慢地说,“你把内核抽掉了,这网鱼还有什么价值呢?”
魏水生心里舍不得卖这条鱼,这种鱼十年不遇,是淮河里的特有水产,是从淮河游过长江,又从长江游入大运河,从大运河流入内河,再辗转汇入这里的樊良湖。小孩生痱子、害疖子,产妇没奶的,老公阳痿不举的,喝上一碗奶白如雪的“淮昂”鱼汤,立马见效。而且这鱼不腥不柴,肉味鲜美细腻,味水(方言,指味道)是下河里的鱼无法比拟的。谢长利能够识得此鱼,也算是没忘本!魏水生想了想,卖给不识此鱼的,胡乱攀扯,讨价还价,生一肚子气,或者吃进自己的狗肚里,暴殄天物,都是不得其所。当下谈妥价格,停船靠岸,魏水生和张玲红把鱼用袋子装好,放进了谢长利车的后备箱。
4
司机把鱼送回来的时候,和老板娘说老板还要陪客人去其他几个地方,特意关照,把鱼用袋子分成份,是要给客人带走的。又把那条“淮昂”单独挑出,用水养好,这条鱼老板自己留着别用,不能轻慢了它。老板娘说知道了,让肖伯琴把鱼处理好,自己急着要出门,她要去美容院做个护理,再请人替她化个妆。老板娘新换了一身裙装,尽管面料考究、式样新颖独特,穿在老板娘身上犹如拉直了两袖挂在竹竿上寡淡。肖伯琴听到自己心底的一声叹息,这衣服若是穿在自己的身上,该是怎样的摇曳生姿,凹凸有致。
肖伯琴把鱼分好,想了想,把那条怪鱼倒进了浴缸,这只浴缸已经废弃了原始的使用功能。老板娘经常吩咐肖伯琴把人送的,或者司机带回的,诸如鱼虾、螃蟹、甲鱼之类放进浴缸里养。所以,肖伯琴自然而然地把浴缸放满了水,让这条鱼在这只大浴缸里伸展得欢畅些。
肖伯琴卡着时间,把菜一一端上会客厅的餐桌。生熟渐变的工序在时下炙手可热的美食频道,是一道道“食如性也”的诱人风景,而在现实生活的操作中,热气的蒸腾,炸、炒、炖、煮,对肖伯琴来说,无不是种戕害和煎熬。肖伯琴每隔一天都要在脸上手上涂满鸡蛋清,面膜舍不得买,就用这土方法,但双手还是像被砧板上的厨刀斩过一样,皲裂如鱼鳞般。饶是这样,每次穆强林在嘴上还要颠倒个三四回,说她浪费,尽管第二天早上他比女儿小小多吃个蛋黄。
肖伯琴解下围裙,把煤气灶上的火开成小火,锅里炖的是牛尾汤,这是今天家宴的最后一道菜,炒菜要等客人齐了,现炒现吃。谢长利一行还没回家,趁这个空当她可以稍微喘一口气。她的屁股还没来得及挨着凳子,小吴在浴室里“坏了、坏了”地尖声叫了起来。肖伯琴循声过去,看见那条怪鱼已经鱼肚泛白地仰躺在浴缸里,两条胡须了无牵挂地荡漾在水面上。
“这也值得大惊小怪的?”肖伯琴故作镇静,嗔怪地看了小吴一眼,“吓着孩子可不行。老板娘刚刚走,你就作怪!”
“这条鱼已经死了!”小吴嚷道,“再不杀了炖汤,鱼就不新鲜了。”
“已经有牛尾汤了!”肖伯琴连忙说,她有点怕这条鱼,鱼眼瞪得浑圆,像是要从眼眶里跳脱出来,鱼嘴大开,露出参差的狰狞的细齿,有点死不瞑目的凶恶。要命的是,她不知道这是条什么鱼,鲇鱼不像鲇鱼,黑鱼不像黑鱼,浑身无鳞,不知道从哪下手。她对无鳞鱼有一点莫名的敬畏,他们家从来不吃没有鱼鳞的鱼,每年正月十五,她婆婆都会买无鳞鱼回来放生。
“难得遇着这条好货,再迟,烧汤就少了味水了。那个时候,老板怪罪下来,你就不好交差了!”小吴看见肖伯琴愣愣地站着,扶了扶她的肩膀,贴近她的耳朵,“不知道怎么剖吧,和平常杀鱼一样,从肚子里剖下去,我的姐姐。”
肖伯琴后来想,小吴估计给她放了猖,下了迷魂药。平时,她不听她的调遣,甚至两个人还明里暗里地较劲。说到底,小吴本和她是一样的人,都是保姆,凭什么在工资上压她一头。她是比肖伯琴年轻,那又怎样,如果自己把手放在裤兜或者戴进手套里,单从脸和身材上看,小吴占不了多大优势。但是这一次,肖伯琴鬼使神差地把刀在磨刀石上蹭了几下,一刀剖下去,鱼居然直挺挺地跳了起来,血水喷了肖伯琴一脸。
“鱼原来也会装死呀!”小吴笑着拍手跳离了肖伯琴。
5
谢长利把省电视台一行人带回家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红酒卧在醒酒器里,像一块瓷实的琥珀。他的这个小厨房在圈里小有名气,这里没有大饭店、小食堂的菜、肉、鱼和人体等各种味道的互相倾轧、浸淫,这里做菜清淡、家常、干净,环境私密,如看惯了灯红酒绿,却在净手的转角处觅得一座碧玉小家。更兼得厨娘风姿绰约,还有一个活泼俏皮的小月嫂,这使得谢长利在他的这个饭圈子里有点面皮。
酒过三巡,肖伯琴把牛尾汤端上桌,谢长利满意地用眼睛的余光睃了肖伯琴一眼,拍了拍肖伯琴的肩。众人笑着当着老板娘的面打趣谢长利和肖伯琴,让老板娘看紧些。老板娘半真半假地笑着说,哪个猫不偷腥,我正好趁便休息。转脸正经吩咐肖伯琴为每个客人舀汤分羹。喝到一半,小吴却又端着另一个砂锅进来。谢长利以为是海鲜粥之类,打开锅盖一看,脸色大变,立身低喝小吴把砂锅端走。小吴的笑脸顿时冻住了,腰肢只扭了半扭便也僵直了。
肖伯琴从来没有见过谢长利这么声色俱厉,即使当着老板娘的面,对她和小吴也是和颜悦色。尤其是从小吴的怀里抱过孩子的时候,谢长利的手有意无意掠过小吴的胸部,小吴看肖伯琴目光里就盛满了恃宠而骄。 肖伯琴虽然有点幸灾乐祸谢长利对小吴的呵斥,但立刻回念谢长利动怒与这条“怪鱼”有关,不由得也冒出一身汗,连忙上前从小吴面前端起那锅鱼,朝厨房走去。
众人也都识相,谢长利虽面子上还挂着笑容,但有点生硬,就像搪瓷脸盆破了,被一块锡补过一样。晚宴草草收场,好在人手一袋的鱼,多少也补救了客人没有尽欢的缺憾。客走主安,谢长利终于把他的脸全部阴沉下来,“这汤到底怎么回事?我一再叮嘱好生养着,怎么就端上了桌,谁杀了它?”
小吴噘着嘴,指着肖伯琴说,“还能有谁?”
“这鱼已经死了呀!”肖伯琴嗫嚅道,“我看它浮在浴缸里了。小吴说不炖了,恐怕不新鲜了!”肖伯琴意识到不能自己一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急忙拉上了小吴垫背。
“这鱼不会死!”谢长利几乎是吼了起来,他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条死鱼,浮在水面上漂荡,四处白茫茫一片水天。他想起他的童年,他的童年是光着屁股的,孤寂的。坐在船舱里,看见岸上的人家炊烟升起,半大丫头小子来码头淘米洗菜,他只有用破了的毛巾围着裤裆,悄悄地钻出船舱。岸上的小孩见他站在船头,立刻像受惊鱼儿一样很快就游走了。他曾暗暗发誓,他将来要到岸上去,去住大房子,而不是像叠咸鱼似的和兄弟几人腚靠着腚挤在一张床铺上。现在,他住上了大房子,不仅国内有,国外也有。他母亲曾对他说,是“淮昂”救了他的命,让他才有了奶喝。所以,不论在哪里,只要看到“淮昂”,一定要了放生,不准吃进肚子里。
他这次见着这条“淮昂”,也是预备着放生,不过这次放生,他是要搞个大大的仪式,为他进军房地产造势。他总觉得他现在这个行业让他走不到人们的面前去,就如锦衣夜行般藏着掖着。每年装混凝土的卡车都要给他出点事故,这让他觉得如鲠在喉。他今天意外地碰到了“淮昂”,他觉得这是天意,是他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如今,这条相当于祭祀用的鱼,却被面前的这个女人活杀了。
“你去太平庄找那个魏水生,或者找那个穆强林,再给我拉条这样的鱼来,否则你明天就不要再来了!”谢长利沉下脸,对肖伯琴呵斥道。
6
肖伯琴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午夜的街灯像死鱼的眼睛,巷子里一片漆黑,她恍惚地摸进家门,小小和婆婆已经入睡,手机幽蓝微弱的光照着穆强林咧开的大嘴,他正开心地刷着手机。肖伯琴又悄声出了门,站在张玲红后门口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张玲红家里的灯已经熄灭,她伸出的手指刚要触碰到门板,又触电般地缩回了手。她最终还是没有叩开张玲红的门,她朝着河堤走去,好像那里才是她的归宿。
肖伯琴在河堤的一段石工防护堤上坐下来,这段陡峭石工护堤她再熟悉不过,以前,她的父亲每次到城里来,都会带她来到护堤上。父亲指着这一段护堤自豪地对她说,这段堤是他身强力壮时带领村里的男劳力修筑的。每年冬天农闲,政府都会组织民工修筑护堤,这一大段就是当年他带队修筑的。每次上城来,她父亲也会带着肖伯琴去穆强林家走走,带些活鸡活鸭,瓜果蔬菜。父亲对她说,那时候他们这些上工的精壮劳力都歇脚在穆强林家,穆强林一家也就不做饭,跟着民工一起吃。穆强林家这一带原来是城里的西菜园,后来土地被征用,穆强林求他母亲去居委会胡搅蛮缠,多要了一个招工名额,就这样,肖伯琴和穆强林结了婚。
时光只是在婚后最初的几年给了她想要的高光。在工厂,她眼疾手快,做事麻利,说话爽快,可谓“嘴一张,手一双”,是她们那个车间的四朵金花之首,如果,如果没有后来的改制,她会接替他们的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快退休了。哎,肖伯琴叹了一口气,搓了搓双手,凝视着与面颊身体肌肤不匹配的、青筋凸起的被衣袖藏着掖着的双手,慢慢地起身想站起来,不去就不去吧,活人嘴里长青草不成。明天,先去买个手推车,在车上支个煎饼锅,可以卖早市和晚市。
突然,河面上有束光亮了起来,突突地有机器开动的声音,船直接开到了肖伯琴所在的护堤下面,穆强林站在船头焦急地向她挥手,示意她去岸边的码头,魏水生稳当当地坐在船尾,网却是在另一个人的手上,那人是谢长利。
肖伯琴的身后伸过来一只手,骨节粗大却是舒舒展展的,大大方方的。肖伯琴转身也把自己的手伸出去,接住了递过来的手。
“你这么晚不回家,你家小穆着急,和你婆婆寻到了谢长利家。听我家水生说,谢长利吃过你婆婆的奶,是他妈妈用‘淮昂’换的。从前,他家的船经常停靠在这个码头,他们三人孩提时就认识。谢长利披着衣服和我们一路寻来,叩开了我家的门。他求我家魏水生带他到河里,他想自己再撒一次网,不管取到取不到‘淮昂’,就权当是放生了。他让魏水生介绍他加入渔民互保协会,他想当回渔民。”
船上的网鼓了起来。
责任编辑 张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