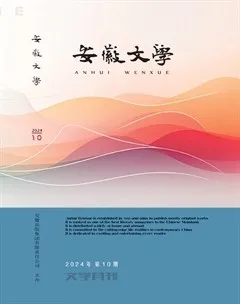为虎作伥
一
老宅已不复存在。深草掩盖了拆除的蛮横,半塌的土墙摇摇欲坠,只有柚子树全然不理会周围的寂寥,落了一地黄色的台湾柚。曾祖母在世时,每谈起这座老屋,都带着尖酸的挖苦,仿佛这是她苦难的见证。但在死前,她却一直念叨着老宅后院的柚子树。我望着车窗外被荒藤落叶覆盖的废园,不知道她见了会有何感想。
上山的车络绎不绝,人们都盼望着讨个好彩头。好不容易找到一处空闲的车位,大殿里已人满为患。往日诵经的早课取消,僧人们记录着香和莲花灯的数目。四处萦绕着白烟,氤氲在人之间的是鼎沸的声响。照例是一盏莲花灯,三根香。先前由我的压岁钱交付,待我毕业之后,便由我这个小辈出面购买,以求家庭和顺。
母亲已经将花茶泡好了。父亲一手端托,一手掂盖,轻轻地拂了拂,盖与碗发出清脆的声响,抿一口,放下。我照做。表妹刚睡醒,口渴,端起碗一饮而尽。叔父瞪了她一眼,又转头夸赞我。父亲摇了摇头:“这孩子前几年也是这样。现在总算省事了。”他们又谈起昨日的团年,搜肠刮肚回想一嘴带过的人名。父亲追忆岁月时,我便去帮母亲烧水。寺里只有小壶,一桌人喝一轮便需要重烧。铁壶发出轻微的爆裂声,煤气的火光,像一朵卷曲的蓝菊花。母亲搭了一块毛巾在端把,坐在小木凳上看视频。我让妈进屋坐,她倒说我没有陪好长辈。铁壶吐出最后一口白气,剧烈的噗噗声消失后只听见隔壁房中的寒暄。母亲怨我连续三年考公失利,在学校教书也没有拿到编制,我自然知道这是她的心里话。大概是等得太久,母亲的手都冻僵了,一哆嗦,剩下的小半壶开水便浇到了母亲的鞋面和裤脚上。洇染出的水迹,看上去像老人尿了裤子。所幸冬天穿得厚实,水仅浸湿了加绒外裤。
“大过年的,”母亲骂道,“真是晦气。”
我让母亲到车上换条裤子,她说,风一吹便干了。父亲在屋内询问水烧好了没,母亲高声应道烧好了。我拦住母亲,叫她赶紧的,先去换裤子。母亲愣了片刻,说:“你和你的父亲倒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她的话像一颗生硬的石子,打在我的心口。
将铁壶里的水掺入温水瓶中,拎进屋,不知道他们还要聊多久,便又回到斋厨里重新烧了一壶。剩菜盛在塑料盒里,敞放在木桌上。昨夜是满桌的红火。东坡肘子、红烧鱼、辣子鸡……一盘盘肉菜上桌,服务员如同街头杂技人,脚不沾地,穿梭在圆桌之间。椅子还没有坐热,便被父亲拎起来到邻桌敬酒,敬了一轮,刚吃两夹菜,又有亲戚领着小孩来敬酒。敬来敬去,推杯换盏,接二连三的咣当声响起,像是厨房里母亲操弄锅碗瓢盆的声音。
他们谈论不景气的股市,自家的孽子,别家的好,似乎这便是最佳的下酒菜。嘴巴说干,暂时歇气时,便聊起了去世的曾祖母。他们记起她喜欢吃红星路的兔头,还有盐市口的荞麦面,讲起她从前的坏脾气,都一笑而过,全当作值得缅怀的趣事。曾祖母在世时,众人都需要看她的脸色。她当了半辈子的小脚媳妇,丈夫咳嗽一声都忍不住发抖。所幸丈夫早死,家中儿孙众多,她便找回了闺中小姐的脾气,稍有不顺心的事情便呼天抢地,几家的儿媳妇都躲着她。爷爷是长男,自然接下了照顾她的担子。众人这才舒心,纷纷说这是莫大的福气,一家子人,承欢膝下。
曾祖母在世的最后半年里,她彻底无法控制自己的大小便。起初,她还会因为尿了自己一身而羞愧不已,别过脸骂我,到后来,已是麻木地被我托起屁股,擦拭下体。一个月的护工费要三千,家里的房贷没有还清,家里人都咬着牙,不愿落得不孝的坏名声。奶奶说,自己当了一辈子窝囊儿媳,现在婆子妈却是这副模样,她连半分怨恨都生不出了,也怪伤心的。她不由分说地把所有事情推给了我。于是,我上班前给曾祖母垫一张尿不湿,到了晚上再取下。
众人口中那个亲切的曾祖母太过陌生,我无法参与谈话,只能在旁桌啃兔头。我将兔头掰成两半,拔出它的舌,这舌腌得极其入味,又含住上半部分,吮吸它的脑花。旁边年幼的孩子已经坐不住,嚷着拿过手机,在父辈的交谈中玩“王者荣耀”,问候队友的祖宗八辈。表妹问我玩吗,我说:“之前会玩,现在已经手生了。”表妹嫌恶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还不如坐到那桌去。”我笑,听着表妹毫无顾忌的话,想象很多年后他们的模样。叔父说,儿时,父亲可是爬树的高手,能爬到树梢摘最红的李子,胆子大,半夜带着生产队的孩子看鬼火,进城工作后人才变得板正起来。父亲笑着和他碰了碰酒杯,说:“人老了,不比当时。”他又转过来教育我,说我吃不得苦,要是他有我这样的条件,肯定干出一番事业。我只能点头,因为我也不知道,同岁的父亲究竟是怎样的。
他们吃倦了,呷一口酒,又开始抽烟。媳妇都让自家丈夫少抽一些,他们板起脸,让她们不要说扫兴的话,一年到头一大家子只能聚这么一回。表叔多次叮嘱我,给曾祖母烧纸钱时记得带好酒,在坟头上洒一圈。我说:“还要带兔头。”他连声附和道:“对,对,对。”大家喝得尽兴,便生出了平日里没有的好心,合计着明日一起为老人家上香。父亲不无夸耀地说,自己每年都到寺里拜一拜,不求佛保佑,但求心安。众人皆说,这才是真正的悟。
父亲总说我没有悟透,所以才想东想西,平添烦恼。
在寺里短暂住过的居士养了几缸荷花,正放在住所前的空地,现在只剩下枯瘦的荷梗立在幽绿的死水之上。缸中生了绿藻,见水面有涟漪闪过,我凑近一看,竟瞧见其中生了一群银灰色的鱼苗。涟漪渐渐大了,抬头,发现天空飘起了小雨。
“嗡”的一声闷响,古钟敲响。铁壶的声音趋为平静,水开了。
二
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名士马拯携仆冶游潇湘,遇一古寺,推门而入。寺中有一老僧,长眉修髯,皓然胜雪,修为精湛,邀马拯入室喝茶。二人相谈甚欢。老僧说山居盐酪用罄,马拯遂令其仆下山购买。少顷,老僧与仆皆不见人影。山径上有一隐士,入舍歇息。隐士说,方才上山时望见有虎食人,食尽人肉,竟变为一老僧。话毕,老僧踏入云屋,合十问好。马拯见其须上沾血,惺惺作态,恐其变虎食人,遂依其行事。当晚,马拯与隐士歇宿偏堂。子夜时分,虎啸大作,幸二人早有防备。天亮,老僧温言叩门,邀二人围炉烹茶。马拯与隐士合力将老僧倒掀至井中。二人分刮财物,下山而去。遇一猎人,邀暂住。二人应允。
深更,云气氤氲间现出人形,又唱又跳,或男、或女、或僧、或道,齐口大喊:“他们杀了和尚,又要杀将军!”少顷,白额大虎至。猎人执弩箭,直贯虎心。而虎伥又至,如丧考妣,齐声哀号:“谁人又杀我将军?”马拯破口暴喝:“无知野鬼,为虎所杀,反哭元凶!”伥絮言良久,如烟消散。三人齐声大笑,欢然而别。
儿时上山时曾听方丈讲过这个传奇,听起来像是盗版的聊斋,一连几日做梦,都见着白雾状的野鬼。我问,伥究竟是什么。父亲说,你需要悟。他曾经在五岁时被方丈摸顶,以保佑此生平安,于是每年初一都来寺里还愿。寺隐于崇州西北群山之麓,共一座大殿、两座偏殿、一口古钟。钟旁有一树环抱古碑,现在已经完全不见古碑的踪影,只有木瘤上挂着的牌子写着:树抱碑。相传那碑由蜀王朱椿题字,至今已没有记载。如今,讲传奇的方丈已经圆寂,舍利子放在大殿的后方。我已经忘却了他的模样,只记得他偶尔摘下土黄色僧帽后光溜的脑袋。他喜欢吃老面馒头,爱到后山摘茼蒿菜,煮一大锅分给前来上香的旅客。八十年代第一次重修古寺,他从自个儿腰包里掏钱。可惜钱不多,只重修了供奉金像的大殿。2003年,一个亏了几千万的房地产商来寺里祈福,刚到寺里,便接到电话,一个制药商买了三幢房屋,于是转亏为盈。房地产商大喜,向寺里捐了一大笔钱,重修古寺,连那口古钟都置在了新建的亭中。后来他又经历了金融危机,虽说也到寺里求佛保佑,但古寺并没有显灵。两个月后,他宣布破产。
这个故事时常被后来的僧人说起,来寺里求清闲的居士也称古寺为风水宝地,但他们都隐去了后半段。父亲曾是房地产商的员工,当年分得了一套房,便记得完整的故事。但父亲从未向他人说起,在寺里碰见僧人向居士介绍古寺时,只是一笑而过。偶尔听到亲友抱怨不顺,他也会让他人上山,来古寺里拜一拜。
半年前,曾祖母去世前,我们正在寺里烧香。这自然是父亲的主意。医院打来电话,通知曾祖母在刚才走了。她中Dq1Ik1zLLvUlhw9PWE2+0f3f/ZTC8XPG6aSn5Jy1Y1E=途清醒了片刻,交代护士立遗嘱。遗嘱只有寥寥几字,说将所有从闺房带出的东西留给我。众人都清点过家中的遗物,彼此心知肚明,遗物不过是一袋线装书和一块玉镯,于是没有异议,只道曾祖母疼我,又嘱咐我年年来寺里烧香,不要辜负了她的心意。我听着寺里的钟声,觉得佛突然伸出赤脚,踹了我一下。
曾祖母说,自己看见了伥。我将此事说给父亲听,他思量一阵,只让我不要乱讲。我记起方丈讲述的传奇,竭力回想那时的答案,却只记得父亲让我参悟。我问寺里的僧人,伥是什么。他们惊诧地望着我,又问伥字是哪一个。我说,为虎作伥。他们恍然大悟,说,便是那行坏事的替死鬼。说罢,他们又看向我,似乎在疑惑我为什么会突然提起这个故事。方丈的回答绝不是这一个,但我依旧点点头,解释道,这是老人家的疑问。僧人夸我孝心可嘉,又说我自有福相。我持香深叩,长久地伏在蒲团之上,来压住内心的酸涩。我决非他们口中的孝子,也不愿意像旁人那般,将家庭时刻含在嘴中,再掉几滴眼泪。对于曾祖母,我是恨的,但似乎也不是在恨她。大多数时候,我都坐在一旁,而她躺在床上。听见她咳嗽,我便倒水;每隔一个小时,拿来便盆,扶她坐下,然后将屎尿倒掉,等待母亲和我轮班。
我、母亲、奶奶,我们总是按照这个顺序轮换。
曾祖母是一位讲究的老太太,未出嫁前是重庆造船厂富商的女儿,结婚之后随丈夫到了四川阆中。出嫁时无比风光,嫁妆是十根金条,光是咖啡的杯具便带了足足五套。可惜到了六十年代,家道中落,大部分的首饰都典卖出去,只余下一块成色不好的玉镯子。金条如今在何处,子子孙孙都说不清楚,只在佛像前盼望老人家回光返照,造福后人。
年轻时,她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最困难的日子也是如此。年过八十,医生说,她不能再喝了,家里人便冲一杯,让她闻气味。要现磨的,速溶咖啡会挨得一顿好骂。我将磨好的咖啡粉倒入滤杯中,压平,倒入烧开的热水,两分钟后,再将咖啡杯放在她的鼻下。这气味似乎是她的命数,她短暂地睁开眼睛,问,是阿焕吗?阿焕是爷爷的乳名,有时候,她也会叫父亲。我一遍遍地告诉她,我不是,但她始终没有记住。父亲说,她老糊涂了,让我不要放在心上。但她分明知道,我不是她的孙子。她总是用咳嗽命令我。
上山前一晚,我将磨好的咖啡粉带到医院,在开水房的药味和消毒水的气味里冲了最后一杯咖啡。例行公事地放在她的鼻下,忍耐着半分钟的流逝。我以为她再也不会睁眼了。忽然,她握住了我的手,插着针头的手掌颤抖着。
她说:“我看见了伥。”
我将玻璃杯放到一边,反握住她的手,轻轻放在病床上。在我小时候,她时常讲一些奇怪的故事,人们都说她得了失心病。父亲只叫我听着。她重复着,虎吃人,人变鬼。等我年龄稍长,才从书中读到,那替死鬼便是伥。《山海经》中记载,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害恶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老虎吃鬼,天命注定,但难以饱腹,遂驯鬼为伥,以人为食。伥助纣为虐,虽为虎食,却心甘情愿为虎寻觅食物。世人不解,遂有为虎作伥之说。这大概和老方丈讲述的传奇是一个东西。
我环视着病房。这里除了我和曾祖母,并无其他活物。
“你疯了。”我告诉她。
她的眼睛瞪得极大,混浊的眼珠转动着,像是泥潭里不断陷落的石子,我几乎能听见细微的嘎吱声。我慌忙起身,想叫医生进来查看。她不知从何处生出了气力,在病床上拼命挣扎。手胡乱挥,脚使劲蹬,语无伦次喊着“母亲”,又扭向一旁,哭得像个孩子。她的脚比我的巴掌还小,身体蜷缩,似乎正遭受着灭顶的疼痛。她又张开身子,每根手指都向外伸,竭力想抓住些什么,像一张濒临断裂的弓。我曾见过她的无数张脸,也曾在深夜里替她抠痰时想过——倘若我的手绕住她纤弱的脖颈,明天怕是会轻松些许。
但当我直面她的衰老,却只觉得惶恐。
玻璃杯被扫到地上,碎了。她用手心擦去脸颊上的泪水,又用手指去擦眼角的泪水,呼吸渐渐平歇,语气也变得和缓起来,似乎认出了我,轻声呼唤着——敏儿,敏儿。我一声声回答着她。她如同一枚孱弱的叶片,眼睛紧闭,又忽地睁开,惴惴不安地握着我的手,确认着我的存在。最后,在闭上眼睛之前,她哆嗦着说:“对不起。”
我怔愣了一会,才蹲下身收拾玻璃片。我无从得知,她究竟看见了什么才如此惊惶。在玻璃杯举起又放下的半刻钟里,她是如此害怕。
古钟敲响了,沉重的声响在寺里回荡,似乎永远不会停歇。母亲叫我拿票打斋饭。菜照例是茄子烩四季豆、蒸南瓜、炒油麦菜和青菜汤。众人各自放下票,拿一碗,寻一空位坐下。父亲问我早上去哪里了,怎么不见人影。我低垂着头,只说自己思念曾祖母,于是在后院走了一圈。亲戚夸:“不像我家那讨债鬼,你们家的孩子就是来还情的,孝顺,又读得书,将来肯定很有出息。”母亲笑着说:“孩子只会死读书,现在工作编制都没有拿到。”父亲更是连连摇头,说我不稳重,再夸几句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
他们又谈论起我的婚事。见我神色不快,母亲连忙按住我的肩,附在耳边说:“大家都是关心你才这么说的。”我心里依旧不乐意,不愿自己像是砧板上的猪肉,被人指点议价。父亲投来一瞥,我便嘘了声。表妹羞愤地看着我,似乎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着急。我安抚地冲她笑笑,她倒是火冒三丈地站起来,说:“不吃了。”表叔吼了一声,没用,于是连连摇头:“这孩子。”表婶说:“得好好教一番,这性子结婚后指定要吃不少亏。”母亲接话,说:“我们家这孩子也是,性子比一头牛还倔。”我听不惯母亲在外一味谦虚,甚至到了贬低我的程度,不知她只是口头上说,还是心底便是这般想的。或许是后者吧。她向来不喜欢我的性格,总教我要显得拙笨一些,才能好好生活下去。我不信,和她争辩几番后发现无法改变她的观念,便渐渐变得沉默。她始终是我的母亲,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也学会了和外人一起,笑话她时不时闹出的错误。她在笑声里大笑,似乎她天生便是这般愚笨。
斋饭的时间结束了,钟声颤巍巍地在古寺里响起。父亲笑道,这敲钟的僧人怕是刚才没有吃饱饭。大家都一同笑起来。我却觉得,这钟声比重复的撞击声好听。
三
我主动提出,去寻表妹。父亲满意地点点头,又让我教育表妹几句。偏殿供奉着送子观音,这两年上香的人已经渐少了。表妹见我,扭头就走,朝另一个地方去了。我追上去,主动邀她到潭边走走。她满不在乎地说:“那个小石潭有什么看头。”我说:“心诚则灵。”她笑了,挖苦道:“你还不如买一只招财猫回去。”院中飘浮着冷冷的气,阳光穿过竹林,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石桌石凳都泛着白光,残损的石碑卧在草丛之中。将草拨开,才发现碑下是一只神龟。赑屃,龙之九子之六子,用以驮碑。我摸了摸它的头,青苔上还残余着没有消散的露珠。我让表妹也来摸,据说触碰它可以带来好运。她说:“老古董。”
“怎么又惹你生气了?”我只当她在耍小性子。她愤愤地看了我一眼,眼神中竟带着怜悯,支支吾吾半天,只道我这几年的书白读了,还没有之前脑袋清醒。我心里门儿清,毕竟我也是从那个岁数过来的,心里不免多了几分惆怅,但面上仍在笑,又问她怎么个白读法。她被我问急了,大吼:“你怎么和父母一个模子里刻出来,只知道教育我!”说罢,她便跑了,背影很是仓皇,只留下我愣怔在原地。
“又是一年了。”门槛边的老人冷不丁说道。
想着刚才的家事被老人看在眼里,我不由脸红,只能应道:“又是一年。”老人十几年前便在这里了,负责打扫和看管偏殿,性格古怪,但和我倒聊得投机,也算得上相熟。平日里没有什么人来,他便抄读四大名著。他没有剃度,却和其他僧人同吃同住,每天清晨和晚间都在大殿里念诵,膝盖处打上了重叠的补丁。他说,自己是舍不掉山脚下的那口烤鸭才迟迟不肯皈依的。所以,每年上山时,我都会给他带半只色泽油润的脆皮鸭。他摸出两个杯子,斟满,自顾自地碰杯,嘴唇一噘,便是一块吮得精光的骨头。据说,他是一个富商,年轻时干了不少胡闹事,老了便到寺里诵经烧香,以求心安。前年他的儿子来寺里闹过一回,惹出了不小的动静,最后捐了一笔钱才平息了寺里的喧嚣。他究竟犯了什么过错,无人知晓。每当有人向寺里的僧人问起,就连看房门的都支支吾吾。父亲远远地瞧他一眼,便躲开了。于是每年,我都到偏殿求清净。
酒是好酒,香醇,但是并不辣嘴;鸭是土鸭,极入味,又有嚼劲,能撕成细条,放入嘴中反复吮吸。旁边的一口枯井没了。我小时候喜欢趴在青砖上往井中丢石子,听枯叶柔软的颤动。某年和表妹一起看了鬼故事,两人害怕从古井中爬出长发女鬼,都不敢靠近,你戳我推,还嘴硬道,并不可怕,最后撒腿就跑,不愿意在此多待。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红砖色的凉亭,漆色尚新,在这灰扑扑的庭院中,又崭新又苍老。
老人又枯瘦了一些,身上散发着劣质墨水的味道,眼窝深陷下去,像缓慢沉落的地基。我问:“又开始抄经文了?”他摇了摇头,称自己没有毅力,只是写着玩罢了。他曾经抄了八十回《红楼梦》,《水浒传》写到第二十三回,便合书睡觉。一连睡了两日,醒来之后便下山,提着一只烤鸭和一瓶红星二锅头,在偏殿喝得大醉。僧人拿他也没有法子,只求他在来往的香客前嘴巴严实,不要破坏了祈福的灵气。
《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是他最喜欢的故事,每年我上山,他都要讲一回,当作烤鸭的谢礼。我推托不过,又觉得贸然闯入了他的清闲之地,便当作租金,耐着性子听他讲那武松打虎。“只见那武松举起哨棒,运足力气,骑在虎背之上,左手揪头,右手猛击,直将那吊睛白额的大虫打得鲜血淋漓,一命呜呼。”说到尽兴之处,他不免手舞足蹈。我笑道:“幸好武都头没有遇见伥,否则就成了虎口中的一块酒糟排骨了。”他的手中还拿着鸭腿,问我:“怎么突然说起这物来了?”我正愁心里堵得不舒服,便将曾祖母去世前的情形告诉了他。他若有所思,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猛地将杯子扔在石阶上,摔得粉碎。我被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勾起了他的伤心事,连声说道:“这都是大半年前的事情了。”
我帮老人收拾残局,他说不用,又把瓷片和另一只完好的酒杯揣入了兜里。老人见我手上戴着玉镯,随口问:“戴了几年?”我说:“刚好三年。”他笑:“这可不是你们年轻人喜欢的玩意。”我说:“但求心静。”他笑得胡子都吹起来了:“你一个小姑娘,求心静做什么,这都是要入土的老人家该做的事。”我告诉他,自己三年前曾经在大殿闹过一回事,之后便一直戴着。老人一顿,说自己想明白了,又低声感慨:“原来是你呀!”
那时也是大年初一,曾祖母尚未糊涂,还说得动话,稍有不称她心意的事便将他人骂得狗血淋头。我没有在上海找到工作,刚大学毕业,又没有积蓄,于是回到家乡打拼,和父母同住,照顾曾祖母的责任再次落到了我的头上。大学四年已经让我习惯了都市的生活。早上七点便拥挤的道路,总是“难产”的城市,以及人与人之间微妙又淡漠的联系。刚回家的几个月里,我苦不堪言,不熟悉的工作岗位,并不信服我的学生,说一不二的父辈,总是向我抱怨的母亲和奶奶,都让我迫切地想要逃离这个家庭。
上山的时候很冷。雾霭之中,初升的太阳都带着冷意,脚步自然就慢下来。待到庙里的时候,其他亲戚已经到齐了。曾祖母被两个当地人用滑竿抬上来,二表姑邀功似的替老人家端上热茶,四表叔将轮椅展开,将曾祖母抱上软垫。父亲恼怒地瞪了我和母亲一眼,又连忙推着轮椅往大殿里去了。早课已经开始。十几号人低声念诵,气象庄严,佛像下的香炉升起袅袅的白烟。我冻得手脚哆嗦,只顾着将双手焐在袖口之中,又昏昏沉沉,打着哈欠。待念经结束,曾祖母被父亲推着先出大殿。路过我时,她用指节敲了敲轮椅的扶手,见我没有理会,又皱起眉,用膝上的拐杖重重打了我一下,神色不耐烦地吩咐道:“咖啡。”她如此理直气壮,仿佛我生来便是要替她端茶倒水,我竟口不择言:“想闻你自个儿倒去。”父亲立刻大喝,又低头向曾祖母赔不是,说我还没有睡清醒。众亲戚瞧了,手忙脚乱地劝架,纷纷让我道个不是。一见他们狗模狗样,我便气不打一处来,吼道:“值钱的东西早没了,你们眼巴巴讨好也没用,什么都没了!”我又指向曾祖母微怔的脸,带着恶毒的喜悦,笑说:“老不死的东西,只会在别人身上出气。”
众人都愣在原地,就连收拾蒲垫的僧人见了,也退到了一边去。直到父亲大喝一声,将我的名字吼得掷地有声,他们才如梦初醒,羞愤地指责我,骂我怎么想法如此龌龊。我被众人团团围住,一时唾沫横飞。混乱之中,我看见曾祖母的神色,她是如此震惊和受伤,仿佛第一天正眼瞧见我这个曾孙女,微张着嘴,手紧紧攥住领口。我带着胜利的喜悦,将佛像前的供台推翻在地。香炉里的香灰和香全撒在了地上,瓜果撒落一地,苹果骨碌碌地滚到了轮椅边。曾祖母盯着我,抿着嘴,忽地哭了。她用手心擦去脸颊上的泪水,又用手指去擦眼角的泪水。但是众人都被突如其来的巨响所震住,没人注意到她突然间的落泪。
僧人忙不迭地跑来,一口一个佛祖保佑。父亲面上挂不住,于是又买了两个莲花灯,供奉在佛像前。下山之后,他把我叫到房中,本以为免不了一顿责骂,谁知道他竟给了我一个玉镯,让我时刻戴在身上。在头顶冰冷又斑驳的白光下,他郑重其事地说:“辛苦你了,孩子。”随即他又皱起眉,说这是你应该做的,不应该对家里人充满怨恨。
似乎是从那天起,曾祖母开始老糊涂。她渐渐忘却了儿子和孙子的姓名,父亲看望她时也不会清醒,但每当我将咖啡放在她鼻下时,她都会短暂地睁开眼睛,问道:“是敏儿吗?”我从没有回答。她或许是想转世投个好胎,才在死前装作一个良善的老太太;抑或是担心死后没有人给她烧纸钱,所以又记起了我这个曾孙女。我和她从没有心平气和地交谈过,她所有的故事,我都是从父辈口中得知。每当看见她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时,我都在恍惚间看见了很多年后的自己——我也正在死去。
那口顽固的古钟又响了起来。竹林簌簌回响,幽长不绝。群鸟惊飞,寺里似乎又来了新客。不断有人上山祈福,以求此生平安。老人说,他要去睡了。不是午休,也不是晚睡,他似乎陷入了一种昏昏然的状态里。我向他告别,不知道明年上山,他是否还在那里。
“伥,”他蓦地说道,“人也。”
“伥,人也。”我重复着这句话。
我依旧想不起来,方丈在讲述传奇时究竟给了怎样一个答案。父亲总是让我去悟,但是他的参悟似乎不是我所想的那个。我想起曾祖母留给我的一袋线装书,其上字迹规整,一笔一画。在最后一页,她写道:“东西都留在柚子树下。”
车绕着弯曲的山路向下行驶。天空是一种奇妙的灰蓝色,在重重的树林中闪现。老宅早已不见踪影,野草茂密,土墙上的青苔一点点增长。柚子树上还悬着几只柚子,树下是满地的深黄。车子正在远去,我再也听不见沉闷的古钟,只听见山林间的鸟鸣。不知道曾祖母在死前念念不忘的,是否是这样的声响。我正在下山,明年的今日,我将会再次上山。
责任编辑 王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