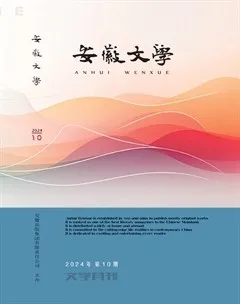红军嫂
她活到105岁,经历的那些令人称叹的故事,足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题记
1
这日,东山岭一带,大雨滂沱。
嘭嘭嘭!夜半,敲门声突兀急促。
“谁?”水燕举着油灯悄悄走到门边,嘴对着门缝小声问。这个才十八岁的女子,因身子瘦而显得修长,鸭蛋形脸庞上,柳叶眉樱桃嘴,鼻头有点翘,两根辫子齐腰,说话办事风风火火,是个典型的山里靓妹。
“是我。”门外传来男子压低的嗓音。
门闩拔开,随着嘎的一声门响,一个黑影裹挟着冰冷的山风和雨水扑进屋来,油灯被吹灭,屋里漆黑一团。
“山根哥!”水燕瓮声瓮气地叫。男子名叫山根,和水燕一样都姓谢。水燕跟他已经完婚,但还是一口一个哥亲昵地叫他。
水燕点亮油灯,仔细端详了山根一会儿,把油灯放在墙洞里的灯台上。
“我们要走了。”山根关上大门,甩了甩箬笠上的水,将箬笠靠在门边,又说,“可能很长时间回不来,你马上去告诉他们,到外面躲些日子,你和娘等下就去大舅家。”山根说的他们,指的是家里有人在队伍上的另外二十六户人家。
水燕不语。驻扎在村里的红军队伍昨晚冒雨转移了,她就猜想可能要出大事,但没料到来得这么快。这会儿,尽管山根一身水淋淋,她还是紧紧抱住他不肯放手。上次山根回来住了一夜,说仗越来越难打了,牺牲了很多同志,她就担心山根有个好歹。山根安慰她,说他打猎的本事不是白瞎的,再说红军是为穷人能过上好日子打仗,万一牺牲了,值!
现在,山根要远行了,水燕不无担忧地问:“知道去哪里吗?”
“不知道。”山根摇头时打了个寒战。
水燕显然感觉到了山根身子的颤抖,从他怀里挣出来,说:“这么大的雨,你穿蓑衣走吧。”她要去取蓑衣。秋天,加上下雨,天气寒冷,蓑衣不仅挡水,还保暖哩。
“不,”山根拽紧她说,“你跟娘带着吧。”他说着解下腰里的竹烟杆塞给水燕,“你们都保重,情况紧急,我走了。”他抓起箬笠,又嘱咐水燕,“我们没回来你千万别回家。”
“等等!”水燕扑上去,依在他怀里,捞起他的手按在自己的腹部,充满幸福地道,“我有了。”
“真的?!”山根喜出望外。
“真的。”
山根紧紧搂住水燕,把她的头往怀里揽。“是儿子。”他摸着水燕的肚子说。
“生了才知道。”水燕有些娇嗔。
“一定是儿子,”山根坚定地说,“他还要当红军哩。”
水燕不语,静静地靠在山根身上。
良久,山根万般不舍地咬着她的耳朵道:“队伍会回来的,我们会回来的。”说完,他扣上箬笠,开门钻进雨中。
“不管走多远,不管有多久,一定要回来,我们等着你!”水燕追出屋,双手撑在门框上,朝着山根的背影大声喊。
欻啦啦——轰隆隆!风雨交加,雷鸣电闪。
水燕冒雨走遍了村里那二十六户人家,然后背上包袱,带着山根留下的竹烟杆,扶着娘,两人头顶蓑衣,一路摸爬滚打,奔三十里外的老舅家而去。
山根是中国工农红军一军团属下九连的一名战士,当夜,他随部队从东山岭出发,连夜向赣南瑞金集结。几天后,他跟着队伍投入惨烈的突围奔袭作战,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2
东山岭系武夷山余脉与雩山山脉相连接地带,峰峦如聚。一处山洼间有个村庄,就叫东山岭村。全村八十三户人家都姓谢,三十一户半农半猎,五十二户半农半林。
十五年后六月里的一天,炎炎烈日高悬在头顶,穿着一身自家织自家染的蓝色粗布衣衫的水燕,嘴里哼着《解放区的天》,带着高过她半头的儿子回到了东山岭村。她娘三年前去世,长眠在大舅家那边的山岗上了。
其实,水燕在离家后的第六天夜晚回来过,那时她女扮男装,结果没遇到一个人。村里半数房子被烧,她家的房子只剩下残垣断壁,瓦砾和灰烬。
全村人都来看她娘儿俩,唏嘘之声此起彼伏。好在解放了,迎来了新生活,乡亲们帮她在原屋址上搭起三间茅草盖顶的竹棚,儿子一间,她一间,还有一间做厨房兼待客。乡亲们东家搬来一把凳子,西家抬来一张桌,连带锅碗瓢盆。那夜得到她通知逃离了险境的人家,更是给她送来了床、柜等大型家具。水燕激动地把从大舅家带来的半只麂子肉连同萝卜干笋干,烩了一大锅,再加两笸箩水蜜桃和杏子,全摆上桌感谢乡邻。往后的日子,只会像顺梢吃甘蔗一样,一节更比一节甜,她不怕吃光用光。
三十三岁的水燕,仍然像做姑娘时那样将辫子留到齐腰。她琢磨,过去十五年了,为了让山根回来时一眼就能认出她,要保持原貌。衣裳裤子大多是新做的,以前的太瘦不能穿了。娘儿俩日里干活,夜晚到祠堂的夜校跟工作队干部学文化。山根说过,他在队伍上就学认字,她不能比山根差太远。
村里那二十六户人家,也像水燕一样在等待亲人回来。
东山岭村虽然地处万山丛中,但村庄地势平坦,村前从高到低依次相连的水田形成一个大田畈。村口的石砌小路笔直伸去半里地,把田畈分成南北两面。石路过了木桥后便窄了,而且成了泥路,沿溪涧顺山蜿蜒蛇行于峡谷间。站在木桥边的一处石崖上,能将弯弯绕绕在峡谷里的小路看得很远很远。每到傍晚时分,水燕就到石崖上站半个钟点。村里人说,她都快站成一块望夫石了。他们清楚,从县城到镇上只有下午一趟车,再从镇上步行到村里就该是傍晚了,要是有人来,站在石崖上的她,能在第一时间看到。
全村人都希望她能早日看见山根回来,或者看见二十六户人家的任何一位亲人回来。
这天傍晚,隔壁的谢奶奶看见水燕又往村口走,轻轻地拉住水燕的衣袖,问她道:“水燕呀,山根咋还没回来?”她的潜台词是,当年除山根外,村里有二十六个后生也跟红军走了,到现在一个也没回来,山根怕也是烈士了吧,别再这样傻傻地等下去了。
水燕笑盈盈叫声谢奶奶,道:“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
她又满怀信心登上了石崖。
天凉了,山上的枫叶开始泛红。这天,水燕和儿子正在吃午饭,村里突然响起人们带着惊喜的呼喊:“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显然,人们是喊给水燕听的,山根要是还在队伍上,现在自然是解放军。
水燕呼地站起,放下碗冲出竹棚,儿子紧随其后。
村外小路上,果然有两个解放军缓缓向村里走来。不是山根,他俩的个头没山根高。水燕立马作出判断。不过,迟疑片刻后,她还是迎了上去。
“妹子,这是东山岭村吗?”身子有些胖,像是首长的解放军问水燕。他四方脸庞,浓眉大眼,外衣敞开,额头上汗水涔涔,听口音也是南方人。他身旁的小战士十八九岁,肩膀和胸前都被汗水濡湿了,但风纪扣系得紧紧的,腰间一边挂着盒子枪,一边挂着黄褐色公文包。
“是。”水燕答道,目光在两个军人身上跳来跳去。
“可有个叫水燕的妹子?”
水燕的心提溜起来,身子颤抖,声音突然变得极其微弱:“我就是。”
“嫂子!”首长有些失态地一把抓住水燕的双手,声音哽咽。
入夜,水燕家的竹棚里里外外挤满了人,隔壁邻居点来三盏松明灯,照得竹棚内外亮亮堂堂。首长当着全村人的面,郑重地把一个浸染着烈士鲜血,工工整整写着“赣东崇仁东山岭”七个黑字的烟荷包交给水燕。
山根在攻占腊子口时,为掩护一位受伤的战友英勇牺牲。他掩护的战友就是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位解放军首长。
唔——有人痛哭起来。
水燕没有哭,甚至都没流泪,泪早就流干了。再说村里另外二十六个后生,也一个都没回来。
第二天,首长把水燕的儿子带走了。
3
剪掉长辫,留一头短发,水燕实打实像个村里的后生。田地里抡锄扶犁干活,上山背绳拖竹拉锯伐树,一切都不在话下。
一个雨后放晴的日子,她扛着镢头和铁锨,到村后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挖了坑,将山根的竹烟杆和烟荷包,外加她剪下的那束头发,拿块干净的布包一起埋了,刨土堆了个坟包。冬至那日,她央人抬来块大麻石搁在坟包前,自己一手握铁錾一手挥铁锤,在石头上凿下“红军哥哥谢山根之墓”九个拳头般大的字,还在字的凹槽里描上了红漆。
那时,水燕本来就年轻,加上日子好了,她神情比年少时更显妩媚,往人堆里一站,楚楚动人,上门求亲的人家不少,谢奶奶也多次劝她找个依靠,但都被她婉言回绝。那时她不知道自己为啥会这样,她只是PXl3v/cZMdp5xtCS8wp4XODmSE6WTpvZ+jJsI5xfD0U=不停地在心里说,头发都和山根哥的烟杆烟荷包葬一起了,自己永远是山根哥的人。
很多年后她才明白,她傻。山根哥是为穷人过好日子打仗牺牲的,队伍上多少人呀,有一次她看见山根哥所在的队伍,漫山遍野的人嗷嗷叫着向前冲,手里的枪杆明晃晃亮闪闪一片,像大山上林子里密匝匝的树木。多少好儿郎,都在为穷人能过上好日子打仗,很多都倒下了,东山岭村就有二十七个哩。现在穷人在往好日子的路上奔,她就想一心一意在这条路上多付出些辛劳,山根哥要活着,一定也会这样。他不在了,她要接着做他要做的事,这才对得起山根哥,对得起那么多红军兄弟,所以她就没多考虑自己的事。
水燕像变了个人,农会主席谢二庆看在眼里。这个不到五十就驼背的山里人,新中国成立前就是党员,他二小子也去当红军没有回来,因此特别关照水燕。有一天,他拦下割菜回家的水燕,对她说:“水燕,你到农会来当干部。”
水燕搁了菜筐,撩了下垂到额前的头发,咧嘴笑着对谢主席说:“伯,我管自己还可以,当干部不行。”按辈分,水燕叫他伯。
“没有天生的干部,肯学肯干就好。”谢二庆说得斩钉截铁。他的眼力不会差,她身上有股子干工作的狠劲。
水燕当上干部后思忖,以后万事就得先为大家伙儿着想。她早些年做下的两件事,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第一件,工作队走了后,东山村的夜校没停,每星期两个晚上,祠堂里松明火把点得透亮,村里最有文化的人当老师,不计报酬。开始,有人泼冷水,说山里佬要那么多文化有啥用。她就拿着儿子写来的信到夜校念给大家听,念完把桌子敲得哐哐响,对大家说:“你们看啊,你们看,要是没文化,我崽能写信跟我说话吗,我能把我要说的话写在纸上寄给他吗?”她的话引起哄堂大笑。崽在东山岭一带是儿子的意思。她又指着那些十五六岁过了上学年龄的嫩后生说:“还有你们,三五年以后,说不定也参军,再说人一辈子谁不要出外,没个文化行吗?”
“是哩!”人群里响起一阵呼应。她的话把大家说动了,夜校就坚持办下去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特别是年轻人,大家在一起学文化,争辩事理,村里人的精气神就跟别村人不一样,生产和建设搞得也不一样。对了,水燕还鼓励青年去参军,村里每年都有后生穿上军装,有的当了军官,有的回村,对村里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从高级社又到大队后,东山岭大队长期是先进,年年受表彰,这是后话。
入党后,她做了第二件事。
那时村里刚成立高级社,一个雪花飞舞的日子,趁社员们都歇了,水燕又扛着镢头铁锨上山。连续三天,她在山根墓后的山梁上掘了两排大坑。次年三月,她在那些坑里栽下了手腕粗一人多高的红枫树。秋风给枫叶染色的日子,山梁上破天荒地烧出了一片艳红。
水燕把社长谢二庆带到红枫林前,对他说:“伯,和山根哥一样,村里二十六个后生都没回来,也没音讯,每家都想得慌,我琢磨了这个法子。”她指了指那些红枫树。
“啥法子?”谢二庆摸不着头脑。
“这二十六棵红枫,每一棵就是一位红军战士,每户人家认一棵,纪念参加队伍的孩子,不管活着还是牺牲了,都是念想。”
谢二庆听了,连连点头。他双手颤巍巍抚摸着那一棵棵细小的红枫树干,眼里噙满泪花。他首先认了一棵,其他二十五户人家,闻讯奔上山梁,都选了一棵红枫树,而且呵护备至。也真是怪了,这以后,这些人家的精神状态都发生了变化。过了几年,有的人家也抬块石头搁在树根处,刻上“红军战士某某某”等字。又过了几年,二十六块石头上都加刻了“革命烈士”四个红字。
东山岭的气候湿润不热,红壤酸碱性适中,枫树叶到了秋天红得像燃烧的火,而且留在树上的时间长达一个半月。没几年,那两排枫树长得粗壮高大,连片的树冠,随着山势中间耸起两边落下,深秋时节火旺火旺得像一抹永不熄灭的火烧云。
后来,这山被人称为红军山。
4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水燕挑起了东山岭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担子。
这一来,谢老刮不爽了。谢老刮大名谢甜瓜,脾气不好,满脸络腮胡也没能掩住凶巴巴的相貌,村人就给他起了个老刮的外号。他比水燕大五岁,因为搞生产有一套,三年前被任命为大队长,还兼着第一生产队队长。在他看来,自己笃定是接任支书位置的人,没想到被妇女主任抢了,窝了一肚子火。
水燕也不是吃素的,直接在饭点去找谢老刮,当着谢老刮婆娘的面,对端着小酒盅借酒浇愁的谢老刮说:“谢大队长,三年,我要是干不好,支书你来当。”谢老刮愣怔着还没把手里的酒盅放下,她又道:“不过这三年,你要无条件支持我。”她没等谢老刮回话,瞥他和他婆娘一眼,微笑着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谢老刮就那样举着酒盅,直到他婆娘把酒盅扯了过去,还没回过神。
担任支书后的水燕表面沉静,心里火烧火燎。日头还没露脸,她已经在村里走了一圈;晚霞退去天刚擦黑,她又到村里溜了一趟。后来,她的足迹踏遍了全大队的山山水水。庄稼,山峦,树木,毛竹,从她身边闪过时都在向她微笑致意,但她没心情搭理它们,直把脑袋想得生痛,耳朵也嗡嗡作响,她甚至到山根哥的坟前坐过好几回。工作该怎么干呢?三把火要怎么烧?她不知道。要是山根哥在,他一定会给她拿主意,她想。
这夜,她做了个梦——山根对她说,他想儿子了。
她去找谢老刮,跟他说她要去部队看儿子。以往,隔一两年儿子就会回来看她一次,她去部队还是头一回。她到隔壁邻居家收了一大袋板栗,儿子是副营长,身边有不少兄弟,不能空手去。
八天后回来,她变了个人。虽是深秋,枫树叶还在树上红着,山里已经有些冷,但还没到穿大衣的时候,可一早一晚,她就穿上了儿子给她的军大衣在村里溜达。晚上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穿着军大衣的她,精气神十足。
“社员同志们,我这一次是长见识了,我们的部队,那精神面貌……”精神面貌是从儿子那里学来的新词。兴许是大衣袖子长了点,她不时地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轮着往上拉袖子,嘴里继续放话:“啥都是横平竖直一条线,床上的被子,比豆腐块还齐整,那队伍,一百多人走路,嚓嚓嚓,就一个声响,钢铁洪流啊,跟过去红军一样,走路就唱歌,扯着嗓门喊一、二、三、四,路边坡沿都打了半尺高的硬土埂。”她边说边比画,心情激动。
“那是部队呀!”人群里有人喊。
“谢宾,谢营长,部队是那样的吗?”人群里有人大声问,大家刷地将目光射向谢宾。民兵营长谢宾当过志愿军。
“部队嘛,就是那样。”谢宾满脸自豪。
“八成我们也要搞成部队那样?”有个后生问。他叫谢子庚,是老支书谢二庆的侄子,大队基干民兵排排长。
“我们哪能搞得成部队那样。”水燕接过话茬,又拉袖子,可军大衣袖子总也拉不上去,引得坐在前面的一群学生伢崽哄笑起来。
“但我们可以学习部队,把全大队建设得更好!”
“悄尬——”社员们热切地呼喊鼓起掌来。悄尬是当地方言,好、圆满的意思。
原来,水燕有了工作思路,她跟谢宾营长谈过自己的想法,虽然那时她还提不出改天换地重整东山岭大队山山水水的系统构想,但有了个基本规划。
然而,在讨论具体工作方案时,谢老刮没能和她达成一致意见。被邀请出席会议的老支书谢二庆勾头瞅着地面,一声不吭。他对水燕的想法,也保持沉默。
“其实,水燕支书的设想很简单,把路拉直加宽,所有的空地,都种上庄稼、果木,就像我们家里,门后、墙角,哪里不摆物件?我们先干起来再说。”谢宾向大家解释。这个曾经的军人,作风跟大家不一样。
听了谢宾的话,水燕欣喜地点头笑了,她进一步给大家描绘东山岭大队未来的景象:“远山高山,森林密布大树参天、近山矮山,风光秀丽景色宜人、边山坡山果树成片瓜地连畦,概括地说就是远山高山森林山、近山矮山风景山、边山坡山瓜果山‘六山’规划。”她停一下又道:“这样一来,能多打粮食不说,还多了水果瓜类,春天花儿开,秋日果子熟,我们东山岭大队就像一座大型花果园。”这些都是儿子带她逛公园和参观郊区果园后产生的想法。
谢二庆听了,慢慢点起头,其他几个大队干部也面露喜色。
“这样的话,要大干一场。”谢宾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生产队长们却闷声不响,他们期待着,都想以谢老刮为马首是瞻。
果然,谢老刮摩挲起满脸络腮胡,瞅瞅另外三个队长,清清喉咙发出了不和谐之音。他说:“作为大队干部,我完全同意水燕支书的安排,但作为生产队长,我有很多困难,这山那山瓜呀果的,都要用劳力说话,我们队劳力农忙时派不出,农闲了要上山,叫谁去修路,咋还能在田边地角村前屋后种瓜果?”
东山岭大队田地不多,打下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只够吃饱,想要手头宽泛些有点零用钱,就要打山上林木毛竹的主意,那年月,打猎已经没丁点收入了。
三队长谢有富是个老实巴交的汉子,对水燕描画的未来远景有些心动,但看到大队长谢老刮的态度不明朗,便附和谢老刮道:“我们队要安排劳力上山,不然明年买薯藤的钱都没有。”生产队旱地里每年都要种红薯,端午节前去县城买薯藤苗,要现钱。
“对的,我们也要上山,不然年底拿啥分红?”四队长谢福荣也火上浇油。
这么多年干部不是白当的,干活当然要人手,水燕把这个问题早就琢磨了好几遍。要劳力,关键在队长。她先朝大里说,让队长们感到为难,而后只向小里要,队长们就不好拒绝了。现在,她听了几个队长的话,胸有成竹地笑着望他们一眼,不紧不慢地道:“劳力是必需的,但我不要多,把你们的基干民兵给我就行,除了农忙‘双抢’,他们都归大队管。”
四个队长愣怔了一下,然后面面相觑,算是交换意见。基干民兵都是十八至二十五岁的强壮劳力,每个队只有五六个,人数不多,不影响上山搞副业。这个条件不答应说不过去,这么想着,队长们相互丢个眼色,都不吭声了。
谢老刮也有些尴尬,不自然地咧嘴嘿嘿两声,喃喃地道:“抢收抢种时基干民兵要回生产队干。”
水燕点头,叮嘱谢宾道:“基干民兵你亲自带队。”
事情就这样定了。
第二天一大早,二十二名基干民兵列队在大队部兼学校大门外操场上。他们锄头当枪,腰间系刀,个个威风凛凛,女民兵们穿得五颜六色,更是一派英姿飒爽。
水燕没穿军大衣,上身是那时流行的蓝色劳动布工作服,下身着肥大的绿军裤,手握镢头走到民兵队伍前。只见她一捋袖子,做起了动员:“东山岭大队现在是啥样子?我们不怕揭自己的丑,露自己的短,不说别的,村里的姑娘大多想嫁到山外去,外面的姑娘难得有人嫁进来,是不是?”她瞪大眼睛问大家,停一下,挥了挥拳头,又道:“我们要改变它,不反对姑娘外嫁,但也要让外面的姑娘能嫁进来。”水燕还真会做思想工作,面对这些后生,她抓住了最能让他们动情的问题,尤其是男青年,面临的就是找对象的事,把这个头等大事解决了,其他事不在话下。
民兵排长谢子庚,二十三岁还没对象,水燕的话说到他心坎上了,他扯着嗓门道:“谢支书,我们跟您干!”
“对,跟您干!”男女青年们齐声喊,干劲冲天。
“好,从今日起,我们大家一起干!”水燕一扬手,扛起镢头领着大家朝村口奔去。
接下来的日子,女民兵班在田边地头,村前屋后的空场子上挖坑,准备季节一到种果树,男民兵沿出村的路开山劈石把路拉直拓宽。这修路工程真是深得人心,多少年来,村里的木竹靠人力驮到八里路外有公路的地方才能出售,效率低还累人。要是路修好了,不说用汽车拖拉机,就是板车拉,一个人也能顶三四个人,还省去多少气力。于是乎,不上山的妇女老人自动加入修路队伍。谢老刮脾气倔说话糙但人不坏,他从山上回来,看见修好的一大截路,半天也没歇,带领全队社员来到修路工地。另外三个生产队社员也纷纷赶来,临近春节那些日子,每天有一百五六十号人在工地干。水燕没想到,大家会如此支持她,心里暖烘烘,看到了早日改变全大队面貌,把日子过得更好的希望。
第二年春耕时节,公社书记来东山岭大队检查播种情况,往年有八里多路要步行,现在路面宽敞,已经平整得可以骑自行车了,水燕的工作受到了表扬。
不久,水燕碰上了实现自己抱负的好机会,要不怎么说时势造英雄呢。这年,上级号召学大寨,她随参观团前往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回来后干劲更足、目标更明确了。
“重整山河,平田修地。”东山岭村喊出了自己的口号。
“学习呀大寨赶大寨,大寨红旗迎风展,它是咱公社的好榜样啊,自力更生改变了穷和白……”“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大寨那个就在山下边,七沟八梁一面坡,层层那个梯田平展展……”
每年村里公布分红决算方案的日子,晒场上歌声震天,全大队男女老少齐聚,四个生产队的社员歌咏队开展歌唱比赛,唱的就是《学大寨赶大寨》和《敢教日月换新天》两首歌。哪个队赢,哪个队率先公布决算方案。那些年,这两首歌东山岭大队人人会唱,个个会哼。
可喜的是,东山岭大队被评为地区学大寨模范大队后,公社9EStgcCKP0EZKF4OAHPqFg==集中三百多个强壮劳力,开来东方红推土机,在东山岭村边的山谷里修了一座水库。水位提高了,东山岭人把原来山坡上的旱地改成了梯田。又利用水库建了小型水电站,与东山岭大队相邻的三个大队都用上了电。
东山岭大队渐渐改变了原来的模样。
5
所有的都可以按下不表,禾秆垛里的爱情故事非细说不可。
东山岭一带,把稻叫禾,稻草叫秆或禾秆。
旱地改成梯田后,头几年肥力稍显不足,收成没达到预期。水燕琢磨,要造农家肥,改造土壤。这年,早禾即将开镰,她把四个队长请到大队部,桌上摆了装着花生瓜子香烟的果篮,泡好了喷喷香的茶水。队长们也不客气,拉开椅子坐下,捧着热气袅袅的白瓷杯一边咕噜噜啜饮,一边嗑瓜子剥花生,就是都不言语。他们虽然不知道水燕葫芦里卖的啥药,但这些年经历过的事不少,他们信得过这位带头人,只等水燕发话。
“有个事跟你们商量。”水燕望着他们四个人说。
队长们都停了吃喝,三队长谢有富咂摸:支书平常雷厉风行,今天咋像小媳妇说话?
果然,今天的水燕是另一种风格。她又瞅着四个汉子,轻言细语地道:“找你们来,就是跟你们商量,今年禾秆不能烧,将禾秆扎成把,全部放到路边田角,晒干后堆成垛。”
队长们明白,禾秆堆成垛,山外很多大队就是这样做的,禾秆是上好的牛饲料。
然而,队长们都不乐意这样做。从古至今,东山岭的禾秆都是付之一炬的,多省事。
“费那力气干啥?”四队长谢福荣问。
水燕耐心地解释说:“做肥,要想庄稼长得好,肥料一定不能少。”她说用禾秆垫猪牛圈,猪牛粪把禾秆沤烂后,是上好的农家肥,把这肥施到梯田里改造土壤,比烧成草木灰强很多,一两年效果可能不明显,三五年后产量至少能增两成。
水燕说得在理,队长们包括大队长谢老刮,没理由反对。
“那就这样,到时你们别忘了。”水燕向他们强调道。
原来就这事,将禾秆扎成把堆成垛,费些工夫而已,再说能多打粮,是好事。队长们释然,应承着起身。谢有富临走抓了一大把花生,水燕端起果篮,示意他们多拿点。谢老刮思忖下抓起烟盒往怀里揣,还朝水燕扬扬手,意思是我就要这,反正你又不抽烟。另外三个队长每人都一手抓瓜子一手抓花生。
望着他们朝屋外走去的背影,水燕心里生出满满的欣慰。别看他们有时不买她的账,一旦思想通了,做起事来从来不打折扣。这些年的工作,全靠他们支持。
接下来,保管好禾秆是个重要问题。不过,这事说起来也非常简单,学山外大田畈上那些大队的做法就行。早禾即将收完,水燕把谢子庚叫到田埂边的一大片禾秆前,如此这般地跟他交代了一番。小伙子开始还神情凝重,但很快就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谢子庚起了个大早,到大队部骑上水燕支书的自行车出村了。这个民兵排长受谢宾的影响,有军人作风。
三天后的傍晚,谢子庚提前两天回来了。在村东田畈边,他拎起一把禾秆,轻飘飘的,干透了,手上禁不住痒痒。恰好,这天是农历十四,明晃晃的月亮挂在半空,田畈上亮亮堂堂,蛐蛐声中和风拂面,比白天凉爽多了。他进村找到女基干民兵班长谢玉秀,叫她把女基干民兵带到村东田畈边帮他搬禾秆。只见他左腿蹲下做圆心,伸直右腿旋转一圈在地上画个圆,然后站在圆心上,让女民兵们将禾秆一把一把扔给他。三天时间学到的本事,他就如此这般地呈现在这个静静的月夜。
第二天一早,出工的社员看见昨夜谢子庚堆的禾秆垛,都奔过去围着绕圈圈观摩,有的还用力推,嘴里不停地呢喃“悄尬”。
六天,全大队二十四个禾秆垛,一水的直径三米高两米的圆柱,上面再压个禾秆叠成一米来高的圆锥形垛顶。这样的禾秆垛,第二年割禾时,垛里的禾秆还很干燥,金黄如新。远远近近矗立在田边的禾秆垛成了东山岭大队的一道风景。
谢子庚堆禾秆垛下了功夫,禾秆层层交替压实,垛中心被掏空了,禾秆垛仍像一间屋,周边的禾秆能撑住垛顶不坍塌,放牛娃们能坐在里面躲雨打扑克。人们没想到,禾秆垛里还会产生爱情。
那时,谢子庚与谢玉秀在悄悄谈对象。冬天里的一个夜晚,村里晒场上放电影,喇叭里的音乐和对话声咿哩哇啦响成一片,两个年轻人一前一后悄没声息地钻进了村边的禾秆垛。可不知咋的,电影刚放完,玉秀爹,就是那个络腮胡子大队长谢老刮,抡着柴杠打到禾秆垛上来了。
人当然没打着,但谢老刮的吆喝声,把电影散场还没回家的人都吸引到禾秆垛这边来看热闹了。眼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松毛火性的谢老刮更来劲了,掏出火柴要烧禾秆垛。
“住手!”水燕一声大喝,镇住了谢老刮。禾秆垛虽然已被掏空,但周边还有上千斤禾秆,加上垛顶,十几担好肥呢。
当着这么多邻里的面,谢老刮咽不下这口气,恼羞成怒地指着谢子庚冲水燕吼:“你是大队支书,你要处理他。”
水燕笑,走到两个年轻人身边,捋着袖子对谢老刮道:“那要看玉秀愿不愿意。”平常她就觉得玉秀和谢子庚关系不一般,年轻人相爱,她乐见其成。而且,玉秀是全大队数一数二的好姑娘,如今不外嫁,说明啥?这样琢磨着,她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哩。
“大家都回吧,回!”水燕摆手对大伙儿说,给谢老刮搭了个台阶。
谢老刮后来还是死要面子,咬牙不同意女儿的亲事。水燕吓唬他:“你要是不同意,我们大队给年轻人办婚礼。”那会儿,村里还有三对青年在恋爱,两对是本村的,在劳动中结下了情缘,另一对女方是玉秀山外的同学,玉秀把她介绍给了村里的小伙。水燕确实想过给他们搞个集体结婚仪式。
谢老刮也不是看不上谢子庚,他只是希望女儿外嫁,眼看事情无法逆转,半推半就不再说什么了。
这年国庆节,水燕自己掏钱杀了一头两百多斤的肥猪,村头高音喇叭里喜庆乐曲从早响到晚,小学操场上锣鼓喧天,大队热热闹闹给四对青年举行了隆重的集体婚礼。这个移风易俗的新鲜事,上了报纸和广播,传遍了全地区。
6
大队改村那年,水燕将支书的担子交给了谢子庚。交班那天,晒场上召开村民大会,谢子庚眼圈发红,当着乡党委书记和全村父老乡亲的面,大声宣布说水燕支书永远是村党支部的顾问。那时的水燕已经有了白发,她脸上笑得灿烂,摆着双手不说话。从那时起,她对村里的事既不顾也不问,过起了逍遥自在的悠闲生活。她有句口头禅:“现在的事让年轻人自己干。”
当然,说悠闲,是因为她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屋,什么时候去看儿孙,每日里从早到晚干些啥,完全由自己决定了,但她并没有真正闲着。她记住了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映山红开了红军就来了的话,在红军山上种满了映山红。清明时节,人们上山祭奠红军英烈,山风呜咽,倾诉着人们对先烈的深切怀念之情,满山红艳艳的映山红花,是当年红军战士年轻生命铸就的不朽之魂。
1999年夏季里的一日,村里鼓乐齐鸣,欢声笑语,迎来了市里授予红军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牌匾,后来,红军山成了人们怀念英雄的红色景点。
也是这年,水燕创办了东山村竹器社,进入新千年后发展成竹业联盟,专搞竹笋加工和竹艺编织,全村村民参与利润分红,她任联盟董事长。那些年,她喜欢穿一件半长黑色皮大衣,加上泼辣果敢的处事习惯,在县里市里,尽显作为农民女企业家的飒爽英姿。有段时间,联盟跌入低谷,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天天往外跑销路,头发熬得全白了。销量稳定后,她拿出资金鼓励和资助村民购买农业机械,合伙帮助年轻劳力外出务工的人家栽禾割谷,其间发生的那些动人故事,将是另一部小说的内容。
重阳节中午,谢子庚请村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吃饭。四对参加集体婚礼的老人,从金婚纪念那年开始轮流做东。饭后,大家坐在谢子庚家屋边的大樟树下歇息讲古。水燕仰靠在竹躺椅上,谢子庚婆娘谢玉秀拿了块薄被单给她盖上,她顺手抓住被单往肩膀上拉了拉,笑着颔首向玉秀致谢。听大家说起红军队伍在村里时的故事,水燕忍不住扬起巴掌把躺椅扶手拍得啪啪响,插嘴道:“有个瘦瘦的小战士,天天帮我家挑水。”马上就有人接上话茬,说那小鬼是二号首长的警卫员,开国少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那小战士美美地称赞了一番。
令人想不到的是,大家散场时唤老支书回去,水燕却纹丝不动。谢子庚撇手让大家走,自己踱到躺椅边俯下身子唤老支书,又推了推她,她的手臂从扶手上滑落下来。不知啥时候,水燕停止了呼吸。
谢玉秀跌倒在地,失声痛哭:“老支书——”
水燕走了,无疾而终,享年105岁。
村委把办事大厅布置成灵堂,水燕安卧在东山岭山上采来的各色鲜花丛中。
除了儿子儿媳和在舰艇上执勤的曾孙女没能赶来,其他孙辈和曾孙、玄孙辈全都到齐。遵照老人的遗嘱,她的骨灰撒在了红军山上的映山红丛中。但村民们把她在竹业联盟办公室用过的水杯和饭盒装进一个竹筒里,在掩埋谢山根的竹烟杆烟荷包旁,也垒起坟包,抬了块大石头搁在坟前,用铁錾子在石头上刻下了“红军嫂嫂谢水燕之墓”九个隶书大字。
东山岭村人用这样的方式,纪念他们曾经的老支书。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