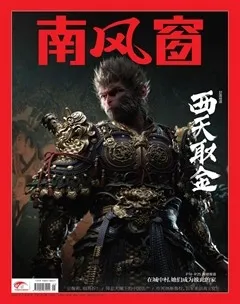当今农村,女性主导了离婚

在河南农村调研时,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陈瑞燕常在村里老农身上感受到对“离婚现象”滔滔不绝的关切。
“离婚”成为继“光棍”之后,农村的又一婚配困境。
不同地区的实地调研发现,尤自2010年起,随着务工群体人数进一步扩大,农村离婚潮尤为显著,群体特点也鲜明:离婚夫妻以青年为主,婚姻持续时间短,且提出离婚的主要是女性。
以甘肃庆阳为例,2018年时,农村女性平均离婚年龄已逐年递减至35.7岁;此前7年间,由女方先提出离婚的占比超八成。
在婚恋自由的现代,人们有自主选择权,但在相对保守的农村社会,是什么推就了离婚潮,又为什么是女性主导了离婚?离婚之后,农村青年男女过得更好了吗?理解村庄的家庭巨变,需要找到其中的风险因素,因为它充分展现了农村夫妻、婆媳、亲子关系如何被微妙地重构,又生出哪些新隐患。
离婚的复杂光谱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师班涛是一名农村家庭社会学研究者,过去10年间,他在全国20个省市100多个村庄驻村调研,也很早感知到农村离婚率显著增长。他在陕西眉县调研发现,一对农村夫妻因为媳妇花钱不够节省引发夫妻争吵,媳妇跑回娘家,坚决要离婚,丈夫公婆反复劝说无效,婆婆于大年三十投水自杀。
极端案例不仅表明农村婚姻关系已不像过去那般稳定,也反映出农村家庭关系的新变化。班涛发现,从离婚发生的原因来看,城郊村以日常生活摩擦型居多,远郊村则以男性经济贫乏型居多。
在城郊村,家务和育儿是日常生活摩擦的主要来源。“我们现在问的年轻女孩,最反感的就是丧偶式育儿。”班涛对南风窗解释。
城郊女性往往更早受现代观念影响,突破了“相夫教子”的传统分工,不愿成为家庭保姆,也要求丈夫参与家务和育儿,生育后有返回职场的计划。而当男性保留着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但又表现出懈怠时,摩擦就此产生。以生育为节点,婚后2~3年是高敏区。
相比之下,数量更多的中西部远郊村,更容易因为“贫贱夫妻”而离婚——首要因素是经济条件,其次才是性格不合、身心缺陷、出轨暴力赌博等恶习。
班涛告诉南风窗,典型如华北农村,因为男女性别比失衡严重,农村女性有更大的择偶空间,对男方经济条件也提高了要求,进城买房几乎成了标配,倘若达不到,就会加剧离婚风险。
而造成农村男性婚后经济贫困的原因之一,是婚前约定的高额彩礼。
班涛对南风窗举例:“我的安徽淮南老家,彩礼就要二三十万,要在县城买房,那至少要五六十万,首付基本上是男方父母出的,还有相应的酒席三金等婚庆开支,至少大几十万是肯定要的……男方家庭很少有因为孩子结婚不负债的,尤其在北方农村,出现了‘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而不再提原来的‘多子多福’。”
在远郊村,本地务工机会少、收入有限,为了还债还贷,男性普遍外出务工。为“挣老婆本”和“减轻债务”的努力,是过去20年间,1.7亿外出农民工大军的家庭动力——但外出务工的一大风险,是大量农村夫妻长期分居,而长期分居是婚姻越轨的温床。
过去,离婚有损声誉,但如今情况不同了。离婚的阻力大大削弱,离婚从家族、村庄的公开事务,变成个人私事。
在河南调研时,陈瑞燕遇到一对父母,女婿2年没进娘家门了,过年时女儿总是一个人回来,他们也不清楚在武汉分居的女儿女婿是否离了婚。班涛在成都农村调研时遇到,因为儿子长期离家,一对父母过了好久才知道自己的儿子离婚了,而询问村民,很多人其实也不清楚村庄内部的离婚状况,那不再是他们的谈资,也缺少信源。
“男方家庭很少有因为孩子结婚不负债的,尤其在北方农村,出现了‘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而不再提原来的‘多子多福’。”
“现在大家没有那么多兴趣去八卦,倾向于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婚姻也从大家庭里分离出来,变成夫妻之间的事情。”陈瑞燕告诉南风窗,“不只是离婚,村庄的公共性都在消解。”
女性掌握离婚主导权
女性先提出离婚,是农村离婚现象的新特征。不仅如此,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师卢飞,从四川5区县763份农村离婚判决书中还发现,在少部分由男性提出的诉讼离婚中,主因是女方长期离家出走。
这打破了传统认知,会是类似“娜拉出走”,彰显女性进步性的解放叙事吗?
“其实它还不太一样”,“至少不是我们常说的主体性觉醒”,班涛和陈瑞燕倾向于否定。陈瑞燕举例,她在河南农村访谈过一位二婚妇女,前夫会体贴人,两人聊得来,她之所以离婚,是觉得前夫不太会挣钱,大手大脚花钱,而女方父母的不看好也起了催化作用——这也呼应了多份调研得出的“经济条件差是离婚首要因素”的结论。再婚之后,她的第二任丈夫是另一种类型,会挣钱,只是心眼实、嘴不甜,两人情感交流少,但她的经济压力和舆论压力变小了。
一份对鲁西北村民的访谈记录,道出了这份舆论压力的意味:“村民笑话不会过日子的人。日子过好了别人看得起,过不好谁都撇嘴。”
曾经,离婚的农村妇女之所以饱受污名化,往往是因为品行有亏或因无法生育而被驱逐,但如今这些污名已淡化。村民普遍重视的是家庭生活安逸的状态和结果,而过程之中的离婚再婚已逐渐为村民所接纳。
“特别是华北农村,因为过去‘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它先天性地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而后天又有大量适婚女性外出务工,以致本地适婚女性少,优势地位由此凸显,还出现一类情况:女方还没离婚,媒人已踏上门给介绍对象了。二婚时,男方同样要支付高额彩礼,和初婚一样操办。”班涛说。
另一种失衡
去年的一次调研中,陈瑞燕发现:农村男光棍迎来了“新春天”,他们的媳妇多是离了婚的女性。而在村民的评价里,再婚的妇女过得一般都比初婚好。
然而离婚的农村男性,再婚非常困难,因为在初婚耗尽了财力。反倒是原先的光棍经过了一轮财富积累,更有比较优势。“离婚之后的男性,在农村里的地位比光棍更低。”陈瑞燕说。
农村夫妻离异后各自再婚成本“男高女低”、生活处境“女向上男向下”的鲜明对比,不只是强化了农村女性离婚时的主导权,也增强了她们在家庭生活当中的话语权和优势地位。
班涛说,在农村,那部分表现为,她们不用工作或下地劳作,主要角色是带孩子,家务由婆婆承担。而离婚之后,女方大多放弃对子女的抚养权,形成了“抛夫弃子”的局面。
李永萍把当中的女性婚姻主导权称为“无义务的权利”,认为它突破了“家庭政治”的框架,导致了家庭生活伦理内容的空洞化。
“去问农村的老人,他们都会跟你讲,现在娶了个儿媳妇,等于娶了一个菩萨,都要给她供起来,否则儿媳妇一不高兴闹离婚的话,儿子就会面临重返光棍的风险。”班涛说。
这意味着农村婆媳关系正在重构,而婆婆“刁蛮耍横”的形象正成为过去时,进入“婆婆讨好儿媳”的局面。
陈瑞燕见过,婆婆因为儿媳的衣服材质娇贵不能放洗衣机而单独代为手洗,听到儿媳妇回来了,赶忙放下麻将回去做饭,眼神举止里唯恐怠慢。
典型的是这样一位婆婆,她早年丧偶,独自抚养儿女长大成家,如今儿子外出务工,她和儿媳守着五六岁大的孙子在村子里生活。家务农活和带孙子基本是婆婆在做,儿媳没有工作,婆婆也不想她出去打工,以免她“心思变坏,跟别人跑了”。
陈瑞燕将这种表面和谐但暗藏异样感的状态形容为“圈养”,儿子外出务工时,婆婆从旁帮助儿子降低离婚的风险,成为“讨好型守卫者”;而在外务工的丈夫,往往采取周期性在家、给妻子买衣服礼物、多做家务说好话,来策略性地维系婚姻,逆转了过去农村妇女常常得在丈夫和公婆面前忍气吞声的局面。
“它没有实现理想意义上的关系平等,夫妻、婆媳之间的关系,是由以前的一种失衡状态,现在到了另外一种失衡状态。”陈瑞燕说。
在这种失衡状态里,“代际挤压”表现为,上对父辈、公婆,是更高强度地务工务农,提供支持,挤压他们本就不多的养老资源;下对子辈,是农村单亲儿童得不到妥善的照顾和教育,身心健康受侵害。
山东师范大学老师吴存玉曾在2020年记录:一位因妻子离家出走而被抛弃的丈夫在外打工,3个孩子由奶奶和大伯照顾,兄妹早上经常饿着肚子上学,放学后还要帮大伯干活,暑假去父亲打工的地方团聚,却是一起帮忙做工。
“婚姻市场”的悖论
在采访和学者研究中,频频出现“婚姻市场”的描述字眼,凸显了农村离婚现象中的悖论。
家务农活和带孙子基本是婆婆在做,儿媳没有工作,婆婆也不想她出去打工,以免她“心思变坏,跟别人跑了”。
一个案例是:陕西丰南村一位28岁妇女,早年被拐卖到四川山区,被迫成婚生女。2014年,她逃回娘家。娘家父母很快给她安排相亲,3个对象都未婚。其中2人愿出10万元彩礼迎娶她,最后姑娘相中了积蓄有15万多的第三位小伙子,亲事以8.6万元彩礼成交。
陈瑞燕觉得,如果说过去农村女性被异化为“生育工具”,如今农村男性也被异化为“牛马”,其实是对人更深层次的异化和双向物化。
资源匮乏的光棍和重返光棍,要承受村庄的舆论压力而“不配成家”,比如一个村支书就在广播大喇叭里批评那些不愿外出务工的光棍。
班涛认为,虽然成为光棍与重返光棍的男性还有大家庭做支撑,但终究自己的核心小家庭才是个体意义归属的来源。当失去组建家庭的信心时,他们也会失去向上奋斗的动力。“他们随波逐流,根本原因是他们已然被‘家’甩出成为原子化的个体。”班涛说。
另一边,边远地区农村女性的确有机会利用婚姻主导权“嫁得更好”,但湖南师范大学齐薇薇的研究显示出她们在当前“婚姻市场”中的上限。
她调研的是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离婚现象,地点在广东顺德一个工业化的富裕村庄,她称之为“全国农村的婚姻高地”。因为产业园名企集聚、就业机会多,外地女性大量流入,使得该地区婚姻市场上的适婚女性要多于本地适婚男性,女性又不占优势了。
这表现为,她们要不到高额彩礼,仅保持着礼仪礼节属性。尤其本地女性一般不会远嫁外地,择偶空间进一步缩小,反而加强了本地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男方家庭也更有底气拒绝或无视女方的诉求。比如一对恋爱多年的男女谈婚论嫁时,因为外地女孩的父母要40万元彩礼拒不妥协,“最后黄了”。
现代语境当中,愈发成为“财富”象征而非“礼节”的高额彩礼像个怪胎异类;但也有很多人视之为物质保障、履行承诺的底气、婚姻稳定的基石。
“确实复杂,也比较诡异。”班涛说,他在浙江农村调研时就发现,男方也有给高额彩礼的,而女方也会给很高陪嫁,当中有父母为儿女争婚后地位的考虑。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好像陷入了新的困境。在农村尚未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地方,农民在婚姻家庭当中已饱尝失衡现代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