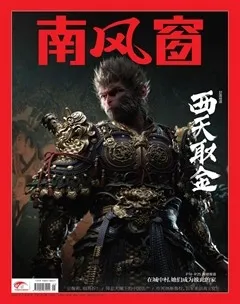降息大潮下的中国资产

美国当地时间9月18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4.75%至5%,即降息50个基点(一基点为万分之一)。
首先,这是美联储在2022年加息以来的首次降息,信号意义极其明显。再者,也是近年来单次降息幅度最大的一次。过去,美联储单次降息幅度一般为25个基点,而现在是过去的两倍,可见提振经济愿望之迫切。
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也宣布,将降低中央银行政策利率,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0.2个百分点,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和存款利率同步下行。
两大经济体先后降息,且幅度不低,对全球经济必将带来重大影响。在美联储宣布降息之前,全球市场对此早有预期,为提振经济,主要央行如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早已在9月之前降息。在美联储本次降息之后,全球新的一轮降息大潮很可能会到来。
在市场资金更加充裕的背景之下,全球主要股市在美联储降息后都出现了上涨。其中,被投资者关注已久的A股和港股,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扬。此外,作为中国人资产配置最大宗的房地产市场,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资产价格的波动固然是货币现象,并受情绪作用,因此难以预测,但资产内在价值或者它的真实价值,则是有迹可循的,它是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从后面一种视角来理解中国资产,更有意义。
全球“闸门”
如果以美联储本次降息为时间基点,很容易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西方经济体的降息,多半在这个时间点前的半年内;非西方经济体则主要在此之后宣布降息,并且在短时间内迅速下调利率。不同经济体在降息时间上的“非均衡性”,并非偶然,而是蕴含着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密码。
西方经济体的本轮降息,始于瑞典。5月,北欧第一经济强国瑞典降息25个基点。之后,美国之外的另一大经济体欧元区宣布降息,6月,欧洲央行将三大利率下调25个基点。7月,加拿大和英国先后宣布降息25个基点。就在美联储宣布降息前的9月12日,欧洲央行再次宣布降息25个基点。
美联储降息之后,非西方经济体的降息潮到来。降息最快的是沙特,在美联储降息后一天之内即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降息时间和幅度,基本上都和美联储保持一致。此外,阿联酋、卡塔尔等也迅速降息。中国香港也紧跟,在美联储降息之后不到一天,香港金管局迅速将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
为何西方经济体降息大都在美联储之前,难道它们故意保持“高度一致”?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央行之间存在着通畅的信息沟通机制,美联储提前释放了信号,大家都坚信美联储将在9月降息。
显然,这种观点无法成立。美联储很难真的“提前告知”任何人自己会在某个时点降息,否则很容易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内幕交易”,并被索罗斯这一类的对冲基金经理所利用。
不同经济体在降息时间上的“非均衡性”,并非偶然,而是蕴含着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密码。
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提前降息,主要原因是经济实在太疲软。比如,2024年上半年,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的GDP为21380.9亿欧元,剔除价格因素之后,同比下降了0.2%。其他经济体,增长也远远没有达到预期,因此降息成为了提振经济的必选项。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经济体有着独立的货币政策,货币汇率并非绑定美元,政策操作自由。
另外一些经济体则没有那么自由。中东各个货币当局宣布降息的时间和幅度,和美联储几乎保持同步,并非如同一些观点所说的那样是因为缺少“经济主权”,而是在于它们实行多年的汇率制度。它们本地货币和美元保持着相对固定的汇率,因此,为保持外汇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必须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保持同步。中国香港的货币政策也是这个逻辑。
中国内地的货币政策则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在美联储本轮降息之前,中国已多次降息,对推动经济快速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从2022年开始,中国就进入了降息通道。当年,中国进行了三次降息和两次降准,为市场释放了宝贵的流动性。此后,降息或降准一直都在持续,并且频率不低。
同一时期的美国,则进入了加息通道。2022年3月,为应对通胀问题,美联储突然加息,到2024年本轮降息之前,美联储加息竟然达到了11次。
但无论本币多么强大,对任何经济体来说,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都不能视而不见。美元的加息和降息,是其他经济体制定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不能忽略的参考变量之一。在美联储降息大约一周后,人民银行宣布降息,既说明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自主性,也说明了货币政策出台的及时性和前瞻性。
从2024年上半年启动,以9月份美联储降息为高潮的全球性降息,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一个逻辑链条开始明晰起来:去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变动,所带来的成本高涨是不可逆的,西方的通胀正成为一种经济顽疾,让人们在情绪上已对通胀“脱敏”,政治家和货币政策制定者治理通胀的压力变小。这意味着发达市场的央行,已经突破某种约束。
于是,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为工具,刺激经济复苏,成为了优先级。换句话说,单纯地治理通胀,很难治好;相反,让人们忍受短期通胀,通过刺激推动复苏,从根本上解决通胀才是更可行的路。某种意义上讲,这成为了西方央行之间的一种共识。
当货币的闸门打开,全球资产的货币之锚将发生改变。中国也必然受到影响。
中国资产
在美联储宣布降息之后, A股很快出现上涨。9月24日上午,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降息,A股再次上涨。尽管涨幅不大,但截至当日上午收盘,上证指数回到了2800点。
于是,在2024年国庆节前,面临裁员压力,并且沉寂已久的一些券商研究所开始活跃起来,陆续发布了各种研究报告,对资本市场的看法颇为积极。一种典型的观点是,本轮上涨只是一种试探,未来或有更多提振措施出台。除了领涨的蓝筹和龙头,未来的上涨板块将更有“普惠性”。
券商研究所在大多数时间都是“看多”的。券商研究员的至高荣誉之一是分析师排行榜,这关乎他们的职业生涯,投票主要群体则是基金经理。而各大基金又是以上这些股票的主要持有者,因此,这一链条决定了券商研究报告只能作为一种衡量市场情绪的参考,并不能成为指导投资的意见书。
当然,过去的价格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资产的价值,只要底层资产足够优质,价值的均值回归只是时间问题。一些外资对中国资本市场依然充满信心。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共有702家上市公司前10大流通股东中出现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外资热情依旧。
楼市显然比股市更加具有“系统重要性”。就在9月24日宣布降息的同时,央行还宣布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和统一房贷最低首付比例,引导商业银行将存量房贷利率降至新发放房贷利率附近,预计平均降幅在0.5个百分点左右。同时,统一首套房和二套房最低首付比例,将全国二套房最低首付比例由25%下调至15%。
降低存量房利率对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意义重大,是真正的“让利于民”,指向了提振消费。而降低首付比例,则指向了楼市的尽快复苏。目前,政策效果还有待观察。
提振楼市并非朝夕之功,它背后还涉及人们对房地产这种特殊资产类别的整体信心。中国投资者对物业资产的笃定始于1998年的房改,之后不断发酵和强化,并在2016年达到顶峰。现在,又来到一个十字路口。
折现思维包含了经济领域很多重要的改革命题。从这种思维来审视中国资产的价格,远比过度关注货币供应量的波动,更有价值。
实际上,在讨论全球降息大潮与中国资产关系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陷入两大陷阱,一是狭隘化,二是短期化。首先,将中国资产的范围局限在股市和楼市,是一种狭隘化。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真正竞争力是强大的制造业供应链,而产业链条上优质公司的股权,才是最核心的中国资产。
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418.6亿元,占实际使用外资比重达28.4%,同比提高2.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637.5亿元,占实际使用外资的12.8%,同比提高2.4个百分点。外资很清楚,中国经济的核心资产在哪里。
另一个问题是,审视中国资产的价值还应该有更宽广、更长期的视野。目前,全球投资界最流行的估值方式依然是现金流折现法,即一切资产的价格都是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分子是未来的现金流,分母是折现率,得数就是资产现时的价格。在巴菲特看来,这不只是一种估值手法,更是一种投资的思维框架。
在这个框架之下,如果要提高一个经济体的资产价格,只有两种方式:一是让资产在未来创造更多的现金流。比如,让房子的租售比变得更合理,让物业租金增长;让股票分红翻倍,让股市“铁公鸡”也能分红;或者让公司通过技术创新或经营效率提升,创造更多的自由现金流。显然,这些提升资产未来现金流的办法,要么指向了宏观层面的改革,要么指向了微观市场主体的创新,都是我们似曾相识的事物。
另一种方式是降低折现率,折现率的本质是风险,如果风险越高,那么资产价格也就越低。在所有的风险之中,政策的稳定性是极其重要的因子。
在估值的时候,波动即是风险,当政策波动过大,风险随即升高,折现率增大。最后,现金流折现之后的现值降低,资产也就不值钱。全球投资者对一些欠发达经济体,如拉美、东南亚的资产进行估值时,就会增加政策不稳定带来的风险补偿,从而拉低其资产价格。相反,对于治理良好、政策稳定的经济体,则赋予较低的折现率,高估其资产价格。
显然,折现思维包含了经济领域很多重要的改革命题。从这种思维来审视中国资产的价格,远比过度关注货币供应量的波动,更有价值。
目前,中国经济各领域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政策的可预见性和及时性也有目共睹。中国资产的价值,不应该被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