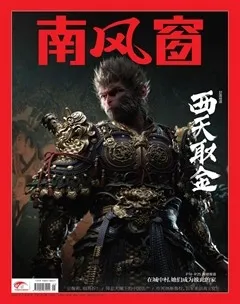佛也被打倒之后

在所有的西游记改编作品里,2000年的电视剧《西游记后传》的故事绝对是最好的之一。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它时的震惊。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祖竟不敌魔头无天,从西天到天庭都被反派攻占;佛道两界包括玉帝在内的众神,全部被打入冥界;如来圆寂转世,入凡界在几段情缘间纠缠……这种想象力不仅在当时堪称大胆颠覆,在那之后直至今天,也少见有如此深度和批判力度的改编。
原著《西游记》,塑造的神魔世界本已相当开阔,其众多隐喻对压抑虚伪的秩序的批判,对悟空这样一个极富个性的可爱形象的塑造,使它的故事,蕴含着意犹未尽的创作空间。《西游记后传》承接原版西游记的结尾,讲述唐僧师徒五人取得真经、归入佛门之后所发生的事,在原有的世界观基础上,写出了一段全新故事。相较于原作,它的批判,在保持水准的同时更直接,更露骨。所以它的生命力也一直持续,在近几年愈益旺盛。
反派无天从得势到失败,如来的退却和复归,悟空师徒在历经更大劫难后的再一次加官晋爵,绝不只是一个可喜可贺、皆大欢喜的故事,而是充满深意,令人唏嘘。
反叛者的诞生
同样是体制的反叛者,无天和孙悟空在许多方面很像,亦正亦邪,不愿服从。但有一点,使他们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
孙悟空虽然有“玉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桀骜不驯,但几乎也只是随着本性本心和一己之欲,因而对天庭不满的他在前两次都被太白金星略施小计就招安,第一次做了弼马温,第二次做了齐天大圣。
当他发现自己其实还是体制的边缘者,吃席赴宴都轮不到自己时,才继续搅闹。而后来他被降服,是因为法力不如如来,被压在五指山下,又被套上了紧箍咒。
孙悟空这样的反叛者,尽管厉害,却是可以用名、利、力制服的,所以能被体制收编。只要给够了名誉和空间,孙悟空就不再是反贼,顶多是刺儿头,因为他要的,只是自己一个人的自在自由,不寻求体制的颠覆和改变。
然而《西游记后传》的反派无天,不是一个像孙悟空一样跟随私欲的享乐主义者,也不是仅仅觊觎权力的野心家;相反,他曾是体制内的高僧,有身份、有能力、有想法,也很忠诚。他曾真心相信世尊所说的“佛门无不可渡化之人”“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身体只是一副皮囊,重要的是精神,只要精神到了,就一定能光大佛门”。
秉持着这种精神,他领受世尊之命,冒着极大危险,在南部信奉阿婆门教的领地传教。在当地教主给他定下的三天限期内,他成功渡化了当地三恶。他让小偷阿溜看到了地狱的可怕,从此不敢再偷窃;他以自残自伤的牺牲勇气,得到了土匪阿刀的折服皈依;他也渡化了自甘沉沦为妓的女子阿羞,不惜破了佛门对性的禁忌。
但让他意外的是,他自以为完成了任务,光大了佛门,却因为渡化阿羞,被世尊斥责为有辱佛门。与之对比,为佛门不耻的风尘女子阿羞却宁愿为他而死。孰为光荣孰为羞耻,孰为正孰为邪,孰为善孰为恶?原本坚固的信仰在这一刻裂开了,高高在上的领袖,大谈正义,高喊口号,但做起事来,言行不一,伪善懦弱——深刻的矛盾和强烈的怀疑在他内心滋长,再也不能遏制。他不再是高僧紧那罗,而成为了魔罗和无天。
自此,“虚伪”,成为无天对佛门领袖的持续批评;对虚伪的拆穿,也凝结起他要反抗佛门的执念。
相比于孙悟空,无天无疑是更具破坏性的反叛者。他不止有武力,更重要的是,他从内部解构了组织的信念,聚集起一帮妖魔鬼怪,共同合成一股组织化的力量。
相比于孙悟空,无天无疑是更具破坏性的反叛者。他不止有武力,更重要的是,他从内部解构了组织的信念,聚集起一帮妖魔鬼怪,那些在原有体制下被边缘化的、压制的、打到反面的失意者、无权者、不满者,共同合成一股组织化的力量。
他们在心理上完成了对体制的祛魅,所以自视正当,理直气壮。无天第一次见到如来时,就暴怒地说“我就是化作灰烬,也不会像你那样虚伪”;在玉帝不屑地蔑称无天为妖怪时,无天反唇相讥:“在你眼中我是妖怪,可在我眼中你又是什么?”在燃灯古佛面训无天“邪不胜正”时,他反问:“什么是邪,什么是正?”
在无天眼里,“如来才是邪辈,说什么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禁食禁欲,人如果连自我都丧失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他欣赏唐僧的诚信,也极其尊重悟空,他只对唐僧和悟空说交心交底的话,并希望求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对孙悟空,他多次自陈“我不是邪,也不是什么妖怪,只是看不惯如来那套假慈悲的虚伪”。他也向唐僧讲述了自己的故事,问对方:“如果你遇到和我一样的事,你会怎样?”
唐僧诚实相告:“我想我会和你一样。”这番话给了无天极大的安慰,因为他说出了,无天的出现,是体制而非个人邪恶造就。一个原本勤勤恳恳的良善之人,为什么变成了体制的反对者?没有成为无天,只不过是一种幸运,而不代表自己的高尚。也是在无天被理解的那一刻,第一次,他长久以来被压制的善人格出现了。
毫无疑问,无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只想用自己的能力改变佛界”。而在注定失败、毁灭前的最后一刻,他仍在斥责佛道界的诸位天神:“你们这些个神们,食人间烟火,却高高在上,不为世事,不明情理,竟都是一些无能之辈。”
这样的无天,尽管失败,但在城府极深的如来面前,显得太真诚了。
如来的权衡
无天和如来的法力是一样的。这件事,无天在后来欲杀死转世灵童却不得时才知道。
无天之所以有自己比如来法力更高强的错觉,是因为在他率领部众攻打到西天时,如来没有抵抗,并叫众人不要抵抗。
但为什么如来不抵抗呢?
公开的理由是,这是天意,是必须经历的劫数。不过比起无天,如来明显更懂得权衡。
在原著《西游记》里,泾河龙王因为私自更改降雨的时辰和点数,被玉帝责令处斩。但在《西游记后传》中,这竟然是一大冤案。
起因是,西海龙王三太子小白龙因为得罪武德星君之子,而被武德星君追上家门。西海龙王敖钦因不喜欢这个儿子而对他无半点保护,小白龙在失望下逃亡至姑父泾河龙王处。武德星君又赶往泾河,却在那里没有要到小白龙而积怨于心。后来发生的私自更改降雨点数事件,本是渭河龙王所为,但武德星君趁机嫁祸于泾河龙王。玉帝失察,轻率决策,导致泾河龙王无辜被斩,罪魁祸首逍遥法外。
如此一件大冤案,由小白龙告诉了孙悟空。此时已被封“斗战胜佛”的悟空,加入了佛门,领导从玉帝变成了如来。悟空为小白龙不平,向如来陈明冤情,希望新领导主持公道。但如来犹豫不决,最关切的不是去指出是非曲直,而是责怪悟空刚加入佛门就如此冒失顶撞,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并以此为理由顺手收走了他的武器金箍棒,使他作乱的能力大大降低。
“做佛做得连金箍棒都收了。”悟空很是无奈,本是自己为他人伸冤,却变成了一众菩萨反为自己求情。
在悟空几次三番地逼迫,唐僧、观音一齐恳请,甚至如来的老师燃灯古佛也下场求情后,如来说出了他不肯出手帮忙的实情:“我岂不知公理之重,然诛杀泾河龙王,是玉帝所为,我怎好当面揭穿?天界与佛界一向友善和睦,我不能为此小事失彼大计。”
一条无辜生命被冤杀,比起玉帝的面子和双方的关系,在如来眼里不过是“小事”。对于无天这样看不惯如来的人来说,这不是坐实了伪善又是什么?
天庭领袖玉帝也懂权衡之术。由于如来不愿帮忙,悟空转而亲自去天庭要求玉帝重查此案。玉帝和如来一样,把注意力放在了悟空又来多管闲事、质疑自己的权威上,与之爆发冲突。事情闹大后,如来闻风赶来,顺势请求玉帝查明真相。此时的玉帝,见状也识趣地给足如来面子,“既然佛祖说了我便看一看”,要求重查真相,这才还了泾河龙王的清白。
可见,冤案翻案之难,不在冤案本身是否难查,而在于它在人情世故间是否重要,牵连多广,在政治上重要性几何。如来和玉帝这两个权场老手,在位年深日久,都养成了相似的脾性,无法容忍下属对自己的质疑,无意承认错误,而更在意维持既有格局和秩序的稳定。只有外部力量干涉,才能促使他们改变。
如来和玉帝这两个权场老手,在位年深日久,都养成了相似的脾性,无法容忍下属对自己的质疑,无意承认错误,而更在意维持既有格局和秩序的稳定。只有外部力量干涉,才能促使他们改变。
统治的艺术,他们驾轻就熟,对于处理体制内的异议和刺儿头,也多的是办法。泾河龙王翻案后,如来棋高一着,并不责怪悟空,反而褒奖了他,宣布“三界之内只有一个人可以不参佛不朝觐,就是孙悟空,今后三界安危就交给悟空”。如此,使得悟空这号关键人物,在后来无天的叛乱行动中,继续稳定地站在西天这一边。
而在如来暂时退却的转世过程结束,回归佛祖之位后,局面对他一片大好。最大的威胁无天被除掉了,本能形成牵制的前任领导燃灯古佛圆寂了,原来体制内不忠诚的人阿难、迦叶等被筛出了,留下的都是经过了考验对组织忠诚的一批人。而如来也获得了前任16个万佛之祖的能力,自己转世下凡一遭,没有受到半点伤害,倒是处处留情,在两个女人三段情缘之间,感受了一次身为佛祖永远不会拥有的体验。
哪怕不以阴谋论来解释,说如来是最大的操盘手,在经历了这一番被坚称是天意而不抵抗的劫数后,如来也无疑是最大的获益者。而无天留下的问题,仍然在风中飘荡。
理想不必幻灭
从管理团队的角度,无天算得上一个好领导。
比起玉帝天威难测般的暴虐——失手打碎琉璃盏的卷帘大将被贬下凡,要承受每七日万剑穿心的痛苦,降错雨的龙王,求告无门,被斩立决——无天对下属相当包容,也常加鼓励。
六耳猕猴被无天所救成为他的部下,在与孙悟空的斗争中数次失败,无天并不责怪,而是屡次表达理解,安慰说“也不能全怪你”“是孙悟空太厉害了”;在团队取得一点点成绩后,将功劳都归于下属,自己决不贪功,称是“有赖于大家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在哪怕胜算几无的情况下,他也仍在鼓舞部下,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
但从统治来说,他很失败。他所依靠的部众,聪明有余价值观全无,他从如来体制收编的人,都是墙头草般的投机主义者,连他自己都看不起,而他真正欣赏的唐僧、孙悟空等人,却无法被他收编。
他也完全没有去建立一套新的统治秩序,基层建设全是空白。他知道自己依靠的妖魔鬼怪不足以服众,就把妖魔鬼怪都变成原来百官的样子,一切照旧,要“别人也看不出”,维持旧有的统治秩序,不做改变。
他没有建立新制,也没有提出愿景。他的行为动机,更多的是来自愤怒和复仇。当他的破坏实现,他也开始迷失,陷入自我怀疑。而他的迷失,促成了他的失败。
无天的核心问题是,他认识到,佛不能代表正义和良善。这没有错,但佛不是善,他自己又是善吗?当他依靠流氓和暴力来建立统治的时候,他显然也不代表正义和良善了。
这样的矛盾,既孕育了无天,也导致了他的失败。在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中,他只能通过自我压制,将自己的善念关到黑暗之渊来暂时制止自我怀疑,可是一旦不能断定自己做的是否正确,出现意识的裂隙,善念就会出现,扰乱他的行动。
善念向无天揭示了他自己所不愿面对的:“其实你很害怕。”佛祖纵然不对,但如果自己也是错的呢?
害怕的无天,压制了善念的无天,只有破坏,而难感召和建设,就像孙悟空对无天说的:“你心中失去了佛,你没有热情,没有感情,没有激情,你冷酷得像一块冰,你只能将周围的人冻住,不能去温暖他们,所以你不会成功。”
这成为悟空和无天最后的分叉口。无天曾问悟空:“佛在你心中是什么?”悟空答:“是善。”在悟空心中,佛是善,所以佛祖做错后,孙悟空的做法是力劝佛祖、解决问题,而不违背自己心中的善念。
而在无天那里,善是佛;世尊和佛祖错了,对他来说,佛就崩塌了,而善也岌岌可危了。

无天直至失败,也没有明白,佛不等同于某个人,更不等同于佛界体制。佛界与天界,虽然有等级秩序,有不公不平,有冤案错案,但是基本的价值观并未崩坏,道之“天”,佛之“善”,还能规范并指引体制内的主流。
无天直至失败,也没有明白,佛不等同于某个人,更不等同于佛界体制。佛界与天界,虽然有等级秩序,有不公不平,有冤案错案,但是基本的价值观并未崩坏,道之“天”,佛之“善”,还能规范并指引体制内的主流。是这样一种对天道和善念的信守,而不是对具体的佛祖或玉帝的拥护,使得一个体系维持,并不断改进,它并不随着某一个官员或领导者的败坏而败坏。
真正的危险在于,体制内的大多数人,不再有共同的价值信念,只追逐利,臣服于力,那时候,才是反叛力量能够推倒将倾之大厦的时机。可是无天起事时,无论天界还是佛界,一帮相信正义与良善的人没有失望四散,统治秩序仍然稳固。
所以无天的幻灭,只是他自己的幻灭,无天的革命,也只是他自己的革命,而不是所有人的革命。那些依附于他的、效忠于他的,并没有他的思考能力,也不共享他的信念,更不明白他的动机,他们只是一帮被体制抛弃和压制的人。但是弱势者和边缘者身份,本身并不使他们的行为正义,也不构成他们的道德优势,所以他们只是靠纯粹的武力,去夺权、去争斗,而没有任何理想。
当无天的手下屠杀整个镇的平民而无动于衷的时候,他们就更加无法争取到自己所需要的力量,也离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世界越来越远了。
反观无天的对手们,却多怀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唐僧自愿进入轮回之道,放弃已成佛的身份,“何惧重新做回凡人”;一向懒惰怕事的猪八戒,也独闯险境,救下悟空;悟空在危急关头,没有任何犹豫地舍身圆寂,化为舍利。
能让他们这样做的,难道是一个如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