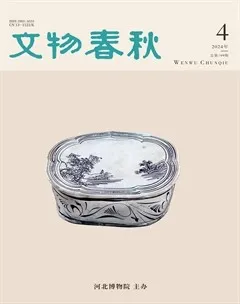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布里村围沟墓发掘简报
【关键词】围沟墓;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布里村;秦代;西汉早期
【摘要】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KGTC-2019-036地块(原布里村)范围内发掘了3条围墓沟及沟内5座墓葬。墓葬及围墓沟年代为秦统一时期至西汉早期,围墓沟经历两次改扩建,体现了该墓地的家族性与围墓沟的沿用过程,为研究秦汉时期围沟墓提供了新的资料。
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广仁大街以北、底张大街以南、崇文路以西、立政路以东的KGTC-2019-036地块(原布里村)范围内发掘了3条围墓沟及沟内5座墓葬。围墓沟和墓葬位于该地块中部偏西(图一)。围墓沟编号为G5、G6、G7,墓葬编号为M28、M29、M30、M33、M36。经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与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共同整理,相关发掘资料公布如下。

本次发掘所在区域的地层堆积可分为三层:第①层,耕土层,厚约0.2米,浅灰色,土质较硬,含大量植物根系及建筑垃圾;第②层,扰土层,厚约0.3米,深灰色,土质较疏松;第③层,垆土层,厚约0.3米,黑褐色,土质坚硬,含白色钙化丝等。③层下即为生土。围墓沟与墓葬均开口于②层下。
一、围墓沟
根据土色深浅的差异,围墓沟分为G5、G6、G7三沟。其中G5为闭合沟;G6南、北沟分别沿G5南、北沟向西延伸,其西、南、北沟与G5东沟形成闭合,围合范围平面呈长方形;G7有东、北、西三沟,东沟在G5东沟的基础上向北延伸,与G7北沟相接,因无南沟,故G7未闭合(图二)。各围墓沟具体情况如下。
G5由东、西、南、北四条沟组成(图三),平面近方形。各沟截面均呈梯形,口大底小,斜壁,底部平坦。东沟长约20米,口宽2.2米,底宽0.5米,深1.8米;西沟长约19.8米,口宽2.3米,底宽0.65米,深1.6米;北沟长19.5米,口宽2.25米,底宽0.7米,深1.6米;南沟长21.5米,口宽1.8米,底宽0.7米,深1.6米。沟内填土均为浅灰褐色,土质疏松。西沟填土被M29、M33的墓道及M36打破,东沟填土被M28墓道东端打破。
G6位于G5西侧,平面呈“匚”字形,仅有南、北和西沟三部分,沟内形制与G5相同。北沟、南沟分别沿G5北沟、南沟向西延伸,北沟长3.7米,南沟长4米。北沟和南沟口宽、底宽及深度分别与G5北沟、南沟相同。西沟长20米,口宽1.3米,底宽0.65米,深1.6米。沟内填土均为浅褐色,土质疏松,内含瓦片、陶片、礓石块等。

G7平面近“厂”字形,仅有东、北和西沟三部分。东沟沿G5东沟向北延伸,长2.5米,延伸部分与G5东沟口宽、底宽及深度相同。北沟长25.8米,口宽1.4米,底宽0.5米,深1.6米;西沟长25.3米,口宽1.35米,底宽0.5米,深1.6米(图四)。填土为深褐色,土质疏松,内含瓦片、陶片、礓石块等。
二、M28
(一)墓葬形制
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多室土洞墓,方向80°。位于G5围合范围内中部偏北,南距M30约2米,南距M33约5.4米。墓葬全长17米,由墓道、过洞、侧室、天井、主墓室组成(图五)。墓道东端打破G5东沟填土,侧室和主墓室分别位于G5北沟、西沟之下。
墓道位于最东端。土圹斜坡底,坡度33°。平面为长方形,口底同大,壁面竖直规整。墓道开口长8米,斜坡底长9.6米,宽 0.94米,深5.28米。
过洞位于墓道与天井之间。根据底部形态不同可分两段。东段为平底,长1.8米,宽0.94~1.04米,顶部大部已坍塌,东部残高1.46米;西段为斜坡底,坡度27°,底长3.2米,宽1.04米,顶高约1.38米。东段南壁有一壁龛状结构,底部与过洞齐平。平面略呈半圆形,宽0.9米,进深0.6米,高1.6米。北壁有通道直通侧室。
侧室位于过洞东段北侧,与过洞之间有甬道相接。甬道平面近似喇叭状,口宽1.8米,最窄处1.08米,进深2.1米,高1.6~1.8米。甬道北端东壁有一长方形壁龛,底部与甬道齐平,宽0.5米,进深0.4米,高0.6米。甬道与侧室间有封门槽,西侧封门槽进深0.21米,东侧封门槽进深0.2米,槽宽均为0.1米。侧室平面近长方形,长3米,宽1.1米,高1.8米,侧室内未见人骨及棺痕。

天井位于过洞与主墓室之间。平面呈长方形,口大底小。上口南北长2.2米,东西宽1.2米,底南北长2米,东西宽1.1米,深6.8米。
主墓室位于天井西侧。平面呈长方形,平顶。长3.2米,宽1.34米,高1.4米。底部沿南、北两壁见有深褐色木椁痕迹,厚约0.1米,残长约2.67米。未见人骨,葬式不详。
墓葬中共出土随葬器物14件(组),分为陶器、铜器、铁器及钱币等。除铜镦出土于主墓室填土、陶缶出土于侧室甬道的壁龛内,其余器物均出土于侧室(图六)。
(二)出土器物
1.陶器5件,皆为泥质灰陶,除陶钫外主体均为轮制,部分构件模制粘接。
鼎1件。M28∶8,鼎盖弧形,顶部较平,上有三乳钉状钮。鼎身子口内敛,弧腹,圜底,上腹近口处附对称的外撇双耳,下腹近底处附三蹄形足,足外撇。腹部饰两周红彩和一周凹弦纹。盖口径16.6厘米;鼎身口径14.4厘米,腹径17.6厘米;通高13.4厘米(图七,1;图一三,1)。
盒2件。形制相似,大小相近。覆碗形盖,圈足形捉手,盖顶略鼓。盒身子口内敛,深弧腹,下腹斜收,平底微内凹。外壁轮制与修胎痕迹明显。M28∶9,盖口径16.7厘米,顶径8.2厘米;盒身口径15厘米,腹径18厘米,底径8.5厘米;通高13.5厘米(图七,4)。M28∶13,盖口径16.9厘米,顶径7.8厘米;盒身口径15厘米,腹径17.8厘米,底径8厘米;通高13.7厘米(图七,3)。

钫1件。M28∶1,覆斗形盖,钫身方口略敞,束颈,鼓腹,高圈足。腹部原应有铺首衔环,现仅存衔环痕迹。方形盖顶一侧边缘饰有红彩,器身腹部原绘有红、白云气纹,现已模糊不清。盖边长11.46厘米;钫身口径11厘米,腹径18.6厘米,底径10.6厘米;通高36.7厘米(图七,5)。

缶1件。M28∶10,敞口,宽平沿外斜,尖唇,短束颈,斜肩略鼓,折腹,下腹斜收,平底。肩部密布轮制痕迹。口径8.8厘米,腹径38.6厘米,底径17.2厘米,通高33.6厘米(图七,2)。
2.铜器4件,包括铜镜、铜盆、铜镦等。


镜2件。M28∶2,弦纹镜,三弦桥形钮,座外有三周凹面纹带,平缘。直径23厘米,钮高0.6厘米(图八,1)。M28∶3,蟠螭纹镜,三弦桥形钮,伏螭钮座。钮座外有三周双弦纹带将镜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两周双弦纹带之间有一周11字篆书铭文带,铭为“大乐贵富千秋万岁宜酒食”,“大”字和“食”字之间有一鱼纹;外区饰四组三叠式花瓣纹,每两组之间各有一组蟠螭纹,蟠螭头小、圆眼、尖嘴,肢爪伸展,身躯盘曲回绕,曲线顺畅自然。最外近镜缘处为一周高卷边双弦纹带。直径14.2厘米tfN8cPi84UZMrKvsa69NtA==(图八,2)。
盆1件。M28∶4,仅余口部及上腹。口沿宽平、略内斜,弧腹。口径17.6厘米,残高3.8厘米(图九,1)。
镦1件。M28∶12,圆筒形,中空,底残。直径1.5~1.6厘米,残高3.4厘米(图九,2)。
3.铁器4件,锈蚀较严重,包括灯、三足炉、柄形器、权等各1件。
灯1件。M28∶6,灯盘圆形,直口微敞,浅腹、平底,细长柄,喇叭形底座。口径13.6厘米,底径9.6厘米,通高16.8厘米(图九,3)。
三足炉1件。M28∶7,敛口,方唇,近口处有一柄,鼓腹,圜底,近底处有三足。口径9.6厘米,腹径11.6厘米,柄长7厘米,通高6.8厘米,足高1.9厘米(图九,4)。
柄形器1件。M28∶11,一端已残,残余部分扁平,实心;另一端中空,内有残留木质。器表有木质及织物遗留,可能为铁凿或铁矛一类器物的柄部。残长11.8厘米,柄底径2.8厘米(图九,5)。
权1件。M28∶14,半球状,平底,实心。顶部凸起部分两侧有凹陷,推断原为一半环形钮。底径5厘米,高2.9厘米,重213.6克(图九,6)。
4.钱币编为1组,M28∶5。锈蚀粘连较严重,难以准确统计,约70枚。可辨识标本3枚,钱文均为“半两”,字体较方正。根据是否有外郭分可为两型。

A型无郭。M28∶5-1,直径2.4厘米,穿径0.8厘米,肉厚0.11厘米,重2.4克。M28∶5-2,直径2.38厘米,穿径0.81厘米,肉厚0.12厘米,重2.1克。
B型有郭。M28∶5-3,正面有一周细郭,直径2.39厘米,穿径0.75厘米,肉厚0.11厘米,重2.1克。
三、M29
(一)墓葬形制
为竖穴墓道土洞墓,方向268°。位于G6与G5北、东、南三沟围合范围的西南部,北距M33约1.3米。墓道打破G5西沟填土,墓室位于G5围合范围内。全长5.3米,由墓道与墓室组成(图一〇)。
墓道位于西侧,平面呈梯形,口底同大。长2.8米,东宽1.6米,西宽1.4米,深4.6米。
墓室位于墓道东侧,平面为梯形,拱顶。长2.5米,东宽0.9米,西宽0.8米,高0.9米。室内见有少量木质腐朽物,原应有木棺。未见人骨,葬式不详。
仅出土一件陶缶,发现于墓道与墓室南侧连接处,陶缶半嵌入墓壁,推测原有壁龛,后坍塌。
(二)出土器物
陶缶1件。M29∶1,泥质灰陶,敞口,宽平沿外斜,尖唇,短束颈,斜广肩,下腹斜收,平底微内凹。肩腹交接处有两周篦点纹,肩、腹部有数周弦纹。口径12.2厘米,腹径40.8厘米,底径16厘米,通高31.4厘米(图一六,1)。
四、M30
(一)墓葬形制
为竖穴土坑墓,平面呈长方形,方向247°(图一一)。位于G5围合范围内中部略偏东处,北距M28约2.1米。口大底小,壁面斜直。墓口长3.8米,宽2.6米;墓底长3.06米,宽1.6米,深5.3米。填土经夯实。距墓底0.6米高处有一二层台,北侧宽0.15~0.21米,西侧宽0.06米,南侧宽0.12~0.22米,东侧宽0.08米。北侧二层台西侧有一壁龛,平面近长方形,宽约1.4米,进深约0.5米,高约0.5米,壁龛内放置4件陶器及1件兽头骨。墓室西南部有一盗洞,平面近长方形,长1.7米,宽0.6米。
墓底见有少量木质腐朽物,原应有木棺。未见人骨,葬式不详。
(二)出土器物

1.陶器4件。均为泥质灰陶,多绘有彩绘。
鼎1件。M30∶4,覆钵形盖,上有三乳钉状钮。鼎身子口内敛,弧腹,圜底较平,上腹近口处附对称外撇双耳,下腹近底处附三蹄形足。器表通体涂白,鼎盖以黑线勾勒云气纹,填以红彩、黄彩,鼎身腹部有两周凸弦纹,上方凸弦纹上部边缘及两周凸弦纹间各涂一周红彩,耳以红彩绘方格纹,足部饰以红彩勾勒的线条。盖口径17.12厘米;鼎身口径14.4厘米,腹径18.4厘米;通高15厘米(图一二,1;图一三,2)。
盒1件。M30∶2,覆钵形盖,圈足形捉手。盒身子口内敛,弧腹,矮圈足。盒盖、盒身涂白,盒盖亦以黑线勾勒云气纹,填以红彩、黄彩,局部可见斑点状蓝彩,盒身上腹部以黑彩、红彩绘一周三角纹,其下饰两周凹弦纹,上方凹弦纹内涂红彩。盖口径15.6厘米,盖顶径6厘米;身口径12.8厘米,腹径17.4厘米,底径7厘米;通高11.6厘米(图一二,2;图一三,3)。
蒜头壶1件。M30∶3,小口,细长颈,圆鼓腹,下腹弧收,平底微内凹。口部形状似蒜头,不分瓣,肩部饰四周凹弦纹。颈部饰红彩,肩部以黑线勾勒云气纹,填以红彩、黄彩,局部可见斑点状蓝彩。口径4.4厘米,腹径19厘米,底径9.2厘米,通高27.4厘米(图一二,3;图一三,4)。
罐1件。M30∶1,直口,宽沿内斜,鼓肩,弧腹,最大腹径偏上,下腹弧收,平底微内凹。肩部有一周折线纹饰带。口径17.6厘米,腹径29.6厘米,底径14.6厘米,通高21.4厘米(图一二,4)。
2.兽头骨1件。保存较差,未采集。长约36厘米,宽约22.6厘米。

五、M33
(一)墓葬形制
为竖穴墓道土洞墓,方向263°。位于G6与G5北、东、南三沟围合范围的西南部,南距M29约1.3米,北距M28约5.4米。墓道打破G5西沟填土,墓室位于G5围合范围内。墓葬全长5.1米,由墓道和墓室组成(图一四)。

墓道位于西侧。平面呈梯形,口底等大,四壁竖直,平底。长2.3米,西宽0.9米,东宽1米,深4.5米。
墓室位于东侧。平面呈平行四边形,呈西南—东北走向,东高西低。长2.8米,宽1米,高1~1.2米。未见人骨架,葬具、葬式不详。西部出土随葬器物2件,分别为陶灶及铅镳。
(二)出土器物
陶灶1件。M33∶1,泥质灰陶,残损严重,仅余灶面一釜及烟孔。釜口径4.2厘米,腹径7.4厘米,深2.4厘米。烟孔平面呈马蹄形,中有一圆孔。残长13.2厘米(图一六,2)。
铅镳1件。M33∶2,条状,中部有两个圆管。通长6.8厘米(图一六,3)。
六、M36
(一)墓葬形制
为竖穴土坑墓,平面呈长方形,方向256°。位于G6与G5北、东、南三沟围合范围内西北部,南距M28墓室约0.3米。打破G5西沟填土。口底等大,墓壁竖直。墓葬长2.3米,宽1米,深4.7米(图一五)。未见人骨架,葬具葬式不详。西部出土铜带钩1件。
(二)出土器物
铜带钩1件。M36∶1,整体呈曲棒形,钩首为蛇首,钩体横截面呈圆形,圆钮位于中部稍偏尾处。长12.2厘米,钮径0.6~1厘米,钮高1厘米(图一六,4)。

结语
(一)墓葬年代
上述5座墓葬均未出土带有纪年信息的器物,只能通过与周边地区考古出土器物比对来判断墓葬年代。M28为带天井的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土圹斜坡墓道西部为土洞式过洞,过洞西段坡度较大,而东段底部平坦,且长度与侧室甬道口宽度一致,据此推测过洞东段平台应是为了方便侧室施工特意设计和修建的;过洞东段南壁有一正对侧室口的壁龛,结合墓道宽度不足1米的情况看,很有可能是为方便在墓道中调整棺的方向,以便葬入侧室而开凿的。根据主墓室底部沿南、北壁发现的椁痕及侧室面积较大、有封门且有一定数量随葬品的情况,推测主墓室与侧室内均有葬人。侧室所出陶器组合为鼎、盒、钫、缶,与西北医疗设备厂西汉早期墓葬中所出同类器物相类。其中鼎、钫与M170出土同类器物[1]166—178相似,盒与M51∶15[1]76—80相似,缶与M152∶1[1]155—159相似。半两钱钱文扁平趋于方正,其中M28∶5-3正面带郭,与M170出土半两钱相似,上述所引墓葬年代皆为西汉早期,其中出土有郭半两的M170年代上限不超过武帝建元五年(前136),故推测M28时代为西汉武帝初年。
M29为竖穴墓道土洞墓,墓室窄于墓道。出土陶缶肩腹夹角为钝角,与西安南郊上塔坡村东M5所出陶缶M5∶18[2]相似,该墓年代为西汉初年至西汉早期,故推测M29年代为汉初。M33与M29相邻,墓葬形制相似,墓向一致,推测两墓时代相近,M33亦属汉初。
M30为竖穴土坑墓,壁龛内出土有彩绘陶鼎、盒、蒜头壶等。陶鼎M30∶4与西安北郊秦墓99乐百氏M39∶3[3]相近;陶盒M30∶2盒体宽扁,与西安南郊茅坡邮电学院M109甲∶2[4]相似;蒜头壶M30∶3与西安尤家庄秦墓99青海军区M22∶2[5]相近,唯颈部更长。乐百氏M39与青海军区M22年代为秦统一时期,茅坡邮电学院M109年代为战国晚期后段至秦统一时期,故推测M30年代为秦统一时期。


M36出土带钩呈曲棒形,素面无装饰,不同于秦墓中常见的琵琶形带钩,但此类型在关中地区战国晚期至秦代墓中也有发现[6]。而根据墓葬方向、位置及打破关系来看,M36与M29、M33方向相近,皆打破G5西沟填土,且未被M28墓室打破,故推断M36时代应与M29、M30相近,亦为汉初。
(二)墓葬之间及与围墓沟的关系
根据围墓沟G6沿G5南、北沟延长,G7沿G5东沟延长的情况,可知G5时代早于G6、G7。G5为近方形闭合沟,M30位于其中部稍偏东,墓向为西向,且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等级,故推测G5为M30的附属设施,其时代也应与M30相同,为秦统一前后。
M29、M33及M36打破G5西沟,其时代应晚于G5。三座墓葬均位于M30的西侧,墓向基本与M30一致,时代也均晚于M30,应是家族墓地的延伸和发展。G6在G5的基础上向西扩展,将M29、M33及M36包含在内,故推测G6是这三座墓葬的附属设施,时代也应相近,同属汉初。
M28为长斜坡墓道洞室墓,墓向朝东,形制、朝向皆与其余4座墓葬不同。其墓道东端虽打破G5东沟填土,但仍基本位于G5(G7)东沟以内,侧室虽已超过G5北沟,但却位于沿G5向北扩展的G7的范围之内。此外,西端主墓室紧邻M36,且与M29、M33和M36三墓墓室基本平行排列。因此推测,G7沿G5向北扩展的目的就是将M28完全围于沟内,其应为M28的附属设施,故G7应与M28的修建时代相近,属武帝初年。该墓地或为家族墓地,M28墓与其他4座墓葬属同一家族。
M28具有一定的规模,M30出土精美的彩绘陶器,显示出两墓墓主应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推测为地方官吏或中小地主。相比而言,M29、M33、M36出土器物较少,墓葬规模也较小,结合墓葬年代来看,可能与秦汉之际战争动乱的社会背景有关。

战国秦至西汉初的中小型围沟墓在陕西凤翔[7,8]、山西侯马[9]、河南三门峡[10—12]等地已有一定数量的发现,此次在西安西咸新区发掘的围墓沟与墓葬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为研究秦至西汉早期的围沟墓与家族墓地提供了新的资料。
项目负责人:柴怡、赵兆
发掘人员:黄佳豪、杨永岗、陈海峰
器物修复、资料整理及绘图:楚展鹏、高一鑫、钟乐彤、王雅楠、武留涵、祝熙、苗楷琳,马玉娴
摄影:黄佳豪、杨永岗
执笔:钟乐彤、武留涵、黄佳豪、高一鑫
————————
[1]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龙首原汉墓[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
[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安市南郊上塔坡村东战国秦汉墓发掘简报[J].四川文物,2024(1).
[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秦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37—140.
[4]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秦墓[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185—188.
[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尤家庄秦墓[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126—129.
[6]王腾飞,滕铭予.关中秦墓出土带钩研究[J].华夏考古,2023(3).
[7]徐卫红,王志友.99凤翔黄家庄秦墓B区发掘[J].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0(2).
[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队.陕西凤翔黄家庄秦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2(Z1).
[9]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东周殉人墓[J].文物,1960(Z1).
[10]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火电厂秦人墓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1993(4).
[11]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大岭粮库围墓沟墓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2004(6).
[1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师范学院考古与文博系.河南三门峡后川村西汉围沟墓发掘简报[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3).
〔责任编辑:陈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