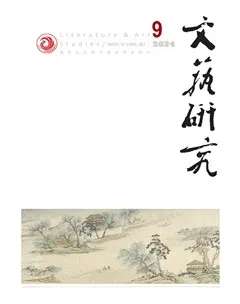“有力”与“无意”:中国诗学中“风”与“水”的意象
优秀的文学作品中,都会含有一些难以用言辞表达的“某种东西”。而文学的魅力也正存在于这“某种东西”之中。“某种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们都致力于以言辞将其表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主要使用的手法便是以物象(image) 作比喻。其中,最常被使用到的是“风”与“水”或与二者相关的意象。
文人们藉由风与水的比喻意图表现什么呢?本文旨在追溯围绕文学展开的讨论中所呈现出的风与水意象的系谱,分析从六朝到唐代再到宋代,中国诗学中广泛潜存的“有力”的和“无意”的两种类型的诗学。在此基础上考察两者之间关系的种种表现,以及由此展现的文学观所具有的特质。
一、“有力”
最早使用风与水的意象来论述文学作品的代表性案例,是陆机的《文赋》。其后半部分有云:“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以“风”和“泉”来比拟文学的思想、趣味及语言,藉由这种方式呈现出文学作品生成过程中具有的情貌。陆机之后,北周庾信的《周大将军豳国公广墓志铭》有云:“思风含臆,言泉流吻。”同样出自庾信之手的《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亦云:“水涌词锋,风飞文雅。”在称赞死者时,两例都以飞扬的风与喷涌的水比喻其文章、言谈的精妙绝伦。前一例承袭陆机的《文赋》,使用了“思风”“言泉”二语。
唐代的文人们继承了陆机、庾信的言辞。现有文献中,以对偶形式同时使用风和水的例子虽然不太多,单独使用风或者水的例子却随处可见。接下来试举部分例子予以说明。王勃《送宇文明府序》云:“言泉共秋水同流,词锋与夏云争长。”用了“言泉”一词来形容宇文明府的文学。虽未提到“思风”,但应该也是受到了陆机《文赋》的启发。王勃文集后附录了杨炯的《王子安集原序》,其中有云:“动摇文律,宫商有奔命之劳。沃荡词源,河海无息肩之地。”以河海的广阔比喻王勃文学的繁富。在杨炯的这一表述中,已看不到陆机《文赋》的直接影响了。此后,在唐代出现了很多脱离了陆机《文赋》、借用各种各样风与水的意象来赞扬文学作品的辞句,可知风和水的比喻已经充分浸透到了文学论中。这类案例繁多,不胜枚举,这里从李白和杜甫的诗中各举一例来说明。李白《赠刘都使》:“吐言贵珠玉,落笔回风霜。”以刺透肌骨的寒风来比喻从刘氏作品中获得的印象。杜甫《醉歌行》:“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则将从侄子杜勤作品中获得的印象,比喻成在三峡倒流的长江之水。
在上述例子中,文人们藉由风与水的意象究竟表现了什么状态呢?当然,各种解释都可以成立。而使用比喻性言辞,原本就是为了具象地阐释难以言表的作品世界,其中难免会包含含糊的要素。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大致将风与水的意象所喻指的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气势之强盛、迅猛、激烈、壮大、丰饶等特质,概括为“力”的表现,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的表现方式,在宋代也得到了广泛的继承和使用。接下来集中举北宋诸例来说明:
风涛借笔力,势逐孤云扫。(苏轼《迨作淮口遇风诗戏用其韵》)
丝虫萦草纸,笔力挟风雨。(黄庭坚《和邢惇夫秋怀十首》之七)
风雷绕纸成千篇,弃遗不惜如零唾。(惠洪《秀上人出示器之诗》)
上述例句中,“风涛”“风雨”“风雷”等词,都以风与水的意象来形容“笔力”,也就是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力给读者带来的印象。
当下,我们常常会以“这个作品很有力”等表述来称赞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实,中国自古以来便有与此相同的说法。宋代诗话中,不乏以“有力”来赞赏文学作品的评语。例如许(岂+页)《彦周诗话》之“诗有力量”,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之“句中有力”,都在举出杜甫的诗作后,用“有力”“有力量”来评价其中蕴含的力量感。
“力”是什么呢?这很难用一句话来说明。那种力本身是我们无法看到也无法触摸到的,但是,我们却可以感知力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事物发生某些运动或变化时,我们能够将其作为力作用的结果来把握,并由此感知某些力发挥了作用。因此,“力”可以按照如下的方式定义:力,乃是带来运动和变化的东西。
就此而言,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规定了中国文学根本原理的《毛诗大序》中的一句话。在序中,围绕文学作品产生的效果,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一句,句中使用了“动”“感”这类表现运动和变化的动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诗大序》将问题聚焦到了文学中蕴含的力上。它讨论的乃是文学中蕴含着的感动人、天地、鬼神也就是引发运动和变化的力。
《毛诗大序》阐发的这种感动之力,在中国文学论中得到了广泛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点可以举杜甫为例予以说明。杜甫在不同场合所作的诗歌中,不时述及文学中蕴含着感动人、天地、鬼神之力的观念。如其《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气动星象表,词感帝王尊”,称自己的言辞可以感动帝王;《寄薛三郎中璩》“赋诗宾客间,挥洒动八垠”,亦言自己的诗可以感动全世界;《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称赞李白的诗可以感动神灵,并使之落泪。除杜甫以外,论及这种力的例子触目可见。
中国的文人们认为,优秀的文学中存在巨大的力量,不仅可以动摇人,甚至可以动摇天地、鬼神这类超人的神秘的存在。文学中蕴含着足以摇动天地、鬼神的力,也就意味着文学中蕴含着能与天地、鬼神相匹敌的力。如前所述,力的最大特征是看不见摸不着。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事实上又是确实的存在。与之类似的,我们还可以想到神灵。天地、鬼神同样也是神灵之类,是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的存在。正因如此,人们常常将文学中的力与天地、鬼神联系起来讨论。
下面举出若干例子,分析那些论及了与天地、鬼神相联结的超人且神秘的力的文学论。韩愈、孟郊《城南联句》:“大句斡玄造,高言轧霄峥。芒端转寒燠,神助溢杯觥。”描述了文学中存在可与“玄造”即“天”的造化相颉颃的力,这种力如同得到了“神”助,“寒燠”则是说可以改变季节的运转。这两联虽然是论述诗得到了“神”之助力,但也意味着诗中蕴含可与“神(鬼神) ”匹敌的力。同样的力,杜甫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反复论述过。除前文所举《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成泣鬼神”之外,其他诸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敬赠郑谏议十韵》“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都写到优秀文学中寄宿着如“神(鬼神) ”般超人的神秘的力,致使“神(鬼神) ”也无法安之若素。所谓“神(鬼神) ”,处于至高的“天”与地上的“人”之间,是“天”之辅佐,可以视作相当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文化圈中天使一样的存在。无论如何,它们总是超人的存在,人力通常是无法与之匹敌的。不过,优秀的文学作品却被认为能够具备与“神(鬼神) ”匹敌的力。诸如此类的见解,在杜甫、韩愈作品之外也广泛可见。
文学中蕴含的超人且神秘的力,有时还会成为令天地万物畏怖的凶暴之力。从本质上来说,力是蕴含在强者身上的东西,对处于劣势的一方构成威胁,如韩愈《荐士》所说:“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自然界中万物被李白、杜甫诗所描绘,竟有被暴力凌辱之感。同样出自韩愈之手的《双鸟诗》,将李白、杜甫比喻成两只鸟,诗中有云:“鬼神怕嘲咏,造化皆停留。”写出了李白、杜甫诗中描绘的景象令“鬼神”感到恐怖,在二人诗中压倒性的力量面前,连天的“造化”都被迫停滞了。前文所举韩愈、孟郊《城南联句》中“大句斡玄造”“芒端转寒燠”等句,说的是创造、改变世界的文学之力。而具备能与天地、鬼神相颉颃的超人之力的文学,不仅仅能创造、改变世界,还可以凌辱、压制世界,令世界陷入混乱。上述韩愈的诗句就揭示了这一观念。
韩愈描写的这类文学作品中的凶暴之力,宋代文学论中也多有涉及。这里从北宋和南宋各举一例以见一斑。苏轼《次韵李公择梅花》:“诗人固长贫,日午饥未动。偶然得一饱,万象困嘲弄。”杨万里《送姜夔尧章谒石湖先生》:“钓璜英气横白蜺,咳唾珠玉皆新诗。江山愁诉莺为泣,鬼神露索天泄机。”两例均刻画了万物和“鬼神”因被诗所咏而愁苦的景象,杨万里诗中的“露索”一词,是被裸身搜索无遗之意。由于诗所持有的暴力,连超人而神秘的“鬼神”也被剥下了神秘的面纱,赤裸裸地暴露无遗。
在描写诗歌凶暴之力的言辞中,不少例子是将诗歌比拟为武器和军队,将诗歌的创作比拟为运用武力。这正是在唐代至宋代文学论中广泛流行的“以战喻诗”观。前文所举杜甫《醉歌行》有“笔阵独扫千人军”,将诗中强大的力比喻为击破大军的军队。在这一意象的使用上,此诗是较早期的例子。同样出自杜甫的《敬赠郑谏议十韵》有云:“破的由来事,先锋孰敢争。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亦是将能威吓鬼神的诗歌语言的力,比喻成准确射穿靶心的箭和打头阵的利刃。
类似的言辞在宋代广泛可见,而北宋惠洪尤其喜用这种表现方式,故举其例予以说明。如《赠王圣侔教授》:“曾经大笔战文阵,豪俊莫敢撄其锋。老师硕儒玉堂上,争看洒笔回春工。”又《见蔡儒效》:“忽惊锋刃攒,凛然为毛竖。可读不可识,森严开武库。”都将诗句比喻成军阵和武器,并描写出这种诗句给读者带来的恐怖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文学论中的一种观念,即优秀文学作品中存在着能与“天”“鬼神”相颉颃的超人且神秘的力,或令万物畏怖的凶暴之力。这种观念可以概括为“有力”的诗学。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在“有力”的诗学观中,文学里蕴含的诸种力,经常与风、水的比喻意象关联在一起。如前引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将使“鬼神”落泪的神秘力量与“风雨”密切关联起来;杜甫《醉歌行》“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将连大军都可击破的压倒性暴力,与逆流的“三峡水”密切关联起来;又杜甫《敬赠郑谏议十韵》,前引诗句被比作威吓鬼神的飞箭利刃,随后一联中则有“波澜独老成”,用丰饶壮大、充满力量动感的“波澜”意象,来表现老练程度。
体现了同样观念的言辞,还可以举出若干宋代的例子。例如苏轼《和王斿二首》之一:“异时长怪谪仙人,舌有风雷笔有神。”将才高如李白的王斿诗中寄宿的“神”力与“风雷”关联了起来。这类表达广泛见于惠洪作品中,如《次韵平无等岁暮有怀》“文章有神惊颖脱,风雷先听毫端落”,《金华超不群用前韵作诗见赠亦和三首超不群剪发参黄檗》之二“却于翛然索寞中,诗句时时出奇古。乃知笔力有神助,三峡迅流辄于住”,将如同有“神灵”附体的诗中的超人且神秘的力,和“风雷”及“三峡迅流”的意象关联起来。惠洪作品中,被比喻为军队和武器的凶暴之力也常常同风与水有关联。例如《谒嵩禅师塔》“齿牙生风雷,笔阵森戈”,表现“戈”林立的言辞与“风雷”相关联;又《次韵偶题》“畏公笔力不可敌,坐令三峡回奔湍。威棱王节照湘楚,夸声众口锋刃攒。此篇意气更倾写,句法超绝风格完”,也还是将如密集“锋刃”般的“笔力”与“三峡回奔湍”联结在一起,这一点承袭了杜甫《醉歌行》之“词源倒流三峡水”。又惠洪《予与故人别因得寄诗三十韵走笔答之》云:“天才逸群君独立,洞彻心胸秋色入。于中堆积万卷余,笔力至处风雷集……翻澜妙语惊倒人,气焰霜锋光熠熠……又如霜晓听边风,十万军声何翕翕。笔锋正锐物象贫,降旌狼籍诗魔泣。”诗的狂暴言辞与“风雷”“翻澜”相结合,堪比锋刃,足以使“十万”大军乃至世间万物困苦不堪,连“诗魔”这种超人的存在也畏惧不已。
如前所述,中国诗学中使用风与水的意象,是为了将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力变得可见可触。深入思考的话,存在于大地上的事物中,最为“有力”的东西莫过于风和水了吧。实际上,风和水也向人类展示着它们那种压倒性的力量。人类一方面从中获取动力源泉等诸多恩惠,同时又面临着风水灾害的侵扰。这种经验积累起来,便让风与水获得了最典型的“有力”之物的印象,被用来比喻“有力”的文学作品。
二、“无意”
绍熙二年(1191),南宋文人姜夔在金陵和担任江东转运副使的杨万里见面时,写下一首题为“送朝天续集归诚斋时在金陵”的诗作:
翰墨场中老斫轮,真能一笔扫千军。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箭在的中非尔力,风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首江东日暮云。
此诗颇令人注意之处,在于前六句称赞杨万里文学时所体现的文学观念。第一句将杨万里比作《庄子·天道》中出现的工匠轮扁,以称赞其文学技艺的老练。第二句沿袭杜甫“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进而强调杨诗具有击灭大军般的强大力量。接下来的第三、四句,写蕴含如此强大力量的杨诗令万物感到畏怖。到此为止,表达的是与诗之力相关的文学观,前文已对此作了论述。那么,沿着这一观念,第五、六句又表达出了什么样的文学观呢?
第五句“箭在的中”,将诗歌言辞比喻为箭矢,显然是有意识地化用了杜甫《敬赠郑谏议十韵》之“破的由来事”,意指杨万里的诗能够切当地表现世界。这一含义同样见于前文探讨的与力有关的文学论中。不过,第五句紧接着说到了“非尔力”。“尔”是指杨万里,也可指普遍意义上的作者。这里是说,成就了“箭在的中”的是杨万里的诗,而非他自身的力。一般而言,杨万里诗歌表现出的切当性,理应来自作者即杨万里自身的力,但姜夔却否定了这一点。为什么呢?杨诗第五句其实用了《孟子》的典故。《孟子·万章下》在论辩应当“圣”“智”兼备的主张时说,“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认为精确贯穿靶心的原因在于“巧”,而不在于“力”。因此,否定作者的力,实际上是在称赞杨万里诗中蕴含着超越了简单的“力”的“巧”。第五句将作者的力否定或者弱化了,沿着这一意脉出现的第六句是“风行水上自成文”。这一句的表面意思是:风吹拂过水面,水面生出涟漪。但这究竟表达出了什么样的文学观呢?另外,此处也使用了风与水的意象,这与前文所论风与水的意象又有何异同呢?接下来笔者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姜夔诗第六句典出《周易·涣卦·象》:“风行水上,涣。”由于是经典中的言辞,中国文人自当无人不晓。不过,对宋代文人而言,“风行水上”还是比喻文学理想状态的修辞,附带有特别的意味。这与苏洵《仲兄字文甫说》中的议论有关:
且兄尝见夫水之与风乎?油然而行,渊然而留,渟洄汪洋,满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风实起之。蓬蓬然而发乎大空,不终日而行乎四方,荡乎其无形,飘乎其远来,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风也,而水实形之。今夫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也……殊状异态,而风水之极观备矣。故曰“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惟水与风而已。
引文第一段的省略部分,如赋一般不厌其详地描绘了风与水的各种姿态。在此基础上,苏洵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由“风行水上”而产生的纹样,即波纹、涟漪才是至高的“文”。从这点出发,在引文的第二段中,作者对此文学观作了更进一步的阐释,指出从“风行水上”生发出的“文”是“无意”的“文”,也就是说,并非有意造作,而是由“自然(自发) ”之力孕育出的“文”。在这里,苏洵阐释的是“无意于佳乃佳”的文学观,不妨称之为“无意(自然) ”的诗学。
苏洵阐述的“无意(自然) ”的诗学,在其后的宋代文人中得到广泛流传和接受。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最大作用的可以说是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轼的文学论中,不少言语透露出受到苏洵影响的痕迹。例如,其《南行前集叙》记录了年轻的苏轼、苏辙兄弟从父亲苏洵处接受的教诲,其中有如下言论: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
引文传达了如下文学观:真正的文章并非出于作者刻意的创作,而是出于不得不作。文末“未尝敢有作文之意”,简而言之,即“无意”。这种否定或将文学中的作者意图弱化的“无意”的诗学,是苏氏一族共同秉持的观念。
不过,对比引文可以发现,在苏洵《仲兄字文甫说》中,风与水的意象在探讨文学时扮演了重要角色,苏轼的《南行前集叙》并未触及风与水的意象。但是,在《书辩才次韵参寥诗》中,能够看到他使用了近似“风行水上”的比喻阐述文学观念:
辩才作此诗时,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学作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而参寥与吾辈诗,乃如巧人织绣耳。
苏轼用“如风吹水,自成文理”来称赞辩才的诗歌创作,并指出,参寥和自己的诗不过是如“绣”般的人为之文,与此相异的则是自然之文。虽然他并未使用“无意”这样的言辞,但藉由风吹过水面的意象来表现自然之文的做法,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苏洵的文学论。
此外,在苏轼《答谢民师推官书》的下述表达中,风与水的意象发挥了极大作用,这段话也为《宋史·苏轼传》引用,可以说是苏轼文学观的代表性言论: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这段话使用了“行云流水”的意象,行云呈现了风的效果,我们根据云的动态,感知眼睛无法看到的风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行云流水”与“风行水上”可以说是基本相同的意象。苏轼将“行云流水”理解为“无定质”,即无确定实体、自在变换姿态的自然存在,并用以比喻理想的文。
与“行云流水”属于同类意象的“泉源”,作为以水喻文的言辞,广为人知的是苏轼《自评文》: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石山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所谓“随物赋形”,是写水顺应周围环境的变化而自在无碍地改换姿态。所谓“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则是用自由、自然运动的水来比喻不受写作者意图支配的文章的形态。
以上分析了苏洵、苏轼利用风与水的意象来阐述文学理想状态的文学论。他们在论述中采用风与水的意象是为了表现运动和变化。如前文所述,在运动和变化的背后,可以想见力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苏洵和苏轼试图具象化论述的正是文学作品中的力。但是,他们试图阐述的力,不是那种拥有暴力特质、向世界发起挑战、对万物施加恐怖的力,而是调和世界、为人和万物带来安宁和幸福的平稳静谧的力。因此,用“力”来表示这一内涵或许不太确切。也许应该说那是使人感觉不到力,否定、弱化了力的运动和变化。苏洵、苏轼使用“自然”“无定质”“随物赋形”等言辞来表现这种运动和变化,进而从运动和变化的底层发掘出“无意”,即超越了作者意图的支配而发挥作用的文学语言的姿态。前引姜夔《送朝天续集归诚斋时在金陵》中的“箭在的中非尔力,风行水上自成文”,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苏洵、苏轼提倡的“无意”的诗学,影响了不少宋代文人。例如,属于苏门的黄庭坚,在《大雅堂记》中如是评价杜诗:“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认为杜诗精妙之处正在于“无意”。同样的文学观也见于南宋。例如,杨万里《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大抵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吾叔谓‘说禅,非文人儒者之言’。本意但欲说得诗透彻,初无意于为文,其合文人儒者之言与否,不问也。”两例均写出作者对文学创作中“无意”状态的期待。特别是像杨万里所说“我何与哉”,更是把从超越作者自身干预的形态中诞生的文学视作理想。
前文所举黄庭坚、杨万里、严羽的言辞中,没有使用风与水的意象。不过,南宋初汪藻的《鲍吏部集序》中有云:“古之作者无意于文也。理至而文则随之,如印印泥,如风行水上,纵横错综,灿然而成者,夫岂待绳削而后合哉。六经之书皆是物也。”汪氏在表达“无意”的诗学时,和苏洵一样,使用了《周易·涣卦·象》“风行水上”的意象。除此之外,宋代使用“风行水上”意象来阐述自然之文的例子还有许多。这里从南宋选一例予以说明。袁说友《跋胡元迈集句诗帖》云:
仆谓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此又文之出于我,而不可御者。
在引用苏轼《自评文》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围绕“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展开议论。末尾所谓“文之出于我,而不可御者”,意指文学作品是超越作者支配而产生的东西,其实也就是在阐发“无意”的诗学。
此外,另有一点值得注意,前引汪藻《鲍吏部集序》中有“夫岂待绳削而后合哉”之语,承袭自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的“不烦于绳削而自合”。“绳削”是指文学的法度,即规范、法则,或者说是遵循法度来调整表现的方式。所谓“夫岂待绳削而后合哉”,是说在文学创作中既不刻意遵循规范或法则,也不苦心雕琢构思,而最终的作品却恰好与创作规范或法则不谋而合。黄庭坚曾在《与王观复书三首》之一、《题李白诗草后》等作品中反复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特别是在《题意可诗后》中写道:“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将“不烦绳削而自合”视为与“有意”相反的创作状态,也就是结合了“无意”的诗学来展开论述。汪藻《鲍吏部集序》中的表述可以说是忠实地继承了黄庭坚的文学观念。
汪藻活动的南宋初,是继承了黄庭坚诗及诗学的江西诗派风靡一世的时代。据说,汪藻本人从学于江西诗派主要成员徐俯和韩驹,因此可以把他视作处于江西诗派边缘位置的文人。与汪藻活动于同一时代的文人吕本中,著有《江西诗社宗派图》,确定了以黄庭坚为宗的诗人集团系谱。从派系的角度来说,江西诗派从此被赋予了明确的形制。在这个意义上,吕本中可以说是江西诗派之父。此后,他自己也被归入江西诗派。吕本中不仅确定了江西诗派的系谱,还深化、发展了黄庭坚的诗学。在吕本中的诗学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与“活法”相关的文学论。而“活法”论正是黄庭坚及其继承者的诗学核心之一。值得关注的是,“活法”论和“无意”的诗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
南宋刘克庄所作《江西诗派小序·吕本中》,记录了吕本中为夏倪(亦为江西诗派成员) 文集所作序文《夏均父集序》的部分内容,其中论到: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元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趋向,毕精尽智,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然余区区浅末之论,皆汉魏以来有意于文者之法,而非无意于文者之法也。
所谓“活法”,是指遵循“法(规矩) ”的同时,又超越它们,实现自在无碍的运动和变化。在这一点上,吕本中主张的“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和黄庭坚反复阐述的“不烦绳削而自合”具有相同旨趣。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尽管这种表述很不合逻辑,但他却尝试将意图遵守“法”的立场与意图否定乃至超越“法”的立场辩证统一起来。虽说“法”是文学创作中任何人都必须遵从的规范,但仅仅盲从是无法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的。那么,应该如何处理与“法”的关系呢?对宋代文人而言,这成为最重大的问题之一。黄庭坚主张的“不烦绳削而自合”,吕本中主张的“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可以说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最终的结论。
在前引刘克庄文中,“活法”和“无意”被关联起来论述。引文末尾称“然余区区浅末之论,皆汉魏以来有意于文者之法,而非无意于文者之法也”,“有意于文”被认为是“浅末之论”,与此相反,“无意于文”则被认为是理想状态。此外,更应注意的是,吕本中在阐述“活法”时借用的比喻意象,是“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即盘子上流畅打转的球形弹丸。这是形容自在无碍地运动、变化的意象。从这一点上看,和苏洵以来为了论述“无意”的诗学而采用的“风行水上”之类的意象有着高度的共通性。如黄庭坚《翠严真禅师语录序》:“行川之水无不盈之科,走盘之珠无可留之影。”惠洪《林间录》卷下:“舒卷自在,如明珠走盘,不留影迹。”两人都以在盘中滚动的珠玉,形容“自在”而“不留影迹”的运动情态,其内蕴可以说与“风行水上”如出一辙。而从这种意象的使用方式也能看出,“活法”论是属于“无意”的诗学场域的文学论。
综上,前文主要着眼于对风与水意象的运用,分析了宋代“无意”的诗学及其系谱。在第一部分所讨论的“有力”的诗学视野下,风与水意象的运用,是为了直观地呈现文学作品中超人的、神秘的或狂暴的力。相对地,在“无意”的诗学中,风与水意象的运用,则是为了直观呈现“自然成文”“无定质”“随物赋形”“变化不测”“不留影迹”等言辞表达出的自在无碍的运动和变化。
三、作者及其“意”“力”
从前文我们观察到,在中国文学论中,用风与水的意象表现出的内容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即“有力”的诗学和“无意(自然) ”的诗学。六朝以来表现“有力”的诗学的风与水意象,到了宋代更增加了“无意”的内涵。但是,且不说“有力”和“无力”、“有意”和“无意”,“有力”和“无意”的关系原本就并非不能兼容。这一点需要格外注意。实际上,在同一文人的论述中不乏两者并存的情况。
北宋初田锡的文学论就对此有所体现。苏洵《仲兄字文甫说》以“风行水上”的意象阐释“无意”的诗学,而文论史上历来备受关注的田锡《贻宋小著书》正是其先驱。此信中有如下议论:
若使援毫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则文章之有声气也,不亦宜哉。比夫丹青布彩,锦绣成文,虽藻缛相宣,而明丽可爱。若与春景似画,韶光艳阳,百卉青苍,千华妖冶,疑有鬼神,潜得主张,为元化之杼机,见昊天之工巧,斯亦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则丹青为妍,无阳和之活景,锦绣曰丽,无造化之真态。
引文谈论了文学作品的理想形态。关于文学作品的生成,田氏借用“微风动水”“太虚浮云”等语,说明了没有“定文”“常态”的文学的形态。这一观点与苏洵的文学观几乎完全相同。引文末尾的“不知所以然而然”,描述了一种超越作者之“意”掌控而生成的文学形态,这里阐述的正是“无意”的诗学。
此外,同样出自田锡之手的《贻陈季和书》说:
若卒然云出连山,风来邃谷,云与风会,雷与雨交,霹雳一飞,动植咸恐,此则天之变也。亦犹水之常性,澄则鉴物,流则有声,深则窟宅蛟龙,大则包纳河汉。若为惊潮,勃为高浪,其进如万蹄战马,其声若五月丰隆。驾于风,荡于空,突乎高岸,喷及大野,此则水之变也。非迅雷烈风,不足传天之变,非惊潮高浪,不足形水之动……若豪气抑扬,逸词飞动,声律不能拘于步骤,鬼神不能秘其幽深,放为狂歌,目为古风,此所谓文之变也。
信中的“文之变”,关乎文学中的运动和变化。就论说风和水的“变”“动”而言,与苏洵的文学论有相通之处。但是,田锡使用的风与水的意象,与苏洵的“风行水上”并不相同。信中所写“迅雷烈风”及“惊涛高浪”,借用风与水的意象比喻强大而激烈的力,反倒与本文第一部分所例举的文学论颇多重合之处。
如果把田锡《贻宋小著书》和《贻陈季和书》中涉及风与水意象的表述放在一起观察的话,可以发现,“有力”的诗学和“无意”的诗学这两种要素并存于他的文学论中。苏轼的情形也是如此。他深化、发展了“无意”的诗学,同时也继承了“有力”的诗学。在前文所举苏诗《迨作淮口遇风诗戏用其韵》中,有“风涛借笔力,势逐孤云扫”之句,肯定了诗中强大如“风涛”般的力。而在《次韵李公择梅花》中,苏轼又说:“诗人固长贫,日午饥未动。偶然得一饱,万象困嘲弄。”他也认可诗中的暴力描写足以令“万象”困苦。此外,前文所举姜夔《送朝天续集归诚斋时在金陵》中,有“真能一笔扫千军”,是体现“有力”诗学的句子,和体现了“无意”的诗学的“风行水上自成文”并存于同一篇作品中。由此可知,这两类诗学同时映现在姜夔眼中。以二者的并存为前提,姜夔的立场如前所述,是否定了“有力”的诗学,而将“无意”的诗学赞扬为理想的文学创作状态。
纵观这些例子,可知中国诗学史并不是单纯地从“有力”转化到了“无意”。下面,笔者尝试分别追溯“有力”的诗学和“无意”的诗学在宋代以前的系谱,在此基础上再次展开讨论,特别关注有关文学创作中作者作用及功能的论说。
首先来看“无意”的诗学系谱。所谓“无意”,指文学作品是在超越作者之“意(意图) ”后“自然(自发) ”地生成的。这种“无意”的诗学的底层潜藏着重视“自然”、否定或弱化作者之力的文学观。例如,南宋杨时在《龟山语录》谈及陶渊明的“自然”文学时说,“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着力之所能成也”,认为陶诗并非作者“用力”“着力”所能达成的。前引姜夔诗句中“箭在的中非尔力”,也表达出相近的文学观。“箭在的中”,指诗歌语言能切当表现对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认为诗歌表现的切当性源自作者的力。然而,姜夔在这里使用了“非尔力”一词,来否定这种观点。此外,前引袁说友《跋胡元迈集句诗帖》中的“文之出于我,而不可御者”,也否定了支配作品的作者的力。
不过,在文学创作中否定或将作者之力弱化的文学观,并非是在宋代兴起“无意”的诗学后才出现的。倘若要探究渊源,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时期。
早期的一个例子见于晋代陆机的《文赋》,其云:“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是指创作的冲动,“兹物”指“文”,“我”“余”指作者。后两句是说,文学作品表面上看是基于作者自身之力而产生的,然而实际是在超出作者自身之力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观念可以视作“无意”的诗学的萌芽。
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指出,陆机的这一言论是“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 的艺术观、文学观。inspiration是什么呢?竹内敏雄编《美学事典》“灵感”条解释称:
不依赖于创作者自身的力量,仿佛是天降的恩赐般,被赋予了作品的构思。
某种更高的存在(超越人类的高级存在——引者注) 赋予(inspire) 了作品生命。
这本是西方的观念,但和中国文论确实存在着共通点。与此类似的思考方式不在少数,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就举出了诸多例子,这里略举数例。梁钟嵘《诗品》卷中“谢惠连条”引用了《谢氏家录》中谢灵运梦中得句的故事,其中有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指出精妙的诗句乃是在“神”(亦即《美学事典》所谓“某种更高的存在”) 的助力下得到的。又萧子显《自序》云,“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描述了作品自动拜访作者的情景。被认为出于谢灵运之口的“非我语”,意指并非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获得的诗句,姜夔的“非尔力”、陆机的“非余力之所勠”基本上也是一样的话。萧子显“不以力构”,指作品并非出于作者自身的力,也具有相近意义。
如上所述,“无意”的诗学,即文学作品是超越作者力的支配而产生的这一文学观,并非在宋代首次出现,其先驱性的思考方式在六朝就已产生。那么,由此还应当继续追问下述问题:自古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蕴含着某些力,这称得上“有力”的诗学,然而,这力从何而来呢?虽说一般情况下会被认为来自作者,但果真如此吗?作品中不是包含着“无意”的诗学,也就是否定或弱化作者的力的要素吗?
为了考察这个问题,先来看一下孟郊《赠郑夫子鲂》:
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
这是诗人向郑鲂解说理想文学形态的作品,其中传达的文学观念,与“有力”的诗学基本一致。例如,第一、二句写足以将“天地”纳入胸中的人物(具体来说,是第五、六句中所举宋玉、李白这样的大诗人) 发出“吁嗟”之叹,其中蕴含的强大力量以“风雷”的意象表现出来。“吁嗟”是诗人精神世界的喷涌,指诗歌的原始姿态。第五句中使用的“大句”一词,与前引韩愈、孟郊《城南联句》“大句斡玄造”相通,是说能与“玄造”即天的玄妙造化之功相匹敌、具备神秘且超人力量的诗句就是“大句”。第七、八句主张,除非是持有圣贤之心的人,否则无法创作出与天的“造化”相匹敌的作品(“该”者,当也,相当、匹敌之意)。可以说,这四联诗句整体上阐述了与天拥有同等力量的诗歌的理想形态。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四句“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意谓:在达到了玄妙境地的文学中,作为作品描绘对象的万物,是作者可以用自身的力量来支配的。“我”可以理解为作者。那么,将孟郊的文学观推而广之,是否可以这样说:“有力”的诗学,就是以作者之力为基点的诗学。或者说,在“有力”的诗学中,文学作品的力的源泉乃是作者之力。
从当前探讨的问题出发,值得注意的是孟郊的盟友韩愈的《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
这里用具有足以使万物“鸣”的压倒性、根源性之力的风(“有力”的诗学范畴下的意象),来表现“有不得已者而后言”的文学创作状态,亦即一种“无意”的诗学。所谓“有不得已者而后言”,与前引苏洵《仲兄字文甫说》“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苏轼《南行前eb09f5cbff28dddc996f00d061e4525d23a42ec1d1b7a54eef95a14bf8bcfd8e集叙》“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等,也都是同一旨趣。
韩愈用激烈而强有力的风与水的意象,表现“有不得已者而后言”。由此可以见出,“有力”的诗学中具备能与“无意”的诗学相通的要素。孟郊“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也有必要从这一角度予以探讨。前文讨论“无意”的诗学的先驱观念时,曾举陆机《文赋》“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为例,实则其间所省略文字中尚有“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一联。而此联也曾在前文作为例证举出,用以论述借风与水的意象比喻文学的强力及气势,也就是立足于“有力”的诗学的观念。这样来看,“有力”的诗学和“无意”的诗学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如前举田锡《贻宋小著书》所见,这两者在同一个文人的文学观中是并存的关系。因此,在考察中国诗学史时,需要留意在“有力”“无意”这两个系谱的演化进程中相互交织缠绕的复杂脉络。
结语:与“天”同化
本文之所以将“有力”的诗学和“无意”的诗学关联起来进行比较,是因为两者共通地使用了风与水的意象。风与水充塞于天地之间,人类既必然地与之存在某种关系,它们在人类面前也呈现出诸种不同的姿态:春风习习,秋风生凉,清澈的小溪潺潺流动,宽阔的湖泊波纹荡漾……种种此类平静、适意乃是风和水的馈赠;与之相对,也存在对人类龇露獠牙的风和水,若疾风、寒风、洪水、怒潮均是。人类对前者怀有感激、亲爱之意,对后者则充满厌恶、恐怖之情。由此可见,人类对风和水抱有的情感多种多样。不过,潜藏在这两个系谱底层深处的恐怕应该是某种敬畏之心。对人类而言,它们是展现了不可及的超人且神秘的“力”和“无意(自然) ”的伟大存在。而无论是“有力”的诗学还是“无意”的诗学,本文涉及的多种文学论所用到的风与水的意象中,也都潜藏着敬畏之心。
那么,中国文人对风和水怀抱的敬畏之心最终指向什么呢?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文化圈中,人们的敬畏之心最终指向了上帝或安拉。如果要勉强举出中国文化中能与之相当的存在,应该就是天了。中国文人在用风与水的意象谈论文学的时候,其言辞背后仰视着的应该也是天。规定了中国文学根本原理的《毛诗大序》将“动天地,感鬼神”视作诗的效能,并述及天所创造的“天地”和天的使者“鬼神”,也正体现出这种思维方式。
“动天地,感鬼神”的说法,又见于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充斥于天地之间的“气”感动“物”,“物”又感动“人”的“性情”,文学于焉而生。在阐述了这一“感物说”后,钟嵘又指出,以这种方式被创造出的文学可以感动“鬼神”。透过这一表述,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宏大的循环结构:“天(天地) ”的“气”生出文学,而这种文学又感动了“天地”。更进一步来说,这种循环结构就是文学和“天(天地) ”的同化。同样地,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开头提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的质问后,接着从“并生”关系的角度再三阐述“文”和“天地”的关系。对刘勰来说,理想的文学应当就是和“天(天地) ”同化的存在。
前文讨论“有力”的诗学时曾以孟郊《赠郑夫子鲂》为例,诗中“天地入胸臆”“与造化该”所阐述的,正是与“天地”及其“造化”之功的同化。在这个意义上,第四句“物象由我裁”中的“我”,也并非现实中存在的真的作者,而是指与天地同化了的作者,是超越了现实作者的存在。因此,可以认为此诗中所体现的观念也和“无意”的诗学一样,主张优秀文学作品是超越作者掌控而创作出来的。
不管是“有力”的诗学还是“无意”的诗学,本文例举的这些文学论都立足于风与水的意象展开探究,这不正可以说,是在与“天”同化吗?
作者单位大阪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
责任编辑 陈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