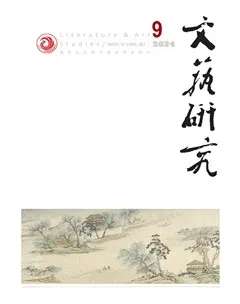保罗·德曼、耶鲁学派与解构主义文学批评
安杰伊·沃明斯基(Andrzej Warminski),出生于波兰城市格但斯克(Gdansk),1972年本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专业,同年进入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保罗·德曼。1980年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沃明斯基在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任教,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文学院副院长兼英语系和比较文学系特聘教授,出版《物质性的铭文:修辞性阅读的理论与实践》《意识形态、修辞学和美学:致德曼》《阐释中的阅读:荷尔德林、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等专著,编有《美学意识形态》《浪漫主义与当代批评》等德曼遗著。本刊特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李圣传副教授采访沃明斯基教授,并撰为访谈录,以飨读者。
一、修辞性阅读、耶鲁学派与解构主义的兴盛
李圣传 沃明斯基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学术访谈,我想先从您的教育背景聊起。1980年,您在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获博士学位,请问您的博士导师是谁?在耶鲁学习期间,您选修了哪些教授的课程?
沃明斯基 我的博士导师是保罗· 德曼(Paul de Man)。1972年,我开始在耶鲁大学读书。差不多同一时期,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Miller) 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来到耶鲁,一两年内,就有13个学生跟着他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但是,对哲学和理论感兴趣的学生,基本都还是围绕在德曼身边。我选修过很多课程,比如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 Hartman) 的“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前浪漫主义”(Pre⁃Ro⁃manticism in England, Germany and France)。这门课主要进行诗歌分析,而我本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那里我们是不读诗的,所以耶鲁的课程给了我一种全新的体验。哈特曼对诗歌有极大的兴趣,他带领我们一起阅读荷尔德林。我还上了一门文学理论课, 是拉里· 尼尔森(Larry Nelson) 开设的“比较文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德曼开设了一门关于“浪漫主义自传”(Romantic Autobi⁃ography) 的课程,主要读卢梭和华兹华斯。对于刚刚进入耶鲁的我来说,这门课可谓大开眼界,德曼在课堂上大声朗读文本并进行解读,在理论意义上提出自传的问题,这是我从未接触过的方法。课堂中涉及的部分内容你可以在《作为破相的自传》(Autobiography as De⁃Face⁃ment,1979) 这篇小文章中读到。给我们授课的知名教授还有彼得·达米特(Peter Dammit),他讲授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詹姆斯·拉尔斯顿(James Ralston) 则讲授“歌德德语抒情诗”,他当时很年轻,还没有获得终身教职,后来成为杜克大学的教授。我从未选修过米勒的课程,德曼最开始建议我不用选,但四五年之后,他又催促我说:“去找米勒,跟米勒谈谈。”因为他知道,我的论文需要米勒的帮助。德曼去世后,我和米勒之间变得更加了解彼此。我们每周都会一起吃午饭,米勒会同我感慨英语系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李圣传 当时,德里达正在耶鲁大学人文学院任访问学者, 哈罗德· 布鲁姆(HaroldBloom) 和米勒是英语系教授,德曼和哈特曼是比较文学系教授,对吗?
沃明斯基 德里达是访问学者,每年有五个星期在耶鲁大学,我们都会去听他的讲座。德里达的讲座是用法语进行的,所以英语系的学生不能真正参与其中,而我们比较文学系的学生则因为必须懂法语和德语,学到了更多东西。很可惜,在今天的美国,几乎不再有比较文学系会对语言提出这样的要求了。德里达的讲座实际上更像研讨会,每次两小时,他在法国巴黎高师的部分学生也会过来。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事实上,我后来之所以从耶鲁大学到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书,原因之一当然是米勒在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和米勒可以一起在尔湾重建一些早先在耶鲁存在的事物,比如德里达曾受邀每年来尔湾授课。
米勒此前一直在英语系,他是被德曼带入比较文学系的,后来他们都在比较文学领域工作。由于德曼的影响,米勒不想身为一个比较文学系教授而不能阅读德语著作,所以他学习了德语。至于布鲁姆,他的情况有些特殊。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或70年代末,研究文艺复兴的比较文学教授巴特利特·吉迈帝(BartlettGiamatti) 成为耶鲁大学的校长,他曾在托马斯·格林(Thomas Green) 手下学习,非常有亲和力,也很有能力。布鲁姆是他的朋友,吉迈帝任命布鲁姆为人文学部的教授,这样,他就不用去参加英语系的会议,也不需要为任何系做事,只是作为独立学者存在。因此,布鲁姆真正的影响力不在英语系,而是通过他的书影响学生,这些学生大多在比较文学系。哈特曼则对英语系的影响很大,他试图将英语系推向一个更为理论化的方向,当然也遇到一些阻力。那时候,比较文学系的规模还很小,而英语系则与意识形态挂钩,全美排名第一的耶鲁大学英语系更是如此,许多学者认为,“我们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在耶鲁大学;耶鲁大学是最好的,因为有我们”。没有人能改变他们的想法,所以哈特曼很疲惫。在德曼去世后,我们每周会共进一次午餐,他看起来都不大开心。因此,哈特曼也是在比较文学系更有归属感。
李圣传 您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期间,解构主义浪潮似乎正席卷美国,能否回忆一下当年的情形?
沃明斯基 关于耶鲁大学的种种说法,既正确又不完全正确。我在耶鲁读书时,解构主义的确作为新闻登上了《新闻周刊》(Newsweek)这样的国家级杂志。但解构主义真正意义上的出现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9年,《解构与批评》(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出版,德曼《阅读的寓言:卢梭、尼采、里尔克和普鲁斯特的比喻语言》(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Language in Rousseau, Nietzsche, Rilke, and Proust,以下简称《阅读的寓言》) 也在同年问世,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一些普及性的书籍也随即出版, 比如克里斯托弗· 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 的《解构:理论与实践》(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1982)、乔纳森·卡勒的《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和批评》(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1983)。需要强调的是,在1979年之前,我甚至没有使用过“解构”这个词。德里达本人其实在1967 年的《声音与现象》(Voice andPhenomenon) 和《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中已经引入了“解构”一词,但在70年代,他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故而对该词敬而远之。我们这些对德里达感兴趣的人大多是德曼的学生,以一种德曼式的修辞性阅读方式,阅读着欧洲大陆哲学的经典文本(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也许在80年代初,这种阅读可以被称为“解构主义的”,毕竟1979年《阅读的寓言》出版后,每个人都在阅读这本书,或赞成或批评,而“解构”在美国也变成一个时髦的词。因此,所谓“解构主义浪潮似乎正席卷美国”,其实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而在耶鲁大学,随着德曼在1983年去世,这股浪潮就几乎结束了。
李圣传 当年耶鲁大学的师生究竟是如何看待解构主义的,能否请您再详细谈谈?
沃明斯基 20世纪70年代在耶鲁大学求学的学生通常认为解构主义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生的, 那里有塞缪尔· 韦伯(SamuelWeber)、卡罗尔·雅各布斯(Carol Jacobs)、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其中,韦伯负责的《符号》(Glyph) 杂志影响深远,该杂志不仅倡导解构,还翻译和介绍法国理论,德曼和我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此外,德里达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行的结构主义研讨会上做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报告,反响非常热烈。所以我们通常认为,解构主义是在那里萌芽的。而耶鲁大学的德曼、米勒、哈特曼和布鲁姆则共同构成了一个解构主义的“小乐团”,这在当时可能惹恼了一些人。试想,当一位耶鲁大学的名教授拿起《新闻周刊》,读到一个叫“耶鲁学派”的团体,却发现自己不是该团体的成员时,他会有多生气。所以耶鲁学派被许多人批评,勒内·韦勒克就是其中一员,作为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创始人,他在我入学的前一年就已退休。但针对耶鲁学派,韦勒克及其学生尼尔森和格林等人都发表了反对意见,比如格林就从阐释学入手,试图把文学从解构主义中拯救出来。尽管当时整个美国都认为解构主义的主要阵地在耶鲁大学,但我认为,德曼、布鲁姆、哈特曼和米勒所进行的其实是一种修辞性阅读,这一共性将他们汇聚在一起,至少在那个短暂的时刻是这样。
李圣传 围绕修辞性阅读,耶鲁学派的批评家们在学术工作上的重心是什么?与德里达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沃明斯基 需要指出的是,德曼的影响是巨大的。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米勒几乎可以被视作德曼的弟子,他从事的研究正是德曼会做的。尔后,在德里达影响下,米勒的作品才开始有了自己独特的方向。布鲁姆也深受德曼影响,比如《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就是题献给德曼的,《误读图示》(A Map of Mis⁃reading) 则涉及比喻、隐喻、转喻,并试图把它们与精神分析的术语相联系。在布鲁姆的研究中,修辞学的主旨始终存在。哈特曼也是如此。这无疑是德曼的影响, 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
德曼转向修辞学是在1967年前后。当时在巴黎,人们也逐渐迸发出对修辞学的热情,代表事件之一就是尼采为修辞学课程所做的笔记被菲利普·拉古-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翻译为法语,发表在《诗学》(Poetique) 杂志上。德里达的论文《白色神话》(1971) 也充分显示了他对修辞学的关注。可以说,德曼转向修辞学与德里达对修辞学的关注是同时发生的。我不会轻易说德里达影响了德曼,其实德曼知道德里达的存在是因为他发现德里达也在阅读卢梭。起初,德曼非常怀疑德里达的研究,还曾写文章提出批评,并用自己的方式对德里达进行了一种解构式阅读,这些你都可以在德曼的首本文集《盲视与洞见:当代批评的修辞》(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Criticism) 中读到。后来人们才意识到,德曼和德里达沿着相似的路径各自独立发展了解构的思想。
李圣传 虽然解构主义起源于法国,但真正形成世界影响却在美国。我想知道的是,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为何能引发耶鲁学者的关注和共鸣?
沃明斯基 应该说,德曼、布鲁姆、米勒和哈特曼四人对德里达的作品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刚刚我们已经简要说过德曼的情况。他曾在哈佛大学接受文学研究训练,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发表过数篇海德格尔研究,而德里达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胡塞尔的,他把一般符号视为现象学还原的一个问题。德里达和德曼以各自的方式走出现象学:德曼通过海德格尔,使现象学变得激进;德里达则解构胡塞尔。因此,德曼关注德里达的作品,特别是《白色神话》及其他修辞学研究。
其他三人也非常熟悉欧陆思想。当时的米勒深受日内瓦学派(Geneva School) 影响,包括乔治·普莱(Georges Poulet)、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让·鲁塞(Jean Rous⁃set) 和马塞尔·雷蒙德(Marcel Raymond) 等人,当中又以普莱的影响为最。米勒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时,普莱是他的同事,那时米勒还相当年轻,他们每周末都会共进午餐,一起聊天,米勒自然也会阅读普莱的文章。日内瓦学派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笛卡尔式的,关于自我、作者和读者如何在文本上融为一体。米勒尽管身在英语系,研究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却对欧陆的学说和思想保持开放态度,甚至会读布朗肖的著作,德曼也会读。布鲁姆的灵感则直接源自尼采和弗洛伊德。哈特曼也很有欧陆特色,他深受韦勒克式训练的影响,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埃里希·奥尔巴赫。我不会说现象学对他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尽管他无疑读过胡塞尔,但影响更大的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在《华兹华斯的诗歌1787—1814》(Wordsworth’s Poetry, 1787-1814,1964) 一书的序言中说,“我想读懂华兹华斯的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黑格尔式的宣言。哈特曼熟悉欧陆哲学,同时对修辞性阅读抱有浓厚兴趣,因而在那一刻与德曼等人聚集到了一起。
李圣传 1979年《解构与批评》的出版被视为耶鲁批评家的“解构主义宣言”。值得注意的是,文集五位作者中,布鲁姆和哈特曼似乎并不情愿被贴上解构主义的标签。为什么?
沃明斯基 德曼和米勒肯定是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一种修辞性阅读,解构阅读也确实是德里达正在做的事情。但是,布鲁姆和解构主义的关系却没有那么舒服。考虑到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误读图示》等论著都直接受到欧陆思想的影响,我们或许会认为他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解构”。但若回顾他的作品就会发现,布鲁姆骨子里是一位美学家,对他来说,文学的价值在于其艺术价值,因此,文学不应过度关注政治和社会,审美才是其核心追求。德曼与他相反,我曾整理出版德曼的遗著《美学意识形态》(AestheticIdeology) 一书,其中有大量对审美的批判。可以说,布鲁姆想要保护的是文学的审美功能和其作为艺术的价值,所以当他看到德曼等人试图拆解审美时,肯定需要认真考虑自己和解构的关系。哈特曼则走向了一种激进的犹太主义,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被视作耶鲁犹太研究的奠基者之一,帮助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建立了大屠杀幸存者证词档案库,并撰写了关于《圣经》的著作。哈特曼有某种宗教式的信仰,如果你要追问的话,我认为他的信仰是一种解释学,即你可以通过《圣经》解释学,或者通过询问教会教父,来弄清文本的含义。这里有一种宗教的精神,即相信人可以抵达文本的终极意义。哈特曼不觉得自己与解构主义之间有什么关联,因为解构隐含着对宗教的批判,而哈特曼的思想在根底上是对宗教价值的审美辩护。所以,布鲁姆和哈特曼并不情愿被贴上解构主义的标签,他们觉得自己在从事的是一种“批评”,这也是这本书之所以叫“解构与批评”的原因。但不管怎样,他们的文章就这样被收集在了一起,成为解构主义批评的经典之作,这也是一本相当精彩的好书。
李圣传 耶鲁学派的批评家在学理上有什么共性呢?
沃明斯基 尽管四人的领域各不相同,在思想上却有一种类似的开放性,也都在欧陆哲学和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工作,正是这点让他们走到一起,共同引发了人们对修辞学的新关注。我认为,他们也分享了德曼的修辞性阅读理念,尽管他们可能自己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当然,德里达肯定也施加了某种影响,但你很难说德里达怎样具体地影响了某个人。可以用农业的方式来打个比方:土壤已经肥沃,四人都对吸收德里达的工作做好了准备,并以各自的方式开花结果。正如我所说的,那是一个独特的时刻。即使对耶鲁大学来说,拥有这四人和德里达作为授课老师,也是意义巨大的。在此之前,新批评主导美国高校,德曼和德里达令他们很不愉快,而布鲁姆虽然不是一个解构主义者,但他相当富有个性,其研究同样被视为对新批评所代表的传统研究方式的反叛。尽管如此,这些令人敬佩的新批评学者依然非常慷慨。试想,德曼、米勒和布鲁姆是如何进入耶鲁的?所有这些人都是被耶鲁大学的新批评学者招入麾下的。后者思想开放,可以从他人的研究中看到价值,他们即便不同意布鲁姆的观点,也相信他应该在耶鲁大学任职。德曼、米勒、哈特曼的情况也是如此。
二、解构主义对文学批评的意义和后果
李圣传 您可以说是在解构主义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尤其是您的导师德曼还被视为解构主义的旗手。在今天看来,解构主义给文学研究带来了什么价值?
沃明斯 基解构主义给文学研究带来的价值体现在很多层面。还是从新批评说起吧。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十分严谨,但这种严谨不是理论意义上的严谨,而是以将文学对象神圣化为基础的。他们真的相信,文学文本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客观对象,只要我们的细读能力足够好、阅读过程足够仔细,就可以读出符合政治观念和宗教价值的文本意义。解构主义则认为,相较于普通的文本细读,理解文本需要更多的理论知识和阅读方式。尤其应该意识到,在文学之外,一切都可以作为文本被阅读。解构意味着,不是所有事物都是语言,但所有事物都是文本,“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这样说并不是真的认为一切东西包括炸弹都是文本,只是为表达一种彻底的开放性。因此,以一种更严格的、更具理论性的方式阅读文本,对各种社会、政治现象采取批判的立场,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人们常认为这种阅读方式来自后结构主义,但实际上它是解构主义的遗产。
李圣传 在当代,文学研究似乎离文学越来越远,许多人认为这是解构主义造成的后果。在美国,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似乎也不再像过去一样阅读文学经典,而是从“纯文学”研究转向后殖民研究、性别研究、族裔研究等。您怎么评价解构主义给文学研究带来的理论后果?
沃明斯基 的确如此,由于解构,没有人再做“纯文学”研究。如果说结构主义建立在社会的语言模式基础上,那么解构主义就是对任何语言理论的所有可能性的解构,因此文学文本的语言结构自然不再是人们唯一关注的对象。解构主义也不是亘古不变的。一方面,可以将解构视为批判性方法。以女性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方式阅读文本,不管这一文本是文学的还是其他的,只要做得好,就是一种伟大的嫁接。譬如,我一点也不喜欢朱迪斯·巴特勒所做的工作,她的“性别操演”概念非常有趣,我却认为这一概念误解且误用了J. L. 奥斯汀的理论,因此完全不能同意她的说法。但不得不承认,这一概念又确实是对玛莎·努斯鲍姆理论极具创造性和批判性的嫁接。这样的个案还有很多,不仅是在性别研究领域,在后殖民、种族研究中,都诞生了非常好的成果。另一方面,解构也导致了广泛的身份政治,像后殖民主义这样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作为后殖民研究的开创者,不仅是德里达《论文字学》的译者,还是德曼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她知道解构主义在做什么,学习并接受了这一理论。我不会说斯皮瓦克是解构主义的背叛者,如果后殖民研究导致解构主义试图撤销的东西重新回归,那反倒才是不好的。
李圣传 因为文学研究越来越远离纯文学,当下学者们也愈来愈多地用“批判理论”代替过去的“文学理论”,您如何看待从文学理论到批判理论的这种转变?
沃明斯基 传统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重心,这是一种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而当下的批判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尔湾”式的理论。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新批评后期代表人物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 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英语系主任哈扎德· 亚当斯(Hazard Adams) 的主持下,“批判理论项目”在尔湾分校正式设立。到1974年,这一项目在加州大学系统内成功申请并建成由国家资助的批评与理论学院(School of Criticism and Theory),不仅组建起豪华的授课学者阵容,还开始在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方向上招收博士生,开美国高校之先河。亚当斯编纂出版了《柏拉图以来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1971) 一书,这本文集影响巨大。1972年我在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读书的第一年,尼尔森就订购了该书作为课程读本,直到现在耶鲁大学依然在用,我给学生上课时用的也是这本书。“批判理论”这一提法的历史本身也很有趣。克里格和亚当斯都是文学批评史家,而非真正的理论家,他们都接受了严格的新批评训练,克里格更是新批评的代表学者。因此,当他们讲授理论时,会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重点在这些先贤如何谈论文学相关问题,可以说,他们把理论当作文学理论史来教。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思想史,而非思辨意味上的理论。
李圣传 在研究和教学中,您如何看待文学理论与当下批判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呢?
沃明斯基 我们需要意识到“理论”存在的必要性。在阅读传统文学理论时,我们会发现那些关于文学语言的理论模式本身并不稳定,富有文学性的文本往往并不作为文学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是由将文本理论对象化的不可能性构成的,因此,尽管传统文学理论想要通过对文学语言的分析划定文学的边界,但我们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结构主义者则认为,可以用某些方式构建起一个稳定可靠的语言理论,如果将这种模式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我们会对对象有一个更好的理论把握,但这也就不再是文学了。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理论家总要在语言学的模式之外找到一种理论模型,以便将其应用于文学研究,比如去弗洛伊德、马克思、解释学那里寻找模型。现在的批判理论也有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的残余,它适用于任何事情,也就是说,批判理论可以是任何东西的理论。所以,“理论”的必要性提升了,而“文学性”会暂时失落。在解构主义的时代,文学理论与女性主义、性别研究以及其他运动是一回事,换言之,都是一种政治批评。这种情况下,“批判理论”这一名称可能更合适。毕竟,既然我们都不是在谈论文学了,那为什么还叫“文学理论”呢?卡勒在那本小书《文学理论入门》(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中就提到,一旦你开始做文学理论却突然不再谈论文学了,那么你研究的就是批判理论。今天,批判理论已经无处不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理论来自法兰克福学派,而当代意义上的批判理论,其源头在尔湾。
三、保罗·德曼的解构观及其思想遗产
李圣传 在中国,德里达和米勒的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德曼则相对陌生一些。您能否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德曼的主要著述情况?
沃明斯基 米勒曾多次访问中国,但德曼早在1983年就去世了,没能有机会访问中国。他自50年代起,就在法国的《批评》(Critique)杂志上发表文章,对《包法利夫人》进行黑格尔式解读。1960年,他在哈佛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马拉美、叶芝和后浪漫主义的困境》(Mallarmé, Yeats, and the Post⁃Romantic Predicament),并在其中细致地解读了叶芝的诗歌。可见,在德曼正式提出浪漫主义的修辞之前,他其实已经在进行修辞性阅读了,只不过那时他尚未意识到这点,认为自己只是在做一种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文学史研究。这篇博士论文在方法上太过哲学化,令答辩委员非常不满,也是出于这一原因,德曼没有得到哈佛大学的聘用。机缘巧合的是,康奈尔大学发现并肯定了德曼的才华,他在那里获得终身教职并受到高度重视。从1960年开始,德曼写了几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只不过这些文章是用法文写就的,其中有一篇名为“浪漫主义形象的意向性结构”(Intentional Structure of the Romantic Image),1960年在法语期刊上发表,后来,布鲁姆把它收进了一本关于浪漫主义的文集中。在60年代,德曼最有名的文章要数1967年发表的《时间性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Temporality),这是一篇关于诗歌、小说中的寓言和讽刺的论说文。根据卡勒的说法,在文学批评领域,这篇文章重印过最多次,也是从这篇文章起,作为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德曼声名鹊起。而直到1971年,德曼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 《盲视与洞见:当代批评的修辞》。其实,德曼在康奈尔大学时并未出版著作,为满足耶鲁大学终身教职的聘用要求,他才在哈特曼等人的帮助下将过往发表的论文编辑出版。这本书甚至不是关于文学本身的,而是关于阅读和批评的,关于批评家如何在他们最伟大的洞见中展示了他们最大的盲目。不得不说,如果没有专著,今天的学者无论发表多少论文、无论论文质量有多高,都不太可能像德曼一样得到聘用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李圣传 在《盲视与洞见:当代批评的修辞》之后,德曼似乎又转至对尼采的研究?
沃明斯基 是的,德曼随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尼采的文章,如《尼采〈悲剧的诞生〉中的发生学与系谱学》(Genesis and Genealogy inNietzsche’s The Birth of Tragedy,1972) 以及《尼采的行动与身份》(Action and Identity in Ni⁃etzsche,1975) 等,这些都是极富创见的文章,被部分收入《阅读的寓言》一书中。我不知道怎样书写一位真实存在的人物才是最好的,但从这些论文中,我读到了一位鲜明的德国诗人。这些论文不再是对尼采的哲学式阅读,而是一种浪漫主义式阅读。在博士论文之后,德曼的浪漫主义已不再限于马拉美和叶芝等人。其实,在60年代对浪漫主义的持续阅读和研究中,德曼曾希望出版一本讨论浪漫主义的著作,但一直未能如愿。后来, 我、艾伦· 伯特(EllenBurt) 和凯文·纽马克(Kevin Newmark) 共同整理出版了《浪漫主义与当代批评:高斯讲座和其他论文》(Romanticism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 The Gauss Seminar and Other Papers, 1992),作为德曼的遗著之一出版。zYzX8+HzCBTmW+XQoqkG1u64T2e9KgSpXxikiT9i4kw=这本书收录了1967年德曼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的系列演讲中的一部分,原本应以“不可想象的时间之触”(TheUnimaginable Touch of Time) 为名出版——这一标题源自华兹华斯的一句诗——但德曼从未完成这一工作。到了1979年,《阅读的寓言》出版。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这本书立刻在学界引发轰动,几乎人手一本,大家都试图从中学习新的方法。为此,人们甚至还研究起了符号学和修辞学。然而,真正理解这本书的人少之又少,除了专门研究卢梭的学者,或许没有多少人会把这本书读到最后。
李圣传 在20世纪70年代,德曼对尼采、卢梭等人的理论阅读和批评实践,是否已经意味着一种明确的修辞学转向?
沃明斯基 19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斯批评讲座”中,德曼受邀讲授“浪漫主义的当代解读”,其中一讲专门讨论了时间模式,这其实就是一种对特定诗歌的批判性元阅读。德曼追问文学形式的时间性并发现,海德格尔虽然严肃思考过时间性这一问题,却并未思考文学形式的时间性。在讲座的末尾,德曼回到修辞阅读和修辞风格问题上。在这一讲的一周后,他又做了一场关于华兹华斯的讲座,这场讲座的内容已经可以被视为修辞性阅读了。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反复进行关于华兹华斯的讲座,并引入了大量关于隐喻和转喻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从中窥见一种隐藏的修辞性阅读取向。此外,他对尼采为修辞学课程所做的笔记(The Lecture Notes on Rhetoric) 的译介工作也在这一时期。几乎可以确定,在1967年到1971年之间,就是德曼修辞学转向的关键节点。当人们研究德曼时,往往对德曼运用解构的方式感到不满,认为这只是对隐喻模式的延伸,对此我并不认同。德曼从70年代起明确转向修辞性阅读,他的工作自此真正启航。
李圣传 但德曼晚年似乎又从修辞性阅读转向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您能否能向我们解释一下原因?
沃明斯基 80年代初,德曼意识到自己即将离世。他开始阅读黑格尔的《美学》,并在纸上写下很多笔记(Paul de Man,“Sign and Sym⁃bol in Hegel’s‘Aesthetics’”, Critical Inquiry, Vol.8, No. 4 (1982): 761-775)。这意味着他是带着已完成的思考去到课堂的,让我感慨我在耶鲁读书的时代真是太幸运。德曼在70年代一直持续思考寓言与讽刺的问题,在当时的课堂上,一堂课整整两个小时的讨论过去后,往往什么都没解决,下堂课又是两个小时,循环往复,直到学期最后,你也不一定能完全想清楚,但一定获益颇丰。等到五个月后,德曼关于这门课程的相关论文就会发表,然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你只须将这篇文章复印下来,去阅读、讨论、争辩,思考不明白的地方。因此,在我们读书的那一阶段,教育是自然而有机的。但到80年代,德曼的思考是一种已经完成的状态。他去世后,我将这些思考整理出版为《美学意识形态》一书。德曼非常明确地称这一阶段的工作为“美学意识形态的批判”(critique of aes⁃thetic ideology)。我想这不是玩笑话,他在认真思考如何将美学批判与政治相结合。遗憾的是,德曼生前未能完成这项工作。纵观德曼的著述及学术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大致将其总结成三个阶段:海德格尔研究阶段、修辞性阅读阶段、美学意识形态的批判阶段。
李圣传 我在阅读批判理论的著作手稿和书信日记等档案材料时发现,米勒在日记中不断评述德曼的学术观点,并反复提到《抗拒理论》(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1982) 这篇文章。您能否再简要谈谈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意义?
沃明斯基 要想简要地说清楚可能很难。我教文学理论的方法就是基于这篇文章。它来自德曼对三艺(Trivium) 模式的介绍,即中世纪欧洲大学里的三学科教育模式——语法、逻辑、修辞。这是一种不稳定的语言模型,修辞在三学科间的位置神秘而不稳定。对我来说,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创造了一种讲授文学理论的方法。在德曼写作和发表这篇文章时, 其实发生了一些事情。受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 委托,原计划这篇文章将作为介绍文学理论的一章收入《现代语言和文学的学术导论》(Introduction to Scholar⁃ship in Moder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一书,但最终的发表并没有通过该书。当时,美国学术圈围绕解构主义产生了激烈争论,有一种批评认为,要防止任何将修辞戏剧化的企图,故而德曼以这样一个颇具挑衅性的标题,讨论了学术体制是如何拒绝将理论接纳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的。而与此同时,这篇文章也闪烁着对美学意识形态的批判,德曼认为传统文学批评是对世界透明的复制,这其实是将语言的运作和真实的世界混淆起来,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样态。我个人非常喜欢《抗拒理论》这篇文章,其中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精彩段落,比如那段与马克思有关的论述:“那些指责文学理论忽视了社会的和历史的(也即意识形态的) 现实的人们,只不过是在说出他们自己的恐惧而已。他们害怕被自己神秘化的意识形态,被他们试图否定的工具所揭露。简而言之,这些人并没有把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读通。”(Paul deMa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 11) 这些论述非常精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抗拒理论》这篇文章上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根据德曼的观点,如果文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讨论语言的方式,那么语言的修辞性使得文学理论文本必须无法讨论语言,任何尝试实现它自身理论计划的理论文本总是以误读告终。文本对理论的抵抗就是对语言使用的抵抗,对阅读的抵抗。没有什么能克服对理论的抵抗,因为理论本身就是这种抵抗,对理论的抵抗正是构成理论之存在和可能所需要的东西。德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不再基于非-语言的研究(即历史的和美学的研究),也就是说文学研究所要讨论的主题不再是意义和价值,而是这些文本及其意义和价值之生产被接受的方式。这也是德曼《重回语文学》(The Return to Philology) 一文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李圣传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解构主义起源于德里达,流行却归功于耶鲁学派,尤其是灵魂人物德曼。您如何看待这种思想观点?
沃明斯基 这种观点有其道理。在美国,德里达《论文字学》的译本出现得很晚。英语系的学者在文学研究中占据主导,比较文学系的声音较为边缘。因此,在美国的英语系,解构主义的传播和流行是一个慢慢普及的过程,它甚至常常被误解为拆解文本的秘密武器。当然,这一过程十分短暂,人们很快意识到解构的重要性,它是一种需要我们学习的方法。一方面,人们将解构主义从巴黎的政治语境中连根拔起,在德里达那里它也基本去政治化了。很难说那一时期的德里达与政治有所关联,他没有也不想被法国的任何一种政治立场卷入或同化。另一方面,当时英语系的每个人都接受了新批评的系统教育,他们通过阅读一些入门性质的普及读物来了解解构主义,把解构视作一种流行的新方法。直到今天,这种观点还在以某种方式延续。所以说解构主义的流行归功于耶鲁学派尤其是德曼,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弗兰克· 伦特里奇亚(Frank Lentricchia) 在《新批评之后》(After the New Criticism) 一书中也评论说,耶鲁有一个“解释学黑手党”(Herme⁃neutical Mafia),而德曼就是“教父”。
李圣传 您先在英语系接受新批评的教育,然后又在比较文学系受业于德曼、德里达等解构主义大师。您如何评价从新批评到解构主义的方法论转变?
沃明斯基 我接受过完整的新批评训练。我现在认为,这种细读法的后果往往是消极的,拒绝像新批评一样将作品看作一个完整的、美丽的对象,实际上会让我们变得更好。从某种程度上,新批评是宗教信仰的替代物。新批评学派相信,如果能够熟练运用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 和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 ——他们合作编写的教材《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ry) 在20世纪60年代一直主导着英语系——的细读法读诗,人的灵魂将会得到拯救。然而这种细读法实际十分粗鲁。如果你读过沃伦讨论柯勒律治《古舟子咏》的那篇著名文章《一首纯粹想象力的诗:一次阅读实验》(A Poem of Pure Imagination: AnExperiment in Reading, 1946),就会明白粗鲁在何处。沃伦认为,柯勒律治是出于普遍的宗教信仰才写作这首诗,而这也是一首关于宗教信仰的诗歌。因此,诗中的人物最后被解读成一名牧师,“既是自然的牧师,也是上帝的牧师”。新批评学派认为,文学可以拯救他们的灵魂,而这首诗就是他们要捧起的主人。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将人从法西斯主义中拯救出来,新批评的根源就在此,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T. S.艾略特。因此,新批评貌似在进行文本细读,假装社会、政治、心理、作者的传记都无关紧要,只是把文本当作文本来读,展示诗歌是如何关于诗歌的,最终要展示一首诗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审美对象。
至于解构主义,我看到的解构主义和美国英语系看到的不同。在20世纪70年代,我必须用法语阅读德里达的著作,我也能够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对我来说,他对哲学文本的细读非常有趣,关于柏拉图和黑格尔的讨论都极其精彩。德里达所做的,是一种系统的解构性阅读,以一种能够阐明逻辑的方式解开文本的逻辑,譬如《马刺: 尼采的风格》(Spurs: Nietzsche’sStyles) 这一奇妙的文本。他总是通过发明新词的方式来戏谑,“解构”一词就是如此。人们曾争辩,该词实际上来自海德格尔,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每当有人问德里达如何定义“解构主义”时,他都非常谨慎,有时他只是说,解构主义就是发生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在耶鲁的人文学院礼堂,德里达为了定义解构主义,用法语写了几个字——plus d’une langue (不止一种语言),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不止一种的语言中找到更多的意义,这就是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你在阅读中就参与了解构。德里达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人,他的方法艰难而又充满价值。
李圣传 您前面也提到过,德曼和德里达独立发展着各自的解构思想。那么,您认为他们在解构层面上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表现在哪里?
沃明斯基 二人都影响深远,然而我不会说他们是一样的。实际上,他们走的是平行的道路,却突然发现了彼此,具体说来,就是两个人几乎在同一时期研究卢梭,然后互相发现了对方。但也有很多不同,比如对逻辑的拆解方式,以及对文本的展现方式。此外,德曼一方面倡导修辞性阅读,另一方面又试图像他那篇文章的标题所提出的那样“重回语文学”。而重回语文学也正是德里达和解构主义在做的事情。
但是,这里又有一种奇怪的倒转。当德里达的写作越有趣、越俏皮,越呈现为一个富有文学性的德里达时,他就越靠近德曼。奇怪的是,尽管德曼是一位文学研究者,但在某种程度上他比德里达更哲学化。这一倒转非常有趣。当然,学术遗产的清理还需时间的检验,清晰地理解德曼与德里达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仍需更多努力。
李圣传 您既是德曼培养的博士,又是德曼《美学意识形态》《浪漫主义与当代批评》等遗著的整理者。与此同时,您还出版了有关德曼的研究专著《意识形态、修辞学、美学:致德曼》等。在您看来,德曼对您启发和影响最大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今天该如何阅读和理解德曼以便更好地继承他的思想遗产?
沃明斯基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德曼对于阅读和思考的不断反思。我在耶鲁的第二个学期(1972—1973), 也就是德曼在耶鲁的第二年,他给我们开设了一门“浪漫主义自传”课程。在学生眼中,至少在那些最具竞争力的学生眼中,有一股神秘的氛围围绕着德曼,令他们渴望在德曼面前展示自己。我和德曼的第一次接触有点滑稽。我当时初到耶鲁,德曼负责比较文学系的研究生工作。他询问我的研究兴趣,于是我告诉他:“我想写一篇讨论小说的博士学位论文,并在三年内博士毕业。”德曼回应道:“从来没有人做到过,但你可以试试。”因此,在“浪漫主义自传”的课堂上,我格外投入和认真,我们重点阅读了卢梭和华兹华斯。这门课程最令人惊叹的地方在于德曼的阅读和思考所展现出的反思能力。尽管一开始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但他关于自传话语和自传体裁的思考无疑是在严肃的对语言的反思中提出的。我当时内心惊叹不已,好奇他是如何做到的,并决心找到答案,试图理解德曼在说什么。这花费了我整整二十年的时间。事实上,我至今仍在思考德曼的晚年文章《黑格尔论崇高》(Hegelon the Sublime) 中萌发的关于“政治性”的话语思想。这篇文章虽短,却包含了某些德曼如果活着可能会继续拓展的内容。无论如何,德曼的教学,以及他在学生面前所展现出的对研究课题的阅读与思考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我和当时同我一道在耶鲁学习的同学。带着这些影响的痕迹,我走到了今天。我在前面也提到过,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有一个“批判理论”的传统,但是克里格和亚当斯的“批判理论”是文学批评的理论史,而米勒和我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尔湾分校从耶鲁大学引进了我们,还有我的同事伯特(她现在是法语系和比较文学系的退休教授),汇聚了一帮具有理论建构能力的学者。除此之外, 我从耶鲁来到尔湾时, 朱丽叶· 弗劳尔· 麦克坎内尔(Juliet Flower Mac⁃Cannell) 就已经在比较文学系了。她是德曼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也是一位拉康主义者。可以说,耶鲁大学背景的学者主导了尔湾的比较文学系。克里格不在比较文学系,而是英语系的学者,我继承了他所代表的批判理论传统,但又不在课堂上讲授批评史,而是讲一些文学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性阅读。在尔湾,批判理论经历了从文学批评史到理论本身的转变。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后半部分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前半部分论述文学理论和文学是如何消亡的。克里格是一位非常慷慨的学者,但他读完也认为这件事有一些讽刺:我在延续由他奠定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批判理论传统,同时却在破坏这一传统,毕竟我没有延续他的路径。我不想说自己在其中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但对我来说,这些时刻的确很有意义。从某种意味上说,这种转变深受德曼启发,也是对德曼思想的一种传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黄雨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