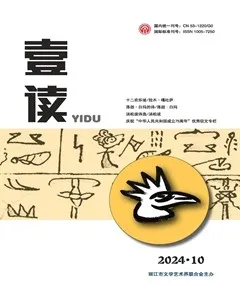谈凌叔华《酒后》女性心理的复杂变化过程
凌叔华作为新文化运动后受过现代教育的新式知识女性,在成名作《酒后》中写了女主人公采苕想要征得丈夫的同意去亲吻男性朋友子仪的一系列心理变化活动,以主人公的情绪和心理活动贯穿全文,展示出采苕复杂的心理活动和变化:本我、超我、欲望的产生、争取亲吻行为的合理化以及封建残留的意识和女性的自虐等心理。
作品一开篇,就有场景描写:“客厅中大椅上醉倒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酣然沉睡;火炉旁坐着一对青年夫妇,面上都挂着酒晕,在那儿窃窃细语;室中充满了沉寂甜美的空气。”营造出一个香甜迷醉的气氛。“而且更重要的是人是醉的:子仪是因为饮了过量的酒而真醉,永璋则是因为人而醉,采苕之醉非关乎酒而系于人。”在人人皆醉的情况下,采苕对子仪的关心已然超越了对丈夫的关心:“等我拿块毛毡来,你和他盖上罢。把那边电灯都灭了罢,免得照住他的眼,睡的不舒服。”“轻轻的给他脱了鞋了罢。把毡子打开,盖着他的肩膀和脚,让他舒舒服服的睡觉。”而丈夫都一一照做,只是丈夫也流露出对妻子忽视自己的些许不满,他提醒到:“采苕,我也醉了。”这句话大可以挖掘出深层含义:我是你的丈夫,我也醉了,你也该如此照顾我。而采苕却反驳说“你没醉”,可以体会出她并不想像关心子仪一样关心丈夫。此时丈夫在察觉出妻子的冷淡时,开始故意找话,先是说采苕脸上的红晕不像桃花、牡丹、菊花、梅花,又说采苕的眉不能形容为远山、蛾眉、柳叶、新月,再说采苕是仙子下凡他千金不换。他的滔滔不绝,并不能博得妻子的好感,甚至被妻子认为是“吵醒子仪”的存在。永璋的聒噪与子仪的安静“他的容仪平时都是非常恭谨斯文,永没有过像酒后这样温润优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得“采苕内心对于子仪的倾慕,由前面的关注上升了高度,感情愈加浓烈。”
采苕在醉的状态下,“醉的状态会引领人进入‘本我’超越‘自我’之中。同时,这种‘本我’在外界压力下或内心的压抑中只有醉后才能得以显现。”关于“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解释,百度百科收录大致如下:本我:“简单定义:依据理论,本我代表所有驱力能量的来源。本我是在潜意识形态下的思想,代表思绪的原始程序——人最为原始的、属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如饥饿、生气、性欲等”;自我:“简单定义:是自己意识的存在和觉醒。其作用主要是调节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它一方面调节着本我,一方面又受制于超我。它遵循现实原则,以合理的方式来满足本我的要求。”;超我:“简单定义:本我的对立面是超我,也就是人类心理功能的道德分支,它包含了我们为之努力的那些观念,以及在我们违背了自己的道德准则时所预期的惩罚(罪恶感)。”采苕的内心充满对子仪的强大感情,在她眼中的子仪是“恭谨斯文”“温润优美”,并且拥有她所青睐的舞文弄墨的丰姿。在醉态下,采苕的超我对于本我的克制和约束显得力度不足,于是采苕也敢于向丈夫吐露自己对于子仪的倾慕:“我自从认识子仪就非常钦佩他;他的举止容仪,他的言谈笔墨,他的待人接物,都是时时使我倾心的。”“他哪一样都好!”等等。不仅敢于向丈夫倾诉对另一名男子的爱慕,也敢于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闻一闻他。没有肢体接触,只有两人距离的拉近,这个行为虽是采苕本我的展露,但这个行为并没有非常失礼,还算是在采苕自己作为一个从封建社会女性过渡到新式知识女性能够允许的道德范围内。但丈夫错听为“亲吻”,而采苕也没有纠正错误甚至采取了默认态度,可以体味出采苕并不拒绝从不失礼的朋友行为(闻一闻)到略显亲密的男女行为(亲吻),这是采苕本我的进一步表露——对子仪存在欲望。
王亮在《“醉”与“欲望”——从精神分析视角解读凌叔华的<酒后>》中提到:“用拉康的话来说,欲望是‘从说出来的需求与需要的差异中产生的,它无疑是主体在其要求中说出来的需要得到满足后仍然缺乏的东西’……对于采苕来说,丈夫或许可以满足她的物质上的生活需要,但不可能无条件地满足她对于爱的要求。这两者之差让她产生了一种欲望,而沉睡中的子仪就成为了这个欲望投射的对象。”丈夫能满足她的物质需求(“给你想要的东西,花钱我是最高兴的”)却满足不了她对于爱的全部需求,比如说采苕的“天生有一种爱好文墨的奇怪脾气”,丈夫是没法满足的,而能满足采苕这一奇怪脾气的只有“有着丰采言语”的子仪。无疑,丈夫给了采苕很多爱:甜言蜜语,金钱,甚至允许她去亲吻男性友人,但是恰恰是无法满足采苕那“爱好文墨的奇怪脾气”,欲望就在此发芽。
但采苕却把这欲望掩饰得很好,亦或者是把这欲望包装成其他的情感。张君在《凌叔华小说<酒后>中的女性意识》中提到:“采苕试图用更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温柔情感’来遮蔽内心‘感官肉欲'的成分。也正因为这种辩护,采苕的越轨之举得到了丈夫的体谅和允许。”而实际上,采苕对子仪确实存在感官肉欲,除却上文分析的欲望之外,原文中还有更直接的视觉描写:“此时子仪正睡的沉酣,两颊红的像浸了胭脂一般,那双充满神秘思想的眼,很舒适的微微闭着;两道乌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鬓角分列;他的嘴,平常充满了诙谐和议论的,此时正弯弯的轻轻的合着,腮边盈盈带着浅笑……”而子仪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生理反应:“采苕怔怔的望了一回,脸上忽然热起来。”很明显,采苕要么是害羞要么是动情。而无论是害羞还是动情都是由于子仪此时的温润优美的形象对采苕的感官(视觉)造成了刺激,从而在超我放松对本我的克制与管束下,欲望透露出来:闻他或吻他。虽然因为“醉”的状态,本我更多地被释放,但超我并未完全丧失管束本我的能力,采苕还是想要为自己的欲望寻找一个较为合理妥当的借口,那就是:“他处在一个很不如意的家庭,我是可怜他”,“一个毫没有情感的女人,一些只知道伸手要钱的不相干的婶娘叔父,又不由得动了深切的怜惜。……他真可怜!”,“愈动了我深切的不可制止的怜惜情感”,总归起来就是对子仪这样一个风姿卓绝的人却有这样一个不如意的家庭的悲悯和怜惜。在张君的观点中,在采苕的辩解中,这种怜惜近似于母亲对孩子的温柔情感,是一种近似于母性的表达。我并不是很赞同这个观点,因为在原文中有“……就是子仪,你也非常爱他,……”以及“夫妻的爱和朋友的爱是不同的呀!”,可以看出采苕的辩解实际上更多地是把这种怜惜归结于对朋友的怜惜,或者是对一个有着绝妙文采却有不幸家庭,甚至还在新年时分醉倒在自家的这么一个个体的疼惜。那么这个亲吻,就可以更多地包装成是一种安慰对方和表达自己疼惜的方式,就像朋友之间的亲吻,传递友好和善意的情绪一样,而自己真正的欲望就被刻意地隐藏和掩饰起来了。
而在去想要亲吻子仪的过程中,采苕一直都在请求丈夫同行。李一媛在《本我·诗意·和谐——凌叔华<酒后>女性意识解读》中指出:“采苕其实清醒地认识到对子仪的这种情感体验和行为在现实世界中是非伦理和非合法性的,在人们的伦理观念中是不会得到认可与同情的。但是采苕还是希望在正常的秩序下使这种‘本我’意识合理化,于是她把问题直接抛向有人伦关系的丈夫的身上,她要求丈夫尊重她的情感体验,尊重她来自生命本能的欲望,以获得人格的平等。”即采苕想要这不被伦理观念认可的情感体验和行为得到自己有人伦关系的丈夫的认可,也就是所谓的外界的肯定和安全感的给予,让她能够减少去亲吻子仪的罪恶感,并且要求丈夫尊重自己的情感体验、本能欲望和人格平等。另外,张君的论文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在潜意识中,她认定自己的行为是越轨的,是不合道德,不合秩序的。所以,她需要得到象征秩序与法律的丈夫的允许,……丈夫就象征着秩序与法律中的‘抽象的父亲’”,“父亲”在孩子们眼中意味着权威和规则,是不可违逆和抵抗的存在,若是与之相悖就是大逆不道。张君在此处用了“抽象的父亲”一词,意味着丈夫是采苕心中的道德、秩序和规范的底线,而采苕亲吻子仪的行为本身已经是越轨的,她惶惶不安,需要得到这条“底线”的承认——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可见,张君的观点是采苕亲吻子仪的行为需要得到丈夫这一“抽象的父亲”的允许,而李一媛的观点则是使“本我”意识合理化并且追求人格平等。虽然二者的观点都根植于采苕需要得到丈夫这一外界存在的认可,但我还是更倾向于赞同张君的观点。因为若是李一媛的观点成立,采苕“要求丈夫尊重她的情感体验,尊重她来自生命本能的欲望,以获得人格的平等”就不会在征得亲吻请求后还一直祈求丈夫陪自己过去并且要求丈夫“我心跳的厉害,你不要走开。”她应会显得更加自信和更加独立,因为她要做的是一场在男权社会中呼吁女性的尊重和平等的反叛运动,绝不会畏畏缩缩地要求丈夫陪着自己不要离开。所以我认同张君的观点,采苕在前去亲吻子仪的路上要求丈夫的陪伴是因为这个行为需要得到象征法律和秩序的“抽象的父亲”的认可。
而在小说结尾,采苕从“心跳的速度愈增”“脸上奇热,内心奇跳”的状态变为“一会儿她脸上热退了,心内亦猛然停止了强密的跳”到最终放弃能够亲吻子仪的机会,反映出来的是由于新式女性思想的不彻底性、封建思想的残余和女性自己的受虐倾向,导致女性本我超越自我的时间非常短,最终还是在封建思想藩篱的禁锢下无法做出亲吻自己倾慕的男性的行为。张君的观点为:“不仅反映了男权社会所规定的社会秩序以及所形成的女性角色定位对于女性的压抑,也反映了女性受压抑的地位不仅仅是男权制社会所强加给女性的,更是女性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所自主选择的,而这也就形成了女性主动的‘受虐'地位。”即这种女性被压抑本我的地位不仅是由于男权社会更是女性自己主动的;冯娣在《凌叔华小说的怨恨心理》中提到:“采苕身上传统社会教化的道德规范,最终还是‘战胜’了女性本初的生命感。……采苕是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女性,……但她还是一个带有封建礼教残留的女性,当情感即qDqNzLDcLZ9hIQgD3Gt2S57Y2W6pgFPTLgtwk+I+GIU=将挣脱捆绑时,来自传统的主导价值观又将它粉碎。”即现代思想还是超越不了封建礼教残余的思想;冯晓青在《凌叔华小说对女性心理的艺术观照》中采苕想去亲吻子仪最终却却步的解释是:“小说刻画了特定的历史时代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女性的特征。”;洪莲在《浅析凌叔华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心理特征》中提出:“五四时期受过新文化影响的知识女性,大胆袒露自己的想法,体现了五四后新女性正视人格独立、自由生活的新追求。……体现了即使是新女性还是无法冲破自我禁锢,这个自我禁锢来自传统意识里封建社会的外部规则,作为女人要‘恪守妇道’”;而张宁的观点则是从自我和本我的角度出发:“她应该感谢于酒后的醉,使她吐出了真言,使她长期压抑的本我暂时超越了自我。可是‘本我’本身的不彻底性导致了这种‘超越’是如此短暂……当‘本我’要对自我进行超越之时也要刻意看一眼周围的社会环境了,并且要仔细认真地看。”这些学者的观点都基本一致,即采苕这个还带着封建礼教观念残余的不完全的新式女性无法翻越内心的禁锢和藩篱去亲吻子仪,所以最终却步。
总之,即使采苕在“醉”的状态下超我放松了对本我的审查,对子仪的倾慕表现为欲望并想把这种欲望包装为更为合理的朋友之间怜惜的“温柔感情”,并争取外界象征法律和秩序的“抽象的父亲”的准许,采苕最终仍然无法跨越她作为有封建礼教观念残余的新式知识女性心中的那一道屏障,最终放弃亲吻的机会。这一心理变化过程复杂且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