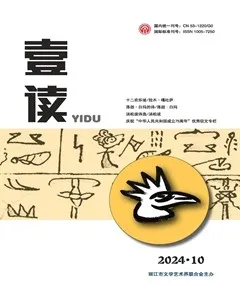远山更在远山外(组诗)
骨头里有一块块铁鸣叫
秋风把一棵树一座塔吹斜
把一个人的影子扶正
把牛角羊角吹弯,然后钻进去筑巢
一夜之间,就是山里山外
就是红脸白脸,就是前世今生
大菜市的吆喝声熟透,冰凉
夹带着几片未落的黄叶和虫鸣
我的身子里有个轮子慢下来
我是人间草木
整个秋天的霜都降在小村子里
降在井台,马眼睛里
降在一个个小时候的名字上
降在我的小小诸侯国,我的江山
村子离月亮不远,比霜白
墙角下
一直加紧地下活动的鬼姜蔫了叶子
妈妈拎起镢头三下五除二
将正要潜逃过墙的一干人等一网打尽
酱泡,盐腌,煎炒,全凭一人发落
炊烟逆势上扬,要趁早洗白天空
早起下地的人,镰刀崩出豁口
骨头里有一块块铁鸣叫
石头含霜,赶远路的人抱紧身子
一夜白头
南瓜记
一只南瓜的一生
和一个人的一生,何其相似
童年,开出一朵懵懂的花儿
不时冒出无拘无束的笑声
灯盏样精致金黄的花
捧着二月天
夏天的雨水多了
褪掉头上的蝴蝶结
偷偷结出小小青涩果实
它少年的愁绪
是不知道自己能长多大
它猜不透蜜蜂的秘密
它读不懂蝴蝶的爱情
秋风起了,绚烂渐渐归于平淡
一天天装满它的内涵
它低调内敛,不与秋风争宠
天气寒凉
它抱紧自己挡住身外的风霜
第二天一早,忽然发现自己
一夜之间,羞涩地红了
把那阳光,永远地留在了自己身上
谁笑到最后
谁就迎来了第一缕春风
它成熟后的甜,起于一段苦涩的童年
和蹉跎的青春时光
当初开花的地方,是童年部分
硬硬的,能敲出一生的回响
小村记事
炊烟翻捡一天里最后的光阴
鸡鸭鹅狗嗓子里有一条回家的路
点起灯火,碗里饭菜明亮
小村子在上一场白雪里落下
更小,更瘦
等着归人
溜进门缝的月光被冻住
现在先用
一两声咳嗽
与影子对坐
电视里过着理想生活
被一遍遍调出雪花
用别人的悲欢取暖
逼出自己体内的黑暗
默念一个人的名字
用掉夜晚
火炕很热,身子是一块石板
很快在鼾声里褪去了火盆的灰烬
故乡是一只回不去的鞋
风吹故乡,故乡草长
月亮埋头吃草,露出宽宽额头
喊着庄稼草木鸡鸭牛羊的名字
风吹啊,用方音
把故乡和乳名一天天喊大
短笛横吹,长箫竖吹
一定要重新吹一次
每一次都吹出不同的我
不同地爱一次
弯弯的风,故乡的外一首
吹进母亲的骨缝,把母亲吹弯
把母亲的头发吹白
白发不断起落
像她一连声的嘱咐和叮咛
她似乎要将手里的风洗白
风吹,不断地吹,吹出我的青草味
把我也吹成一缕风了
拍拍身上的尘土
我却不知道该属于哪一条磨损的衣襟
故乡是一只回不去的鞋,不怨路不平
埋头在一片树荫下,如一只知了
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一棵蒲公英
要顶风找回失散的孩子
故乡的倭瓜爬过了墙头
提水人桶里晃动个月亮
卷心菜收回层层包裹的小心脏
弦上晚来风紧
离家人比乡间小调走得慢
我比风更凉,走累了
靠上你的肩膀
小脚的奶奶
小脚的奶奶能说会道
把世事看得很开
很多道理被她一说
就明亮了
地瓜地走出个山里人家
挨饿年月
奶奶和爷爷用一块地瓜地
养活了一大家人
又像一只地瓜秧,结出串串后代
这些地瓜姓王,我的生命里
就总洋溢着地瓜的香气
如今
奶奶和爷爷已睡在地瓜地旁
阳光照临地瓜地
爷爷奶奶,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
他们通红的面庞,向我飘来
小脚的奶奶会经商
把爷爷织的粮口袋
卖到了山里山外
那些口袋多年装着暖心的话
一张口就说出了粮食的香味
可小脚奶奶走了这么多年
好像还一直为我们挣着口袋
不识字的小脚奶奶
留给我的课本一遍遍读不完
读湿了星星,读矮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