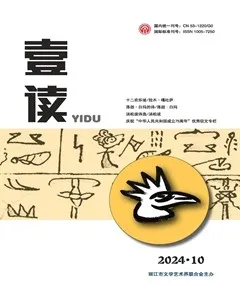写在群山之上
一
大约初中毕业前后的某天晚上吃晚饭时,父亲抱来一堆书,说是学校某某老师搬家时准备当垃圾扔了,碰巧遇着就全要来了。什么书都有,五花八门,很少看到过这么多的课外书,连饭都顾不上吃就读了起来。有一本书名叫《你想成为一名诗人吗》,当时随意翻了翻,一下就被深深吸引住了。之后如果说我与诗歌有缘的话,可能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上师范学校时,学习压力也没那么大,有很多时间可以一整天地泡在图书馆里。图书馆里的诗集大都是世界名著,厚厚一大本。说实话,云里雾里的,看不懂。包括学校阅览室里的那些诗歌杂志,也是云里雾里的,看得我昏昏欲睡。总是想不通,为什么诗歌就非得玄虚、不能说人话呢?当时我自己认为好的诗集,好像都是从路边的旧书摊里淘来的。总感觉“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的作品更好读。
直到2001年来宁蒗工作,第一次接触到时任宁蒗县财政局局长的鲁若迪基和其他小凉山诗人们的作品,我才发现:哇,原来诗歌还可以这样写。简单、易懂、口语化,而诗里的意境却让人回味无穷。这才是我一直追求的诗歌应有之态。
当时单单宁蒗县财政局一个单位里就有好几个诗人,有的是局长,有的是总会计师,有的是部门主管,都是管钱的专家,钱的味道和诗的味道、现实派和浪漫派就这样互相交织着,弥漫在财政局院子的上空。那时县里开“两会”,财政局局长和发改局局长还要在会上念财政预算报告和计划报告。时任县长的沙万祥跟时任财政局局长的鲁若迪基调侃道:鲁若,你干脆用诗歌来朗诵财政预算报告吧,标题就叫:“赤字啊赤字!”当时,宁蒗县财政收入才几百万,财政支出却超过几千万,真的是赤得一片通红。后来聊到这事时,已经成为我的上级领导的鲁若迪基说,当时就完全依靠“向上跑”,跟省里要钱。以普米大汉的酒量加上《小凉山很小》和《1958年》,整个县的赤字才算“抹平”。
他的《小凉山很小》,在当地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高度。后来被一位大凉山的彝族歌手编成歌,在宁蒗传唱至今。特别是在外求学、工作的宁蒗人,百唱百听皆不厌。听说这首诗曾被外地的某个诗人“抄袭”过,活生生把“小凉山”名称换成另一个地名,就变成了一首“名作”。殊不知,《小凉山很小》因为有“小凉山”才出名,没有“小凉山”了,换成什么山也都是沐猴而冠而已。
被称为云南“小凉山”的宁蒗县一直都是国家级贫困县,直到我来宁蒗工作二十年后才摘掉这个帽子。小凉山虽贫困,但有两样最出名,一个是东西部教育合作的“宁海模式”,带动了一大批贫困学子改变了命运,2020年还获得国家脱贫攻坚奖;另一个就是“小凉山诗人群”。就这么一个小县城,出了许多在全省全国都很有名的诗人。有3人获得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有多人获“边疆文学奖”、“云南日报文学奖”、“文学界诗歌评论金石奖”和云南省文艺创作基金奖、云南省文艺界“四个一批”人才“文学创作新人奖”、“少数民族文学之星”等等。小凉山诗人群与昭通作家群,被评论家认为是云南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广泛关注的以地域命名的两个作家群。
“小凉山诗人群”正式命名也是近十来年的事。2006年,有人提议,这么多人了,是一个大家庭了,应该有个名字才行。于是,这一群有着共同爱好的人聚在美丽的泸沽湖畔一起开了个会,从此这个大家庭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小凉山诗人群”。随后,每隔一两年,大家都会聚在一起,每人一两首,合起来出一本合集,至今出了五六本。书名也从未改变,叫《小凉山诗人诗选》。有时候,在国内有影响的刊物上开设专栏,大家一起以“小凉山诗人群”名义亮亮相。一个总人口只有十几万的小小县城,能有这么多诗人,着实让人料想不到。我很惊讶是什么东西给予了小凉山这片土地那么多灵性,“小凉山诗人群”里总是冒出几个新人来,好像雨后的小凉山深山里从不缺少松茸和鸡枞一般。这个群体数量大概在一百人左右,至今没有谁正儿八经统计过,也没有什么门槛。只不过平时嘛各忙各的,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战”时谁登高一呼,哗啦啦,从四面八方冒出来,满山遍野,像古时的“寓兵于农”。
十几年前,丽江电视台做了一期“小凉山诗人群”专栏采访我时,我说“小凉山诗人群”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个的个体的简单相加。整体大于个体的总和。就像一个家庭,有父母,有孩子,也有老人。“父母”(六零七零后)支撑着这个家庭的运转,是核心,是支柱;“老人”们(五零后之前的小凉山诗人们)不怎么露面,但他们是这个家庭的摇篮;孩子(八零九零后,也包括零零后)的性格不尽相同,成长得也各不一样,但都得到家长们的呵护。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家庭会源源不断接纳新人,而且新人也源源不断地涌现。
这个群体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一路生花,自带一股强大的吸力,如木星一般,总是把大家吸引在“小凉山”这三个字的周围。它是我们的身份,是头衔,是割不断的血脉。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好像都与“小凉山诗人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不连着就那里连着,割都割不断。
二
2009年,我在宁蒗县广播电视台工作时,在没有一毫一厘经费的情况下,创办了一本新闻时评类的内刊《新闻与评论》。先是每月一期,后来经费紧张,改成双月刊,再后来经费又紧张,改成了季刊。在无经费、无人员、无办公地点的“三无”情况下,还是坚持了下来。一年后,在众多读者的建议下,改成了纯文学内刊,名字也改成了《宁蒗》。我从《县志》里找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亲笔写的“宁蒗宝地”中“宁蒗”二字,作为这本刊物的“亲笔题名”。从封面设计、内容编排、文字编辑到审核、校对和发行,基本都是我们一群文学爱好者,一边学习一边摸索搞起来的。每期印好后,我们会抱着杂志给每个单位挨家挨户送。后来,发行范围也从最初的县内扩展到县外,扩到市外。我们所有编辑,包括我这个自封的“主编”,都是没有酬劳,作者也是没有稿费,就寄一本样刊代为稿费。而印刷用的经费就只得想办法筹集。为了找一家价格便宜的厂,我跑丽江、跑昆明,连续换了四五家,最后才固定了昆明的一家印刷厂,价格便宜质量也可以,每个月两千元左右。经费主要来自“化缘”所得,每次我们会带着一堆杂志,利用我的电视台台长的身份,跟县直单位的一把手们要个几百上千的小钱。给多少不计较,只要给就行,是当时我们经常“磨”他们的招数。两百三百,那是常态,遇上给两三千的,那个兴奋,从他们办公室门口出来时感觉轻飘飘的。当然,当“叫花子”的事是叫上我的几个电视台的同事一起去的,叫上“清高”的文人们肯定不会干的。每每看到通过自己努力而诞生的崭新的一期《宁蒗》杂志摆在眼前,闻着那些刚出炉的新书散发出来的淡淡的书香味,好像再多的委屈和误解都值得。
我在编《宁蒗》内刊之初,定位就是办宁蒗人自己的杂志,重点刊发的对象是“小凉山诗人群”。后来许多人提出改版意见,但这个初心始终未变——不遗余力致力于推介“小凉山诗人群”这个品牌。每期推一位小凉山诗人群诗人,封面刊登这位诗人一张大大的近身照——我们戏称为“封面诗人”,然后正文里开设了一个专栏,专门介绍这个诗人的创作情况,刊登代表诗作以及评论家对这位诗人的评论。另外,作为补充,还开设了一个栏目,专门介绍年轻的诗人或新发现的诗人,或者单纯是为了激励新人而刊发——自家人写得再不好毕竟都是自家人,别人写得再好终究是别人。
当时,还专门为宁蒗在外读书的大学生出了一期专刊,封面是所有作者的照片,大小不一、密密麻麻,像夜空中璀璨的群星。当然,这群大学生的作品,诗歌类占了一半以上篇幅。如今许多活跃在云南诗坛的“小凉山诗人群”中九零后诗人,当时都曾在这本专刊里闪烁过。
如今,小凉山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总是在国内大报大刊上惊现我们并不熟悉的诗歌创作者名字,我们就像在茫茫森林中发现了一朵松茸一样,自然而然地把他们拉入“小凉山诗人群”。也没什么“入群”仪式,只要一“出现”就被“变”成我们的人。我说,“小凉山诗人群”,从不会断代,他们会一代接着一代传承下去。
2015年,我在宁蒗县文广局任副局长时,以《宁蒗》内刊编辑的身份获得了云南省优秀编辑奖。第二年,调到丽江市文联工作。从县里调到市里来并不容易,我想与我创办的《宁蒗》有一些关系,也与我默默地一直坚持做“小凉山诗人群”幕后工作也有关系。每个群体都需要冲锋在前的勇士,也需要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
三
2016年是我诗歌创作的“爆发”年。一年里大大小小诗歌创作了两百多首,基本每天一首。灵感忽现,一首诗立马就出来了。当时感觉写得很顺手,一点也不卡壳,等灵感在脑子里一闪现,后面的句子随之而来,水到渠成。那一年的感觉就好像我脑子里的水龙头突然被谁打开了一样。有可能每个诗人都是一座“活火山”,也有那么一两年是“爆发”期吧。挑一些自己觉得好一点的,投给《民族文学》《星星》《诗选刊》《边疆文学》《滇池》,发了一些。当然,绝大部分石沉大海。幸运的是有的还选入《中国诗歌年度精选》《中国少数民族作品选》《中国青年诗人诗选》,入选国字头的选集,感觉蛮好。至于剩下的作品,一直到七八年后的今天,我还在固执地、不断地投。好像一只在空树干里藏了许多板栗的松鼠,每天偷偷拿出一颗,直到另一个丰收季节的来临。
而有灵感的仅仅这一年,后来偶尔来一首,自己感觉也没有那么好。可见灵感对写诗是如此的重要,至少对于我是这样的,没有灵感写出来的诗,像是没到秋天就被风打落的果子。再加上后来被下派到村里当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压力更重,每天睁眼闭眼都是贫困户,天天都感觉身心疲惫,好像一个没气的篮球一样。
驻村四年多,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感觉很是对不起“小凉山诗人”这个身份。有一次,我在朋友圈发感慨时,一位多年的朋友、也是“小凉山诗人群”的重要成员之一、宁蒗县作协主席李永天在我的朋友圈写了这么一条评论:
“你不是没有作品,你是把诗写在了小凉山的群山之上。”
我为之一震,好像确实如此——也貌似为自己的“失职”推脱“责任”——但不管怎么说,如果说脱贫攻坚是一首写在群山之上的诗,一点都不为过。
这确实是一首深深写进大山骨头里的诗。
每行诗句,都表达出外人无法理解的艰辛。那些深深地留在每一条进村路上的脚印,甚至用生命和鲜血,使这首诗变得惊天动地。跑马坪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长沙天文,沙力村总支书杨大林,以及全国牺牲在扶贫一线的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们,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歌颂了这个时代的光荣,他们是用那金黄色的铁锤一句一句地把诗镌刻在共和国的群山之巅。
2017年3月,我刚被派往宁蒗县翠玉乡春东村驻村时我就想,如不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哪怕很小的实事,以后回去了人家问我驻村这几年做了哪些事该如何回答。第二年,我成了第一书记、工作队长,还挂职乡党委副书记。有了这些头衔,我为老百姓办实事就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尽心尽力为群众办事的初心和坚持,一年后得到了回报,大家都觉得这个戴眼镜的队长是个实在的人,对我的称呼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从“队长”变成了“干儿子”“亲家”“兄弟”。
扶贫工作是艰辛的。有一次,有个喝了点酒的村民,站在路边往我们正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的车子吐口水骂道:人嘛天天来下乡,路嘛不给修一下。这个吐口水的,后来有一次我们去他家走访,完了拉着我们不让走,说现在路也修好了,水泥路都打到家门口,产业也发展了,这几年你们为了我们老百姓的事受尽委屈,必须在他家吃一顿饭再走。那天晚上,我们喝干了他家的一大坛自烤酒。
2019年,丽江广播电台记者胡世芳的一篇叫《老百姓的“干儿子”》的报道,使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许多朋友都戏称我为“春东的干儿子”。这篇报道我的文章不长,写的事也不多,却被春东村的许多老百姓在微信里不断转发,也获得了许多点赞和好评。从那次才发现,自己的坚守没有白费。2020年,市里安排采访团到宁蒗县采访脱贫攻坚,县里推荐我作为第一书记代表接受采访。几天后,丽江电视台记者闵志龙打电话给我,说我的事迹素材被央视的一位编导看中,要重新采访,而且要在“五四”青年节那天作为青年代表播出。当时都快五月份了,却突降大雪,使我的工作看起来似乎平添了几分艰辛。几天后,节目在央视《新闻联播》《新闻30分》《午夜新闻》以及云南台《晚间新闻》、丽江台《丽江新闻》播出。节目播出那天,有好几个村民激动地打电话给我,好像看到自己的某个亲戚上了电视一样。
2020年10月,经过半年多的倒计时,宁蒗县终于迎来脱贫攻坚第三方评估。验收结束那天,我们躺在村子边的林子里,安心地睡了一个下午。我反复念道:没想到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就这样在一个安静的午后结束了。始终无法相信,辛辛苦苦了五年的工作,突然间结束了,像做梦一样。感觉从那分钟起,看见路人的脚步似乎放慢了许多,吹到脸上的风似乎也轻了许多,连天上的白云也暂停不动了,好像这个地球突然停止了转动似的。
验收完第二天一早,村子里有一位老乡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要回去了,回去之前务必去他家坐坐。我说不会马上走,还要等北京的习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脱贫了,我们才能走。之后一两个月了,我也没去赴约。喊了我几次,我都以各种理由推掉后,他干脆“先斩后奏”,跑到街上的饭馆订了一桌饭,然后打电话给我说:“现在脱贫了,我代表全家请你喝一杯酒,这是我一家人的共同心愿,饭已经上桌了,退是肯定退不掉了,这次务必赏脸。”他的名字叫熊文,是一家七口人的“顶梁柱”。曾经因母亲患病去世,兄弟又得大病,差点拖垮了整个家庭。经过国家的帮扶和他自己的努力,现在家里每年收入达十多万——他的事迹曾被新华社云南网报道过。2020年,他向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乡里高度重视,单独给了他们村一个指标。他家脱贫到致富这一过程,我一直是见证人和参与者。
我的同事们写了许多关于我驻村的文章,黄立康的一篇散文《木呷的身份》,写得入木三分,把我媳妇都看哭了。我媳妇问我黄立康是你的什么人,怎么对你了解得那么透彻?儿子说他写得不对,做那些造句题时我没有想这么多,也没“靠在椅子上,看向窗外……”随后,我们都哈哈大笑。那是一种放开心思的大笑。大笑间,我突然想起与我们一起并肩作战过、已牺牲在扶贫一线,永远留在那儿的战友。他们,没有写完自己的这首诗,却把自己永远铸成了中国脱贫史诗上最明亮的诗句。
但是,这首诗,至今谁也没有写完它。
你看,那满山遍野的索玛花之绽放,白雪之皑皑,是不是像一页页洁白的稿纸,在小凉山群山之巅缓缓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