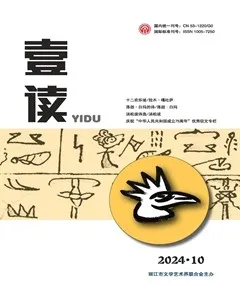垂直下落的雪
开头已是结局,人生不过倏忽而已。
——题记
一
倒计时,从十默念到一。大约又过了四五秒的样子,电脑屏幕右下方的数字才从59变成00,11月12日,新的一天开始了。我将电脑息屏,站起来走到窗边,心里对自己说:生日快乐。
长春的夜晚,大雪漫无边际地下着,寒风把窗子拍打得噼啪作响。透过水雾弥漫的玻璃看去,外面昏黄路灯下的雪花四散飞射,像粗盐,一粒粒狂乱着,相互碰撞,或打在一些树、公寓楼、地面、车辆之类的物体上,使它们遭遇成倍的风雪摧残,风中不时传来“咔嚓”的断裂声,有时是“咣”的倒地声。风稍静些,雪也下得柔和了,像下面条一样,簌簌往十楼底下的地面瘫软下去。其中有一捧雪很大,掉落的速度也更快,也许是更重的缘故,它还包裹着其他东西,可能是树枝、瓦片,或窗木什么的,我看得模模糊糊。那么一大团雪直直往下坠落,只听“嘭”的一声,雪团就砸在了坚硬、结冰冻僵的地面,散开了。
我不禁打了个哆嗦,想起尚未完成的论文,心里就直犯冷。按照我的预算,大概还有一两万字才能写完初稿,一个硕士论文,八九万字已经绰绰有余。现在,是彻底写不下去了,紧绷的线终于断了,我不停叹息,心跳就没有正常过,尽管是凌晨,头脑昏昏沉沉,但就是睡不着。我没敢打扰导师,实际上,我已经两个月没有联系他了,按惯例,只要我不主动联系他,他就不会想起还有我这个学生。
我真想推开窗子跳下去。想起江学长曾对我说的这句话,那时他正为他近三十万字的博士毕业论文而焦躁不安,我坐在他对面,将夹起正要往嘴里送的土豆片停在嘴前,一脸诧异地看着他。按我对他性格的了解,他绝不会对我开这样的生死玩笑,他老实,近乎迂腐,就像我村里人背地里说我的一样:读那么多书,都读傻了,有什么用?对这样的言论,我从来不屑,我天生话少,也不会跟他们辩解,但我有时竟觉得这样的评论无比贴切于江学长。大多数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痴痴的,木讷、沉默寡言,除了在导师办公室、图书馆、食堂,就是关在寝室,有时我去找他,发现他一个人对着窗子低声自言自语,因为久坐而长成一副臃肿的身体,远远看着就是一个傻子样。我有些担心他,透过火锅的热气,我看到他那张因熬夜写论文而苍白、憔悴的脸,上面布满了凄凉与绝望,他才三十一岁,但已经头发稀疏,头顶正中露出远大于实际年龄的地中海。我暗自叹息,似乎看到一颗未来的子弹,直指我压抑的人生尽头。
怎么,又遇到瓶颈,写不了吗?我试探着问。
他摇摇头,苦涩地说道,是平时论文。我想起他曾经说过的平时论文达标发表情况,庄教授要求至少四篇sci以及两篇核心,否则不能毕业。实际上,这只是庄教授的个人要求,按照雪宴大学的研究生毕业条件,达到他博导要求的一半原则上就没问题,他早已过半,但离毕业仍遥遥无期。我安慰他,万事不要想得太悲观,放平心态总会看到曙光。
他艰难张口,想对我说什么又仿佛难以言状,最后才重重叹气,毕业好难!
二
是的,都很难。时间在我们身上随意踩下它野蛮的兽蹄,一脸戏谑地看我们垂死挣扎。
我看向十楼的窗外,想:如果跳下去会是什么样子?会疼吗,头会破吗,脑浆与肠子流一地,在别人看来过于凄惨?这多少有些尴尬。或者并不直接死去,撞上窗台、树枝、石头等坚硬物体,眼睛被刺穿,余生在残疾中度过,这更加让人难以接受。我不禁退后几步,陷入霎时的矛盾境地:不想继续活着,但畏惧死;想要死的结果,但怕死H8GioA55qvoK3If8fb8WbN7o2Ff/B/6dGxubH4tICDc=的过程;或者只是一条通往死的残缺之路,那比死不如。还有就是,这面窗子下是研究生公寓的后檐地带,离外街道隔一堵厚墙,一般不会有人去,倒可以死得很安静,但那里有一排因积雪停着的自行车,我并不想死在别人的臭屁股之下。我告诉自己,要尽量死得勇敢、壮烈一些,像雪一样洁白地往下坠。
“苏教授”带着他那愁容问我站那干嘛,为什么还不睡觉?他是我室友,一个东北人,因为一脸络腮胡酷似某教授,被我们戏称“苏教授”。他的愁容是因为要在紧张的时间里重写并完成万字以上的文献综述。我反问,教授不知?“苏教授”低头惨笑,说,我只是个狗屁教授。我俩都因这简单的回答而稍有快意。他软绵绵爬上床睡觉,我则拿洗漱品去公共盥洗室。女装大佬也在,他仍然是以往那副扮相,长发披肩,格子短裙和白色长袜,只是那张脸稍显沧桑,嘴唇上还有未剔除干净的胡子。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私下听别人叫他女装大佬。实际上,这是他独特的解压方式。这些研究生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解压方式,有人养乌龟仓鼠、有人抽烟喝酒、有人吃零食泡面,有人手淫等等,不一而足。我接着洗脸水,女装大佬突然扭头问我,兄弟,你刚才有看到什么东西掉下去吗?
我看着他近乎惨白的脸色觉得奇怪,但还是摇摇头。他看着我,支支吾吾说,似乎……是,一道人影。我被他的话电了一下,有些惊疑说,也许你看错了,那么大的风雪。他颤抖着说,是,是的,可能错了。说着端盆匆匆离开。
只剩我一个人,以及窗外呼呼的风声,灯光散发着死猪一样瘆人的冷气。我回到寝室,但不再靠近窗子,也不敢再往下张望。我临窗而睡,心里颤颤,女装大佬的话一遍遍在我耳边响起,恍惚中,似乎有一座坟墓似的黑影就紧贴在窗子上注视我,我闭眼强迫自己入睡,但并不能,我抱着自己狂跳的心脏辗转反侧了许久才睡着。
我睡到中午醒来,头脑一片昏沉。并没有做梦,也许做了,一些乱糟糟的影像,但醒来即忘。按照“苏教授”说的,我们记忆力下降,反应变慢,对生活一片空白,从开始写论文起就是这样。“苏教授”应该见他导师去了,空荡荡的寝室只有我一个人,每次我醒来,都仿佛是从一座死寂的坟墓里醒来,要多呼吸几下,空气才渐渐变得熟悉,慢慢引领着我回到熟悉的人世。我起来习惯性地打开电脑,只是茫然看着,并不想写一个字。我忐忑等待“苏教授”给我回复消息,看到他说,没什么新消息啊,能有什么事,除了论文与工作还能有什么事?我突然长松了一口气。我站起身,准备发消息叫江学长一起去吃饭,他太孤独了,但想了想终究没有。
我一个人冒雪去食堂,天地白茫茫一片,雪又堆厚了许多,风几乎要把人刮走。
多点一条鸡腿给自己额外加餐,这天最重要的仪式就算完成了。
我吃着总共不足六块钱的饭菜,偶尔心酸地想:人命卑贱,有时连富人家的宠物都不如。我想起江学长来,江学长最怕吵闹,因此他早在上个学期就搬到了十一楼的一间空寝室,一个人住下,反锁上门,一头扎在研究与论文的苦海里。我有几次去找他,敲了好久的门他才慢吞吞打开,愣愣地看着我说,是你啊,学弟,有,有事吗?我说周末一起吃个饭,他面无表情但并未拒绝。他坐我对面,一贯沉默,并不擅闲聊,但只要跟他说起在意的某个学术话题,他又往往能头头是道地说出许多独到的见解来。他问我,你论文应该早就写完了吧?我说没有,七万多字,大概差个一两万字才能交初稿。他显得疑惑,硕士论文两三万就行,需要写这么多?
我说,这其实和你们一样,博士只要十五万左右,你为什么写到三十万?
江学长一愣,是的。太卷了,像学术阴谋,你知道,但你不得不。只是没想到硕士也这样。
我说,现在大家都在凑字数,仿佛越多越好,越受重视。老师们虽然没有明说,但正是他们的沉默助长了学生论文卷字数的乱象。
江学长说,论文不像论文,做研究的人也跟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总在想,这书读着有什么意义?
我撇撇嘴,混个文凭,找个工作,继续等死呗。
这句话说完,我看到江学长原本颓丧的脸色又挫了几分。他端起面前的茶杯一口喝完,随后才充满迷茫地问我,学弟,我问你啊,你认真回答,如果你一早就知道你正在做一件毫无意义,最终也可能没有结果的事情,你还会继续做下去,或者有什么坚持的理由吗?
他巴望着我,就像在巴望一个渴求已久的答案,让他不至于枯竭而死。
我感到压力,想了想,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他,你知道人最终都会走向一个共同的,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终点吗?他点点头,说,都会死。
我叹气,是的,我们一早就知道我们最终都会死,一个毫无意义的结果,可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死?反而是更加努力地活着,难道你就可以说你正在毫无意义地活着吗?
江学长沉默良久,最后才平静地说,我想我懂了。
我则暗自长舒了一口气。当时想的是,江学长懂了,或者说想通了,世间万事万物并不一定是要有明确因果和意义才得以存在的,一个事物有时仅仅只是一个事物本身,而不需要通过他者来关照才得以自证。就像我们活着,一步步走向死亡地活着,我们最终会走到那个毫无意义的终点,但我们并不是为了走到这个终点才活着;我们活着,毫无意义地活着,无奈地活着,不被需要地活着,我们以活着的过程来嘲笑必然的结果,就像一个出生就被指定为救世主的人最后成为恶魔,这个世界本不需要人来救,强加太多的主义反而让我们终生被囚;就像在某一刻,真空说爆炸就爆炸,然后有了时间、空间、能量与物质,没有因果、没有定数、没有意义,在毁灭的时候,宇宙无中生有。
我以为江学长懂的是这样,后来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或许江学长并没有按照我的轨迹去想,而是走向了完全相反的另一端。而我的话就像蝴蝶效应的起源一样,让他直接看到了透明的结果。
三
我的担惊受怕在第三天达到顶峰。中午,我又给江学长发去微信,依旧不见回复。我知道他基本不怎么登微信的,之前有一次联系,他是隔了一个星期之后才回复的我。我也并不敢贸然直接敲门去打扰他的学术研究,虽然熟悉,但次数多了总归不好,于是只能干等着,但这次不一样,我总感觉冥冥之中有多个无形的征兆指向那个最坏的结果。
我连日来忧心忡忡,睡得并不好。实际上第二天下午时分我就联系过他,并无结果。其间我又问“苏教授”有没有什么新消息,“苏教授”照旧摇头。在昏暗的走廊我再次碰见女装大佬,他没有作声,瞥了我一眼之后就匆匆离开。我回到电脑前坐下,二十度恒温的暖气将我浸泡得身体发软,头脑昏胀,生活又回到一潭死水的样子,三天的时间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腐烂并长满蛆虫的,我们活在一片窒息似的空气里,有时,我竟无比渴望发生一场突然的意外或死亡,在巨大的爆炸中,肢体残碎、规则破损,我们麻木的悲伤举着我们,我们得以重生,眼睛长满青草般水嫩的空气,地球获救般大口呼吸……
是的,存在毫无意义。但我不像暴君国王卡利古拉一样拥有毁灭一切的权力和勇气,我只能虚假地在近乎绝望的江学长面前说,活着本身就是意义,我们还能比《活着》里的福贵更悲惨?萨特告诉我们,存在无意义的意义在于空白的人生我们要自己去选择,自己负责,将你的生命轨迹尽量生动地填满这张空白的纸,这就是存在的意义。
自己选择?生命轨迹?我那时清楚地看到从江学长嘴里发出嘲讽的嗤笑声。
我们从出生开始,一切就已经被选择好了,不是吗?我们读书,不停地读,读到某一天,茫然毕业,找工作,匆匆结婚生子,然后慢慢老死。一切不过都是提前预定好的而已,我们只是僵硬地配合着表演,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轨迹,像透明胶带,我们能一眼看透,但还是不得已被它粘住,缠死,我们又何曾真正有过选择?江学长说着,脸上布满落日般反复重演命运的悲壮,我想起推石头的西西弗斯。
突然,江学长向前倾近,问我,你相信命运吗?学弟。
我有些迷茫地说,也许吧,有时候……
有时候,就仿佛冥冥之中发生的事本应如此,是吗?他看着我,我没有回答,实际上我那时竟然愣神想起了被命运悲惨捉弄一生的俄狄浦斯王。江学长又喊了一声,我惊醒,他自顾自说,或许你并不相信,我起初准备写杜甫的论文的,但后来重新开题改写了卢照邻。
学长,你的《卢照邻后期诗文研究》还在写?最初是写杜甫?
是啊。最初我以为杜甫是命运,包括我的名字来源,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无奈杜甫的研究太多了,已经没有可挖掘的余地,我只能相对性选了卢照邻,现在嘛,我似乎终于看清楚,卢照邻才是真正的命运。江学长低声冷笑。
我听得糊涂,但江学长偶尔露出的神态让我陌生且害怕,仿佛自从上次的谈话后,他身上那股迂腐气就变成某种偏执,几乎疯狂,待我再细看时,一切又仿佛不过是错觉。
他没再说起命运,连命运本身也像一种错觉。
我们坐在食堂二楼靠边的窗子,窗外大雪漫天,在肆意的寒风呼啸下,雪花像无数被驱赶的细碎的梦,怎么也连缀不起来。我想,雪花也是一种花,只有在寒冬才遍地开放;春天也是一种死亡,以无数的腐烂堆积出来的生机;这样的时节,说不清好坏,辨不清真假。
卢照邻诗云:“雪处疑花满,花边似雪回。”
四
只是难以理解,为什么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导师、教授……
我接过话说,为什么他们有时幼稚、自私小气,心胸狭窄?或者一个看上去过于清高、冷淡的教授最后往往成为最难以理解的反面,难以接受?
江学长支支吾吾,……也不全是,只是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对待男女感情的,我看到的,很乱,特别是教授们,庄老师也——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
江学长以手掩面,我能感受到他因他敬爱的老师而产生的极度失落、痛惜的心情。这就像一个圣人弟子有天看到圣人落魄的场景,或再贴切点,就像虔诚的和尚有一天看到佛祖奸了一个女人,他们那难以置信、失落、破碎的心境,一瞬间,信仰崩塌,好坏倒转,真假错乱。而作为信仰的他们的倒塌对外人的打击与距离又是相关的,距离越近,受到的打击越大,反之,则并没有什么,在无关紧要的人眼中,顶多就是一个人对多年前亏欠的自己用化身野兽般的方式去恶补。
我只能用我所观察和所想到的向江学长解释,且同时悲哀地发现,我们正走在一个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中。
我说,学长你看啊,从年龄上开始分析,那些与女学生或其他女人乱搞关系的老师、教授们基本都处在三十末近四五十岁的样子,为什么?这么大的生理与心理年龄的反差?因为他们在年轻、在最合适的时候错过了太多太多了啊。凡能走到教授这个高度的,谁不是读书的能手?但,也正是因为他们读了太多的书,在正当玩耍的时候他们只读书;在该谈恋爱,体验情感的时候他们只读书,后来又忙工作、做研究、评职称,等终于都熬过来了,身心也放松了,巨大的落差与亏欠感也在对过往的回忆与思考中浮现出来了,这时他们会普遍产生一种对于人生的虚度与无意义感来,他们悲哀地发现,人过半百,他们的童真、欢乐、青春、爱情、性体验一片空白,他们更不平衡,更空虚了。于是他们开始以恶补的方式,甚至是歇斯底里地去对当初那个失去太多的自己进行补偿,哪怕毫无理性,哪怕罔顾人伦,他们也要填满那片人生的空白,追求所谓的人生圆满,所以,各种乱象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江学长问,真是这样吗?
我说,学长,问你个问题,你谈过恋爱吗?
江学长淡然摇摇头说,没有时间。
我说,你看,我们不也是这样?我们活生生就是那些教授这个阶段的样子嘛,或许,未来某一天我们最终也不过就是他们现在的样子。
江学长显然被吓了一跳,我看到他坐在椅子上的身体猛地向后一缩,脸色苍白到毫无血色,我也会成为他们?不能避免?但我——不想成为他们!
我说,谁都不想,可我们不过是个俗人,固然我们坚持初心,但设身处地想一想,现在我们的所思所想是否还能镇住那时的所思所想,我觉得,恐怕恰恰相反。
不,不会的,总有办法避免,我可以不当老师的……
学长!不知道怎么的,我突然感到愤懑,这一刻,我似乎能理解村里面的人背地里说我读书读到迂腐的嘲讽表情了。我看江学长也同样如此,我脑袋一发热,开始冷语输出,是对他,又仿佛是在针对某个我不愿承认的自己:谁不想当圣人,纤尘不染?但这个世界并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好与坏、美与丑、黑与白总是相生相伴,相互依存的。当你看到一件过于完美的事物时,你就要同时想到,在它的美破碎时所爆发出来的巨大的丑恶,丑是美的代价,美是丑的遮掩。你要去试着接受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它那残缺、肮脏、邪恶的一面,你不是也经常看到吗?在美的旁边,通常紧挨着丑,比如银河紧挨着黑洞……
雪越下越大,在这一片晶莹剔透的洁白之下,是黑乎乎的土地,土地下是无数交缠的污水、粪水的管道。或许,这大雪还隐藏了其他,等待被挖掘。
那个最坏的结果像梦魇一样折磨着我。到中午十二点,我终于下定决心看看十楼窗下那座想象中的坟墓,深呼吸之后,我拉开窗帘,缓缓打开左边的窗户,水滴像血线,冷风灌入房间,我身后的寝室门在压强下被嘭地关上,我浑身一震。我踮起脚尖俯身在窗边,往十楼下的地面看去,地面白惨惨一片,一些树与瘦弱的房屋在大雪覆盖下不堪重负地强撑着,公寓后的地面冷清、萧索,一排自行车停靠那里,有些被吹倒了,大雪淹没了它们,使它们只露出部分来,远远看去,就像一些动物的断肢。
我关上窗子,感到一阵轻松。至少,在我看来的情况是,那个悬空的结果并没有落下去,此刻,对我来说,没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
我发消息给学长,仍旧没有回复,连同上面的几条也是,我的心又不安了,一个星期虽没到,但我时刻感受到一种不能继续等下去的焦躁。下午近傍晚的时分,我来到十一楼,江学长的房间关着,我叫了许久他都不曾开门,或许他在,也或许在导师办公室,甚至和庄老师一起讨论、研究学术并未归来也是常见的事。
从最近一次交流的情况来看,他的论文似乎进入了某种难产期,甚至有回炉重造的可能,也是那时,我看到他脸上那彻底的绝望,带着死亡的气息。
五
十一月十二日的前一天,在购买圈有个俗称,叫“双十一”。
一个所有东西都被贱卖和被抢购的日子,半带欺骗的性质,被那些躲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便宜之人当神一样供奉的日子。在下午江学长来找我之前,我也买了衣服、裤子和鞋,全身上下算起来不超过六十块钱,便宜之人说的就是我自己。说起来,江学长还是第一次主动找我,这让我感到很惊讶,我差不多以为我们不会再愉快相处了,特别是在上次我们有过不愉快的交谈之后。他或许排斥我的俗气,而我讨厌他那无可挽救的迂腐,但我知道,我们本质上是同一种人,箍住我们属于共同属性的词有很多,比如“穷酸”、“乡野”、“内向”等等,我知道,我们这具廉价的身体能读书一直读到这里,都受过了太多难以言状的屈辱,他只不过比我多受了几年。
我问他不买点什么东西吗?机会难得,他冷冷说,再也不需要了。我的话又被哽住了,于是不再问,而且我能看出来,他的状态完全不对,平静、淡漠,有一种魔鬼附体的死寂。我想起浮士德。突然他说,我请你。我有些生气,还没待我说话,他又说,你师门的那个什么珊请了全部男生没有请你,你也不要总是放在心里,不要在乎他们,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精神上超越他们就够了。我突然想哭,一种受尽屈辱后被看到的大哭。
他凝视着我说,学弟,好好完成论文,祝你如期毕业,找到一份好工作,去改变你一直想改变的根本性东西。
我说,学长你也一样啊,而且你比我前途更好,机会更多。
他只是平静地摇摇头,不一样的,我没有可能了,我永远毕不了业的。
我疑惑地问,怎么,是平时论文,还是卢照邻的研究,你不是加班加点都快赶完了吗?
他惨然一笑,是完成了,但是,他是不会放我走的,只要我还能出力,我就会永远被困在这里,退不了,出不去。
他?庄老师?我问,江学长点点头,其他老师都说没问题,但他说推倒就推倒了,叫我重新开题,那是三十万字啊!我也算是看清楚了,他是不会放我离开的。
可是,为什么啊,他凭什么这样,他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我的不满与愤怒一下子就出来了,一想到三十万字的鲜血被寥寥几句就无情地推翻了,我的心就痛得难受,我对学长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上诉、举报,去校长那里反应。
学长淡漠地摇摇头,没有用的,作为博导,他有一票否决博士论文的权利,校长也没辙,我是真的走不了,像卢照邻一样,到最后了,进退无路。
我说,学长,你不要着急,一定还有办法,我们找人,我们去告他!我们还可以网上公开他,让他现出原形,身败名裂。
不,不行的,我不能这样做,他再怎么说也是我导师,在我心中等同于父亲,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
又来了,又来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我站起来大吼,学长!他算个什么狗屁导师,禽兽还差不多,你就是太顺受,思想包袱太多,他才这样为难你啊!
他叹气道,也许吧,我们不说他了,快坐下,别影响你吃饭的心情了。
我虽冒火,但也坐下来。他说,学弟,其实你比我更有前途,你的很多思想、见解,读过的书,在我看来,很多博士都不如你,你一定要顺利毕业,去实现你的精彩人生。
我点点头,这一刻,我重新看到这个满脸沧桑,憔悴堆积如霜的人,他像风中摇晃的微弱烛火,随时有被扑灭的可能,我可怜起他来,但也是在那时,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我,不会想要继续攻读博士了。
以往“双十一”。江学长坐在我面前自顾自说着,以往我买很多东西,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都不需要了,感觉很没意思呢,你说,我们这些便宜之人,是不是天生就和这些便宜之货搭配在一起才最合适?为什么啊?因为我们生就如此啊,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甚至就算我们一步步忍受着走到了这里,也仍然毫无希望,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没法子呀,我爸妈希望我“江间波浪兼天涌”,一路飞上高空,逆袭人生,改变命运,带他们享福,所以我叫江勇,勇敢的勇。可惜,我这一生都在辜负这个名字,辜负我爸,辜负我妈,是我对不起他们,我,我又怎么能空荡荡回去面对他们,他们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他们在等着我,我怎么可以让他们这穷苦的一生,再次失望……
我看到他流下眼泪。我关心道,学长,不要太担忧。
他平静地摇摇头说,我没事,别担心,既然生得便宜,这不可选择,那我就与这便宜的人生抗争到底,所以你看,我不买东西了,甚至也不会这么便宜地死。
我顿时放心下来。
但现在仔细想想,我觉得我可能理解错了江学长所谓的对便宜之人的“抗争”。或者说,他把这个“抗争”的时段缩短成了特定的今天和明天,而不是现在和余生。巨大的不安在我心中像原子弹一样爆炸。夜晚,我仿佛枕着冰冷的坟墓入睡。
第四天一早,我就跑到公寓楼窗子下方的地点查看,除了一排自行车,地上就只有一些脚印,雪有被翻动的痕迹,又新下了一层薄雪,从现场的痕迹来看,大概是有人来推走了自行车,不会再有什么新情况出现了。我这样想。
我站在大雪中,几朵雪花落在我的额头,滑过脸颊,像亲人安慰似的,温柔、细腻,我感到无比安心,连日以来的猜想与紧张一下子就得到了松弛,疲倦也袭来了,我大步走回寝室,准备补个觉,然后静待江学长看到消息之后回复我,或者来找我。
在梦中,我看到卢照邻人生的最后一幕是这样的:具茨山下,幽忧子再度咳血,他长叹一声,站起来推开窗子,看向田地外的颖水,一个早已在病痛与绝望的双重折磨下蠢动的心思在此刻终于决然。他环顾四周,先拿起《释疾文》扫了一眼,又捧起《五悲文》哽咽而读,读至“神若存而若亡,心不生而不灭”,手里的书落地,风灌门而入,快速翻动书页,幽忧子得以快速回顾他短暂而又多难的一生。书合上,他回过头,看向窗外不远处的坟墓,曾经有多少无眠的日子他都在那坟墓的温床里度过的,他的心再次安静下来。他站起身,一步步走到环绕自己小屋的颖水河边,像睡觉一样,闭眼,然后躺下去。
六
尸体是后来被人发现的。
“苏教授”摇醒睡梦中的我,我看到时间跳过12点,第四天的中午看起来像垂垂老矣的下午。我看到“苏教授”震惊的脸色,听到他急剧的喘息,显然,他是着急跑回来的。他一把拉住我说,雪宴大学都在传,有研究生跳楼自杀了。他一脸惊恐地看向窗外,听说就是从十一楼的这面窗子跳下去的,是个博士,已经死了好几天了,被埋在大雪下,今天才被人发现的。
我陷入巨大的沉默当中。“苏教授”自顾自说着,听说发现的人是去推自行车的,然后翻开大雪,发现了早已结冰、冻僵的尸体,头碎成了几瓣,身体破了一地,但并未腐臭。发现的那人随后通知了学校,学校联系警方,大概在早晨五六点的时候尸体就被运走了……喂,你怎么了,被吓到了?说话啊!
我问,是谁发现的?“苏教授”想了想,说是一个女生,但立即就摇了摇头,又说是一个男生,有胡子,且嗓音浑厚。我和“苏教授”对视一眼,我想,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学校公布有官方消息吗?具体身份报道了吗?为什么自杀?“苏教授”像看傻子一样盯着我,然后说,这种事,学校怎么可能会有官方公布?他们希望的是事情闹得越小、影响越小最好,或者是能私下悄无声息地解决就尽量私下解决,你也知道,自杀这种事,校方其实是没多大责任的,就算要赔,也赔不了多少。
他拉着我的胳膊来到窗边,问我,前几天晚上,你听到过什么动静吗?我看着他,发现自己说不出话,于是只好对他摇头。他说,听说是庄教授的博士生,具体自杀原因不知道,但我猜,大概率是论文不过关,压力太大跳楼自杀的。庄教授历来对学生就很严格。
又过了一个星期,学校和死者家属私下解决了,由于是自杀,最终学校赔了十六万。一条人命,曾经活生生的人,一个三十一岁的博士生,在他死后,被定性为一个冰冷且低廉的数字:十六万。
我颓然坐在椅子上,翻看微信上我发出的信息,我知道,永远不会再有回复了。手指一按一点,就像被系统删除一样,这个人,也彻底被这个世界删除了,仿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下午我买了一束花来到宴湖边,发现沿湖岸的一圈雪地上都摆放着鲜花,这是不相识的研究生们自发为他送行和祭奠。他们或三三两两,或一人单行,放下鲜花就走,因为学校禁止学生搞祭奠,周围还有保安环伺,他们眼神冷冽,仿佛随时都能逮住一个学生,给他定罪。来祭奠的人都没有说话,他们的沉默是在为你呐喊,为你感到不值,悲愤。或许,他们也——羡慕你的勇敢。
你死得那么洁白、高贵,而我还在廉价地活着。
我才是那个躲在角落里的可憎的便宜之人,当然也包括他。实际上,当你熬过便宜之日,抵达新的凌晨时,你从十一楼像雪花一样高贵地垂直坠落,“嘭”的一声之后,你的死让你完成了新生,却让另外两个人陷入了挣不脱的死之迷瘴。我终日沉湎梦幻,不敢去揭开那个真相;而他,日夜被那死亡的阴影所笼罩,他脸色苍白,胡子疯长,我们承受的折磨和压抑在第四日都达到了一个崩塌的临界点。他比我去得更早,理由是推自行车,这显然有悖于常理,大雪淹没膝盖的情况下,自行车没有丝毫用处,他就这样把沉睡的你当做真相一样挖了出来,你破碎的样子令我不忍细看,在他走后,我也走到了那里,除了脚印,那里只有一座真相的废墟。像我们在人世低微的呼吸。而在我的记忆中,你一直停留在坠落的时刻——
好吧,现在让我们三个人一起再重新数一遍,不许出差错,从十默念到一,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