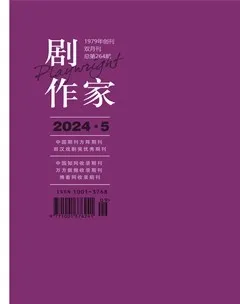美学视域下歌剧《江姐》中的戏曲元素分析
摘 要:歌剧《江姐》是一部具有深厚历史背景和艺术价值的经典之作,它融合了丰富的戏曲元素,成功地将中国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歌剧形式相融合,展现出独特的美学价值。本文从美学视域出发,深入分析歌剧《江姐》中的戏曲元素,包括唱腔、表演、舞台布景等方面,探讨其对作品艺术魅力的提升和对中国歌剧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歌剧《江姐》;戏曲元素;美学视域
歌剧《江姐》是以长篇小说《红岩》为蓝本,1964年由阎肃编剧,羊鸣、金砂、姜春阳作曲,共同创作而成。讲述的是江姐和丈夫在华蓥山组织革命斗争,她先后经历丈夫被杀害、被叛徒甫志高出卖、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坚决保护党的秘密,直至最后牺牲的故事。在优秀的文学剧本基础上,歌剧《江姐》将戏剧化的情节与民族化的音乐巧妙融合,将戏曲的唱腔、表演、舞台布景等元素运用到歌剧之中,将革命先烈对党的绝对忠诚和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精神完美呈现,在我国歌剧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重要地位。
一、美学视域下歌剧《江姐》中的戏曲唱腔元素
歌剧《江姐》中戏曲唱腔元素的运用,既保留了传统戏曲的精髓,又与现代歌剧艺术相融合,展现了中国歌剧的独特魅力。这部歌剧不仅是对革命烈士江竹筠英勇事迹的颂扬,更是对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1.灵活丰富的板式结构变化。纵观整部歌剧,音乐结构比较丰富,一方面板腔体和歌谣体结合使用,另一方面借鉴了戏曲中的板式变化手法,如慢板、快板、散板等,使全剧的音乐富有变化和节奏感,有抒情、有激动、有平静,色彩丰富,起伏兼具。其中,板腔体作为我国传统戏曲的一种唱腔结构体制,通过板式变化来展现歌剧的音乐唱腔。在《江姐》中,巧妙地运用这种板式变化来塑造人物性格和推动剧情发展。例如在著名的咏叹调《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中,板式从慢板到紧拉慢唱,再到一拍一板,最后又回到慢板。这种板式变化不仅展现了江姐在严刑拷打下的坚贞不屈,更凸显了她对党的无限忠诚。板式变化的合理运用,采用慢板、快板、散板等戏曲中的板式变化手法,使音乐旋律富有变化和节奏感[1]P41,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细分了歌剧的表现层次,以更强的艺术感染力来塑造江姐的形象,让观众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歌剧所传达的精神内核。比如在表现江姐面对敌人的坚定与勇敢时,使用了快板,旋律节奏明快有力,能够生动地展现出她毫不畏惧的精神风貌,让观众能直观感受到那种紧迫和坚决的情绪;在表现江姐内心的柔情、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及对战友和亲人的深厚情感时,使用了慢板,仿佛娓娓道来江姐内心深处的故事,让观众沉浸在细腻的情感氛围之中。
2.多种类别的润腔技巧使用。戏曲中的润腔技巧,如滑音、颤音、倚音等,在歌剧中得到巧妙运用,使演唱者能够更细腻地表达情感。润腔,是在主要音符的上方或下方添加一个或多个小音符。在歌剧《江姐》的多个唱段中,通过细腻的润腔处理,展现出人物内心的情感,丰富了人物的形象。在歌剧《江姐》中,倚音的运用非常广泛,《红梅赞》中“红梅花儿开”的“开”字上就使用了倚音,使旋律更加悠扬动听[2]P93。波音,是在主要音符的上方或下方快速地波动一个或多个音符。歌剧《江姐》的《绣红旗》唱段中,“线儿长针儿密”的“密”字上就使用了波音,使旋律更加欢快、跳跃。滑音,是在两个音符之间通过滑动的方式连接。歌剧《江姐》的《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唱段中,“春蚕到死丝不断”的“断”字上就使用了滑音,使旋律更加深情、动人。颤音,是在主要音符的上方或下方快速地颤动一个或多个音符。在歌剧《江姐》的《五洲人民齐欢笑》唱段中,“万里山河尽朝晖”的“晖”字上就使用了颤音,使旋律更加激昂、振奋。
二、美学视域下歌剧《江姐》中的戏曲表演元素
戏曲表演元素在歌剧《江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身段、表演的巧妙运用,不仅更加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江姐及其他角色的形象,更进一步增强了歌剧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展现,增强了歌剧的艺术表现力。
1.身段动作。戏曲身段动作在歌剧中的运用,是一种对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在《江姐》中,演员们通过精湛的表演,将台步、手势、眼神等戏曲身段动作与歌剧的情节、人物性格和情感表达紧密结合,创造出了极具感染力的舞台效果。从整体舞台调度看,演员们的走位和姿势转换流畅自然,富有节奏感。例如,在江姐出场时,她的步伐稳健而端庄,身体微微前倾,展现出坚定的使命感和不屈的精神,这种身形的塑造不仅突出了江姐的人物形象,也为后续的情节发展奠定了基础[3]P85。从身姿变化看,通过弯腰、转身、俯仰等动作,展现出人物的情绪变化。比如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时,江姐挺直脊梁,毫不退缩,以挺拔的身姿展现出英勇无畏的气概。而在回忆往事或表达内心的柔情时,身体则会微微弯曲,呈现出柔和的曲线。从手势运用看,动作细腻、恰到好处。比如江姐在表达决心时,双手握拳,有力地抬起,展示出坚定的信念;在与同志交流时,手指轻柔摆动,体现出亲切与关怀。此外,还有一些特定的动作组合,如甩袖、移步、旋转等,都增强了剧情的张力。例如,在高潮部分,江姐的大幅度旋转动作,象征着她与敌人的坚决斗争和对正义的不懈追求。
2.虚拟表演。虚拟表演是戏曲表演的重要手法之一。在歌剧《江姐》中,演员们借鉴了戏曲表演中的一些技巧和方法,通过象征性的动作和表情来表现情境,深入地刻画角色的内心世界,更是打破现实的局限,让观众在想象的空间中感受到更加丰富和深刻的情感与故事,使歌剧具有了更广阔的表现空间,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作品所传达的革命精神和崇高价值。比如,为表现江姐身处狱中的状态,演员通过身体的姿态、眼神的方向及手部的动作,虚拟出牢房的狭小空间和恶劣环境,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江姐所面临的困境;为增强角色之间的互动,当江姐与战友交流时,演员简单的挥手、指向等动作,仿佛真的在传递重要的信息或物品,使观众能够凭借想象构建出具体的交流场景;为展现角色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不屈的意志,演员通过坚定的目光,让观众能够感受到她内心的强大力量,通过望向远方,展现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观众也能随之想象到革命胜利的美好前景[4]P97。此外,歌剧《江姐》还通过虚拟表演与音乐、灯光等舞台元素的紧密配合,进一步增强了表现力。音乐的节奏和旋律为虚拟表演提供了情感的烘托,而灯光的变化则营造出不同的氛围和场景,使得虚拟表演更加真实可信。
三、美学视域下歌剧《江姐》中的戏曲舞台布景元素
舞台布景是歌剧演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演员提供了表演的空间,还能够营造出剧情所需的氛围和情感,引导观众更好地理解和感受歌剧的内涵。歌剧《江姐》是中国歌剧史上的经典之作,其舞台布景设计也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1.现实主义风格。《江姐》的舞台布景采用了现实主义的设计风格,注重细节的真实和准确性,舞台上的道具、服装、灯光等都力求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使观众能够更加真实地感受到剧中人物的生活和斗争。不同版本的《江姐》在舞美设计上可能会有所创新和变化,但无论如何变化,都保持了现实主义风格的核心特点,即对真实的追求和对生活的反映。比如,2000年世纪版的《江姐》将自然优美的重庆风光,如朝天门码头、华蓥山的自然风貌,以及渣滓洞看守所等场景生动地呈现在观众眼前,逼真地还原了各种环境细节,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能够深切感受到那个特定时代的氛围和情境[5]P34。新版《江姐》突出了海派风格,其舞美设计以黑白基调展现舞台,用素描的绘画手法来表现写实场景,从当代角度讲述那个时代的故事。
2.象征手法的运用。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江姐》的舞台布景还运用了象征手法,通过一些具体的形象,将抽象的情感、主题和意义具象化,让观众在欣赏演出的过程中产生更多的联想和思考,以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主题深度。例如,以黑与白两种对比鲜明的颜色来构成舞台的主基调,隐喻了光明正义与阴险恶毒两股势力之间的激烈对抗交锋,其中在表现重庆山城的场景中,房屋下部的阴影及混杂其中的支撑杆影子,代表着黑暗处敌特活动的区域;而为共产党打探情况的“报童”等的调度则始终在光亮之下,这种对比暗示了正义与邪恶的对立。例如,在某些场景中出现的红梅,象征着江姐等革命者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红梅在冰冷坚硬的环境中绽放,寓意着革命者在艰难困境中依然保持着高尚的品质和不屈的意志。
3.空间的巧妙利用。舞美设计充分利用了舞台的空间,通过多层次的布景和道具布置,营造出丰富的空间感和立体感。在歌剧《江姐》的舞台布景中,通过软硬景和舞美道具的设置,把舞台切割成纵深交错的多维空间。例如设置不同层次的平台、悬挂的布景等,使舞台空间更具层次感和立体感,让观众仿若置身于剧中的不同场景之中,增强观演的沉浸感。贯穿整个舞台的主平台采用斜面,从左至右、从前至后都有不同的倾斜。这种设计可以暗示剧情中动荡的年代、混乱的局势及老百姓内心的惶恐与不安。此外,根据剧情的需要,使用可移动的布景可以改变场景的布局,以展现不同的地点或情节的发展。一些可升降的装置,如升降牢笼、吊桥等,可以进一步丰富舞台空间的变化。
歌剧《江姐》在唱腔元素、角色表演、舞台布景等方面都充分融合了传统戏曲元素,这是其艺术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美学视域进行分析,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感知和理解其所独有的艺术魅力,既有民族性与时代性的体现,还将抽象的革命精神、民族情怀赋予形象化和深化表达,更将歌剧艺术与戏曲艺术相融合,创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舞台艺术。这些戏曲元素的运用,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也为中国歌剧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未来的歌剧创作中,我们应继续探索戏曲元素与现代艺术的融合,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1]侯天举:《民族歌剧〈江姐〉的演唱特征及技巧分析》,《艺术大观》,2023年第12期
[2]郭清波:《人人争唱红梅赞,〈江姐〉感动芙蓉城——歌剧〈江姐〉的舞台形象塑造》,《学园(教育科研)》,2013年第1期
[3]朱艳彬,张黎明:《歌剧〈江姐〉选段〈青松林内红旗扬〉的情感把握及演唱技巧》,《喜剧世界(下半月)》,2024年第3期
[4]胡晓娟:《歌剧戏剧结构与音乐结构的统一性——兼论中国歌剧戏剧性的音乐呈现》,《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5]金砂:《谈谈歌剧〈江姐〉的音乐创作——民族歌剧作曲和戏曲音乐手法初探》,《艺术百家》,1992年第4期
责任编辑 岳莹 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