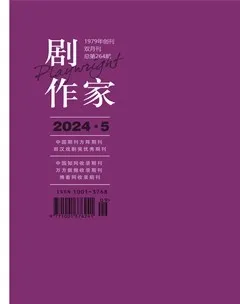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摘 要: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的剧作《一个夏日》以独特的剧场空间寓意婚姻生活,剧作家采用大量的“静场”处理以展现人物内部的心理世界和外部的人际关系,从而揭示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该剧的主题思想与表现形式完美融合,传递出剧作家具有东方哲学特征的形而上学思考和接近于“无”的人生况味。
关键词:约恩·福瑟;一个夏日;戏剧空间
2024年的春天,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Jon Fosse)的作品《一个夏日》(Ein sommars dag)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D6空间上演。这部由王魏导演的戏剧作品如一块漂浮在北欧深色海面上的冰块,它的质地纯粹、透彻而坚硬,于阳光下折射出别样的梦幻色彩。
海边的家
寡淡的灰色布面沙发,线条利落简洁的一对桌椅,冰块状的白色舞台,周围四散着灰黑色的粗糙砂砾,一面光洁而平整的落地窗位于舞台中央,在开幕之际毫无防备地闯入你的眼帘——《一个夏日》的演出开始后,上述种种具有某种内在关联的舞台装置共同构成了一幅极简主义的北欧图景,几束冷蓝的光悠悠地照进舞台,在剧场内渲染出静谧而忧悒的气氛。这是一栋坐落于峡湾边高山上的古老房屋,它面朝大海,遗世独立,曾经是一对年轻夫妻的栖身之地,也是戏剧事件发生的主要场所:一位老妇独自在屋内,怀想起多年前丈夫不辞而别的那个夜晚,戏剧情节由此在人物的回忆中缓缓地铺陈开来。她的丈夫为何出走?他去向何方?还会回来吗?三则疑问久久地盘旋,构成了吸引观众一探究竟的戏剧悬念。
“海边的家”是戏剧中的一个关键意象,它既是观众认知中熟悉的日常空间,也含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栋房屋一度承载了夫妻二人对于婚姻生活的美好幻想,后来成为了他们爱情破灭的事件发生地。多年之后,老妇固执地选择在此孤独终老、独自凭吊,房屋又成为收纳往昔纷繁复杂回忆的物质性“容器”。为了呈现剧情,福瑟采用了不同时空并置、交叠的叙事结构,让两位演员同时饰演不同年龄段的同一人物,老妇和年轻时的妻子一同出现在舞台之上,老妇以复杂的神色站在舞台的一隅,静观当年夫妻二人产生争执、丈夫离家出走、友人夫妇帮忙寻找的完整过程。此种处理让“过去”和“当下”同时出现,虚实相生,使得舞台不再是遵循线性时间逻辑的物理空间,而是成为了心灵空间的外化。观众不仅仅跟随剧情走进了那栋海边的房屋,更是走进了一位老妇尘封已久的心灵“暗室”。
在海边的家中,“落地窗”是一样重要的物件。正如18世纪美学家狄德罗指出了绘画艺术和戏剧艺术之间存在着难舍难分的相近关系,《一个夏日》采用了无场次的布景方式,演出中并无换景,使得戏剧场景好似一幅静态的古典油画,落地窗便是存在于舞台之上的“画框”。当落地窗静静地横亘于观众和演员之间时,它将舞台空间进行切分。此举不仅让观众拥有了适度的抽离感,能够以静观一幅画的心态观摩一部戏剧,同时还增加了戏剧场景的丰富性与可阅读感。随着情节不断深入,旋转舞台发生了多次转动,落地窗所构成的“框式构图”还能让戏剧画面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规整、平衡的美感。此外,落地窗还能在视觉上凸显人物主体,使观众的目光始终聚焦于人物的动作上。观众注视着演员在窗的内外徘徊、走动,妻子、丈夫和友人夫妇凭窗而立的姿势,在舞台上外化了人物内部的复杂心境及外部的人际关系。
从文化意义上来看,一扇落地窗是分割室内与室外、家庭与社会、已知与未知、安全与危险、文明与自然的分界线。窗内是为人遮风挡雨、提供庇佑的封闭性家庭空间,窗外则是一片原始、荒蛮、无法被灯光照亮的黑暗大海。开窗抑或关窗,对于剧中人物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外部动作,更是一种富有象征性的选择。观众能够见证在戏剧的后半部分,当婚姻生活走向崩溃、命运发生激变之后,年轻的妻子做出的动作是:打开窗户,坦然地迎接窗外的急风骤雨。
海的语言
如果说“以对话推进情节”是话剧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种类的本体特征,那么《一个夏日》则是一部相对而言较为安静的作品。福瑟在创作过程中采取了和哈罗德·品特相似的技术手法,即安排了大量的停顿的静场(pause),让“静默”成为该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通过阅读《一个夏日》的戏剧文本可知,短暂静场、长长的静场、突然停下来不说了、没有反应等话语在舞台提示中共出现了86次。这些长短不一的静场穿插运用在戏剧结构之中,或发生在妻子对丈夫进行了一番神经质的追问之后,或发生在妻子和友人谈论自己所经历的婚姻危机之时,或发生在妻子和友人夫妇艰难地寻找过程中……显而易见,“静默”是福瑟作品中重要的戏剧语言,正如福瑟所认为的那样:“戏剧语言是无需语词的语言……动作,或者动作的缺失,声音,以及演员的个人魅力,这些才是最具表现力的东西。”[1]这些静场的编排,或许是为了表达在特定情景下语言工具的失效,人际交流将遭遇到不可抵抗的障碍与失败。身处孤绝之境的老妇,她的内心的状态过于复杂,难以言说,因而只能以“静默”的形式对抗外部世界。莫里斯·梅特林克在提出“静态戏剧”理论之时,便认为适当的无声表演能营造别样的现场氛围,使得演出具有巨大的情感张力,感染着台下的观众,从而达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艺术效果。
除了难挨的沉默,在福瑟作品的戏剧语言中,处处出现着失败的沟通、无效的对话、无意义的重复、答非所问和梦呓一般的自语。例如,在夫妻最后的一段谈话中,妻子反复询问丈夫为何痴迷于大海,问他“你跟我在一起不开心吗”,却始终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丈夫也曾试图邀请妻子一同去海边,妻子却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他,因为到海上去让她感到“害怕和无聊”。在丈夫走出家门时,妻子多次叮嘱丈夫“别待太久”,丈夫虽表明自己会马上回来,实际上却离奇失踪、杳无音讯。这一系列事件彻底表明了语言作为表达工具的不可靠性。剧中大多数的沟通都是失败的,妻子无法说服去意已决的丈夫,友人无法安慰极度失意的妻子,角色们徒劳地在舞台上诉说,这些对白凭借着长短不一的语句、不同的词语发音而产生了节奏感、音乐性。在时进时退的情感拉扯中,对话无法打破心灵的壁垒,人与人之间难以借助语言而实现真正的沟通。
在静场和对白之外,通过收集海浪声、风声、雨声、海鸟鸣叫等自然界噪声而制作的音响效果几乎贯穿了演出始末。自然界噪声元素的运用,在剧场中营造出贴合现实、贴近生活的气氛,令观众仿若置身于北欧的海边,在剧场内真切地感受到从四面八方猛烈吹来、凛冽而潮湿的海风。
海的哲学
作为当代戏剧界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福瑟被认为是承袭了“若干代际、流派和风格的欧洲剧作家的创造”[2]P27:他对于婚姻家庭和两性关系进行细致而深度的描摹,与亨利克·易卜生相似;他热衷于书写日常生活中大段静滞的沉默,令人联想到品特惯于使用的技艺;他将戏剧性事件处理为蛰伏在表层之下的深层“潜流”,无疑延续了契诃夫的传统;他在戏剧中通过循环往复的对话推进情节,形成了语言的节奏感,则有几分塞缪尔·贝克特的风格。除此之外,福瑟的剧作中还弥漫着令人难忘的东方美感,其作品和东方文化存在着某些内在一致性。福瑟曾称赞日本东京和中国上海的剧团对其作品《有人将至》做出了近乎完美的舞台呈现,坦言“东方人仿佛比西方人更好地理解我的作品”,中国版本的演出“对我剧作的理解是那样的透彻、完整”[3]P1。可以见得,福瑟作品的“东方性”并不是将西方戏剧技艺单纯地放置到东方的表现框架中,而是曲径通幽式地和东方美学体系交相辉映,产生了深层次的联结和共振。
从《一个夏日》的演出风格来看,福瑟有意弱化外部动作的表演幅度,使得演员在演出过程中少有激烈的面部表情和夸张的肢体动作,其行动的节奏也是徐缓的。此种处理方法强化了观众对ec4f3ca118d112825c2c406a3ae71deec74e04d724fd5b6c4e3902b0569d3f80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关注。例如,当妻子发觉丈夫可能不再回来后,她流露出的神色并非过度的悲戚和绝望,而是一种沉静的感伤,她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便有了更微妙、细腻的含义。在戏剧的后半部分,当友人夫妇和妻子一起寻找失踪的丈夫时,三位演员并未采用生活化的表演技巧,而是围绕着舞台反复地缓缓行走来表现。
在友人夫妇积极寻找丈夫的时候,妻子的表现值得深思:她似乎已放弃了“寻找”的动作,不再追问丈夫不辞而别的动机,而是处于一种精神“休克”的状态。那一夜,妻子多次打开窗户,呆呆地站在窗边寂听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企图将渺小的个体置身于宇宙的无限黑暗之中,站在舞台中央自白道:“此刻我是如此的空虚,就像海浪和黑暗。”通过直面风暴,妻子渐渐地从失去丈夫的不安中解放出来,感到自己和黑暗融为一体、成为空虚的一部分,这一生命体验和日本美学理论家大西克礼所言“哀”的体验有相似之处。大西克礼认为,“哀”的体验源自认识到生命中存在着超越个人意志的深刻悲剧性,即“在人生与自然的深处,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虚无’的形而上学的‘深渊’(Abgrund),人间的所有悲哀、愁苦、喜悦、欢乐最终都被吸附进去”[4]P94。
戏剧的尾声,友人向老妇诉说自己过上了怡然自乐的婚姻生活:“买了块地,自己造了幢房子,按我们自己想要的样子。”主人公夫妇和友人夫妇形成了对位的镜像关系,前者天人永隔,后者则白首到老。诸行无常,老妇却早已释怀,她达观地面对命运中的所有挫败,选择独自留在承载痛苦回忆的老屋内。戏剧在老妇静静靠窗站立的画面中结束,未发一言,传递了接近于“无”的人生况味。
结语
和福瑟的其他作品一样,《一个夏日》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与气质,它在形式和结构上遵循的极简主义美学,使得该剧在国内的接受范围相对而言较为“小众”。此外,挪威语的发音曲折多变、较为复杂,汉译对白往往难以保留原作的风味,因而部分观众在观剧过程中难免感到违和,无法领略原作独特的音韵之美。总体而言,《一个夏日》是一部精致而意蕴深长的作品,福瑟的到来也将会在中国戏剧界留下一道独特的印迹。
参考文献:
[1]《约恩·福瑟谈当代戏剧创作》,《东方早报》网页版,详见:https://www.sohu.com/a/72755906_117499
[2]郭晨子:《福瑟来了》,《上海戏剧》,2015年第1期
[3]约恩·福瑟著,邹鲁路译:《有人将至》,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4]大西克礼著,王向远译:《幽玄·物哀·寂——日本美学三大关键词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
责任编辑 姜艺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