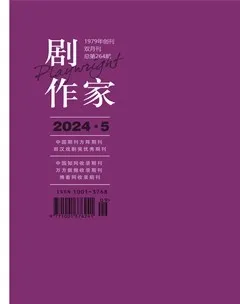亦师亦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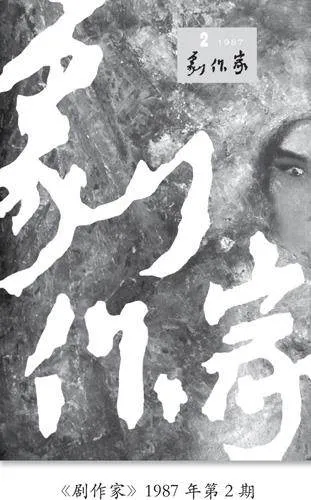
在我的印象中,我其实是见过《剧作家》的创刊号的。
那是1980年的春天,我上小学三年级。我父亲当时是哈尔滨话剧院的演员。有一天夜里,他演出结束后回到家中,带回来两本崭新的杂志,一本是《外国戏剧》1980年第一期,其实这期由中国剧协主办的杂志也是创刊号,只不过当时没这么叫罢了;第二本就是那本1979年创刊的《剧作家》了。哦,不对,它当时的名称还是《黑龙江戏剧》,它是1985年才开始改叫《剧作家》的。
现在的孩子可能很难想象1980年代的小学生有多少适合他们阅读的课外书,我印象中当时填补我的精神生活的是《少年文艺》里的小说诗歌、《中国少年报》中知心姐姐的回信,以及广播电台里孙敬修老爷爷讲的故事。对了,还有叶永烈老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所以可以想见的,我对这两本杂志进行了非常认真的阅读。因为家里总有我父亲带回来的他们排练演出的话剧剧本,当然,那时候哈话的剧本都是手写刻版然后油印出来的。我经常假模假式地拿着看,不过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所以后来对剧本格式很熟悉。但应该说,阅读体验是很差的,所以这两本杂志上铅字刻印无比清晰的剧本,当即就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虽然看着还是有点吃力,但我还是兴趣很高。我印象中大概过了半小时不到,我不得不把两本杂志都抛在一边了,一方面是我父母不停地催促我赶紧睡觉,另一方面是因为《外国戏剧》我看不太懂,所以主动放弃了。《黑龙江戏剧》我觉得我能看懂,但是爸妈不让看了,我只好去睡觉。
然后我第二天放学回来找这本《黑龙江戏剧》接着看的时候,这本杂志却怎么找也找不到了,回来问爸妈他们也不知道,我记得自己好像还哭了一通,然后很不情愿地去看那本《外国戏剧》。直到今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回想四十多年前的这个时光片段,我忽然意识到,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是生活给我的一个印记,似乎在暗示我,或许我今后的命运,会和戏剧有很深的牵缠。
后来的日子就乏善可陈了,在满18岁之前,我和《剧作家》杂志再没有过任何关联,直到我考上省艺校编剧班,开启我的写作之路的时候,《剧作家》突然就成为了绕不过去的学习材料,一是艺校资料室每期都有订阅,二是管理资料室的王老师是我们当时的班主任、后来的校长高德峰老师的爱人,三是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泡资料室,所以《剧作家》就成为了我的必读刊物,只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它就是曾与我擦肩而过的《黑龙江戏剧》。
其实还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有些难以描述,怎么说呢,举个例子吧。比如我在编剧班上课的时候,学校请了很多当时省内知名的剧作家来给我们讲课,其中就有李景宽老师。而在景宽老师给我们上课的前一天,我们刚在《剧作家》上看到景宽老师当时的新作《马铁匠、冯鞋匠和他们的女人》,结果第二天就看到作者坐在我们面前给我们讲课,那感觉相当奇妙。就有点像我的电影第一次投拍,我在现场听演员说出我写的台词时候的那种感觉,这可能是独属于作者的一种奇特感觉吧。
回想起那个时代的《剧作家》,至今我还会有那种“心潮澎湃,难以自已”的感受。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剧坛思想最活跃、碰撞最激烈的时代,席卷全国的“戏剧观”大讨论就是从《剧作家》发表的马也老师的文章开始的,开启了几乎整个戏剧届人士的……我愿意称之为“心灵震荡”,让我们的戏剧艺术观念开始有了崭新的变革,摆脱了旧有戏剧观的羁绊,大胆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出现了一大批的好戏。谭霈生谭先生的《戏剧本体论纲》也开始在《剧作家》连载,我每期追看,期期不落。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看利民老师的成名作与代表作《黑色的石头》,看完之后我心里闷闷的,想哭又哭不出来,想喊又张不开嘴,我第一次无法以好坏来判断的一个人物,那就是秦队长。我甚至第一次理解了什么是对情感与灵魂的摧残,那就是庆儿的野鸭子被宰杀的时候。我也第一次意识到,一部作品如果真的能够触动观众的话,观众是会产生生理反应的。细思起来,戏剧艺术的力量其实无比强大。所以我当时就开始了我的野望,我什么时候能在《剧作家》上发表一个大戏呢?我觉得相当遥远。
编剧班毕业之后,我分配在省艺术研究所地方戏研究室,工作了大概两年半的时间,别的不敢吹牛,但我敢说,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艺研所资料室里的书我读了大概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但我的同学们已经发表和制作完成了许多作品,我除了在省报上发表了一篇两千字的散文、在艺研所的刊物《艺术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之外,就再没有什么作品了。我当时的女朋友问我说,你不是学的编剧吗?怎么不见你写剧本呢?这问题让我相当难回答,我只好向她举起我手中的《剧作家》,说也许你能在这上面见到。说实话,心虚得很。虽然我最后实现了这个目标,但她也没兴趣看了。
1993年省里搞天鹅艺术节,我被抽调到简报组,随后又被借调到省文化市场管理站综合科工作,又工作了两年多,其间,我又泡在了厅里的资料室,没想到,《剧作家》所在的省戏剧工作室搬到了厅里,我于是又多了一个戏工室的资料室可以泡,管资料室的是隋兵隋姐。直到我在资料室里碰到书彰老师。
刘书彰老师是谭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分回省戏工室,我在艺校编剧班时,他带过我们班一个学期的写作课,绝对是亲老师。我写过一个名叫《迟到》的小品,书彰老师给了90分,这是我当时最能拿得出手的创作成绩了。他在资料室碰到我的时候很吃惊,了解到我的关系已经转到文化市场管理站了,就更吃惊,问我为什么还总泡在资料室里,我就偷偷告诉他,因为还是喜欢写剧本。我就把我业余时间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龙虎父子兵》的剧本拿给书彰老师看了。就是这一次的师生邂逅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命运——1996年10月到1998年5月,我和付军凯、炜立、杨晓泉等兄长一起被推荐到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为省里代培的高级编剧研修班,而我的电影也在我到达北京上学的前一天在北京怀柔开机了。
上学以后,我的关系就从省文化市场管理站调入了省戏剧工作室,毕业以后我正式成为省戏剧工作室的正式员工。但当时我从北京回来没有分配正式工作,我给《剧作家》当过一段时间的栏目编辑,但这点儿活儿不够我干的,我就翻译了塞缪尔·贝克特的一个哑剧剧本《没有语言的行动(一)》及相关的评论和我翻译之后的心得,发表在《剧作家》1998年第四期,没想到这居然是我发表在《剧作家》上的第一部作品。而我在研修班创作的毕业大戏《赵氏孤儿》发表在1999年第六期,孙天彪老师在卷首语里很是“飘扬”了一下我这部话剧处女作,他说的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与其说我们为了一部优秀的作品而兴奋,不如说我们为发现了一个年轻的“戏剧人才”而更欣慰,总觉得天彪老师是“谬赞”了,但我总算终于完成了我当年的那个梦想。在1999年第一期,我又发表了一部翻译作品,美国剧作家哈维·菲尔斯坦因的独幕剧《整洁的结局》。因为有了这么一点小小的成绩,1998年,我被吸收进入了省舞台艺术创作中心,当时中心成员男士中廉海平廉哥最小,35岁,女士中辛彩屏辛姐最小,33岁。我加入的时候,28岁,是最年轻的中心成员。廉哥当时兴奋地说,太棒了,终于有不到三十的小嘎儿了,我退位让贤。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剧作家》已经四十五岁了,可是我们的戏剧事业并没有蒸蒸日上,反而肉眼可见地进入衰退期了,如果没有郭玲玲,54岁的我可能还是创作中心最年轻的成员,已经有太多人离开戏剧舞台了,而愿意学习舞台剧创作的年轻人少之又少。但《剧作家》一直还在,很有趣,现在的《剧作家》编辑部全员女将。编辑部的这些妹妹们还在坚持,我相信,还有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坚守在戏剧的岗位上,为戏剧的薪火传承代代守望。
我记得《小说选刊》在1989年8月停刊了,这也是我当时最喜欢读的刊物之一。刘震云老师写过一篇文章纪念这件事,在文章中他提到了自己和《小说选刊》的关系,大意是,这次停刊,有点像是胡同口最熟悉的二大爷没了,心里空落落的。但万幸的是,1995年6月,《小说选刊》又复刊了,不知道震云老师有没有为二大爷的复活再写一篇文章。
《剧作家》对我来说,不是二大爷,而是老师、是朋友,还是同事。我衷心期望着《剧作家》创刊的五十周年,哦,那时候我应该快退休了吧,六十周年,七十周年,《剧作家》会一直在,因为戏剧,也一定会在。
责任编辑 姜艺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