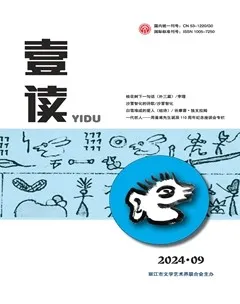文行大道,致敬先贤
作为晚辈后学,很荣幸能够参加周善甫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这是一次向一代哲人致敬的幸事,更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我省文坛盛事。吾辈何其有幸,前有先贤道德文章,亮如火炬,照耀前进之路;现又躬逢盛世,伟大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如火如荼。今天,我们重温一代哲人周善甫先生的生平业绩、精妙华章,不啻为学习先生“为往圣继绝学”之难得机会。
周善甫先生作为纳西民族的佼佼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者、弘扬者,其毕生秉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人生,堪称当代士林典范。周善甫辉煌哲学巨著《大道之行》,奠定了周善甫先生一代哲学家的学术地位。从尧舜禅让时代到夏商周秦、唐宋雅范、再到明清至近现代,中华民族文化源流、思想哲理、儒释道文化,乃至汉语词义辨析,既有黄钟大吕之宏阔呈现,也有鞭辟入里、切中肯綮的精妙高论。至今捧读,仍令人眼界大开、醍醐灌顶。先生将中华文化的内核归纳为“中华自成世界”,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认为:“自古以来人类文化,总不出爱好和平的农耕文化,和崇尚竞斗的非农耕文化。中华文化是农耕文化的代表,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爱和平、崇公益、尚勤俭、重情谊、尽义务为正则,本仁人之心,实现‘我为人人’之理想”。其文化自信和自豪,实为我辈终生学习之楷模。
周善甫先生虽出生于滇西北偏远的纳西民族聚居地丽江,却是当地难得的诗书旧族,家风雅望非常。青壮年时期的周善甫先生在省立东陆大学(云南大学)主攻的是理工科,但渊源的家学使他毕生自觉地肩负起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而且矢志不移。我们知道,高度的文化认同是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尤其是在多民族的祖国西南边疆,周善甫先生的业绩显得更具有时代意义。这就是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云南多民族地区的具体体现。我与周善甫先生的交际是1990年代的晚期,我和原云南省作协副主席汤世杰老师编省作协的机关刊物《文学界》,汤老师和晚年的周善甫先生过从甚密,常向周老请益、求教、探讨,也曾有几次带回周老的文章让我编辑。在1997年第二期《文学界》“作家随笔”栏目中,我们编发了周善甫先生的《重上云杉坪》。这是周老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在这篇生动有趣的文章里,周老回忆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和毕生热爱玉龙雪山的杭州艺专毕业生李霖灿、李晨岚,及其哥哥周霖雇了马帮,带上帐篷炊具,枪支画夹,结伴登上云杉坪的往事。他们从丽江古城出发,历经三天跋涉才抵达云杉坪,先生形象生动地写道:“蓦地里,见到那五百年风流孽冤地。身入这壮丽的自然宫,大家先是一怔,随即就都疯开来。哥哥跪了下去,匍匐在开满鲜花的草地上放声呜咽;我和霖灿则翻筋斗、立蜻蜓,遍地打滚;而晨岚则着迷发呆,坐下来‘啊’个没了。”这次青年时期的壮游令周善甫先生终生难忘。半个多世纪后,周霖、李晨岚死于动荡年代,身在海外的李霖灿先生病中寄来一缕白发,埋于云杉坪,以象征他对这片壮丽山川的回归。尤其令人感慨的是,周善甫先生在八十四岁高龄时,借助省文史馆采风调研之际,竟重上云杉坪。据说行前,云南省文史馆的领导担心年过八旬的周善甫先生年老多病,怕出意外。但周老却豁达地说:“请带上把锄头,死便埋我。”面对这样一位对人生如此旷达洒脱的长者,有谁能轻言婉拒?从来“江山助性灵”,在雄伟瑰丽的大自然面前,我们看到了周善甫先生豪迈真情的一面。
我编辑周善甫先生的第二篇文章已是他的遗作了。时在1998年初,周老刚刚过世。该文成稿于1997年夏季,《文学界》98年第一期“98文论”栏目刊发了周善甫先生的雄文《道德与文章》。周老向来对汉语词汇敬重有加,辩理析义,严谨精微。在他看来,“道”是“德”的思想基础,“德”是“道”的行为表现;而“文章”则有行施教化、“文以载道”之功能。道德出于人性,文章关乎社稷。周老提出“善善、恶恶”为文章之天职。“善善”是指彰扬美好、“恶恶”则指 批判丑恶。周老还指出“ 中华文化较宜于‘善善’一路文章发育的土壤,而西方文化则偏于‘ 恶恶’一路文章繁殖的温床。” 因此,中国文章积极肯定道德,具备建设性的教化作用,才让中华逐步形成伟大国家。今天重温周善甫先生的两篇旧文,再展读《大道之行》 附录的《周善甫先生年谱》,回顾这位哲人丰富多彩、跌宕不羁的一生,不能不令人掩卷长叹,敬佩有加。周老学术生涯的巅峰期,不在他的青壮年,而是退休以后的暮年。《大道之行》《老子意会》《春城赋》《简草谱》等华彩篇章都著述于周老古稀之年。现在我们难以设想一代哲人是如何在喧嚣繁杂的闹市之中,蛰居于昆明翠湖北路的一处斗室之内,青灯黄卷之下,披肝沥胆、孜孜不倦地梳理中华文明渊薮,赓续数千年文脉精髓。是可谓“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堪称“为往事继绝学”者。周善甫先生是一个寂寞坚韧的文化先行者,独步在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文化长廊里。睿智、隐忍、执着、刚毅。他的晚年留给我们一个清癯平和的儒者身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学人的形象,是我辈治学为人的终生楷模。
(作者系云南省文联副主席、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