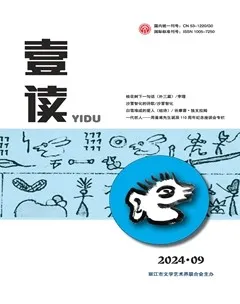嘱托
一
下飞机天就黑了,停机坪昏暗的灯光下,乘客彼此是看不清脸廓的,人们仿佛都戴着一副灰色面具。摆渡车迟迟没有来,乘客们集体朝一个方向看,仿佛眺望挂在东边苍穹的月亮。
嗨!一个肩挎白色手提袋的女子跟我打招呼。我瞥她一眼没搭理她,她就挨过来,用近乎祈求的口吻说,帅哥,我怕走夜路,搭个伴行吗?我脑子里忽然闪出她的狡黠,瞪她一眼,不耐烦地转身九十度,试图避开她的纠缠。她转一百八十度绕到我面前,依然是祈求的口吻说,不要这样嘛,我方向感差,就想搭个伴,不答应也就算了,何必这样!我心里动了一下,妹妹也有这个毛病,有回找不到回家的路,打110才找到她。但我还是决定拒绝,冷冷回答,找别的人吧!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她悻悻地转过身去,像受委屈似的,用一只肩头对着我。我正想着离她远点,她突然又转过身来,眼里含着一汪清澈,弱声说,我很讨厌吗?我突然心肠一软,说,一路就一路吧!她转忧为喜,叠声道,谢大哥!谢谢大哥!
刚才彼此没注意,即使注意也像在雾里,朦胧不清,现在一接近,我才发现她长得挺精致,二十七八岁年纪,身高一米六左右,眼眸像光珠一样灿亮,穿一套阿迪达斯白色莫代尔棉运动衫。
摆渡车终于来了,上车的人像蚂蚁一般拥挤,她生怕挤丢了,捻着我的一只衣角,我就像牵着一只羊。
几分钟后,摆渡车停在入港大厅门前,她像押解犯人一样“命令”我,你先下。我下了车,她也跟着下来了,捂着嘴一个劲笑。
妻子走之后,我天天看她的遗像,享受着一时的清静。莱州颁奖会本不打算参加的,主编打电话给我,说颁奖期间要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我只好强压悲痛前往,想不到一下飞机就碰上了这个女人。实际上这女人并不讨厌,只是看妻子遗像时间长了,感情上一时不能接受。
我问她来烟台干嘛,她说去蓬莱。去蓬莱旅游?我问。不全是,为一个诺言。她说。我揶揄她,这年头还有信守诺言的人?她说,怎么没有,你没有发现不等于没有。我笑她幼稚,她说我冷漠。
那年秋天,一个懵懂的女孩考上H大学。报到那天,她按时到新校区报到,到学校才知道报名处临时改了,因为路盲,女孩找了许久没找到。眼看黄昏临近,她还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蹿。报不上名,意味着住不上学校宿舍,住不上学校宿舍就得住校外酒店,住校外酒店就要花费父母的血汗钱。她不想这样,荷包里的钱都是爸妈东借西借凑来的。她下意识地捏了捏缝在内衣口袋的钱,像钻进大山迷失方向一样绝望。女孩望着穿梭不息的人流,问这个不知道问那个不理睬,她就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急得差点哭了。此时,一个学姐模样的女孩走过来,她赶紧凑上去,问新生在哪里报到。那女孩先是一愣,随即粲然一笑说,报名处改在老校区了。女孩问,咋走?那女孩犹豫一下,说,新老校区相距30多公里,不好找呢,这样吧,我带你去。遇到好心人,女孩激动得差点想去拥抱她。
她们打的去报到处,女孩要付的士费,那女孩已付了。后来她们同一个学院,千年修得同室住,她们住上下铺,成了最知心的朋友。毕业那年秋天,那女孩邀女孩一起游蓬莱,游完八仙渡,到了栈桥,那女孩眺望深蓝大海,说一定要许个愿。她们就朝烟波浩渺的蓬莱山双手作揖,嘴里念念有词,许下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的诺言。那女孩又说,将来谁先死,活着的人一定要来栈桥作最后的送别。
我就是那个找不到报名处的女孩。她说,我的方向感不好,最怕一个人外出,若不是为诺言,打死我也不会一个人出来的。我安慰她,方向感不好并不可怕,高智商也有方向感问题,现在有智能手机,一键导航就解决问题。她转过脸来,目光一下撞上我的目光,我的心一下子有涟漪般的荡漾。
那件事发生后,我特别害怕走夜路,仿佛走夜路会碰到鬼。她说,如果你不愿意,我也不会勉强,我会找其他人,但不会找男人。其实烟台我也不熟,我说,但答应的事我不会反悔,更不可能做小人们做的事情。
你是来旅游的?她问。我告诉她,我去莱州开会。她就有些怅然,嘀咕说,这么说来,我又要一个人去蓬莱了。我赶紧解释,陪她去蓬莱完成心愿可以,不能陪她一路。她说不成,我去哪她就去哪。我说我有活动,不方便带她。她说我活动我的,她可以等。我想了想,征询说,愿意参加我们活动吗?我可以给你申请自费名额。她欢快得像只小鸟,忙不迭说,愿意,太愿意了。很快我就觉得我这是作茧自缚,会议通知家属才能自费参加活动,她算什么呢?
二
入港大厅灯光如昼,取行李的人像蚂蚁一样聚成一堆,我得同她一道取行李。环形输送带运转着,一件一件送过行李来,她那个旅行箱像一个集装箱,一看就挺沉。对上号牌后,我帮她从传送带往地上搬,第一次没搬动,第二次才请人搭手挪到地上。什么鬼东西呀!这么沉。我嘟囔着。她说是化妆品。又问我订酒店没有。我说订了,维也纳国际酒店。她吐一下舌头,说,住这么高档的酒店呀!我说不贵,一晚两百多块钱,如果嫌贵,可以订便宜一点的。她瞥我一眼,噘着嘴嘀咕,小瞧人!随后拿出手机,打开微信里的“酒店”,订了同样的酒店,又指着行李箱说,箱子沉,滑轮有点卡,请帮个忙。话说得我没理由拒绝,我伸手接过来推着。她乜我一眼,掩着嘴笑,好像占了我便宜似的。我说刚才还眼泪咕噜的,现在倒开起心来了。她说散心就是散去不快之心,伤心人老得快,她不想老得太快。
大概女人都怕老吧!就像妻子,她性格内向,一天沉静得像只花瓶,还有洁癖。要是像她这样开朗,或许她就不会走得这样早。想到这里,我问,美女咋称呼?李静,娄底人。她问,你呢帅哥?阳刚子,阳城人。她一听说我是阳城人,不说话了,埋头就走,像谁得罪她了似的。
刚才你说那件事是什么事?我挑起刚才的话头。发生在阳城的事。李静像回忆一段不愿诉说的往事那样说:那次阳城之行,既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次旅行,也是我一生中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次旅行。我惊奇,问她,怎么讲?她捋捋耳鬓头发,说,我的同学就是阳城人,她后来的不幸与那次旅行有关,说白了都是我的错。我大惑不已,有这么严重?她就把那个夏天发生的事复述了一遍:
大学毕业后的第二次省考,我同学考上公务员,她微信给我,邀我去阳城玩儿,说阳城小吃天下第一,包我吃货满意。我心痒痒的,但忙于找工作,一直未能成行。直到去年夏天我才去了阳城,广州太热,我决定在阳城避暑。阳城生态好,甲秀楼的鹭鸶,花溪的水,黔灵山的猴,天河潭的溶洞,那真是绝妙的风景。她带我玩遍阳城所有知名景点,吃遍阳城所有的小吃,肠旺面,“丝娃娃”,恋爱豆腐果,我吃上了瘾,乐不思归。
不幸的事情就发生在我避暑结束的那个深夜,第二天我要离开阳城回广州,老同学硬要拽我去吃当地最有名的烤豆腐,烤豆腐真香,我们边烤边喝啤酒,喝到微醺才发现夜深了。她家住一个老巷子,离烤豆腐的地方大约一公里。我说打的,她说不远,走路醒酒。我们就嘻嘻哈哈,晃晃悠悠沿南明河走。那晚月亮不知死哪去了,巷子阒寂如地狱,若明若暗的灯光像狼眼一样,发出幽暗的光。她是本地人,不害怕,我却瘆得慌,背沟发凉,仿佛背着一块冰。
巷子不长,这端到那端大约三百米远,越走巷子越昏暗。我们走到一个豁口处,灯光惨淡得像萤火虫,我感觉一股冷风吹过,随之蹿出一个人来,戴着面罩,样子狰狞。他朝我们笑,我和同学穿的都是短裙,高跟鞋,要跑也跑不快。她急中生智用阳城话说,我就住这巷子,你想怎样!那家伙并不理会,像鬣狗一样横在路中间。我颤抖着过去,那家伙一把抱住我,像抱一只被惊吓的兔子。我挣扎,他铁钳般的手箍得我无法动弹。我喊叫,嘴巴被捂住了,喉咙发出嗯嗯的声音。她突然清醒,抢上一步,打A6+FNL7Agl0VPb+ebIKZV+Qh3mb1JFnMtavlNTd71WM=了那家伙一记耳光,她毕竟力气太弱,根本无济于事,她又低头去捡石块,巷子竟然连一根草都没有。她脚踢手抓,那家伙一点不疼,依然攫住我不放,嘴里喷出像大粪一样的恶臭,我几乎眩晕。她情急之下狠狠咬那家伙手臂一口。那家伙哎呀一声松手,我乘机挣脱,扭头就跑。流氓随即抱住她,她叫我快跑去叫人。我边跑边喊救命,一直跑到邮电大楼。黑咕隆咚的夜,像死了一样,只有空旷里我那无助的呼喊。等我一脸沮丧转回来,坏蛋已经得手,同学裙子已被撕成两片,一片遮着裸露的下半身,一片遮住脚踝。她瘫坐在矮墙边,呆滞的目光望向那盏若明若暗的路灯,如同一块岩石。
后来我回广州,没再联系。但那晚发生的事,像梦魇一样潜伏在心里,想起来就害怕。李静说,一年后,她发来一段微信,全文是这样的:李静,可怕的抑郁症又犯了,它像暴徒一样追逐着我,逼喝孟婆汤。无路可走,道一声:永别了。
我仿佛听到了那个绝望的声音,它像一生还不清的银行贷款那样,随时被催付利息的煎熬。我想起结婚的晚上,她不知从哪寻来一块红布搭在头上,说是红盖头,要我揭盖头,说揭了红盖头就白头到老。我揭开红盖头,她的目光像燃烧的火焰,一下子把我融化了。她问,将来我老了,你还爱我吗?爱!生不同时死同穴,你说的。我说。她又说,我不想老,我要一辈子年轻。妻子小我八岁,结婚时不到二十五岁。我说,要老也是我先老,你永远二十五岁。她就咯咯咯地笑,好啊!我喜欢。她闭合窗帘,摁灭台灯,一下子把月光堵在了窗外。清晨醒来,我发现她美丽的脸庞有滑过的泪痕。我问她为什么哭。她一头埋进我怀里,抽抽噎噎讲述了那个夜晚发生的遭遇。
其实我和妻子的结合纯属缘分。
那天我是去机场接一个生意上的朋友燕飞雪的,燕飞雪和她同机,刚好邻座,两人聊起来,一聊就聊成了朋友。下了飞机,燕飞雪说有朋友接她,一起坐车回市里。她就坐我的车进了市区。她回观山湖,燕飞雪非要拉她吃晚饭,我也尽力邀请,说吃完饭送她去观山湖。她答应了。
饭后,我们互加微信,送到观山湖后再无联系。燕飞雪要回南京那天,她又微信她来陪她吃告别饭,她半天不回。燕飞雪叫我打电话,电话很快通了,原来她把手机放包里了,我说燕飞雪要回南京了,请她一同吃个饭。她很快就打车过来了,在公司喝茶聊了会儿天,一同去鼎罐城吃凯里酸汤鱼。其他人她不熟,悄然坐在燕飞雪身边,落寞得像只落单的雁。燕飞雪倒是见人熟,一桌人很快就混熟了,她反而成陌生人,晾在一边。但她不显得冷落,甜甜地抿笑着,沉静得像一株不爱热闹的雏菊。燕飞雪回南京以后,我约她吃过几次饭,她没有拒绝。一年后,我们结了婚。
三
甬道很长,李静说要上厕所,叫我守着行李。我站在开水炉旁等她。她从厕所出来,张嘴就说“大姨妈”来了,烦死人。她把我当成女人了。谁是“大姨妈”?我不知道女人来月经叫来“大姨妈”。她发现失了言,吐一下舌头,接一杯水递给我,喝杯水吧!故意岔开话题。我喝完,将小纸杯丢垃圾桶,夸她不错,有礼貌。她做个鬼脸,头一歪,说,不错也没人要。说完,匆匆朝前走,脑后“马尾巴”像一束移动的柳枝。
我追上她,说,不怕迷路了。她说,迷路也不会有人同情。她这一说,我反而无话可说了。她又说,求人不如求自己。她发泄对我刚才的态度的不满。我说方向感差不怕了,一部手机走天涯。她反唇相讥,什么意思,又想甩我?我说,我可没那意思啊!她说,反正是赖上你了,你走到哪我就跟到哪。
她一说,我倒觉得有些对不起她了,想着如何弥补,没搭她的话。她就不高兴了,抢上一步拦住我说,喂!不说话不准走啊!我扑哧一声笑出来,说,哪有这样逼人说话的呀!她说,不是逼,是需要沟通。我笑她,一分钟没讲话就憋不住了?她说,你这人真的坏!
这不由让我想起妻子,她也爱说这句话。恍惚看,李静真有点像妻子,个头,穿着,说话的语气,走路的姿势都像,还有一模一样的运动服。只是脸盘子不像,她是鹅蛋脸,妻子是苹果脸;她的脸红润,妻子的脸白皙。
李静从挎包里掏出化妆镜照了照,说,阳刚子,你老婆一定漂亮吧!是的,她很美,但她已不在人世了。我幽怨地回答她。对不起对不起,我让你伤心了。她轻打自己的小嘴说。没什么,我喃喃呓语,天堂是归宿,早晚人如此。夫人是怎么走的?她又问。原本这是我最不愿提及也不想回答的问题,既然李静要执意知道,我只好说:抑郁症自缢。她震惊,拎着包的手抖了一下:我同学也是。同病相怜的遭遇,李静的眼圈有点红,我则是心境凄凉。沉默是最好的互慰。
人生中,有些事是可以不说的,可妻子包不住秘密,她把那个坏蛋性侵的事全告诉我了,我一时不能接受,或者说根本就不接受。那段时间,妻子像一个犯错的孩子,说话做事小心翼翼,生怕我不高兴。贞洁这个魔咒折腾得我们不得安宁。她提出离婚,我没有同意,因为她已经怀了我的孩子,我们之前同居的孩子。我信誓旦旦表白,不是她的错,是社会上有坏人。她信我的话,相信我会真心待她,因此精力充沛,对做爱表现出极大兴趣。她越这样,那个浑身腌臜的家伙越会偷跑出来,我就力不从心,像吃泻药一样疲乏不堪。膈应,厌恨,绝望,像抽丝拨穗的绵虫,慢慢使我枯萎下去。我羞愧地对她说,我不行了,对不起。她就匍匐在枕头上嘤嘤哭泣,而我,竟麻木得像没听见一样。
不久她就抑郁了,我又怕她犯傻,经常回来“监视”她。她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穿着白色阿迪达斯莫代尔棉运动服。见到我,她无精打采的眼睛就会突然放光,她也像孩子一样扑进我怀里。一个劲说她怕,怕我不回家了。我心疼地将她搂进怀里,哄她说,不会的,不会的。她就埋进我的怀里抽泣起来,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我摩挲着她的头发,她的头发软软的滑滑的。她很快就睡着了。我怕她受凉,抱她去床上睡,她又醒了,继续抱紧我不放,生怕我真的会离开似的,我的心像被锯子锯一样,碎裂般疼。
贞操这面魔镜,终于照出人性的虚伪。我表面上维持一种幸福的体面,心理上却是丑陋的嫌弃。我变得苦恼,烦躁,冷漠。我不愿回家,甚至不回家,我拼命请人喝酒或是找酒喝,直到喝得酩酊大醉,成为行尸走肉。
这一段我隐去了,我不想让污浊的自尊玷污纯净的灵魂,掐头去尾给李静说了下面的事情:
她抑郁后完全变了个人。眼睛再没有先前那样灵动有光泽了,整天呆滞地望向一个方向,像没有灵魂的木偶。偶尔会干笑一声,笑声仿佛从地里冒出来,阴森可怖。我怕她对孩子不利,把孩子送乡下老家,专门请了一个奶妈。孩子离开后,她的心性就完全变了,吵着闹着要孩子。我给她解释,她竟然大打出手。我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说是重度抑郁症,要我多陪陪她,开导她,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给她服舍曲林,陪她散步。有天她忽然对我说,刚子,活着太没意思了,我想死。我被吓出一身冷汗,之后我更不敢离开她了。一段时间,她变得跟正常人一样,完全不像有病的样子。
一天清早,她催我去上班,说不能耽搁公司生意,疫情之后,生意的确难做了。她给我做早餐,做我最喜欢吃的西红柿鸡蛋面。我不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因为她一年多没有做过家务了。她笑说,咋地,整得我像第一次给你做早餐似的。我苦笑,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吃完早餐,她又恋恋不舍,絮絮叨叨讲了一大堆我听得害怕的话,什么少熬夜,少喝酒,要学会照顾自己。她甜甜地笑着,叫我早点回家,她做饭等我,我答应她一定早点回来。她就送我下楼,直到看我开车走了才返回屋里。
那天我特别心慌,六神不定,可公司琐事太多,因为好多天没有正规上班了,一直忙到六点钟,我才匆匆开车回家,大脑一片混沌,路上压死一只猫也不知道。到了家,发现妻子没在门口接我,往常都是她接我,时间算得精准。我预感事情不妙,一间间房子找她,她像消匿了一样,不见她的踪影。当我在卫生间找到她的时候,凄惨一幕令我窒息。地上有几粒药丸,原来她根本就没想控制抑郁症的发作。
四
走出大厅,李静说坐航空大巴好看烟台的夜景。我说大巴到航站楼还得转车打车,不如直接打车方便。她说行听我的。刚统一意见,一辆绿色的士就开过来了,司机是个青年人,耳朵上挂个耳麦,摇头晃脑在听歌,手指敲击着方向盘。我叫他打开后备箱,他像忽视我们的存在一样。值班员曲着食指敲玻璃,他才打开后备箱。我将行李箱放进去,行李箱太大,几乎填满整个空间,所幸能盖上后盖。我欲坐副驾驶,李静扯我的衣角,示意我坐后排。我就开门让她先上,她弓着身子钻进车里,浑圆的屁股像只大南瓜,让我有了想象的对比。
脑子里又浮现出妻子挂着的样子,她像挂在衣架上的一件单衣,没想到会瘦成这样,肥硕的臀部像风干的丝瓜。我打110,警察很快就来了,法医把她放下来仰躺在地板上,脸灰白得像石灰,好看的酒窝干涸了,像一个死水氹。乌黑的舌头伸出来,硬翘翘的,法医像塞一块冻肉那样硬塞回嘴里,依然闭不住嘴唇,露出一条缝。她就这样被安放在殡仪馆的冰棺里了。
司机听音乐,我在想心事,李静斜躺着闭目养神。司机摘下耳麦,主动介绍烟台的来历。他说古时候烟台是个渔村,渔村最高的山叫烟台山。当时沿海一带常受倭寇骚扰,老百姓苦不堪言。为尽早知道倭寇动向,当地驻军就在烟台山设立烽火台,发现敌情点狼烟报警,人们称烽火台叫烟台,这就是烟台称谓的由来。哟,你知道的掌故不少嘛!我夸他。他嬉笑着,好高兴的样子,烟台是我的家乡,宣传烟台就是宣传自己嘛!呵呵!我说,挺有觉悟。这有啥的。他说,俺烟台发展了,俺生意就会好,收入就会高,双赢嘛!我问机场离市区多远,他说40多公里。李静冷不丁插话,40多公里要150块钱,这不是宰客吗?先前她和司机讨价还价,心里窝着火。俺烟台人讲诚信。司机说,我开出租好几年了,从不宰客。鬼知道。李静不相信。
啊——我倒是听出味儿了,司机一脸堆笑,指着副驾驶挡风玻璃下方工牌说,这上面就是投诉电话,你可以投诉。我换个坐姿说,现在出租车行业有些乱象,我在南昌就被宰过,司机欺负我路不熟。别的地方我不清楚,俺烟台不会。司机呷一口茶说,我是北马路国营化工厂工人,企业改制后出来开出租。我宁愿少赚点,也绝不昧良心。我说,你讲良心别人不一定讲良心。司机傻笑,说,我相信好人有好报。
李静挨我很近,身体散发的热量,像燃起来的一团火。司机拿名片递给我,说,你们夫妻要包车就打这个电话,全天候服务。李静像放开的弹簧,一下子弹起来,申明说,我们不是夫妻,别张嘴乱说。嘿嘿,司机干笑,这么般配,我还以为是呢!对不起了美女。去去去!李静又往后一靠,说,乱点鸳鸯谱!司机讪笑,现在的事情不好说,说是夫妻吧没结婚,说不是夫妻吧又住一个房。他的话像子弹一样击中李静,白皙的脸庞瞬间涨得通红。你说什么呢,把我当什么人了?玩笑,玩笑!司机赶紧认错,我没说你啊美女!李静还不解气,拉着一张脸:谁跟你开玩笑!我用手肘拐她一下,示意她少说两句,她反拐我,你听他说得多难听!我说,师傅说的是社会现象,没说我们。
阳刚子,她突然像睡醒一样问,你晓得嗣子巷吧!当然知道,是个老阳城人都知道。我说,我岳父家就住嗣子巷。李静坐直身子,我同学也住嗣子巷,一幢新修的三层楼,我在她家住了十多天。我惊讶,她是曾筝同学?正想问个明白,她像看穿我的疑惑一样,说她同学叫曾筝,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
我妻子就是曾筝啊!
你妻子是曾筝?
我们相互对望着,车内陷入沉静。司机加大油门,车速提到120迈,唰唰的声音像风吹木叶的啸响,路两旁的参照物飞扬而过,恍如闪电。李静突然脸色煞白,嘴唇发青,右手紧紧抓着我,身子像打摆子一样哆嗦着。我叫司机降速慢行,她就斜靠在我左肩胛闭目养神。我不想让她靠我,又不得不让她靠着。
汽车进入烟台高新区,车速慢到90迈,李静睁开眼,脸上渐渐有了红晕。她说她看见曾筝了,穿阿迪达斯运动服,就在汽车前面向她招手,汽车撞了她。她说得阴森可怖,我汗毛都竖起来了。我说是幻觉,她说真的,曾筝那套阿迪达斯运动衫,是她送她的生日礼物。李静还想说,司机刹了一脚,说,到了。她就把话咽回去了。
我扫二维码支付车费,她抢先扫了。司机将车停在迎宾通道上,打开后备箱,我先下车取行李。行李箱太重,我提几次都没提出来,服务生过来帮忙,直接推进了大堂。
服务员是个国字脸姑娘,皮肤白晰,身上散发出油菜花的香味。我拿身份证登记,服务员登记完递给我,李静抢过身份证,问她有没有和我挨近一点的单间。服务员打开电脑查了一下,告诉她有。她说,开一个单间。登记完,国字脸递还身份证。我问李静,为什么一定要住我隔壁,她装出一副诡秘的样子,顽皮地说,你懂的。
五
第二天早上,我想睡个懒觉,李静按响了门铃,催我起来吃早餐。我不情愿又放不下面子,赶紧爬起来漱口洗脸,收拾完出来,她已变了一个人,穿一套灰烟色牛仔新装,干净清爽,更显朝气。我们坐电梯到二楼餐厅,她叫我坐着别动,她去取早餐,说是回报。我叮嘱她,一碗皮蛋粥,一个鸡蛋两根油条够了。她说好。
她的早餐简约得近乎抠门,半块红薯,一片面包,一杯牛奶。我们面对面坐着,我喝粥,她呷牛奶;我啃油条,她咬面包,像两个不相干的陌生人。吃到一半,她拢拢头发说,你想知道曾筝走前的情况吗?
我最怕提曾筝,又矛盾地想听她所知道的曾筝。她说,女人遇到那种事真的很无奈,可遇上了就是命。不!是我狭隘,偏执了。我说,没想到会害她得了抑郁症。她宽慰我说,先生,抑郁症这个病谁也说不清楚。说难听点是命,说不该点是天意。
她眼望窗外的天空,又说,那晚我跑通整条巷子,连一只老鼠都没看到,太恐怖了。要说有愧的话,我才有愧呢!李静收回望向窗外的目光,懊悔地说,我如果当时勇敢一点,一起对付那家伙,悲剧就不会发生。其实巷子不长,我拼着命跑,可脚像抽筋一样,迈不开啊!事后想来,我太自私,留下一个柔弱女人,怎能抗得过牛高马大的流氓呢?当我倒回来的时候,那家伙已经得手了。曾筝呆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像一座冰雕。我的心彻底碎了。我哭,居然没一滴眼泪,我安慰她,居然说不出一句话。我依偎着她,她的身上寒如冰块,冻得我直发抖。
天快亮的时候,她抖索着整理好裙子,低沉地说,李静,回广州吧!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我期期艾艾说不出话来,没说再见,只留下那条昏暗的巷子在我的记忆里。她后来结婚也没通知我,我也没有当成她的伴娘,或者在她心里就是不想见我。我好孤独好孤独呀!像失去亲人一样孑然。
李静说到这里,泪水像一颗晶莹的珍珠,悄然从眼角滚落。我不知所措,慌忙摸出一张纸巾递给她。她轻轻拭去眼角的泪水,仿佛在销毁一段伤心的记忆,而我,仿佛一个迷途的孩子,在虚幻与现实之间挣扎。
一年后的一个午后,李静说曾筝突然发微信给她,她忐忐着读完微信:李静,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呢?原以为有一个爱我的人会幸福,结果我自毁幸福。要不是之前怀了他的孩子,我会狠下心来和他分手,他不同意,我痛苦悲伤,变得沉默寡言。我以为坦白就是坦荡,结果我错了,女人贞操像一块美玉,有瑕疵会大打折扣。人都是虚伪的,只会顾及那点可怜的面子,他也一样,但我是原罪,再有千般理由,身子不干净是不争的事实。他不再碰我,我理解他。
李静忆及于此,虚脱般哎了一声,我的心犹如波涛汹涌的大海,若不是在公众场合,我会放声大哭。李静说微信很长,最后几句是这样的:李静,他的心魔,我没办法消除。他借酒浇愁,一天喝得酩酊大醉,我心疼啊!我强忍着爱而不得的忧伤,孤独地过了一段日子。我想,与其这样痛苦下去,不如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了,一切就解脱了。静妹妹,其实刚子人挺好,我知道我们走不到尽头,可我放不下东子啊!我走后他定会娶别的女人,我怕东子遭罪,请你替我照顾东子,好吗?
我惊愕曾筝走时没给我留下只言片语,却给李静留下许多。李静用纸巾拭去眼角的潮湿,眼巴巴望着我,好像在问,曾筝有错吗?我的心像针扎一样难受。原来曾筝已经交代了后事,安排了结局。那晚发生的事情,她说得轻描淡写,我被贞洁的执念蒙住心智,我恨得发疯,巴不得宰了那个家伙,可我是个不敢面对的懦夫。我后悔,愧疚,而她,我再也见不到了,留下一个无法弥补的爱情黑洞。
李静说要不是曾筝挡住那个流氓,被害的是她,她说她要完成她的嘱托,担起抚育东子的责任。我说,谢谢她,我会把孩子培养成人,这是我唯一对妻子的报答。她一时语塞,呷一口牛奶,左手撑着下巴,出神地望向窗外。过会儿,她郑重而执拗地说,阳刚子,曾筝托付的事,我想你不会拒绝吧,我良心会不安的。良心不安又能怎样!我说,毕竟你不是她。我可以变成她。她说,这是唯一解决矛盾的办法。爱情不是感恩,是需要培育的。我拒绝。
说实话,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我们性情相投,有好多共同点这就是基础。她说,我在等时间。我喝我的皮蛋粥,她说的话,我还没有想好回答的词语。
慢慢吃,李静站起来说,我收拾一下东西,一起去蓬莱。
哦。我木然地看着她移动的背影,就像看到曾筝的背影一样,当初就是这样的背影迷住了我。走过身边,李静身上散发出栀子花的香味,幽幽的,细细的,犹如迷香一般。曾筝当年的味道,也是这样的香味。
责任编辑:何顺学 夏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