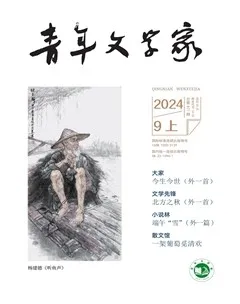西塘,那一廊烟雨

知晓西塘,是源于陆毅早年主演的一部电影。后来,电影名全然想不起来了,“西塘”这两个字却在心里扎了根。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于是,便有了2012年春节我一念而起的西塘行。
“青砖伴瓦漆,屋檐洒雨滴。”这是我心中江南的样子。因为爱,我早已融入了江南的春梦秋云里。那些年,我一次次奔赴苏杭,去了河道如织、水阁飞檐的乌镇,看了因水而筑的“江南第一古镇”周庄,游过清丽古朴的“东方小威尼斯”同里小镇,欣赏了小莲庄和嘉业藏书楼的灵韵,也站在甪直小镇的古银杏树下幸福地笑过。那个腊冬,当黄包车拉着我们来到西塘古镇,我仍为那如诗如画的清丽地而心旌荡漾。
眼前的西塘,恬静、祥和,宛若世外桃源。长廊、弄堂、拱桥、红灯笼,构成古镇清逸脱俗的水乡风情。这个地方,要么独自来感受它的旖旎,要么和爱人一起来体悟它的浪漫。
初见西塘,我便心生出偏爱来。
我们住在古镇弄堂里的特色民居,屋里既有泛着旧时气息的雕花大床、青花瓷烟缸、竹藤椅子,又有现代人离不了的电脑、空调、电视。
过年期间的西塘被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浸染得格外喜庆,我的红色休闲裤、红色拎包、白底红花长围巾,与古镇的氛围很是相衬。古镇与人相得益彰,让人忽然想起“红艳艳”这个词。原来,红色真的可以生出一种艳的感觉来。就像夜晚的西塘,在漆黑的天空下,缓缓流动着墨黑的河水,对岸那一簇簇黑魆魆的树枝,仍被沿河蔓延的红灯笼渲染得艳丽无比。风过处,摇曳了水中的氤氲的红,也朦胧了游人的梦境。
江南的夜,向来比白天多了几分无法言说的韵致与情调。
西塘古镇将旧时模样保持得十分完好,悠长、逼仄的青石板小巷被细雨浸润后焕发着动人的光亮,自是带着旧时光的印记,我脚踩厚底皮靴走在幽静的小巷里,不禁后悔起来:“青石板小路是要细高跟鞋来敲打,跫音长送才别有韵味的。”
这遗憾一旦生出,心里便仿佛有了一丝愁怨,再补上一句:“我该撑一柄油纸伞,便是丁香一样的姑娘了。”他只是笑,知道我又犯了文艺女青年的毛病。
弄堂的尽头是一座小桥,显得尤其娇小、玲珑,西塘的桥多,随便一个转弯便可遇见。腊月的风从水上飘过来,带着一股凛冬的寒,全然没有春风拂面的温柔。我的脸庞躲在柔软的围巾里,只露出一双眼睛来,站在桥下眺望那一水涟漪,橹声穿过拱桥,徒留了乌篷船的尾。抬头望上去,桥上的人正专注地拍着这一船一人掠过的背影,那情那景,像极了《断章》里的句子:“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不知是因为窄长的巷口,还是脚下的流水携着寒气,那天的风冷飕飕的,一个劲儿地往我的脖子里钻。在桥上留影的时候,我试图将缠绕密实的围巾松散成随意的样子,却被接二连三的喷嚏逼退。他走过来,重新将围巾在我的颈间缠绕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结。
我活跃在他的镜头下,笑成了一朵花的样子。我知道,那笑容明媚而温暖。尽管,风吹个不停。
西塘的美是轻灵而古朴的,像冬天的雪花,凛冽中飘洒着梦幻的诗意。走在那条烟雨长廊上,处处感受着江南人的温婉情怀:那一宅深幽却浸透着浓郁书画韵味的小院,那挂满了游人心情碎语的小屋,转角处悬挂着“聊天、发呆、做梦”木牌的茶吧,回旋着一首首老情歌的淘碟音乐屋……最动人是那飘荡着糯软苏腔的水上舞台,袅袅余韵荡漾而来。诚如《红楼梦》里贾母所言,要“借着水音更好听”。古韵今风,如此完美地嵌入,牵绊着游人的脚步。
他说,游江南是需要一些雨水才更有味道的。那天,雨在我们的期盼中缓缓落下。沿河漫步,雨意渐浓,一路有廊棚可遮风挡雨,穿行于烟雨长廊,听雨水滴答,赏廊外秀色,轻烟迷蒙中的西塘越显神秘,美得像一笼轻梦。
白墙黛瓦,尖斜的屋顶,河面上桨声摇曳的乌篷船,是这般江南模样,让我追寻着它,并延伸到心里的角角落落。冬日枯垂的树枝,依稀葆有春日窈窕的神韵,让我开始憧憬着春的到来。是西塘,触动了我心底最柔软的一角。
我们漫步在江南的烟雨里,内心缱绻,忽觉有些遗憾—没人拍下这一瞬的柔情。“有太多地方要去,西塘,不知何日才会再来?”说这话的时候,他侧过脸看着我。迎着他的目光,我看到时光匆匆地从眼底流过,那些甜蜜和忧伤,泛着岁月的光。
西塘的夜是静谧的。偶尔,远处会响起一两声新年的鞭炮声。夜,又迅速恢复了最初的宁静。
西塘的夜是热烈的,华灯初上的那一刻,我看见两只蝴蝶身披一袭霓裳,在西塘的夜空朝着光亮飞啊飞,彼此追逐、缠绵,翩舞在江南的水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