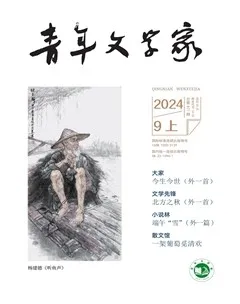母亲的谷雨
我们坝上草原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每年到了三月,随着冰雪的消融,春天似乎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但寒潮总是反反复复。直到谷雨时节,随着春种的开始,春才正式拉开帷幕。
记得小时候,看着母亲开始整理上一年储备在粮仓里的种子,我问:“是又要种田了吗?”
母亲说:“有句老话,谷雨不冻,摁住就种(方言,要毫不犹豫地抓住播种时机)。”
我好奇地问:“什么是谷雨呀?”
一旁的父亲说:“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时节,气温上升快,雨水会增多,是播种的最好时节。”
我又问:“是要在谷雨前后,埯瓜点豆吗?”
母亲说:“在坝上,到谷雨开始可以种小麦了,埯瓜点豆要等到小满前后呢!”
于是,我悄悄地翻开日历,在“谷雨”这一页折个角,作好了标记。
二十四节气,本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的产物,古代劳动人民从中总结出很多用来指导农业生产的经验。渐渐地,节气也融入了很多生活习俗,成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母亲似乎对节气有着极其敏锐的感觉,甚至比虫鸟草木更善于捕捉时令的讯息。她经常和我们讲一些早已烂熟于心的与节气相关的谚语,这些有着地域特色的谚语大都与农事和农时有关,也有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在母亲看来,珍惜每一个节气,把握每一个时令,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不仅关系到春种秋收,还关系到一家老小的衣物增减、饮食起居。
四月,谷雨如期而至,春种也就开始了。在我的记忆里,谷雨这一天云很淡,风很轻,风里掀起阵阵新翻泥土的气息。我们全家一起去田里种小麦,母亲裹着蓝色方巾,披着一件葱绿的大棉袄走在田间小路上。一家人劳作一天回来后,母亲就开始在厨房里忙碌起来,待到傍晚时分,她从锅里端出一笼热气腾腾的白面馍馍,再喊我到小菜园里拔上几根返青的大葱,做一盘小葱炒鸡蛋,一家人沉浸在无比的快乐之中。母亲把谷雨过成了有仪式感的节日。在她看来,能抓住谷雨时节地不冻的时机,种下了小麦,就意味着如果不发生意外,秋天一定会有个好的收成,忙了一天的家人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吃一次香喷喷的白面馍馍了。“谷雨过后再无寒”“春雨贵如油”……谷雨过后,雨水也渐渐多了起来。看着这一场场春雨,母亲念叨着农谚的嘴角,多了一丝掩饰不住的笑意。
种完大田,父母就开始整理院落里的小菜园了,为小满的播种移苗、埯瓜点豆、种花种菜做准备。父亲会从柴房里抱出去年收起来的篱笆,将院子里的小菜园重新圈好。一有时间,他就翻地、平地、做畦、叠垄。在这些方面,母亲才是行家里手,她讲究畦平垄直、精耕细作,把小院的边边角角都打理得整洁利落。
从春种到秋收,母亲就是这个院落的设计师—父亲平地,母亲整畦;父亲刨坑,母亲栽种;父亲施肥,母亲浇水……经母亲的一手布局,每到夏天,小院一片葱绿,生机勃勃,每一位来家里的客人,都会对小院赞不绝口。
母亲跟随着二十四节气,张弛有道,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也让简朴的生活富有诗意,充满温情。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父母都老了,但他们还是闲不住,他们对劳动的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特别是母亲,只要闲下来,似乎浑身上下都难受。近两年来,因母亲身体有恙,行动不便,谷雨过后,父亲便成为小园子劳作的主力,但母亲并没有放弃指挥权和决策权:如果她说东墙边种南瓜或大豆预留的地方小了,就会让父亲把刚栽好的菜椒、葱苗移走;如果她看到西墙边的西红柿苗稀了,会让父亲再点上几颗芸豆。我心里暗暗佩服母亲的这份认真。
今年是母亲离世后的第一个谷雨。我回到老屋,看到老式红木柜里放着母亲用碎花布缝制的大大小小的袋子,袋子分类装着去年秋收后她带病挑拣出来的黄豆、芸豆等各种种子……那一刻,我泪湿眼眶。
母亲,谷雨时节,如若你在,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