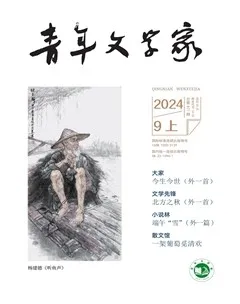时光,未曾走远


谨以此篇拾起我在额尔和乡这方遗落的世间冷暖。借此表达在这里的遇见、感恩、怀恋。逝去的时光在有温情的山水间流淌着,在家乡的味道里,在老铁钟的声响里,在曾经奋斗过的宁静山乡中漫步……
—题记
那年,好多燕子在电线上忙着开会,准备飞往南方之时,我被调到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第一中学任教。
在额尔和乡中学工作十余年,直至临行前,我好像还没有仔细打量过这儿的样貌。想着有空时,拾起遗落在这里的世间冷暖。可一晃二十载过去了,其间往返故乡的途中,即便偶尔路过,也只是匆匆一瞥。然而,在时光的来来往往中,我的心里始终有它的一块自留地。
额尔和(达斡尔语“岸边”之意),因其地处甘河岸边而得名,是乡政府所在地。缘分使然,又是一个晴朗的秋日,我有幸和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文联一行来此参加额尔和中心校组织的“放下手机,捧起名著”的读书倡议活动,回到这片既熟悉又有几分“陌生”的土地。
一进校门,一条地毯似的红色塑胶甬道铺展开来,那时的平房早已被现在的教学楼所取代。蓝天白云下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草绿色的操场弹跳着生机和活力,教室里不时传出清朗的读书声。微风跟着同仁们的问候漫进楼门。顿时,我感受到这里的爽洁和亲切。
翠英、宝芬、春凤、陈伟、玉红等老师在这里忙忙碌碌,各尽其责。“老师,你还是老发型,状态还是这么好……”杜旭和志勇瞅着我咯咯地笑着说。是啊,从上班那天起,我就一直梳短发。
昔日的时光并未走远,她们的话语让我内心溢出感慨,顿时把我拉回刚来这里工作时的时光。那天同样秋高气爽,我穿着统一定制的灰西服,和老教师们在一起欢庆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从此,努力伴着勤奋,意志携着坚韧,一路摸爬滚打……
那时,夏日里、夕阳下,小学校园东侧的那棵大树下,时常响起我们荡秋千时的笑语。亚娟的笑声尤为响脆,偶尔还会从记忆里跑出来。那口锈迹斑斑的老铁钟,每天上课下课由它“发号施令”,时光好似都淹没在了它的气息里。
雪花飘落的冬季,我们几个组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备课办公。炉膛里的柴火噼里啪啦地响着,火焰涨红了半个油桶的炉身。坐在旁边的宋大姐,脸上开出一朵红花儿,一个劲儿地往后挪椅子,却丢不下手里的那道数学题。看似简陋的条件,大家的工作热情丝毫不减。
当春风拂绿山冈,中学小路北侧王嫂家的一垄垄葱绿得诱人,好像把春天搬到了自家园子。转眼间,那一串又一串的红辣椒被她挂在房檐下时,曾面色红润,走路带着跳跃,哼着“阿哥阿妹情意深”的阿兰,我们真诚祝福的阿兰,不知何故,忽然有一天,她捏烂了手里的一片黄叶,目视着以前很少注视的山峦和庄户人家的房屋,一转头拖起行李箱,告别了这里。到底世间情为何物?
距我的故乡几十里地,位于嫩江西岸的额尔和,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驿站。昔日的时光,一直驻扎在我的心里。这不,凤超他们的话语好似还在耳畔,那个胖墩墩,圆圆红苹果脸的卢同学,表演的小品哪有不叫好的……
读书倡议活动中,穿着葱绿外衣的小男孩,托腮、锁眉,又微笑,听得十分认真。到了孩子们即兴提问的环节,气氛更为活跃。结束后,我们先到华达奇(达斡尔族村)旅游度假村。民宿房、游乐园早早地扑入眼帘。河边的卵石细沙还是那么美,甘河水三弯五绕,竟在这里无意中冲出一个“河套子”。我们全校师生在这里野游的那个儿童节,夏风融融,鸟语啾啾。多年过去,时光未曾褪色。
这时,我一回头,河岸上的大饭店居高临下,进出的游客真不少。一想到人们围着当地的美食不肯挪步,那唏嘘几近垂涎的神态,也让我禁不住要流口水。尤其江鱼、山野菜等,绝对纯天然,一下子就能打开人们的胃口。可一边把酒临风,一边观赏甘河水。今年首届的华达奇旅游艺术节,让人耳目一新。这里的自然环境天生丽质,加之政府的协助与支持,现已成为较有地方特色的景点。
随后,与未曾见过面的甘河李屯大桥碰一面。这桥,横跨李屯、何屯两岸,还真有些气派。立桥环顾,如饱览一幅山水素描画。登上李屯的隆华山庄(栖居于窟窿山顶),秋阳在凉亭上欢跳。二十余里外南面的嫩江市和这里相望。凭栏俯瞰对面,一片深绿,熟悉的何屯松树林,传说为达斡尔族先民所栽植的。
高大粗壮的那棵松树据说几百岁打不住,想必又壮了些许。
遐迩尽知的那日松蒙古部落随之进入视野,创建者融合了这里丰厚的天然资源。目光北移,同行者说那是近十年建成的吉尔格勒庄园,看得出主人是下一番功夫的。若坐在河边,听着甘河的流水声,会不乏惬意之感。
据说,窟窿山大大小小的二十几个窟窿,上下错落分布于山腰,山体陡峭,几乎无人进过洞里。冬季常有鸽子和飞鸟出没于此。夏天好多蛇爬进爬出,隆华山庄的美味时而引来蛇的到访。它们伸着脖子、探着脑袋东闻西嗅,有时还拱拱厨师的脚,爬上灶台。庄主言:“不要打它们,咱们是占了人家的地盘呢。”
时光载着我对这方山水的记忆,从未断流。发源于大兴安岭山脉东麓的甘河,其清冽之水从源头汩汩而出,一路汇聚了众多支流,轻柔着,热切着,奔腾着,流经额尔和全境,为嫩江干流。她滋养着额尔和14个行政村、32个自然村组,滋养着总面积670平方公里上的生灵。她无疑成了境内所有人的母亲河。
旧日里那些跟着甘河水从上游而来的一张张木排,越激流绕险滩,还时常再现于眼前。伴着“口耶”(达语,放排组长)一声声粗犷的号令和排夫们的即兴调子,木排流过平阳、伊哈里故乡、蒋柳屯、李屯、额尔和村,以及老头队新老村落。木排每每经过故乡时,常惹得岸上的人也对喊对唱着,连拽着大轱辘车的黄牛都扭过头听上一会儿。“口耶”又一声,木排即将拐过山弯,带上那彼此的笑声、吆喝声驶向额尔和,转过貌似神龟的团山子奔向甘河口。至此,甘河水走完了几百公里的行程,嫩江水拥其入怀。
这方神秀的土地,有着浓郁的民间习俗。多样的饮食更是夺人眼球,柳蒿芽、苏子饼,堪称一绝不说,南北二屯,十里八村的米肠,你吃过就忘不掉。土里土气的方言,情真意切。肥田沃土,豆麦碧浪层叠。泉流溪淙,山间可闻;河味山珍,独具一方。
要下隆华山了,我再次依栏俯瞰着河水。心想,眼前的河段要是有一条船该多好。“快看!”我们顺着一个人手指的方向望去,晴天,河面却突然起了一团白雾,我睁大眼睛再一瞧,雾团消失,一艘小船身披斜阳,沿江而走。坐船的收网,摆船的唱着:“对面的窟窿山,脚下的甘河水,不知是先有山哟,还是先有河,这边的松树林,里面的蒙古包,来尝尝我们的炖鱼和烧烤……”声调酣畅、激昂。
额尔和的历史、底蕴、风情,无法用我笨拙、粗陋的小文来描绘,只能借助我熟知的、记忆里的、此行听说和看到的,来表达我的一份心意。
返回小城前,昔日同事季井臣老师请大家过了一把杀猪菜的瘾。逝去的时光在这方山水间流淌着,在家乡的味道里,在老铁钟的声响里,在曾经奋斗过的宁静山乡中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