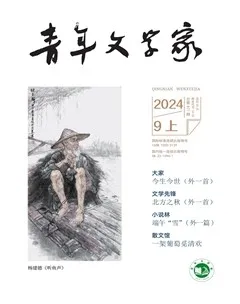麦秸扇
雪,孕育了麦种;春风,成熟了麦穗;夏风,熏黄了秸秆。当麦穗昂起头颅,即将撑破麦壳的时候,大地就呈现出收割的姿势了。
在天气干燥的日子里,打麦子的季节就开始了。一束束麦子放在麦石上用力鞭打,三两下,麦粒就跟母体骨肉分离,饱满的麦粒四处飞散。脱了粒的麦秸一束束丢在地上,散漫舒雅地躺着。不过,它们的使命还未完成—编织麦秸扇的季节来了。
女人们会细细地抚摸、分拣麦秸,她们往往会挑那种颀长且亮度饱满的秸秆,先摘下麦秸末梢一尺见方的长条子,褪去它们的外衣,就看到了金黄透亮、光洁细腻的芯条,在太阳下特别闪亮,姐姐们用手密密地分排开麦秸芯,仿佛端详精致的艺术品!这麦秸芯真的会变成我们小时候难得的“艺术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山村还是没有通电,也没有任何电器。唯一能够让我们觉得跟电有关的,就是春节那几天村里电站自己发电供应的电灯。其余时间,每天晚上我们都是在煤油灯下度过的。夏天的日子可想而知,白天苍蝇成群,夜里蚊子乱舞,至于炎热那是必然的。于是,编麦秸扇就成了这个季节收割麦子后的女人们最重要的活计。
我从来没有编过,只是看着母亲和姐姐们编。我对麦秸扇编织的方法还记得一二。先将麦秸编成一个小圆,然后沿小圆盘外围编成长辫子,辫子长短依扇子面积大小而定,两只手,十个指头来回活动,麦秸在手指的拨弄下,灵活晃动。一根麦秸编完了,就拿起另外一个麦秸,为了编织方便,先是将一端用牙齿咬住,用手将整根麦秸捋一下,压得稍扁些,这样形状的麦秸柔软而有弹性,不至于在编织过程中破裂。当然,编织麦秸扇辫子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风格也各不相同,有的编得简单大气、粗疏木讷;有的编得精致细腻、光洁均匀。
待完成编辫子这一工序后,就用针线以中间小圆为中心一圈圈缝制起来,这就成了扇盘。扇柄是用短竹棍做成的。母亲和姐姐们偶尔会让朴素的生活花哨一下,她们用做衣裤剩的碎花布缝在扇子的中缝上加以点缀,朴素的麦秸扇顿时就有诗意了。我记得大姐还专门为我和妹妹打了扇盘很小的小扇,妹妹甩着辫子,摇头晃脑地炫耀着自己的小花扇,大姐总会开心地笑了。
没有电的晚上,干农活的父亲和叔叔们就把扇子插在后背的裤腰间,随时可以拿下来驱赶蚊子和纳凉,有时候边吃手擀面,边轻摇麦秸扇。小孩子们手摇麦秸扇,在夏天的午后看蚂蚁搬家。姑娘们轻轻摇着麦秸扇,刘海儿就在额前一起一伏。母亲们从田野回来,为了驱热,拼命摇扇,衣服快速在胸前舞动。老奶奶们扇出了额头的皱纹,白发在麦秸扇的摇送下显现。男孩们在麦秸扇的拍打下长高,麦秸扇轻摇出了青春期的勃发。
当时,小伙子如果青睐哪位姑娘,都非常渴望能够得到她编织的麦秸扇。听母亲说,她年轻时,有一个姑娘钟爱村里一个小伙子,父亲却将她远嫁村外。临嫁时,送了意中人一把她精心编织的麦秸扇,连同她自己的爱意。后来,姑娘很早就去世了,那位小伙子却一直珍藏着这一把意义非凡的麦秸扇。
夏天的傍晚,妹妹们就由大人搂在怀里,不断扇扇子纳凉,慢慢进入梦乡。天河沉静,星星安然,睡在露天的一张张席子上的村民也已酣然,麦秸扇还握在手里,垫在头上,窝在胸间。长长的夏天,暗暗的夜,麦秸扇遍布生活的每个角落,填补生活中的每个细节。这样编织麦秸扇的日子,在我的家乡没有通电的岁月里一年年绵延着。轻摇麦秸扇,很多人走了,很多人又来了,很多故事发生了,很多情感消失了。随着电的到来,麦秸扇再也不编了,开始几年,大家还会拿出早几年的麦秸扇用用,后来,只能在家里的柜子里看到,后来的后来便杳然了。麦秸扇—有快乐,也有悲伤;有甜美,也有凄凉。
如今,麦秸扇那泛黄的样子还是会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些绑在扇柄上的花色布头还是会清晰地让我想起它的花纹,被汗渍浸透的扇柄依然让我感觉光亮而实在。可是,它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总有那么一些人,会消失,会湮没,会淡褪,但他们确实来过。